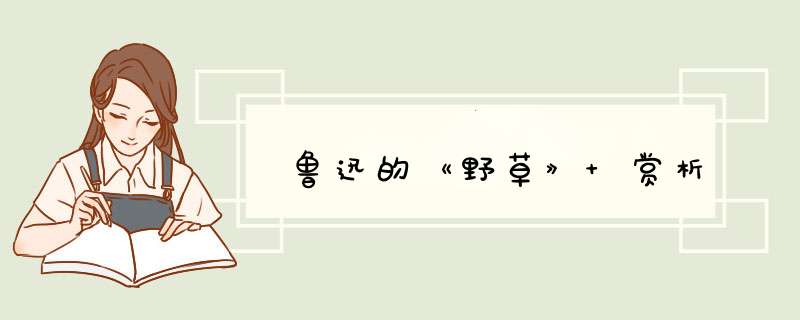
赏析:
《野草》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一本散文诗集,《野草题辞》是《野草》这本散文诗集的序。《野草》这本散文诗集写了近三年,《题辞》是最后一篇。既是序言,又是总结。
《野草题辞》写于1927年4月26日,这时正是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的第14天。这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是鲁迅世界观发生伟大质变的关键时刻。鲁迅先生从进化论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从苦闷、彷徨中走了出来,决心去迎接新的战斗。
在写《题辞》的二十天之后,北京的友人约稿,鲁迅先生说:“你要我的稿子,实在是一个问题,因为我现在无话可说。”在完成《题辞》写作后一个多月,鲁迅对他的朋友说:“这里言论界之暗,实在过于北京……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
因此,《题辞》是全集中最晦涩难懂的。这正是不能说、不敢说的困境,导致本文文字表面意思模糊不清,歧义丛生,极度依赖内在语,让读者自行体会。
当年9月,鲁迅在广州作的《怎么写》一文中,曾描绘过他在厦门时的这种心情: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
这时,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这也就是我所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这便是鲁迅写《题辞》的时代背景和心境。
回首过去,这一段路已走过,向命运、时代、现实抗争过,这抗争恰恰证明了自己曾经的生活和战斗,因此,作者面对这已经过去的生命历程,有“大欢喜”。这是一种豁达的正视过去,告别过去,勇敢地迈开步伐走向未来的态度。
最后一句话,则是一种决心的表露:《野草》的生存就是为了灭亡,它的灭亡就是鲁迅所渴望的一种与旧世界的决绝!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文化背景
《野草》是一部充满着象征主义的散文诗集,象征主义作为一个自觉的文艺流派运动是从19世纪80年代法国作家让·莫瑞阿斯在《费加罗报》发表《象征主义宣言》时开始发展起来的,到20世纪20年代形成一个具有较大影响的世界范围的现代派文艺运动。
散文诗在新诗革命初期就开始有人创作,1918年到1923年,初期白话诗人刘半农,在创作新诗的同时,写了《晓》 《饿》《雨》《静》《墨兰的海洋深处》等散文诗篇;新诗奠基者郭沫若于1920年12月20日,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用“我的散文诗”为总题。
发表了《冬》《她与他》《女尸》《大地的号》四首短小的散文诗作品;在此前后,从1918年到1924年,《新青年》《晨报副刊》《小说月报》《文学旬刊》《文学周报》《学灯》《觉悟》《语丝》等刊物上。
陆续发表了刘半农、沈颖、周作人、两谛(郑振铎)、沈性仁、张定璜、苏兆龙等人翻泽的屠格涅夫、波德莱尔的散文诗,有的刊物还专门发表了介绍和讨论散文诗的文章。作者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陆续发表了23篇散文诗,编成《野草》。
-野草
《题辞》写于1927年4月26日的广州,正当将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广州"四·一二"大屠杀之后。这时无数***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戮,到处笼罩一片白色恐怖,鲁迅先生的处境十分险恶,随时有被反动派逮捕和杀害的可能,但他坚持革命立场,毫不畏惧。对中山大学被捕的进步学生,他极力进行营救,营救无效,愤然辞去中山大学所任一切职务。在这篇《题辞》中,更是写下了他满腔的悲愤。
《题辞》的思想内容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全文划分五部分来分析体会。
第一部分(第1段),鲁迅先生抒写对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人民的血腥暴行的无比悲愤的心情。一开始,鲁迅先生就写出他当时是处在"沉默着的时候"。这"沉默"是对反动派愤怒到极点的一种表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也曾写道:"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这已表现出鲁迅对段祺瑞"执政府"屠杀爱国青年的极大愤怒。那么,现在面对着的是蒋介石更大规模更凶残的屠杀,可想而知,鲁迅先生在沉默中蕴藏着的愤怒,更不知要增加多少倍!所谓"充实"。正是反动派数不清的血腥暴行,使鲁迅先生"艰于呼吸视听",有倾诉不完的悲愤。为什么将要开口时又感到"空虚"呢?这是鲁迅先生在反动派的凶残屠杀下,感到"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三闲集·怎么写》),正所谓吟罢低眉无写处"(《为了忘却的记念》)。这里的"空虚"之感,包含了对反动派的极端激愤之情。
第二部分(第2、3段),写鲁迅先生以不断革命的观点看待自己"过去的生命"从而点出作为"过去的生命"的记录的"野草"。此时的鲁迅,世界观开始发生质变,由于他在思想上不断革命,严格要求自己,为投入新的战斗继续前进,所以他对于自己"过去的生命"的"死亡"和"朽腐"并不惋惜,而"大欢喜"。但同时,鲁迅先生也没有完全抹煞过去。所谓借"过去的生命"的"死亡"、"朽腐"可以知道它"曾经存话"、"还非空虚"。就是说,他过去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曾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及其走狗文人进行过激烈的战斗,并没有虚耗岁月,《野草》就是他用自己的生命培育出来的作品。就是记录这一战斗的业绩之一。
第三部分(第4、5段),写《野草》的产生和遭遇,以及鲁迅为"野草"的遭遇而欢欣。"野草"很平凡,"根本不深,花叶不美"但它是在战斗中求生存,发挥了战斗作用的。它既从"露"和"水"(比喻进步势力)获得滋润,也从陈死人的血和肉(比喻历史经验和文化遗产)吸取精华。以顽强的生命力同反动派挑战,因而不可避免地遭到反动派的"践踏"和"删刈"。"野草"在"存活"中完成了对反动派无情的揭露和尖锐批判的历史任务。为此,鲁迅先生情不自禁写道:"我将大笑,我将歌唱",笑敌人的卑劣,歌唱"野草"的胜利,完成了战斗任务。
第四部分(6、7、8段),写鲁迅先生对革命高潮必将到来的更大欢欣。鲁迅珍视发挥了战斗作用的"野草",也憎恶这产生"野草"的黑暗的社会现实。"装饰"一词正写出了敌人的虚伪和狡狯,"以野草作装饰"不过是在压抑不了进步势力崛起时玩弄的手法而已。装出一副"公平""开明"的面孔,用以欺骗人民,实则暗中在对进步势力进行扼杀。但鲁迅先生并没有被黑暗淹没,被屠刀吓倒。从英勇奋战的革命人民身上,他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地大在地下运行,奔突",看到了中国***领导的潜在的巨大革命力量在推动历史前进。因而,他坚信革命高潮必将到来,为此,他更热烈地欢呼,纵声歌唱,表现出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从黑暗中看到光明的无比乐观情绪。
第五部分(9--末尾),进一步写鲁迅先生对革命高潮到来的渴望,鲁迅先生始终是执着现实,坚持现实的战斗的。"天地有如此静穆"比喻革命风暴到来之前的沉寂。鲁迅先生怀着对敌人的极大的仇恨,仍沉毅地进行战斗,留下可以证明战绩的"野草"。这"野草"写于光明与黑暗交替,新的方生与旧的未死,将过去而未过去与将到来尚未到来的时刻。它献给人民,唤起人民的觉悟;它献给敌人,揭露敌人的黑暗统治。"去吧,野草,连着我的题辞!"这结尾一句,更强化了彻底革命的精神,有力地结束了全篇。鲁迅先生如此毅然决然摈弃旧时代的一切,以至自己过去生命中留存的战绩,都毫不惋惜,这是为了迎接新的革命高潮,投入新的战斗!
《题辞》的思想意义在于它是一篇革命的预言,它既标志看鲁迅先生世界观的跃进,也是鲁迅先生开始新的进军的誓词。
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凝聚着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以后思想上处于彷徨时期对人生、对人的存在价值、对中国文化的特征和社会发展的深沉思考。在鲁迅生命最痛苦的时候,"五四"运动高潮后的回落、"新青年"阵营的裂变、统治阶层的专横和欺压……一系列社会的矛盾让鲁迅陷入消沉抑郁的海洋、感受心灵苦闷的煎熬。黯淡的情绪和痛苦的情愫孕育了《野草》的诞生。这部作品是鲁迅以其独特的个性和方式同痛苦作"绝望的抗战"而催生的小花,是他灵魂深处流淌出来的心泉所化成的艺术瑰宝,是一部"心灵斗争的记录"。鲁迅以他不可模仿的艺术才华,将自己微妙的感觉、情绪,难以言传的心理、意识,复杂万端的心态与情感,愤激与焦燥,感伤和痛苦,苦闷与彷徨,探索与追求,溶入这丛野草之中,从而把内心的痛苦转入《野草》,这是他建立在精神死亡之海上的墓志铭。他的一生就是这样以绍兴人那一碗黄酒垫底的生命底气,以来自尼采权力意志哲学的那一派野力,绝望、反抗绝望、坚持绝望。这种绝望的坚持尤其艰忍。殷海光先生曾说,鲁迅既感觉到了生命的虚无,又要在为虚无的压迫下致力于求索一个民族,一个文明的新生之路。这是一个极大的悖论。更痛苦的是鲁迅在求索民族新生之路上又是这样四处碰壁。这样的鲁迅我们可以把他描写成一位举着盾牌的战士,盾牌的后方是生命的虚无,盾牌的前方是出路的虚无。战士要博击的是双向的虚无。这种战斗就尤其惨烈。这样的鲁迅才是一个够味的鲁迅。这样的鲁迅才配称中国在二十世纪的精神高峰。 鲁迅毫不讳言现实在他看来乃是实有的黑暗与虚无,却又认为,不是没有可能从反抗中得救。他一面揭示生存的荒诞与生命的幽黯,一面依然抱着充沛的人文主义激情,这是他高出许多存在主义者的地方。他说,他的哲学都包括在《野草》里面。野草》的低沉阴郁、桀骜不驯,体现出彷徨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作者孤愤苍凉的心情,是作者真实的灵魂袒露;是追寻生命意义却感到死亡的悲怆时的焦虑;是独自与黑暗搏斗的直面真相的勇气,是在无路之处走出路来的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
《野草》的语言风格也很有特色。激越、明快、泼辣、温润,它都具有;但是更多的是深沉悲抑,迂回曲折,神秘幽深。作者表现的主要是一种悲剧性情绪,它源自生命深处,许多奇幻的想象,其实都是由此派生而来,因此,最富含热情的语言也都留有寒冷的气息,恰如冰的火,火的冰。《死火》中描写死火:"一切青白冰上,却有红影无数,纤结如珊瑚网,"《野草》的语言,正是那青白背景上的无数张开而又纠结在一起的红艳的珊瑚枝。 作为一部灵魂之书,《野草》开辟的境界,在中国的精神史和文学史上,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散文诗《野草》被许多评论者认为是中国20世纪文学的颠峰之作。
鲁迅曾对人说过,他的哲学全在《野草》里。《野草》所表现的正是作为孤独个体的鲁迅的种种生命体验和认识。传统文化被冲击后与西方文化的交融构成其独特的思想基础;在极其残酷的生存环境中找不到希望的绝望;独自面对死亡而体验到的生命的荒诞和虚无……。把主观心理体验作为思考的中心,并以此为出发点探求个体存在的意义。《野草》是鲁迅最个人化的著作。《野草》是鲁迅心灵的诗,揭示了鲁迅的个人存在,个人生命的存在,文学个人话浯的存在,相对多的露出了鲁迅灵魂的真与深。《野草》只属于鲁迅自己。曾在作者心中酝酉良10年之久的《过客》,又可以看作是《野草》的“主将”。《过客》熔铸了鲁迅个人生活的痛苦经验和独异思考。鲁迅后来把这种永远向前走的过客精神概括为“反抗绝望”。
我对他的散文曾研究过,是浅的那种,一直处于朦胧感觉,但总感到鲁迅的笔像刀,锋利的刀,那东西不是写出来,是雕出来的,是刻出来的。无疑,他那激励的文笔和深刻的思想,赢得了人们的热爱和尊重。
《野草》是鲁迅精神世界的集中体现。第一部分 ,中国传统文学是鲁迅的精神内核。第二部分 ,鲁迅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存在主义作家。第三部分 ,鲁迅理解的进化论是怎样的 鲁迅在理智层面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 ,在内在意识又主要是受传统文化的影响 ,那么进化论与历史循环论形成了鲁迅在中西文化的夹缝中求出路的状态。鲁迅并没有根本肯定西方主流文化 ,这样 ,鲁迅既不可能根本上从中国文化中寻出路 ,也进入不了西方的信仰之路 ,这样发展到极端时 ,就处于一种分裂状态。那么《野草》中的分裂表现出来的虚无感有从佛教的虚妄向存在主义的虚无过渡的可能性。佛教的虚妄的灵魂与儒道主体的那种复合体所达到的虚无边界与存在主义的虚无有一定的相通处 ,这样鲁迅的生存体验就有一种存在主义的特色 ,但鲁迅没有进入存在主义的语境之中。这样鲁迅的进化论是一个没有找到真正出路的死结。鲁迅的精神世界没有跳出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大循环结构 ,于是产生了鲁迅那种黑暗 ,孤绝的灵魂。
鲁迅的《野草》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最早散文诗集之一,构思奇特、新颖,形式多姿多彩,思想深刻。作者的思想重要是通过诗的形象来表现,寓意深远,感情浓郁。由于当时的环境,很多意思难于直说,是采取了隐晦的表现手法,读起来比较难懂。
一.《野草》的产生。
薄薄的一本散文诗集《野草》,是鲁迅先生送给中国新文学的一份厚重的礼物。《野草》在文学界始终被认为是鲁迅创作中一部最美的作品。它有如《呐喊》、《彷徨》那些叙事书写作品所没有的幽深性、神秘性和永久性,它在整体上有一种难以破解而又可以永远引人沉思的艺术美的魅力。对《野草》从20世纪二十年代最初产生的零散浮泛的感言,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众说纷纭的理论诠释,人们都可以做言无不尽的论说,而又觉得言犹未尽。一些难懂的晦涩篇章和抒情的意象、语言,至今很难做出无可辩驳的解释。但有一点却是大家公认的:到现在很难有人敢言,我已经把一本《野草》都说清楚了。可以这样说,《野草》已经成为鲁迅全部文学创作中留给后人的一个世纪性的“文学猜想”。
《野草》一共有24篇散文诗,最早发表的《秋夜》写于1924年9月15日,最后一篇《一觉》写于1926年4月10日,前后历经一年零七个月。1927年4月26日,在作品结集出版之时,鲁迅又写了代序言的《题词》。前23篇,都是写在北洋军阀黑暗势力笼罩下的北京,《题词》是写在国民党实行“清党”、对革命进行大屠杀、十分恐怖的广州。写作时间和环境,虽然有所不同,而作者的心境和思想、艺术手法,却大体是一致的。
《野草》于1927年7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五年后,鲁迅曾经这样说明自己写作《野草》时孤独寂寞而又不断求索的心境:“后来《新青年》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做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哪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些自述,包含了关于自己的《野草》、《彷徨》与他那时“荷戟独彷徨”心境之间的关系,它们所产生的思想情绪的根源,也说明了散文诗《野草》里那些小感触,隐含着怎样一种沙漠里走来走去的孤军奋战者的痛苦与沉思,它们是与叙事书写不同的内在情感世界哲理化了的结晶,一种深层情感意识的艺术凝聚与升华。《野草》将五四时期产生的哲理性美文提到了一个前无古人的高度,它比《呐喊》、《彷徨》更深邃、更神秘,也更美。它展示了一种接受者必须具有驰骋猜想力才能探寻的文学心理空间。
二.《野草》的生命哲学。
我过去的“现代文学”老师川岛先生,是鲁迅的朋友,《语丝》杂志的创办者。他告诉过我:那时他常到鲁迅家里去取写好的《野草》稿子,很幸运是《野草》各篇的第一个读者。但对于《野草》许多篇,读起来觉得很美,可是大家看不懂,但又不好意思一篇一篇去问鲁迅先生,只好不懂装懂。《野草》区别于鲁迅其他创作的一个最大的特征,是它隐藏的深邃的哲理性与传达的象征性。不满足于当时一般闲话或抒情性美文来传情达意,而将从现实和人生经验中体悟的生命哲学赋予一种美的形式,创造一种特异的“独语”式的抒情散文,是鲁迅先生写作《野草》时的一个非常自觉的追求,这里先讲哲学性。
这是70多年前的一条很有趣的材料。鲁迅的《野草》在《语丝》上还刚发表了11篇,经常出入鲁迅家里,并为《语丝》同人的章衣萍,通过《古庙杂谈(五)》无意之中给我们透露了两个重要的信息,一个是读者的反映,对鲁迅先生的《野草》,人们普遍都说不懂;一个是作者的自白,“他的哲学都包括在《野草》里面”了。由此,鲁迅自己是毫不遮蔽他对于《野草》生命哲学承载的创作追求与传达意图的。
因为大都是针对不同缘由而各自独立写成的“小感触”,写作时间又拉得比较长,就很难说有一个什么统一不变的内涵,可以成为笼罩全书支配性的命题,比较大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韧性战斗的哲学,反抗绝望的哲学,向麻木复仇的哲学和爱憎与宽宥的哲学等等,这些生命哲学,都是属于独特的个人精神的开掘与显现,它构成了《野草》中鲁迅作为一个孤军奋战的启蒙思想家的丰富、深邃的精神世界。
韧性战斗的哲学,主要是指对于旧的社会制度与黑暗势力,对人和人性摧残压迫所采取的生命选择和心理姿态。基于对改革中国社会艰难的深刻了解,对于五四以后青年抗争黑暗势力过分乐观和急躁的观察,鲁迅以一个启蒙者独有的清醒,提出坚持长期作战的韧性哲学。他说他佩服天津青皮的“无赖精神”。他主张同敌人战斗中,要坚持“壕堑战”,尽量减少流血和牺牲,他告诉人们:“正无须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韧性的战斗。”《野草》第一篇〈秋夜〉暗示的就是这个思想。
《过客》中,具有这种韧性战斗精神的枣树,变成了一个倔强的拔涉者的动人形象。对于过客的形象,在他心里已酝酿了十余年的时间,用短小话剧形式写的《过客》,一致公认是《野草》的压卷之作,这里包含了鲁迅自辛亥革命以来,所经历所积蓄的最痛苦、也最冷峻的人生哲学的思考。在写完《过客》的两个月后,鲁迅在一篇文章里说:“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峡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
《这样的战士》、《淡淡的血痕中》,或是“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而作”,或是愤慨于“段祺瑞政府枪击徒手民众”的声音,也都能在具体现实斗争事件的关注与介入中,进行诗性的想象与升华,抒发和赞美了一种永无休止、永远举起投枪的生命哲学。
与前面韧性战斗哲学联系的,是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反抗绝望的哲学,是鲁迅转向自己内心世界进行激烈搏斗的产生的精神产物。所谓“反抗绝望”并不是一个封闭世界的孤独者自我精神的煎熬与咀嚼,而是坚持叛逆抗争中感受寂寞孤独时灵魂的自我抗战与反思。它的产生与内涵,都与现实生存处境有深刻的联系。
《影的告别》是《野草》中最晦涩、最阴暗的作品。假托影与形的对话,它最痛苦也是最痛快的选择,是在黑暗中无声的沉没。《乞求者》抒发了在冷漠无情的社会里,对奴隶式求乞行为的厌腻、疑心与憎恶。《希望》是将“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表现得最充分也最直接的一篇。
复杂的人生哲学,是鲁迅出于改造国民性思想而对于麻木群众一种愤激批判情绪的升华与概括。鲁迅在《野草》里连着写了《复仇》、《复仇(其二)》两篇散文诗,将这一人生思考传达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创作的目的,前者是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后者是有感于先觉者与群众麻木之间可悲的隔阂。
文学家对生命哲学的倾诉并不等于哲学家、政治家的哲学理论的阐发。它没有理论哲学的系统性与严密性。
三.《野草》的象征艺术
《野草》这部作品运用了一种与《呐喊》、《彷徨》不同的艺术表现方式,这就是象征主义的表现方法。创造者的独特追求造成了艺术传达的幽深与神秘美,同时也造成并加大了作品与读者接受之间的陌生感。
有一篇散文诗《颓败线的颤动》,里面写了“我”的两段梦:第一个梦,是一个年轻的妈妈怎样忍着羞辱与痛苦,靠出卖自己的肉体养活自己两岁的女孩。妈妈看着女孩,欣慰于今天会有烧饼给自己的女儿吃了。她同时却为自己付出的代价时而“无可告诉地一看着破旧的屋顶以上的天空”。“我”被沉重的空中的旋涡呻吟着压醒了。“我”在一间紧闭的小屋里接着再续着残梦,但这已经是隔许多年以后了,屋的内外已经这样整齐,里面是一对青年夫妻,一群小孩子,他们都怨恨鄙夷地对着一个垂老的女人。男的气忿地说:“我们没有脸见人,就是因为你,你还以为养大了她,其实正是害了她。倒不如小时候饿死的好!”女的说:“使我委曲一世的就是你”,还指着孩子们说:“还要带累他们哩!”。最小的一个不懂事的孩子,玩着一片干芦苇叶,这时便向空中一挥,大声说道:“杀”,那个垂老的女人,口角痉挛,登时一怔,接着,冷静地骨立的石像似的站起来,迈步在深夜中走出,遗弃了背后一切的冷骂和毒笑。
比较流行的观点,如李何林所说,这是一篇现实主义的散文诗,同《祝福》中祥林嫂一样,它的旨意,是在描写中国下层社会妇女命运的悲哀。我在重读中发现,这是一篇典型的象征主义的散文诗。这个故事在一定的氛围中展开了一个多义性的象征世界。作者对于忘恩负义这种人类丑恶道德行为的愤激批判与复仇,才是这篇象征散文诗的最核心的意旨所在。
《野草》中的24篇作品,并不能说都是象征主义作品。但就其大多数来讲,就其整体艺术追求而言,它是一部运用象征主义方法创造的杰作。这种象征主义方法,主要通过以下形式体现:第一,通过象征性的自然景物的意象和氛围,构成象征世界、暗示作者的思想和情绪。如《秋夜》、《雪》、《腊叶》等;第二,通过编造幻想中的真实与想象纠缠的故事,构成象征的世界,传达自己的思想和哲学,如《求乞者》、《复仇》、《复仇(其二)》、《好的故事》、《过客》等;第三,完全用非常荒诞的现实中不可能发生或存在的“故事”,传达或暗示自己的旨意,如《影的告别》、《死火》、《狗的驳诘》、《失掉的好地狱》、《墓碣文》、《死后》等,这一部分作品由于过分怪异和晦涩,往往难以弄懂。
鲁迅很早就接触过西方象征主义文学思潮。20年代中期,在北京大学等院校讲课,又讲过并翻译了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里面就介绍和提倡广义上的象征主义。鲁迅还接受了波特莱尔、屠格涅夫的一些象征主义散文诗的影响。80年代初发现了他在1919年发表的一组小散文诗,可以说在五四新文学发生时期,鲁迅创造新的现代散文诗的文体意识,是非常自觉的。鲁迅自觉而不留痕迹地借鉴西方散文诗的艺术方法,吸收中国寓言或短小散文传统的营养,不仅使他的这本薄薄的《野草》,成为中国现代散文诗的开山性的珍贵果实,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个艺术珍品,也是迄今为止中国现代象征主义散文诗中一座难以超越的喜玛拉雅山峰。
嗯,这是我找到的一篇文章,希望可以帮到忙吧
作品评价
现代诗人李素伯:极其诗质的小品散文集—《野草》。这是贫弱的中国文艺园地里的一朵奇花。那里面精炼的字句和形式,作者个性和人生真实经验的表现,人间苦闷的象征,希望幻灭的悲哀,以及黑而可怖的幻景,使之想起散诗的鼻祖波德莱尔和他一卷精湛美丽的《散文小诗》来。
只觉得它的美,但说不出它的所以为美。虽然有人说展开《野草》一书,便觉冷气逼人,阴森森如入古道,而且目为人生诅咒论;但这正如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花》一样是不适合于少年与蒙昧者的诵读,但是明智的读者却能从这里得到真正希有的力量。
现代诗人痖弦:《野草》的问世,为中国新文学中从未有过的散文诗立下范式,可惜后来者从之不多,未能使此一新兴的诗体得到进一步发展。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孙玉石:《野草》有如《呐喊》、《彷徨》那些叙事书写作品所没有的幽深性、神秘性和永久性,它在整体上有一种难以破解而又可以永远引人沉思的艺术美的魅力。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李欧梵:个人杂感的诗意的变体。
近代评论家夏济安:“萌芽中的真正的诗;浸透着强烈的情感力度的形象,幽暗的闪光和奇异的线条时而流动时而停顿,正像熔化的金属尚未找到一个模子。”
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钱理群:幸而有这一部《野草》,还能够多多少少走进鲁迅的内心世界,能够看到鲁迅灵魂的真和深。所以《野草》是一部相对真实地揭示鲁迅个人存在的作品,多多少少揭示了鲁迅个人的真实生命状态和真实话语的存在。
同济大学鲁迅研究中心主任张闳:《野草》是诗,但迄今为止却还没有被真正当作诗来阅读。而严格意义上的诗学解读,应服从作品的诗学本质及诗学研究本身的规定性。
扩展资料
《野草》区别于鲁迅其它作品的一个最大的特征,是它隐藏的深邃的哲理性与传达的象征性。不满足于当时一般闲话或抒情性美文来传情达意,而将从现实和人生经验中体悟的生命哲学赋予一种美的形式,创造一种特异的“独语”式的抒情散文诗。《野草》承载的生命哲学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⑴韧性战斗的哲学,主要是指对于旧的社会制度与黑暗势力,对人和人性摧残压迫所采取的生命选择和心理姿态。基于对改革中国社会艰难的深刻了解,对于五四以后青年抗争黑暗势力过分乐观和急躁的观察,鲁迅以一个启蒙者独有的清醒,提出坚持长期作战的韧性哲学。
他说他佩服天津青皮的“无赖精神”。他主张同敌人战斗中,要坚持“壕堑战”,尽量减少流血和牺牲,他告诉人们:“正无须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韧性的战斗。”《野草》第一篇《秋夜》暗示的就是这个思想。《过客》中,具有这种韧性战斗精神的枣树,变成了一个倔强的跋涉者的动人形象。
对于过客的形象,在他心里已酝酿了十余年的时间,用短小话剧形式写的《过客》,一致公认是《野草》的压卷之作,这里包含了鲁迅自辛亥革命以来,所经历所积蓄的最痛苦、也最冷峻的人生哲学的思考。
在写完《过客》的两个月后,鲁迅在一篇文章里说:“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峡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
《这样的战士》、《淡淡的血痕中》,或是“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而作”,或是愤慨于“段祺瑞政府枪击徒手民众”的声音,也都能在具体现实斗争事件的关注与介入中,进行诗性的想象与升华,抒发和赞美了一种永无休止、永远举起投枪的生命哲学。
⑵反抗绝望的哲学,是鲁迅转向自己内心世界进行激烈搏斗的产生的精神产物。所谓“反抗绝望”并不是一个封闭世界的孤独者自我精神的煎熬与咀嚼,而是坚持叛逆抗争中感受寂寞孤独时灵魂的自我抗战与反思。它的产生与内涵,都与现实生存处境有深刻的联系。
《影的告别》是《野草》中最晦涩、最阴暗的作品。假托影与形的对话,它最痛苦也是最痛快的选择,是在黑暗中无声的沉没。《乞求者》抒发了在冷漠无情的社会里,对奴隶式求乞行为的厌腻、疑心与憎恶。《希望》是将“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表现得最充分也最直接的一篇。
彷徨苦闷的产物,坚韧战斗的见证
《野草》是五四退潮后鲁迅思想彷徨、苦闷的产物,反映了鲁迅彷徨、思索、坚韧战斗的心路历程。
(1)无归宿感:深刻的焦虑与不安,处于一种“无物之阵”。是一种找不到立足点的无归宿感。它不是来自于某一方面的原因,是对自己根本性的忧郁,站在世界“边沿”、“无地”的孤独感和身处“无物”之阵的悲剧感和绝对的无依靠感,一种被抛入世界的悲剧性体念。作者进行的是自我灵魂的严酷拷问,“过客”意识。
过客意识,折射出鲁迅的虚无感和孤独感:自己成为了一个倔犟的过客,一个从虚无走入虚无的过客,揭示的是人的意义在于行动的过程,而非目的本身的哲学命题。《影的告别》“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我只能“彷徨于无地”。
《颓败线的颤动》的主题略近于《复仇(其二)》。前者写一个因为要养活孩子而失身于人的妇女,垂老时却受到孩子和亲人的鄙视。后者借用耶稣的故事,勾画了一个为人群谋福利而又为人群所唾弃的改革者的形象——虚无和孤独、悲剧感。
(2)必死的主题:对死亡的阐释和态度构成了《野草》哲学的重要内容和基本逻辑。死亡在《野草》中不是把人的生命引向顶峰。相反,死亡是进入并存在于现实的生命活动中,作者通过认识死亡来强化人对生命过程的自觉意识。(这种意识中国人是缺乏的,没有生命自觉意识的人他会成为历史盲目的追随者而不可能成为历史的推动和改造者)人是在对死亡的认识中来思考生命的意义和进行生命的选择。体现的是作者对现实生命的执着和对生命价值的认识,作者是从生命的终点(死亡)来反观生命的价值。在《野草》中,作者超然面对了死亡的恐惧,死亡并不等于空虚,它是生命流程中的必然。《野草》是用文学的形式,从哲学的角度把死亡转化成对生命意义,生命价值的思考。
(3)荒诞的主题:无物之阵,虚无的战斗,无归宿感,对生命和虚无的体验。荒诞背后是对历史和现实的发现。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立论》等篇,则是对奴才哲学和市侩习气和讽喻。《立论》:一切围绕权利的立论都是权利化的表现,都是谎言和无意义的闲话,都是对现实的逃避,同时也深深地痛批了当时所谓的“骑墙派”文人的奸诈嘴脸。
《求乞者》:对虚无和虚伪的认识,以及对当时国民的奴性的鞭挞。
《狗的驳诘》:对人势利和虚伪的讽刺。
(4)绝望的抗战:是鲁迅反抗绝望的哲学(汪辉语),是在无可挽回的结局后对现实的选择。“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希望》。绝望而非失望,是绝望地进行没有希望的抗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鲁迅现实战斗精神的体现。
《野草》的内容比较复杂,贯串在不少篇什里的主要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也体现了存在于作者自己思想里的同样的冲突。他感到黑暗势力的浓重,着力描绘了它;同时又觉得战斗之不能松懈,坚持顽强不屈的精神。《这样的战士》和《过客》在这点上表现得特别鲜明。“过客”经过长途跋涉,疲惫而又劳顿,然而生命的声音在叫唤他,他还是不停步地前进着。无论是世故的恳挚的劝告,还是天真的热情的安慰,都无法使他改变主意。他不清楚前面是什么所在,料不定能否走完,却还是谢却一切"好意”,拒绝一切"布施”,依旧昂着头,奋然向前走去,这既象征了作者自己当时内心的忧苦愤恨,也象征了当时的变革社会、拯救中国的力量的不屈不挠的一直奋斗不息的精神。“这样的战士”处身在“无物之阵”里,遇见的是对他“一式点头”,同声立誓,他们头上有“各种旗帜”,绣着“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等等“好名称”,他们头下有“各样外套”,绣着“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等等“好花样”,面对这些变形的假象——“杀人不见血的武器”,“他举起了投枪”;当一切都颓然倒地,他发现“其中无物”,最后甚至连这“无物之物”也已经脱走,但是,"他举起了投枪”;他不管自己是“战士”还是“罪人”,是胜利还是失败,在“不闻战叫”的境地里,依旧和原先一样,“他举起了投枪”。这里虽然流露出孤军作战的寂寞之感,却充满着一个战士的自我策励的精神:毫不懈怠,永不退转。《过客》用对话体,《这样的战士》里出现反复重叠的语句,以表示战士的坚韧和执着。
《这样的战士》:绝望的抗战。对所有物的反叛和决绝。在无物之阵的战斗。
诗与思的存在方式
思是一种父性存在的本能,它把生命的丰富性加以贮存,肢解和研究;思是生命丰富性的死亡档案图,理性碾碎了生命鲜活的躯体。诗是鲁迅存在的母体,它以母性存在的慈爱和宽容接纳每一位宽容的旅客,迷津于途中的人常常回到诗的怀抱。《野草》表现了诗歌与哲理性的内在思想。
《野草》总的艺术特征是内敛的抒情的倾向,它所表露的是灵魂的“真”与“深”,是对于人自身存在的困境的自觉体验与突围,表现了人的生存矛盾与心理困惑:生与死,爱与恨、希望与绝望、存在与虚无的缠绕与挣扎。《野草》也呈现出主题的丰富性和不确定性,是鲁迅情绪、情感、性格甚至整个内心世界各个侧面的反映,它是鲁迅从启蒙的文化批判者向启蒙后的战斗者转折过渡阶段的心灵史。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