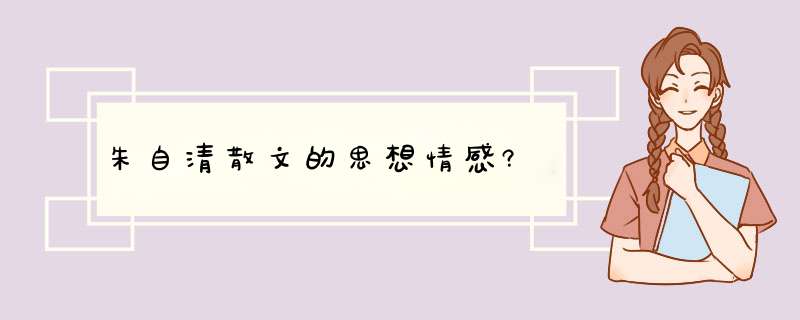
他散文的核心是一个“真”字。用真挚的感情,写真实的见闻和感受,记写真实的景物,发表真实的议论。朱自清的散文,从题材上说是比较狭窄的,不过是亲友的交往,家庭的琐事,即使后期那些议论的文字,也很少发空论。但就是这样,因为时时追求真切的内容,却能感动读者。正如当年作家赵景深说的:朱自清的文章,“不大谈哲理,只是谈一点家常琐事,虽是像淡香疏影似的不过几笔,却常能把那真诚的灵魂捧出来给读者看”。就是因为这样,朱自清散文才取得了感人的力量。
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名篇里大都是身边的凡人琐事,但是在这些事情中传达着他对生活的思索和感悟。先生的语言清丽凝练,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在平淡中传递着真挚的感情:《背影》、《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匆匆》等都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名篇,打动了无数读者的心,也让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因树立了“白话美文的模范”而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周作人《乌蓬船》一、作家简介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鲁迅之弟,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他比鲁迅年少四岁,早年也和鲁迅一样东渡日本留学。他禀赋聪颖,精通日语,又通英语和希腊语,中国的古书也看了很多,以至被人誉为“博识”。一九一一年回国以后,他也和许多人一样深恶黑暗的社会现实,“五四”文学革命时,他就曾举起人道主义文学的旗帜,为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更在挽联上奋笔直书:“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但是,就在这积极入世的姿态背后,却还隐伏着另一种情感,那就是对于社会进步的悲观看法。他曾说:“昔者巴枯宁有言,‘历史唯一的用处是警戒人不要再那么样’,我则反其曰,‘历史的唯一的用处是告诉人又要这么样了!’”在写于一九三三年的《知堂文集序》里,他更说自己“常有故鬼重来之惧”。这使人想起鲁迅,他也同样痛感到封建历史的沉重因袭,也曾多次以宋末、明初的黑暗世道来例比现实。但在鲁迅,失望越深,反越煽旺了“绝望的抗争”的冲动;而在周作人,博识和敏感加在一起,却蒸发出一股销蚀斗志的冷气。倘说鲁迅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周作人却可以说是知其不可为就不为。在愚民专制的国度里,清醒当然是一件难得的好事,但如果被这清醒浇灭了热情,那就反而成了坏事。周作人似乎正是这样,年岁越长,阅历越深,他就越少有激动的时刻。既然不相信有身外的目标可以追寻,他就只能以调整主观态度来稳定自己;既然无需急急地赶向前方,那就干脆放慢脚步,随意游逛消闲吧。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他在《雨天的书》的序言中写道:“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景地”,虽然“生在中国这个时代,实在难望能够从容镇静地做出平和冲淡的文章来”,他却仍然祈望自己的心境不要再粗糙下去,很怀念那种“田园诗的境界”。在写这段话的时候,他似乎还在田园诗和道德文章之间犹豫不定,一面追求平和的情趣,一面也禁不住要发出《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那样的怒叫。但到写于一九三五年春天的《关于写文章》里,他却明确宣布了自己的选择:“我想写好文章第一须得不积极。不管他们卫道卫文的事,只看看天,想想人的命运,再来乱谈,或者可以好一点,写得出一两篇比较可以给人看的文章。”倘按照这个标准,《乌篷船》大概就是属于这样的文章。二、作品分析有许多散文一下子就能够吸引住我们。因为它们那饱含深情的辞句和激动人心的内容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就像把你拉到一道壮阔的大瀑前面,不由得你不动心。但也还有另一种散文,它本身并没有涂着鲜艳的色彩来惊撼我们,但在它那些貌似平常的辞句后面,却往往流动着一种特别的情趣,宛若浓荫下的一条暗溪,悄悄地滋润我们的心田。周作人的《乌篷船》似乎就属于这一类,倘在嘈杂的车厢里一目十行,你很可能觉得它淡而无味;但如果在静夜的台灯下从容品味,你或许却会在掩卷之后浮出会心的一笑。(一)情绪内涵1、写出不慌不忙,娓娓道来的从容心境,用轻描淡写掩盖思乡感情。《乌篷船》是周作人早期散文中很为人所称赞的一篇。初读有琐细和平淡之感。说它琐细,《乌篷船》里记叙乌篷船的用途、种类、结构、外形,几乎是絮絮地谈,状物唯恐其不细,绘貌唯恐其不周。那些工匠式的介绍特别是那几句对船头的描述:“船头著眉目,状如老虎,但仍在微笑,颇滑稽而不可怕。”分明流露出了对家乡风物的亲近感情。尽管作者的语气很平静,我们却不难揣想他那副津津乐道的表情。那些似乎漠然而处的形容句更都一个个活动了起来:跨上脚划的小船,“仿佛是在水面上坐,靠近田岸去时泥土便和你的眼鼻接近”。这感受多么真切,我们仿佛也坐在左右摇晃的小划子里,迎着岸边的泥土和小草靠过去了。《乌篷船》用的是简体文字,是为外乡朋友子荣君介绍家乡风物而写的,记叙中的琐细,微微沁出一种人情味的温暖。2、表现作家内心情绪的闲适、自如,完全放松的态度。作家正是用一种洒脱的笔调、平淡的语言,渲染出一种物我两相会的情境。说它平淡,《乌篷船》在细细介绍船本身后,转而向收信人建议一种乘乌篷船的态度。作家的意见是:以为船速度是缓慢的,乘客坐在船上,“应该是有山的态度”。我们在阅读过程中期待作家把船行水上的见闻尽情地写上几段美文,但读下去,却很平淡:四周的景物,无非是“随处可见的山,岸旁的乌桕,河边的红蓼和白苹,渔舍,各式各样的桥。”仅此而已。没有辞藻装饰,而行船夜景,也只有这么的一句:“夜间睡在舱中,听水橹声,来往船只的招呼声,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也都很有意思。”而泊船看庙戏,则只说“在船上行动有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酒,我觉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乐法。”然后引申到对“布业会馆”里上海的猫儿戏的讥评。真是平淡得可以!但,假若你再细细玩味,就又会发现这种平淡是作家有意识的一种平淡。3、明显地表现出一种特殊的人生态度。看上去他是在历数沿河的景致,从岸旁的乌桕、红蓼和白苹,到稍远处时时可见的山,各式各样迎面而来的桥,都记得那样清楚;看上去他是在讲述夜航的趣味,从舷下的水声橹声,到岸上的犬吠鸡鸣,描绘得那样生动;看上去他是在怅叹旧俗的衰亡,从庙戏如何有趣直说到那些新建的“海式”剧场多么粗俗,好恶又是那样分明!可实际上,这一切都不是他要说的主要的话。他并不仅仅要告诉我们他家乡有哪些风物,他更要让我们知道应该怎样去领略这些风物。他一开头就告诫说:“你如坐船出去,可是不能像坐电车的那样性急,……倘若出城,走三四十里路(我们那里的里程是很短的,一里才及英里三分之一),来回总要预备一天。”这岂不太慢了吗?可作者说,正是要这样慢:“你坐在船上,应该是游山的态度,……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写到雇船看庙戏时,他更明白说:“在船上行动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觉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乐法。”原来,作者笔下的那些山、水、树、桥,都是要用这样慢悠悠的态度才能欣赏的,重要的不是田园景致,而是抱着闲适的心情去亲近它们。不是匆匆忙忙,更不是步履沉重;不是愁容满面,更不是怒气冲冲;心平气和,悠闲自在,不惊不乍,随遇而安——这似乎就是《乌篷船》作者偏嗜的处世态度。(二)美感特征对于浮躁时代里的芸芸众生来说,领略周文,能唤起一种乡土情结,升腾起一种淡淡的心境。周作人的选材极平凡琐碎,一经过他的笔墨点染,就透露出某种人生滋味,有特别的情趣。尽管那种情趣可能未免落寞、颓废,适合所谓“中年心态”。周作人的小品常将口语、文言和欧化语杂糅调和,产生一种涩味与简单味,很耐人咀嚼。他的闲话体散文有些类似明人小品,又有外国随笔那种坦诚自然的笔调有时还有日本俳句的笔墨情味,周作人显然都有所借鉴,又融入自己的性情加以创造,形成平和冲淡、舒徐自如的叙谈风格。人们常用“闲适”来概括周作人的散文风格,期间蕴涵着丰富的审美内容,一方面是淡而且深的寂寞之苦,另一方面又别有一种淡淡的喜悦,可以说是“苦中作乐”,忧患中有洒脱,也就是周作人所说的“凡人的悲哀”。
在一个各式各样“经典”层出不穷的年代,人们以诸如“红色经典”、“鲁迅经典全集”、“朱自清散文经典全集”、“中国中篇小说经典”等名义,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甄选,一方面是势所必然的,另一方面又不禁让人心生疑虑:由于缺乏必要的距离,这些所谓的“经典”真的能经的起岁月的淘洗吗或者说,如果真的有所谓“现当代文学经典”的话,又是哪些质素的存在,使这些作品区别于中国古典及世界文学史上的其它经典之作,而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呢
虽然对于《憩园》的评价一直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但是,现在的大多数现当代文学研究者还是倾向于承认,《憩园》至少是包含了一些可以构成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的因素的。因此,通过分析《憩园》文本所包含的经典性因素,或许将有助于我们发现构成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的部分典律之所在。
一
与巴金的其它小说相比,《憩园》的最大特征在其复杂性。这种复杂性首先表现在小说的结构方面。相对于巴金小说经常采用的单线结构,《憩园》的结构非常类似于一出戏剧:《憩园》讲述了“我”、姚国栋、杨梦痴、万昭华、姚小虎、寒儿等人的身世经历和情感体验,故事的主体是“现在的故事”,各个人物“过去的故事”通过回溯来体现,并对“现在的故事”的发展、突变造成直接的影响。再加上瞎眼女人和老车夫的故事这条隐含线索,使《憩园》在较短的篇幅内包含了繁复的内容,“而且故事之间及其各自内部意绪的冲突构成了文本价值取向与情感指向的复杂性,形成了作品的复调品格。”也就是说,由于《憩园》中“各个故事中的多种思绪彼此诘问、相互质疑,”即使是人物的同一行为,出于不同的价值立场和观察角度,也有着迥乎不同的认识与评价。因此,作者对于人物的价值判断在这里被暂时搁置,《憩园》在情感表达方面因此呈现出一种复杂难明的特质。
比如,在批判杨梦痴腐化堕落、自私自利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他对于家园的深深眷恋、对于美好事物的无限热爱、对于家人的真诚忏悔,都让人不由自主地对他有所宽宥;姚国栋的眼高手低、言不顾行固然让人觉得好笑,但他对朋友的古道热肠、对亲人的深挚之爱,又让人不禁对他的不幸遭遇给予深切同情;万昭华的温柔善良、充满爱心使《憩园》整体上的灰暗色调带上了一抹温暖人心的亮色,但她种种帮助别人的设想却只是停留在口头,对于所处环境的无力摆脱使她成为一只无法真正飞翔的“笼中鸟”;“我”对于社会的冷静观察、对于他人的真诚救助、对于存在意义的痛苦思索,体现出一个启蒙者的可贵品质,可“我”始终只是一个无能为力的旁观者,不管是杨梦痴、姚国栋,还是万昭华、寒儿,“我”的介入对于他们的命运没有产生丝毫的改变……
就像许多论者指出的那样,使《憩园》包含了如此丰富歧异的情感的缘由,是因为巴金本人人到中年、初建家庭,心态变为平和;是因为时代的变迁,过去家族罪恶的制造者如今也成为封建制度的牺牲品;是因为战争的艰苦环境,使巴金进一步体认到人的凡俗本性;是因为“‘我’对写作价值的消解,意味着对五四新文学确立的改良人生、疗救人生的启蒙主义功用的怀疑,一定意义上也是对时代赋予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变革社会责任的疑虑”。这一切使得《憩园》中的人物更接近生活本身,而不是某种价值观念的载体,《憩园》因此也就成为一出关于“人”的悲剧:“《憩园》真正要哀悼的主要是作为‘人’的杨梦痴、万昭华、姚国栋等因自身存在的人性弱点而导致或将要导致的‘非人’待遇。这是难以避免却又不能不正视的人间悲剧。”
对于“人”的悲剧的揭示及正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同于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人”的意识的觉醒,使现代中国人不再把人生的希望寄托于外来的拯救上,而必须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必须独自面对“人”的生存困境并做出自己的选择。在这一选择过程中,由于发现社会的黑暗与不公、人性的丑陋与卑劣以及“人”的脆弱和无奈并产生悲剧精神也是在所难免的。在此意义上,“在文学经典的价值维度中,文学精神始终是最重要的一维,而对于‘五四’后的中国文学而言,悲剧精神及其衍生的批判精神构成了其文学精神的某种核心。”这种现代文学精神使中国现当代作家不能仅仅满足于为读者营造一个远离尘嚣的美丽梦境,而是借助自己的作品书写普通人柴米油盐的琐碎生活和备受煎熬的内心世界,再现他们挣扎求生过程中感受到的希望与幻灭、幸福与失落,现当代文学作品由此也很难拥有简单明晰的价值判定和包治百病的万用良方,而充满了种种必须承受的人生苦痛,表现出一种浓重的悲悯意识。
那么,面对“人”存在的苦痛与人生的荒寒,必须自我负责的现代中国人该如何应对以暴易暴,用自己和他人的牺牲换取未来美好生活的选择是否值得践行,就像巴金早期小说中的主人公那样
《憩园》中对于杨家长子杨和形象的处理因此变得极富暗示性。与巴金笔下的其他“长子性格”不同,杨和不仅意识到自己身上肩负的家庭责任,更有决心和能力履行这一责任;他不会停在原处、自怨自艾,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人走向末路,而是一个有着铁一般手腕的坚决地行动派;他敢于挑战父亲的权威,动用自己的关系逼父亲出去工作,甚至不顾社会舆论将不成器的父亲赶出家门;在家产被父亲全部败光的情况下,他用自己的双手养活了家人,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爱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巴金小说中少有的成功者,一个充满希望的新人。然而,与杨梦痴和寒儿对于憩园的深情依恋不同,他对这个生长于斯、充满祖辈温馨记忆的园子没有丝毫的温情,而以强硬的态度代父亲签字将憩园卖给别人;在杨梦痴已经表示了对于家人的真诚忏悔,也了解到他食不果腹的生活处境之后,杨和依然对父亲拒不接纳,这也是导致杨梦痴最终悲惨死去的一个主要原因,小说对于他心理活动的刻意回避,正反映了巴金对这一人物的复杂态度。“如果说在他身上体现了巴金的毁灭冲动的话,那么这可能不是本我的弑父冲动,而是作者内心的通过毁灭来谋求新生的欲望。这个欲望在巴金40年代之前的作品中有着大量的表现,但却是第一次被作者与无情二字如此彻底地嫁接在了一起。”下意识中,巴金希望塑造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强有力的人物,以满足他改变现状的强烈内在需求,却又无法接受与这种性格伴生的杨和的冷酷无情,在他身上,反映了巴金对于暴力与正义问题的深入反思,体现了巴金对于知识分子或者说文学价值的重新定位。
五四文学精神指五四运动时期创造和形成的文学精神和文学传统。
五四文学精神指五四运动时期创造和形成的文学精神和文学传统。其内涵包括:
1 强调文学要走出象牙塔,关注社会现实,关心人民疾苦,表现时代精神,为人民大众服务。
2 强调文学要追求个性解放,反对封建传统,反对封建礼教,强调人的自由和尊严。
3 强调文学要创新,反对模仿和抄袭,强调文学的创造性和创新性。
4 强调文学要注重思想性和艺术性,强调文学要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
五四文学精神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精神和传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现代"作为一个时间概念:
①传统分法:1917—1949 多数学者如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程光炜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等
②现在分法:包括当代文学,1917至今南方不少学者如朱栋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上即指1917—1949,下指1949至今
另外,还有一种把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都包括进去的说法: 20世纪中国文学不过,上限又推到1898至今如孔范今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下,山东文艺出版社1993;黄修己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上,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刘明馨,赵金钟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纲》上,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等
2,"现代"作为一个性质概念:
《三十年》"序言":"所谓'现代文学',即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
①语言上,白话文代替文言文
②文学形式上,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的内涵和地位古今均一样
③创作方法上,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并重
④内容上,真正属于"现代人"的思想,情感,审美心理,审美标准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个性主义,劳工神圣,儿童崇拜,妇女解放最关键一点,个人的出现——现代意义上的个人的出现于是,一切思想,情感 和审美心理均从个人出发,皆因个人变化特别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和出现
中国现代文学起于新文化运动胡适鲁迅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带领中国人开始了新文化的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进入了新的文学思潮改变了人们的一些封建观念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但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些绝对否定的错误态度也是毋庸置疑的2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特别是西方的文艺思潮对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很大,也很复杂。
首先说西方现实主义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关系。在“五四”时期,西方的很多文学思潮被引进中国,但“五四”文学却独尊现实主义。但是,“五四”文学的现实主义又与西方现实主义不同,它显现出宽泛化的趋势。只要是现实主义价值取向所需的,统通作为现实主义。反映了“五四”文学主体心态的开放性。却也牺牲了其它美学观念、思潮的独立性。
其次说说西方浪漫主义思潮与五四浪漫主义文学的关系。“五四”文学在理论上并不提倡浪漫主义,因为觉得它不够趋时。但有些作家的作品实际上已经有意无意地趋近于浪漫主义了。比如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创造社是从情感表现角度选择与接受浪漫主义的。但“五四”文学的浪漫主义并不等同于西方浪漫主义,它带着浓郁的时代特点,同时又倾向于现实主义。
郁达夫是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代表人物,他的小说以“自我抒情小说”为主,代表了“自我抒情小说”的最高成就,其在1921年10月于创作社成立后出版的小说《沉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小说集,也是其著名的代表作之一,形成了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一股浪漫派的壮观潮流,也使“自我抒情小说”成为一种流派。
其影响及其意义:
一、推动了以“自我表现”为中心的新艺术观的发展。
它不再强调文艺创作的“事真”,“理真”,不再把现实生活作为艺术创作的准绳,而是在意人的情感和直觉,它改变了五四时期写实小说的历史地位,冲击着文人尤其是青年人的心灵,使他们不再拘泥于对现实的表现,而是随意的抒发自己的情感,以表示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因此我们说它推动形成了一种新的艺术观,即“为艺术而艺术”。
二、促进了青年人的思想启蒙和人性解放。
在《沉沦》中,他注意到了性欲和情欲在人的内心世界的重要性,他对此进行深刻的剖析。郁达夫认为人的合理欲求应该得到自由发展,因此他在著作中毫不遮掩的直接写“性”,对虚伪的传统道德及国人的矫饰习气进行了公开的挑战,“艺术的写出升华的情色”,这些将人性主义,个性解放表现至极,他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一时间引起强烈反响,出现了“郁达夫热”的局面,从此青年人开始试图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爱与情欲,中国人的情欲开始逐步得到释放。
三、开创并推动了“自叙传”小说的发展。
我们都知道中国现代小说的最初体式是“自叙传”抒情小说,而作品多集中于创作社,其实“自叙传”小说的真正开始应该始于郁达夫1921年的《沉沦》。郁达夫在五四后竭力标榜“文学家的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因此他的很多作品,如《茑萝行》,《青烟》,《春风沉醉的晚上》,《迷羊》,《银灰色的死》,《怀乡病者》,《采石矶》等无不映射着他自己的身影,这些著作大部分素材取材于他的个人经历和情感变化,郁达夫深刻的认为“除了自己之外,实在另外也没有比此更真切的事情了”,他觉得作家的作品就该“赤裸裸的把我的心境写出来”,以求“世人能够了解我内心的苦闷就行了”。因此他在创作过程中,用充满激烈的情绪和语调抒发感情,力求做最坦率的作家,我们后人将他开创的这种文学体式称为“自叙传”,毫无疑问的,这种体式保存了下来并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四、饱含了爱国主义情感,对中国人的觉醒起到了激励作用。
郁达夫一生中所创作的作品,无一不表露出其强烈的爱国情感。从其开始创作至终,一直都是中国文坛抨击旧道德,旧礼教,宣扬个性解放的代表和先驱。他对拘泥人性的衰落的社会原则进行了毫不避讳的强有力的抗争,以文人式的不乏夸张情绪的激愤在当时获得了青年人的共鸣,他一直抒发着对这个任人凌辱的弱国的忧伤,并不断替妇女和下层人民鸣不平,他憧憬着有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会重新出现光明,终于他的苦闷化为激愤的控诉,他用大胆的暴露及无所顾忌的语言文字充当革命的武器,尽管很多文字语言有失理性元素,尽管他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但他却实实在在的是一个革命者,他以一个文弱书生的形象为救国图强奉献了自己短暂的一生,激励了一代年轻人的继续奋斗。
总之,贯穿郁达夫一生的是个性主义和爱国情感,这两大元素在其短暂的生命旅途中不断得到延伸和升华。我认为他的“自我抒情”抒的不是“自我情”,而是“民族情”。因为他汇聚了一个时代的情感,说出了一个被压迫民族的历史要求,他的憧憬实际上是整个民族的憧憬,所以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闪耀明星。
自文艺复兴以来,始终存在着对宗教进行严厉批判、妄想消灭宗教的思潮和代表人物。但宗教始终没能被消灭。事实上,除了象道教这样缺乏改革冲动的宗教以外,世界上主要的宗教不但没有衰亡,反而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象基督教神学在二十世纪就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产生了一批世界级的思想家。佛教和伊斯兰教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曾经有人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以科学代宗教”的主张,但他们的论点不但从学理上站不住脚,而且也已为历史事实所击碎。值得注意的倒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吕澄、李淑同和刘小枫等美学家和艺术家从美育走向了宗教。这说明了宗教有其本身不可代替的价值。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没有也不可能摧毁宗教,其他文化形式也不可能取代宗教。
宗教是不可以被取代的。我们不能设想没有宗教的文化会是什么样子。假如阿拉伯人没有伊斯兰教,假如西方人没有基督教,假如中国人没有佛教,那么他们的文化会是什么样子?设想有一种文化会脱离了宗教而发展是愚蠢的。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蠢事,蠢事是不可能成功的。宗教是人的终极关怀,因而与人的生存本质相关。历史上的宗教可能被意识形态的毒质所污染,但宗教的本质是不会被污染的。宗教的本质是永远是纯净的。它既在于它自身之中,又内在于一切文化形式中。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皆不能摆脱宗教。
回顾一个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研究历程,可以看到宗教与文学的关联。我们可以列举出相当一批与宗教文化关系密切或有着不同程度关联的现代中国的重要作家,诸如鲁迅、周作人、巴金、老舍、曹禺、冰心、许地山、丰子恺、郭沫若、郁达夫、茅盾、沈从文、艾青、徐志摩、戴望舒、朱自清、林语堂、废名、张爱玲、庐隐、萧乾、宗白华、夏沔尊、冯至、施蛰存、张资平、何其芳、孙犁……等等。“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各不同时期有特色有影响的作家都与宗教文化有着某种关联。”(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3页)这种关联的发生是很自然的。尽管五四时代及其以后的科学主义思潮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占有压倒优势,但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宗教情结却始终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近代传入的基督教和固有的儒、佛、道传统合流,在新的历史情境下维系了中国人的终极关怀,并若隐若现地通过种种途径表现出来。在观念层次上,尽管与日本、与西方有很大的差距,也还是不乏对宗教的深入研究与探讨。
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当属基督教和佛教。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引起了许多复杂而深刻的矛盾冲突,对它的影响要做正确的评价和分析。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基督教激活了中国人已经气息奄奄的信仰精神,使中国人从委顿中醒来,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一如当初佛教初传时候一样。中国新文学的先驱们就已经注视到了基督教文化的独特作用和价值。陈独秀1920年2月1日在《新青年》第七卷第3号上发表《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对基督教的平等博爱、牺牲奋进、至上人格、反思忏悔等精神品格表示了热烈的颂扬。在他看来,“基督教是爱的哲学”,“基督教的根本教义只是信与爱,别的都是枝叶”。他呼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如果说陈独秀还主要限于从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来鼓吹基督精神的话,那么鲁迅则直接切入了文化和文学的内核。他在著名的《摩罗诗力说》里高度评价了希伯来文学的殊胜意义:“虽多涉信仰教诫,而文章以幽邃庄严胜,教宗文术,此其源泉,灌溉人心,迄今兹未艾。”他呼唤“精神界之战士”在中国的出现,这里面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深沉的基督教精神。周作人所提倡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以人道主义的“爱的哲学”通向了基督教的“博爱”主题。他说:“现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差不多也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近代文艺上人道主义思想的源泉,一半便在这里。”(《圣书与中国文学》)还从艺术发展的角度肯定“文学与宗教确有关系”,“文学的发达,大部出于宗教”。“人类所有最高的感情便是宗教的感情,所以艺术必须是宗教的,才是最高尚的艺术。”
从创作实践来看,新文学中出现了一批深刻体现基督教精神的作家和作品。冰心 作品中的“爱”的主题,明显来自作者对基督教的博爱精神的深刻体认。而随着新文 学的不断深化,基督教文化的更深层次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来。如有的学者所指出:“郁 达夫作品中无休止的忏悔意念,曹禺作品中摆不脱的原罪倾向,巴金作品中醇厚执着 的人道主义责任感,老舍作品中无处不在的平民意识,以及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等等, 这些蕴涵着基督教文化精神的艺术思考,无疑使中国现代文学在思想内涵方面具有了 某种新的文化特质。”(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
佛教在近代中国的文化影响也许更加值得我们注意。以杨仁山先生为首的佛教居 士和僧人,使中国佛教从明末以来的极度式微的局面中摆脱出来,逐步走上了复兴之 路,给中国近代文化以深刻的影响。佛教中本来所有的自由精神、独立意志、进取精 神和牺牲精神与近代西方文化的自由精神相结合,使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活动重 新焕发了活力。一方面是新的具有入世精神的“人间佛教”佛教的形成和发展,另方面是文学艺术活动中的佛教精神的新展现。以鲁迅为例。鲁迅可以说是现代中国作家 中对人生的认识和体验最深刻的人物。他的作品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而他对日常生 活中的平庸和卑微的小人物的描写,常常使人喘不过气来。他关注人的苦难,关注中 国人的国民性,其实都与他对佛教的偏好有关。佛教本来就起源于解脱人生苦难的要 求,而人生最难摆脱的当然是死亡的威胁。鲁迅从自身的苦难中体会到了人的生存的 严酷,从而孳生出解脱的大愿。他探寻过多种道路,包括外在社会政治革命。但鲁迅对政治革命实际上并不报多大的希望。《阿Q正传》典型地表明了这一点。所谓的“国民的劣根性”其实植根于人性的黑暗中,也就是佛家所说的“无始无明”中。所以鲁迅始终是很悲观的,这使他既摆脱了一般作家的肤浅的乐观主义,也使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看穿人生的苦难,与政治操作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其他一些人那里,佛教文化的表现采取了不同的形式。苏曼殊的作品尽管不多, 却能以惊才绝艳的文笔,写出佛法追求与爱欲之间的深刻纠缠,突显了悲剧性的意味。而周作人、废名、丰子恺等人则以从容而优雅的笔触,表现了一种禅的精神。宁静淡泊、清幽旷远的人生境地和舒缓雅洁、坦荡从容的心绪,使读者在动荡混乱中依稀看到了一片古老的精神家园。但这决不是对传统佛教和禅宗的简单回归,而是灌注了近代文化精髓、荡涤了传统文化渣滓的新的精神意向。其他的作者如许地山、沈从文等则表现了一种把多种宗教结合起来的意向。许地山的《债》里即包含着三层意蕴:第一层是还债人的佛家慈悲为怀的心肠和儒家高度自觉的忧患意识;第二层是岳母所信奉的顺着境遇做人,弃绝非分之想的道家人生哲学;第三层则是“还债人”那种深刻而莫名的基督教的忏悔意识和献身精神。这种多重宗教意蕴还可以在林语堂等人那里看到。
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不止体现在宗教情结上,还体现在叙事结构、艺术语言和艺术意境上。中国现代文学的浓烈的抒情性和深层次的隐喻性,显然来自基督教文学的刺激。佛教文化对现代白话文运动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而艺术氛围和意境的营造,则与宗教意识的流注密不可分。
文学与宗教是不可分割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宗教文化同样是不可分割的。尽管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对宗教采取了极端的态度,但改革开放以来宗教又明显地呈现出自身固有的活力。在作家的笔下,宗教精神和宗教意识也多姿多彩地表现出来。贾平凹、张承志、张炜等人的创作,显然自觉地走向了某种宗教追求。尤其是张承志的《心灵史》,极其悲壮地展示了一个民族为信仰而战的历史,在当代文学中具有震撼性意义。这也许象征着未来中国的精神路向。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