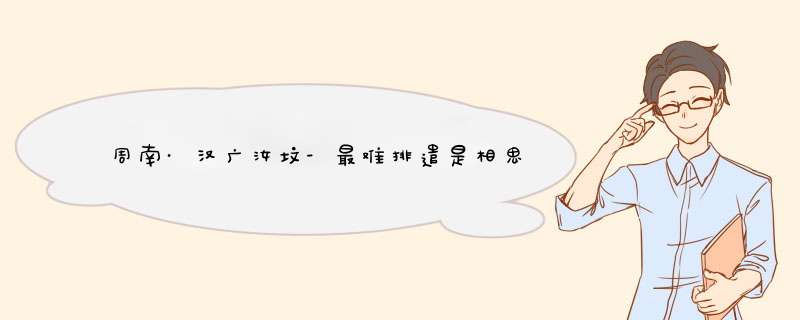
相比于螽斯桃夭的意思浅近,汉广和汝坟这两首则显得格外晦涩。正是因为这种晦涩,让历代注释家在这两首诗上找到了发挥的余地,有人结合政治,说汉广赞美文王治下民风淳朴,游女不可求,而汝坟是女子劝勉丈夫为国效力。有人结合历史,说汉广是周天子警告楚人不要渡过汉水,王师正盛不要自讨苦吃;说汝坟是镐京被焚,平王东迁。
当然我们之前说过“诗无达诂,断章取义”,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解读诗经,这个就是夫子所说的“不学诗无以言”,你不学诗经,就不知道怎么跟人讲话,为什么,不信你看《孟子》 ,动不动就拉一段诗经出来,把对手说个云遮雾罩。
我们不是注释家,就不要尝试给自己加戏了,毕竟戏份太多对表演痕迹太明显,脱离了思无邪的精神。
这两首就是情诗而已,汉广说男子思念游女;汝坟说女子思念征夫。游女,出游之女,一面之交,求而不得。征夫,结发恩情,一旦出征,再不回头。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蒌。之子于归。言秣其驹。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不押韵的诗,读来自然费劲,前面我们说过诗经其实是押韵的,我们正是通过这个理论,去反推很多雅言的古音。
汉广相对而言,诗经里面算生僻字很少了,但由于押韵方式不合中古诗歌的方式,读来还是有点佶屈聱牙。
矣和思可以算语气词,也可以算虚词,作用只有一个,凑数,不仅凑字数,还凑节奏,诗经中普遍存在为了节奏牺牲韵脚的做法,但通过适当的读法,还是可以读顺的。
南有乔木,不可休-汉有游女,不可求-,这里思做助语词,轻读或停顿都可以。
江之广-不可泳-江之永-不可方,这里用的是回环韵,矣和思只要没有重音,并不会影响押韵。
这首诗,描绘了一位男子出行,在汉水边看到一位同样出游的女子,惊鸿照影之下,一见钟情,从此相思成疾,喂马想她,劈柴也想她,还怪汉水太宽阔太长远,没办法过河去找梦中情人。
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未见君子,惄ni4如调zhao1饥。
遵彼汝坟,伐其条肄。既见君子,不我遐弃。
鲂鱼赪cheng1尾,王室如毁。虽则如毁,父母孔迩。
巧合的是另外一首写相思成疾的诗,也是发生在水边,似乎相思如水,是很自然的事情。
汝坟,指汝水边的堤岸。这是一个**,在河堤上抱怨自己的丈夫,开征夫怨女诗先河。
汝坟,与卷耳类似,也是怨妇怀念征夫,但与卷耳不同,卷耳是丈夫已离家多时还未回来而心生埋怨,而汝坟是留不住刚走的丈夫而忍不住抱怨。
未见君子,既见君子,两句在反复中递进,起兴都是在汝水堤坝上砍伐树枝,没看到你的时候如饥似渴,好不容易看到你了又离我远去,这里征夫依然归来却又远去,让人生疑,所以接着下句意向转换递进,不再是堤坝上的树木,而是水里的鲂鱼,鲂鱼现在叫鳊鱼,无论是方还是扁,指的都是形状,鲂鱼赪尾,是说鳊鱼的尾巴都红了,古人认为鱼用力过猛会尾巴发红,指代忧劳成疾,才刚回到家又要再次出征,王室如毁,因为王室遭遇了大难,要报效国家,就算要报效国家,你也要惦记自己的父母啊,这里不说自己单提父母,一个小媳妇的精明心思,忠孝难两全的困境,都跃然而出格外形象。
汉广和汝坟,都是发生的水边的故事,君子求偶,女子望夫,都是文学中经典的母题,求而不得相思成疾,也是亘古不变的故事情节。从这两首诗歌,我们大致可以窥见两千多年前,这片土地上生活的风采,也可以领略汉语诗歌一脉相承的抒情性。
原句:“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出自《诗经·国风·周南·汉广》
译文:汉江之水浩荡宽广,不能让我游泳渡河。汉江之水漫漫长流,不能让我坐木筏渡江。
注释
①汉:汉水,长江支流之一。
②泳:泅渡,用游泳的方式游过江河。
③江:江水,即长江。
④永:水流长也。
⑤方:桴,筏。此处用作动词,意谓坐木筏渡江。
赏析:这是一首恋情诗。诗人钟情于一位美丽的姑娘,却难以如愿,面对浩淼的江水而不能泅渡,唱出了这首满怀惆怅的欹。
读完《诗经·国风·周南》,为其中充溢着的美好情感感动着。
“周南”是当时周公统治下的南方地区的民歌,范围包括洛阳以南,直到江汉一带地区,具体地方包括今河南西南部及湖北西北地区。
《国风·周南》是《诗经·国风》中的部分作品,包括关雎、葛覃、卷耳、樛木、螽斯、桃夭、兔罝、芣苢、汉广、汝坟、麟之趾11首诗。
第一篇《周南·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写“君子”对“淑女”的追求,男子日思夜想,梦中与该女子鼓琴、弹瑟、起舞,不亦乐乎,醒来黄粱一梦。
第九篇《周南·汉广》: “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汉之永矣,不可方思。 ”
描写主人公偶遇“游女”产生感情,由希望到失望、由幻想到幻灭这一曲折复杂的情感历程。
第六篇《周南·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在最美好的年华,遇见最好的你。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女子嫁到丈夫家才算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意味着夫妻要把共同构成的家当做自己的家,生儿育女,和睦相处。
第三篇《周南·卷耳》:丈夫外出服兵役,常年不在家,妻子日思夜盼丈夫能早日平安回家。丈夫凯旋而归,在归途中表现归心似箭的心情。
第十篇《周南·汝坟》: 丈夫外出为朝廷服劳役,常年不回家,妻子在家劳心劳苦,无依无靠,希望自己的丈夫能够回来。但回来后却不能久待,还要离家。
时光在流失,但人类的美好情感是永存的。
《诗经 汉广》
南有乔木,不可休息①。汉有游女,不可求思②。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③。(一章)
翘翘错薪,言刈其楚④。之子于归⑤,言秣其马。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二章)
翘翘错薪,言刈其蒌⑥。之子于归,言秣其驹。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三章)
①姚际恒曰:“乔,高也。借言乔木本可休而不可休,以况游女本可求而不可求。”
②毛传:“思,辞也。”朱熹曰:“江汉之俗,其女好游,汉魏以后犹然•”
③毛传:“潜行为泳。永,长。方,泔也。”按泔也作桴,即竹木筏。
④朱熹曰:“翘翘,秀起之貌。错,杂也•”楚,马鞭草科,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南北皆有,又名荆,俗名荆梢。多隆阿曰:“荆为薪木,关左有二种,俱长条,高者七八尺,其一叶微圆,花紫色,枝条柔细,皮色赤黄,可编盛物器具者,俗名紫条;其一皮黑,叶碧,叶有岐杈,花紫,实黑者,俗名铁荆条。紫条为楛类,铁荆条即楚类。”
⑤《周南•桃夭》“之子于归”,朱熹曰:“妇人谓嫁曰归。”
⑥蒌,菊科,多年生草本。陆玑曰:“蒌,蒌蒿也。其叶似艾,白色,长数寸,高丈余,好生水边及泽中,正月根芽生旁茎,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叶又可蒸为茹。”桂馥曰:“陆疏云‘其叶似艾,白色’,余目验其叶青色,背乃白色,疏当云‘背白色’,疑转写脱谬。”
《诗》中的女子,有一类是可以明白见出身分的,如“平王之孙,齐侯之子”(《召南•何彼铱矣》),如“东宫之妹,邢侯之姨”(《卫风•硕人》),乃至“宗室牖下”习礼的“有齐季女”(《召南•采苹》)。如果“两姓之好”要求于女子的有所谓“公众的标准”,或曰“俗情之艳羡”(范家相说《硕人》),那么这是很重要的一条吧。所以她们在《诗》里都有一个在旁人看来一定是十分圆满的归宿,如《何彼襛矣》,如《桃夭》《硕人》所咏。但另有一类女子,则不然。若“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郑风•野有蔓草》),“有美一人,硕大且卷”(《陈风•泽陂》),既不及身分地位,也不论是否“宜其家室”(《桃夭》)、“宜尔子孙”(《周南•螽斯》),而纯是一片私心的慕恋。至于《汉广》,更干脆不把他私许的标准说出来,只道“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诗》中的这一类女子,我们是不知道伊之归宿的,我们只看到慕恋者在绵密的情思中建筑起一个实实在在的希望。
不过,即便作“空中语”,《诗》中也没有神奇幻丽之思。《汉广》中的“汉上游女”算是略存飘忽,三家说诗于是衍生出郑交甫遇神女的故事:郑交甫遵彼汉皋,台下遇二女,与言曰:愿请子之佩。二女与交甫,交甫受而怀之,超然而去。十步循探之,即亡矣。回顾二女,亦即亡矣。只是这样一来,便成了完全的神话,虽然此中的幻丽也很美,但离《汉广》则已经很远。
游女虽然不是神女,却是神女一样的可望而不可即。“不可求思”,不是怨恨也不是遗憾,万时华曰“‘不可求’,语意平平,着不得一毫意见,如言欲求之不得,则非诗人言;昔可求而今不然,则非游女”,是也。然而无怨无憾的“不可求思”,却正是诗情起处。戴君恩曰:“此篇正意只‘不可求思’自了,却生出‘汉之广矣’四句来,比拟咏叹,便觉精神百倍,情致无穷。”贺贻孙曰:“楚,薪中之翘翘者,郑笺云‘翘翘者刈之,以喻众女高洁,吾欲取其尤高洁者也’,此解得之。盖汉女惟不可求,此乃我所欲求也,故即以‘之子于归’接之,此时求且不可,安得便言于归,凭空结想,妙甚妙甚。至于愿秣其马,则其悦慕至矣,却不更添一语,但再以汉广、江永反复咏叹,以见其求之之诚且难而已。盖‘汉广’四句乃深情流连之语,非绝望之语也。”“凭空结想”、“深情流连”,所见透彻。江永、汉广,全是为“不可求思”设景,则刈楚、刈蒌,秣马、秣驹,自然也都是为思而设事。“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古诗十九首》之句由《汉广》脱胎,但《汉广》却没有如此之感伤。《诗》有悲愤,有怨怒,有哀愁,却没有感伤。这一微妙的区别,或许正是由时代不同而有的精神气象之异。而《汉广》也不是“今朝两相视,脉脉万重心”的无奈。实在说,这里并没有一个“两相视”,《汉广》没有,《关雎》《东门之池》《泽陂》《月出》,这样的一类诗中,都没有。这里似乎用得着“乐而不*”、“哀而不伤”的意思,但它却与道德伦理无关,而只是一份热烈、持久、温暖着人生的精神质素。《诗》写男女,最好是这些依依的心怀,它不是一个故事一个结局的光明,而是生命中始终怀藏着的永远的光明。它由男女之思生发出来,却又超越男女之思,虽然不含隐喻,无所谓“美刺”,更非以微言大义为为政者说法,却以其本来具有的深厚,而笼罩了整个儿的人生。
《汉广》,《诗经·国风·周南》里排在第九篇的诗歌。在历来注家的解读中,对该诗的诗歌主题争议较大,大致形成 “神女遗佩说”、“文王德化说”、“樵夫歌唱说” 三种主流观点。
非主流观点更是若干,如关乎“成妇之礼”、“留马、返马之礼”的婚俗说;关于楚人先祖季连、穴熊“逆水求女”的抢夺婚俗说;立足“游”字贬义的告诫周族子弟说等。
虽然各家说法差异较大,各执一词,但不难看出他们的共通点,即都认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的诗歌核心。只不过对于为什么“不可求”的解释不一样罢了。对此,他们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游女”的身份及所处的文化背景之上。
首先看“神女遗佩说”。它的典型代表是《鲁》、《齐》、《韩》三家诗。这三家解说《诗经》的学派,同属今文经学。他们对《汉广》的注解属于一种富于意趣的附丽,他们将诗篇本意和汉水女神结合起来的做法,比较传奇。
根据清代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所言,三家诗所叙述的“神女遗佩”故事大同小异,基本剧情如下: 汉水女神为二女。一日出游于汉江之湄,路遇郑交甫。交甫心悦之,借橘柚之事求其佩,受而怀之。去十步,佩遗。顾二女,不见。
这故事是不是听起来很熟?仿佛在哪儿听到过。没错,这种浓郁的熟悉感来源于文学作品中“神女原型”的广泛运用。这早在屈原的《九歌》中就有明确的篇章,如《湘君》、《湘夫人》、《山鬼》等;还有宋玉《高唐赋》和《神女赋》中所绘的巫山神女之事;以及曹植《洛神赋》中的洛水之神宓妃等。
三家诗以汉江女神故事注解《汉广》,可能基于以下三点原因:
第一 ,借女神之不可求得来证“汉有游女,不可求思”的说服力强。毕竟,若将游女定为汉水之神,那么凭借着神灵的虚幻莫测之能,不可求思的说法便极其可靠。这也和诗篇的大部分内容侧重说“不可为”相契合。
第二 ,借女神之不可求得来比喻心上人之不可求思。换句话说,这是一首男子单恋诗,诗中的游女是现实中人,因种种原因所限不可求思,如汉水女神一般,遥不可及。
第三 ,汉江流域为楚地,楚地信巫奉鬼、重视神明,将游女注解为汉水女神,更符合当地的民风民俗,这应该是直接受《楚辞》等文学作品中“神女原型”的影响。
当然,“神女遗佩”这种注解过于虚无缥缈,主打现实主义风格的《诗经》不应当有此浪漫主义的乱入。所以,这种说法并未得到多少后学者的拥戴,信奉者寥寥。但这至少说明汉儒解读《诗经》的路子颇广,具备很好的发散思维。
按孔子所说,《诗》本来就是“可以兴”的东西,汉朝的董仲舒也说“诗无达诂” ,可以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那么,发散式解《诗》也就不足为奇了。
接下来看“文王德化说”。实际上,这是古文经学一脉对《汉广》诗的主流解读,发源于《毛诗序》,以后诸家多有拓展,如《郑笺》、《诗集传》等。
其中,《毛诗序》认为:《汉广》诗是文王之道对南国施加有利影响的表现。其解诗的逻辑是: 正因为有周文王广及天下的德化教育,才有汉江流域男女知礼节、守礼义之举,才有男子对心仪游女的“无思犯礼,求而不得”。
《郑笺》的说法是: 在商纣王时期,*逸之风遍及天下,维江汉流域最早接受文王之化。 朱熹《诗集传》则结合前两家,指出: 文王之化先行于江汉之间,移风易俗,故游女端庄静一,不复前日之可求,《汉广》对此再三咏叹之。
由此看来,“文王德化说”的核心要素是“礼” ,具体囊括了周王朝时期所施行的一系列礼仪制度和礼乐精神。正是受这些周礼的影响,汉江流域的游女们一改之前自由奔放的民风,修得端庄淑静,从而使该地的男子在面对心爱的游女时,因不能冒犯礼教,故求女不得。实际上,这是《汉广》诗的道德主题。
联系《毛诗序》对《诗经》其他篇目的解读,可以看出:国风的《周南》、《召南》自成一个教化体系。如《毛诗序》说《关雎》:“后妃之德”;说《葛覃》:“后妃之本”;说《卷耳》:“后妃之志”;说《樛木》:“后妃逮下”;说《螽斯》:“后妃子孙众多”;说《桃夭》:“后妃之所致”;说《兔罝》:“后妃之化”;说《芣苢》:“后妃之美”;至《汉广》,则由后妃之德转为“文王之道”……
如此这般,煞有介事,简直像是道德家精心编撰的教化讲义体系,且后来者多宗之。 所以,古文经学家解读《诗经》,免不了要穿凿附会。只有这样,才能使预先设定好的教化框架不乱,最终成为面向广泛大众的教化普及工具。
实际上,就汉朝的历史背景来看,这种以“人伦教化”为中心的体系,是应着东汉时期“名教”兴起的产物。
时光流转,到了清代,不同的解《诗》思路生根发芽。最为人瞩目的是方玉润的《诗经原始》,它从整体上一反旧规陈矩,沿着文学角度注解《诗经》,可说是离“经”叛“道”。但是,这恰恰就是今世之人赞赏最多之处。
方玉润认为,《汉广》是一首“樵唱”诗,诗中的“刈楚”、“刈蒌”、“错薪”即是证据。而且,南方多高山,樵夫进山打柴,多有唱山歌的风俗。此外,《汉广》诗的具体词句,俨然也是采樵活动的摹写。所以,这首诗大抵是樵夫歌唱对游女的爱慕,以及求而不得。
这种说法,突破了传统经学“谲谏主题”和“道德主题”的束缚,不再强调诗歌的“美政刺政”、“教化民众”之功,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影响较大。 但不得不说,方氏沿袭诗歌文本解读《诗经》的方法,基本抛弃了诗歌的创作背景,忽略了历史文化内涵的发掘,有些片面了。
那为何这种解读反而更受欢迎呢?这就涉及到文学理论层面的知识了。常言说, 一千个读者一千个哈姆雷特。 对文学作品的欣赏过程,本身就是读者对该作品的再创造过程。由于不同读者所具备的价值观、知识水平、思维能力、审美能力等不同,对同一作品的认识和理解自然不同。上升到群体层面,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价值观、知识水平、思维能力、审美能力等也是不一样的,那他们理解《诗经》的角度自然也不一样。
换句话说,解读《诗经》角度的差异在于解读者本身思想的差异。 这种差异,跨越时空存在。但在同一历史时期,总有一类思想占据主流地位,因而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在一定时期内大方向上基本一致。但从纵向看,即不同历史时期,对同一作品的理解差异便异常显著了。
明白了这些,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清代方玉润的《诗经原始》更受欢迎。因为,这是更接近于我们的时代,思想的差距远没有自汉朝到今天那么大。所以,我们不容易接受汉儒以来的经学解读,甚至屡屡尝试推翻它。但方氏基于文学视角的解读,我们则偏爱一些,哪怕它有着明显的缺陷。
近些年,研究《汉广》诗的论文文献不少,尤其是对诗歌主题的研讨。其中,大多数都是对前述三种主流观点的延伸,落脚点主要还是游女的身份及“不可求思”的原因。
总结说来,比较常见的游女身份有: 出游的女子、贞洁的女子、汉水女神 。具体到出游的女子,还有婚否的讨论、家庭背景的讨论等。各种猜测论证的目的,都是找出此游女“不可求”的原因。比如: 游女已婚、身份悬殊、游女贞洁、神人相隔之类 。说到底,还是跳不出“礼制”的范畴。
此外,倒是也有一些别出心裁的解释。比如,有些学者认为此游女的行为不合礼制,成诗《汉广》实为劝诫周家子弟莫要“求思”;还有学者认为此游女是正在行三月“成妇之礼”的女子,因婚礼未成,故“不可求思”;还有学者认为这是反映上古时代楚人特殊的族外抢婚习俗。
首先说游女不合礼制的解读 ,其主要依据是对“游”字的含义剖析。有学者指出,“游”字包含“*逸”这个贬义义项。而且楚地自上而下信巫奉鬼,重*祀,至唐代仍然如此。在婚恋上,即便到了汉朝时期,一些楚地民族依旧没有婚嫁礼法,男女交往仍带着远古朴素的色彩。
所以,对于重视礼教的周王朝子民来说,江汉流域的游女虽好,却仍然“不可求思”。这也正好体现了《毛诗序》中所说的“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换句话说,这种解释的立论根基是“无思犯礼”,属于预先设定好的礼制框架,这与前述古文经学家的解释思路基本一致。
其次说说周朝时期的“成妇之礼”、“留马、返马之礼”等婚俗与此诗的关系。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上古时代的贵族阶层结婚,有一种特殊的礼仪制度——成妇之礼。即贵族之女出嫁时,男方亲迎女方至男家后,不是立即举行婚礼同居,而是要教导三个月。教成之后,还要在祖庙举行祭告仪式,即“庙见之礼”,才算正式建立夫妻关系。
至于“留马、返马之礼”,则主要指男子迎娶女子时女方所乘车马的“留返”问题。彼时,女子出嫁,使用女家车马。到夫家后,女方将车马暂留男家。如婚姻礼成之后,夫家遣使将所留之马送返女家,仅留其车。
那这些婚俗跟《汉广》诗有什么关系呢?有学者认为,诗歌中的“游女”,就是指出嫁女,核心依据是诗句“之子于归”。这在《桃夭》篇中讲过,是女子出嫁的意思。女子所嫁的对象,就是《汉广》诗篇中的主人公。但他受限于三月“成妇之礼”,故而对游女“不可求思”。紧随其后的“言秣其马”、“言秣其驹”就是“留马、返马之礼”的写照。
从这个角度看,《汉广》诗所要表达的内容就不再是自然的男女情爱,更在于男主人公严守礼法、无逾礼制的精神。 也就是说,并非“游女不可得”,而是要遵循礼制而为。这就与《关雎》诗的自然求偶转礼乐婚姻一脉相承了。不过说到底,这还是基于“礼制”框架下的拓展解读。
最后,结合楚地婚俗说一说其他观点。 根据清华简《楚居》记录的楚人先祖传说,楚地民族早期盛行过抢夺婚俗。比如楚人祖先季连与盘庚之女妣隹之间、穴熊和妣列之间成婚的故事。
因为《汉广》所述,与《楚居》中两位楚人先祖“循水求女”,最终与其成婚的情节相似,所以有学者认为《汉广》为此类“抢婚习俗”的遗风。不仅如此,《诗经》中的《蒹葭》篇,基本的“求女”情节也是如此。还有源自楚地的《楚辞》当中,也有多个“求女原型”,如《离骚》中的三次“求女”;《湘君》、《湘夫人》中的“求神”等等。如此这般,若说它们之间毫无联系,显然不可能。
对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汉广》诗产生于江汉流域,难免受到楚地族群记忆的影响,这种“求女原型”的反复出现,是楚地族群早期历史记忆在后世文学作品中创造性地“再现”。
综上所述,对《汉广》诗歌的主题理解,关键在于确认“游女”的身份,并结合《汉广》诗创作的历史文化背景等信息。 但由于时间久远,文献资料匮乏,很难对这些问题做出定论。不过,历来钻研《诗经》者无数,各有各的讲法才是常态,不应该拘泥于所谓定论。
我们学习《诗经》,研讨《诗经》,主动梳理各家说法,其根本目的也不是要得出个什么真理或标准来,而是要在这些浩繁的言论中,理解《诗经》的时代价值。
要知道, 即便是同一部经典,在不同的时代,也有它不同的使命和价值。 因此,我们完全没必要争个你死我活。只要顺应时代浪潮,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便好。
——全文完——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