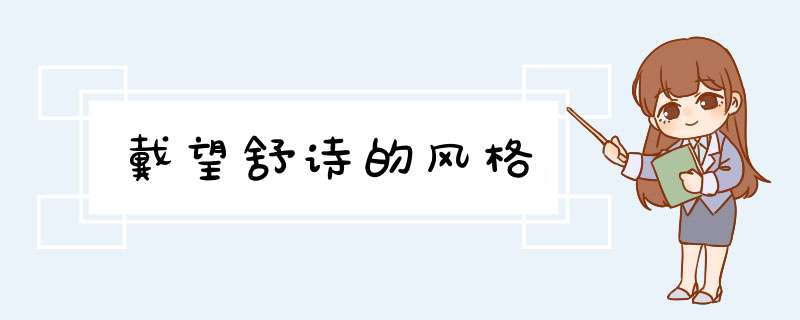
戴望舒一生的诗歌创作主要集中在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诗作数量不满百首,但却在中国新诗史上占据了一个重要地位,这一方面是因为戴望舒诗歌本身的质量决定了他的地位,另一方面是因为戴望舒的诗歌风格多变,基本上代表了那一段时期中国诗坛的演变史,具有相当的典型性。
诗人生前出的诗集有《我底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灾难的岁月》,其诗歌按照诗风的变化,可分为三个较明显的阶段:早期(1924年-1929年)、中期(1929 年-1937年)、晚期(1939 年-1945年)。
《我底记忆》为第一期,包括戴望舒早期诗作二十六首,分为《旧锦囊》《雨巷》《我底记忆》三辑。这三辑中也体现出在同一时期内戴望舒诗歌趋向的微妙变化。《旧锦囊》有着旧体诗词,特别是晚唐诗、宋词的哀艳感伤缠绵华丽的特色,也显现出英国颓废派和法国消极浪漫派的影响。《雨巷》辑则体现了诗人“对诗的音乐美,诗的形象的流动性和主题的朦胧性的追求;法国早期象征派诗人魏尔伦的意象‘模糊和精密紧密结合’、把强烈的情绪寓于朦胧的意象的主张,对他的影响甚为明显”[1],而《我底记忆》辑中的诗作则追求诗的口语化和淳朴自然,受到法国后期象征派果尔蒙、耶麦等人的影响。施蛰存曾说: “戴望舒的译外国诗,和他的创作新诗,几乎是同时开始”, “译道生、魏尔伦诗的时候,正是写《雨巷》的时候;译果尔蒙、耶麦的时候,正是他放弃韵律,转向自由诗的时候。后来,在四十年代译《恶之花》的时候,他的创作诗也用起韵脚来了”[2]。可以看出戴望舒诗歌每次诗风的转向都与西方诗歌的影响有关。
戴望舒二十年代中期开始写诗,当时诗坛的状况一方面正流行以坦白奔放为标榜的新诗,另一方面闻一多、徐志摩等人又正在进行新诗的格律化实验。戴望舒的诗作是对前一种取向的反叛,而对新月派等人的成果却有所借鉴。《旧锦囊》辑尚未脱去旧诗的痕迹,除了诗的外在形式是新诗而外,辞藻华丽雕饰、色彩浓艳,其意象古典化、题材意境也接近古诗,诗歌的情绪情感则显豁明白,悲哀伤感。从其用词中,我们可略窥一斑,如其景物词汇多为晚云、溪水、古树、远山、落叶、寒风、残花、蝴蝶、香泪等,抽象词汇则大多是忧愁、寂寞、伤感、孤苦、凄凉等,更像是古诗今译。不过在形式上还是有多方面的尝试,除对旧诗词的模仿外,也有注重口语化的《静夜》以及十四行诗的拟作。
戴望舒很快转向了《雨巷》阶段,着重表现在对新诗音韵的追求上,虽然此辑中的诗仍还有浓重的古诗意味,但已化用得很自然了。戴望舒虽非新月派诗人,但他《雨巷》一诗对新诗音乐化的贡献,却使得叶圣陶称赞他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纪元。《雨巷》以三顿诗行为主,间以二顿诗行,皆以双音节收尾,交错押韵,每节诗末一行以相同的脚韵呼应。间用句中韵,首尾二节重复一遍,特别是用了连续意义音节的跨行法,使音节的停顿若断若续,使诗义的连绵与音节的回环相应相合,同时又采用了几组排比句,更增加了诗的音乐感。朱湘曾赞美《雨巷》兼采有西诗行断意不断的长处,在音节上比起唐人的长短句来,实在毫不逊色。另一首《不要这样盈盈地相看》则很注意音韵的回旋往复,全诗共五段,一、三、五段的前三句重复同样的内容,只有末一句稍有变化,形成反复咏叹的效果。
-戴望舒并未在追求音韵上停留太长时间,不久之后,他写出了《我底记忆》,从对外在韵律的注重,上升到追寻诗的内在情绪的节奏和旋律。中国最初的白话新诗追求自然音节,近乎散文而失去诗的韵味,后来新格律诗派矫枉过正,对诗的音乐化作出了贡献。戴望舒在经历了新诗的格律化后,另辟新路,他吸取两种方式的优长,使不讲传统音律的新诗,在散文化的外表之下,也具有了内在的音乐美。《我底记忆》句式长短不齐,而且没有固定的韵脚,诗句舒缓自然,为其后期的《我用残损的手掌》等诗作开了先声。《独自的时候》以两组对立的意象相互映衬,一边是笑声、梦、音乐、白云等流逝把握不定的东西,一边是稳固不变的物象木器、烟斗等,形成诗歌的张力,写出了“人在满积着的梦的灰尘中抽烟”这样具有表现力的句子。《秋天》中“我对它没有爱也没有恨,我知道它所带来的东西的重量”等自由的语句,有着娓娓道来的平实亲切。
二
戴望舒中期诗作包括《望舒草》和《望舒诗稿》,他这一时期的诗作受法国象征派诗歌影响。象征派诗反对客观描述,强调表现自我内心,而这种对于内心的表达又不是用理智解释得明白的情绪,而是一种朦胧、复杂、幽微、深潜的感觉和情境。象征派主张这种情境应该通过对与之对应的大自然等外在景象的暗示描写才能捕捉到,因此在写诗时多采用象征、暗示等手法。象征派的这些特点又与中国传统诗词讲究含蓄、比兴的特点相契合。因此,新诗人们将其用来矫正新诗平白浅露的弊病,形成现代诗派。戴望舒就以其《望舒草》成为现代派的代表诗人。
《望舒草》带有很明显的象征派诗歌特点,摒弃了《雨巷》时期对音乐性的追求,以口语入诗,注重感觉和情绪的微妙对应,也注重通过暗示、通感等手法来表达内在不确定的情感。正如诗人在三十年代初写的《诗论零札》所提倡的一样: “新的诗应该有新的情绪和表现这情绪的形式”[3],诗人应该选择适合自己的诗歌形式就像选择适合自己的鞋子。这一时期的诗作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夜行者》《寻梦者》《乐园鸟》等诗都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每首诗中都有一个整体的象征笼罩。《夜行者》中是一个寂寞的夜行人,行走在黑夜中,像夜一样静,而围绕这个主体意象,则有冷清的街、黑茫茫的雾。全篇没有直接抒写诗人及同时代人的苦闷,但却借助这些自然物象恰切微妙的传达出了诗人的情绪,与前期诗作充满眼泪和哀叹的直抒胸臆相比,更含蓄也更有艺术的回味。
戴望舒在诗体的实验演变中,实际上内心是矛盾的,在不同时期仍会重回到诗歌的音律性上,诗人并未完全按照自己的诗歌理论去写诗,但此时的音乐性已不将诗囿于格律之内,而是注重新的自由诗的音律。《寻梦者》胜在作者对情感的准确把握和表现上,诗歌音乐感仍很强,但不曾像《雨巷》那样刻意追求音律。音韵运用自然,流畅的音韵排比的句式,便于作者抒发久藏于心的激情、沉郁与梦想。《寻梦者》如依据象征诗派的原则也许是不太标准的,但仍是一首好诗,因为诗歌的激情弥补了它不够含蓄的缺点。“你的梦开出花来了/ 你的梦开出娇妍的花来了/ 在你已衰老了的时候”,当人们读到这种句子的时候,会被它深深打动,而忘记它的技巧。余光中在批评戴望舒的诗论“诗最重要的是诗情上的nuance,而不是字句上的nuance ”时曾说: “诗情原藉字句以传,本无所谓谁更重要,真正重要的还是诗情所至,字句能否密切配合,正如颇普所云‘音之于义应如回声’就诗而言,最重要的该是有话要说,而不是在镜花水月暗香疏影之间顾盼斟酌,味其妙变。”[4]虽是批评之辞,我却觉得倒正好可以用来说明这首诗的成功之所在。戴望舒的创作虽属于现代派,但并不像现代主知派一样,以不使人动情而使人深思为特点,避免感情的发泄而追求智慧的凝聚,他诗歌的重心还是放在对情绪和情感的表达上,其方式正如他自己所言的是在隐藏和表达之间。
《乐园鸟》对理想的寻觅和求索是与《寻梦者》一样的,只是其中充满了更多的怀疑和绝望,再不像《寻梦者》那样怀抱着希望,诗人问着“华羽的乐园鸟/自从亚当,夏娃被逐后,那天上的花园已荒芜到怎样了”,乐园鸟是诗人的自况,表现出诗人的彷徨与抑郁。《乐园鸟》在诗歌节奏上实现了诗人的主张,即强调诗歌情绪的内在起伏,诗句长短搭配, “飞着、飞着,春、夏、秋、冬,/昼,夜,没有休止”用短促的顿来表现乐园鸟飞翔的情景。
这两首诗可以看作诗人中期的代表作,是诗人人生困境和精神困境经过审美抽象凝结同时又通过贴切的意象和诗情形象化了的象征体。
此期戴望舒也有其他诗体风格的尝试, 《印象》《秋天的梦》如轻轻的铃声的音乐美, 《烦忧》整齐匀称的回文形式美, 《村姑》富有戏剧色彩的白描, 《妾薄命》对古诗的仿拟, 《旅思》中现代白话与古典意韵的完美结合以及《秋蝇》对日本俳句的化用。说明戴望舒中期诗作虽深受象征派的影响,但也未放弃多种样式的探索。
三
戴望舒晚期的诗作主要集中在《灾难的岁月》中。当抗战的烽烟燃遍神州,惯于歌咏内心的诗人也不满足于一己的小悲欢,在大时代的震荡和巨变中,诗人改变了自己的诗学观念和诗歌风格,二十五首诗中有十六首写于抗战中,其诗风的转变也主要体现在这些诗中。诗人的这种转变并非很轻易,内心也并非毫不矛盾,他自己就曾批评过国防诗歌: “诗中是可能有国防的意识情绪的存在的,一首有国防意识的诗可能是好诗,唯一的条件是它本身是诗。但是反观现在的所谓‘国防诗歌’呢,只是一篇分了行、加了勉强的脚韵的浅薄而庸俗的演说辞而已。”[5]他在给艾青的信中说对自己抗战以来的诗很少满意,抗战初他还处于将诗艺探索和时代精神完美结合的尝试中。
不过,这种苦闷并未持续多久,从一九三九年戴望舒写出《元日祝福》开始,他后期诗风逐渐成型,主题和题材都有了新的拓展,在诗歌艺术上也出现了与此前截然不同的转折。“祝福!我们的土地& 血染的土地,焦裂的土地& 更坚强的土地将从而滋长”。这样的诗句中再也找不到那个伤感徘徊的“雨巷诗人”的任何影子。在香港沦陷后,诗人被日本特务逮捕,写了《狱中题壁》,出狱之后则有《我用残损的手掌》《等待》《等待·二》《口号》等。诗作中有了亮色和力度,对民族国家命运的关注,使得其诗较以前的作品视野更开阔,并充满了勃勃生气。这些诗篇大多都没有使用政治口号,但却准确地把握了时代脉搏,尤为可贵的是他克服了“国防诗歌”之弊,诗歌传达了民族情爱国心以及处于沦陷区的苦痛,但却未流于空洞和愤怒,激情充沛语言平易练达。正如孙玉石指出的那样: “望舒的诗的特征,是思想性的提高,非但没有妨碍他的艺术手法,反而使他的艺术手法更美好,更深刻地助成了思想性的提高。”[6]
戴望舒这些诗作增加了生活的实感,并突出地运用了白描手法,更注重表现由激情而产生的内在节奏。如果说《口号》太直白,宣传味太浓, 《等待·二》则沉郁有力,诗用叙述的语调简洁的短句抒写了诗人苦痛的心境。《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是此期的代表作,特别是后者,诗歌很有张力,节奏随着诗情起伏,想象驰骋的空间也很大,长短句错落有致,达到了既为自由诗同时又具有音乐美的较完美的境界。
戴望舒的后期诗作也还存在着另一种倾向,仍然创作了一些表达内心低徊情绪的诗作,如《白蝴蝶》《寂寞》《致萤火》《过旧居》等,不管他的诗风如何演变,这些悲哀的感喟似乎从未离开过他。他的《萧红墓畔口占》则赢得了余光中、臧棣等诗人的一致称赞,这是一首繁华落尽见真淳的好诗,余光中评其像唐人绝句的意境“初读似无文采,再读始见真情”#,戴望舒的多种风格的实验在这首小诗中达到了一个圆融的境界。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