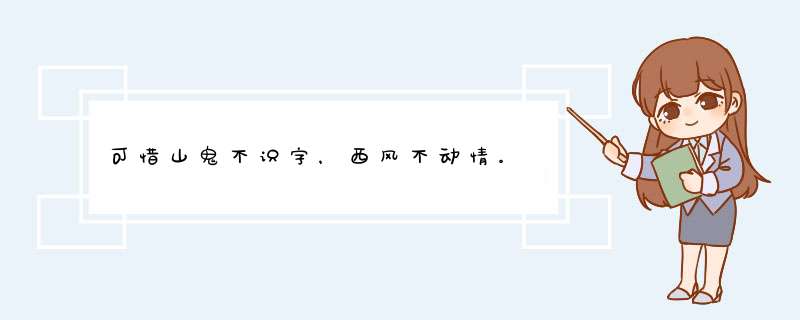
“可惜山鬼不识字,西风不动情”的意思是我的情书无人可给,心事无人可听,只好将情书给予山鬼,将心事说与西风,可惜山鬼看不懂,西风不解情。
作品出处
“山鬼”出自战国时期楚国伟大诗人屈原的作品《九歌·山鬼》,这是一首祭祀山鬼的祭歌,叙述的是一位多情的山鬼,在山中与心上人幽会以及再次等待心上人而心上人未来的情绪,描绘了一个瑰丽而又离奇的神鬼形象。全诗把山鬼起伏不定的感情变化、千回百折的内心世界,画得非常细致、真实而动人。
作品原文
九歌·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
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
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
表独立兮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
杳冥冥兮羌昼晦,东风飘兮神灵雨。
留灵修兮憺忘归,岁既晏兮孰华予?
采三秀兮于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
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
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
君思我兮然疑作。
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鸣。
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
作品注释
山之阿(ē):山隈,山的弯曲处。
被(pī):通假字,通“披”。薜荔、女萝:皆蔓生植物。
含睇:含情而视。睇(dì),微视。宜笑:笑得很美。
子:山鬼对所爱慕男子的称呼。窈窕:娴雅美好貌。
赤豹:皮毛呈褐的豹。从:跟从。文:花纹。狸:狐一类的兽。文狸:毛色有花纹的狸。
辛夷车:以辛夷木为车。结:编结。桂旗,以桂为旗。
石兰、杜蘅:皆香草名。
遗(wèi):赠。
余:我。篁:竹。
表:独立突出之貌。
容容:即“溶溶”,水或烟气流动之貌。
杳冥冥:又幽深又昏暗。羌:语助词。
神灵雨:神灵降下雨水。
灵修:指神女。憺(dàn):安乐。
晏:晚。华予:让我像花一样美丽。华,花。
三秀:芝草,一年开三次花,传说服食了能延年益寿。
公子:也指神女。
杜若:香草。
然疑作:信疑交加。然,相信;作,起。
靁:同“雷”。填填:雷声。
猨:同“猿”。狖(yòu):长尾猿。
离:通“罹”,忧愁。
作品译文
好像有人在那山隈经过,是我身披薜荔腰束女萝。
含情注视巧笑多么优美,你会羡慕我的姿态婀娜。
驾乘赤豹后面跟着花狸,辛夷木车桂花扎起彩旗。
是我身披石兰腰束杜衡,折枝鲜花赠你聊表相思。
我在幽深竹林不见天日,道路艰险难行独自来迟。
孤身一人伫立高高山巅,云雾溶溶脚下浮动舒卷。
白昼昏昏暗暗如同黑夜,东风飘旋神灵降下雨点。
等待神女怡然忘却归去,年渐老谁让我永如花艳?
在山间采摘益寿的芝草,岩石磊磊葛藤四处盘绕。
抱怨神女怅然忘却归去,你想我吗难道没空来到。
山中人儿就像芬芳杜若,石泉口中饮松柏头上遮,
你想我吗心中信疑交错。
雷声滚滚雨势溟溟蒙蒙,猿鸣啾啾穿透夜幕沉沉。
风吹飕飕落叶萧萧坠落,思念女神徒然烦恼横生。
创作背景
此篇为祭祀山神的颂歌。至于诗中的“山鬼”究竟是女神还是男神存在争议。宋元以前的楚辞家多据《国语》《左传》所说,定山鬼为“木石之怪”、“魑魅魍魉”,而视之为男性山怪。但元明时期的画家,却依诗中的描摹,颇有绘作“窈窕”动人的女神的。清人顾成天《九歌解》首倡山鬼为“巫山神女”之说,又经游国恩、郭沫若的阐发,“山鬼”当为“女鬼”或“女神”的意见,遂被广泛接受。郭沫若根据“于”字古音读“巫”,推断于山即巫山,认为山鬼就是巫山神女。楚国神话中有巫山神女的传说,此诗所描写的可能是早期流传的神女形象。
自苏雪林提出《九歌》表现“人神恋爱”之说以后,大多数研究家均以“山鬼”与“公子”的失恋解说此诗。该说法似乎不妥。按先秦及汉代的祭祀礼俗,巫者降神必须先将自己装扮得与神灵相貌、服饰相似,神灵才肯“附身”受祭。但由于山鬼属于“山川之神”,古人采取的是“遥望而致其祭品”的“望祀”方式,故山鬼是不降临祭祀现场的。此诗即按照这一特点,以装扮成山鬼模样的女巫,入山接迎神灵而不遇的情状,来表现世人虔诚迎神以求福佑的思恋之情。诗中的“君”“公子”“灵修”,均指山鬼;“余”“我”“予”等第一人称,则指入山迎神的女巫。
作品赏析
此诗一开头,那打扮成山鬼模样的女巫,就正喜滋滋飘行在接迎神灵的山隈间。从诗人对巫者装束的精妙描摹,可知楚人传说中的山鬼该是怎样倩丽,“若有人兮山之阿”,是一个远镜头。诗人下一“若”字,状貌她在山隈间忽隐忽现的身影,开笔即给人以缥缈神奇之感。镜头拉近,便是一位身披薜荔、腰束女萝、清新鲜翠的女郎,那正是山林神女所独具的风采!此刻,她一双眼波正微微流转,蕴含着脉脉深情;嫣然一笑,齿白唇红,更使笑靥生辉!“既含睇兮又宜笑,着力处只在描摹其眼神和笑意,却比《诗经·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之类铺排,显得更觉轻灵传神。女巫如此装扮,本意在引得神灵附身,故接着便是一句“子(指神灵)慕予兮善窈窕”——“我这样美好,可要把你羡慕死了”:口吻也是按传说的山鬼性格设计的,开口便是不假掩饰的自夸自赞,一下显露了活泼、爽朗的意态。这是通过女巫的装扮和口吻为山鬼画像,应该说已极精妙了。诗人却还嫌气氛冷清了些,所以又将镜头推开,色彩浓烈地渲染她的车驾随从:“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这真是一次堂皇、欢快的迎神之旅!火红的豹子,毛色斑斓的花狸,还有开着笔尖状花朵的辛夷、芬芳四溢的桂枝,诗人用它们充当迎神女巫的车仗,既切合所迎神灵的环境、身份,又将她手燃花枝、笑吟吟前行的气氛,映衬得格外欢快和热烈。
自“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以下,情节出现了曲折,诗情也由此从欢快的顶峰跌落。满怀喜悦的女巫,只因山高路险耽误了时间,竟没能接到山鬼姑娘(这当然是按“望祀”而神灵不临现场的礼俗构思的)。她懊恼、哀愁,同时又怀着一线希冀,开始在山林间寻找。诗中正是运用不断转换的画面,生动地表现了女巫的这一寻找过程及其微妙心理:她忽而登上高山之巅俯瞰深林,但溶溶升腾的山雾,却遮蔽了她焦急顾盼的视野;她忽而行走在幽暗的林丛,但古木森森,昏暗如夜;那山间的飘风、飞洒的阵雨,似乎全为神灵所催发,可山鬼姑娘就是不露面。人们祭祀山灵,无非是想求得她的福佑。现在见不到神灵,就没有谁能使我(巫者代表的世人)青春长驻了。为了宽慰年华不再的失落之感,她便在山间采食灵芝(“三秀”),以求延年益寿。这些描述,写的虽是巫者寻找神灵时的思虑,表达的则正是世人共有的愿望和人生惆怅。诗人还特别妙于展示巫者迎神的心理:“怨公子兮怅忘归”,分明对神灵生出了哀怨;“君思我兮不得闲”,转眼却又怨意全消,反去为山鬼姑娘的不临辩解起来。“山中人兮芳杜若”,字面上与开头的“子慕予兮善窈窕”相仿,似还在自夸自赞,但放在此处,则又隐隐透露了不遇神灵的自怜和自惜。“君思我兮然疑作”,对山鬼不临既思念、又疑惑的,明明是巫者自己;但开口诉说之时,却又推说是神灵。这些诗句所展示的主人公心理,均表现得复杂而又微妙。
到了此诗结尾一节,神灵的不临已成定局,诗中由此出现了哀婉啸叹的变徵之音。“靁填填兮雨冥冥”三句,将雷鸣猿啼、风声雨声交织在一起,展现了一幅极为凄凉的山林夜景。诗人在此处似乎运用了反衬手法:他愈是渲染雷鸣啼猿之夜声,便愈加见出山鬼所处山林的幽深和静寂。正是在这凄风苦雨的无边静寂中,诗人的收笔则是一句突然迸发的哀切呼告之语:“思公子兮徒离忧!”这是发自迎神女巫心头的痛切呼号——她开初曾那样喜悦地拈着花枝,乘着赤豹,沿着曲曲山隈走来;至此,却带着多少哀怨和愁思,在风雨中凄凄离去,终于隐没在一片雷鸣和猿啼声中。大抵古人“以哀音为美”,料想神灵必也喜好悲切的哀音。在祭祀中愈是表现出人生的哀思和悱恻,便愈能引得神灵的垂悯和呵护。
名家点评
朱熹:“此篇鬼阴而贱,不可比君,故以人况君、鬼喻己,而为鬼媚人之语也。”(《楚辞集注》)
汪瑗:“诸侯得祭其境内山川,则山鬼者,固楚人之所得祀者也。但屈子作此,亦借题以写己之意耳,无关于祀事也。”(《楚辞集解》)
王夫之:“此章缠绵依恋,自然为情至之语,见忠厚笃悱之音焉。然必非以山鬼自拟,巫觋比君,为每况愈下之言也。”(《楚辞通释》卷二)
钱澄之:“山鬼,盖山魅、木魈之属。往往能出而魅人,然人不慕之,亦不为所惑。篇中状其妖柔之态,婉娈之情,盖深足动人思慕者。惑者忘其为鬼,一则曰‘若有人’,再则曰‘山中人’,自惑之者言之也。述其居处服食,则分明鬼趣也。至欲留灵修,使之忘归,鬼情甚可畏也。” (《庄屈合诂》)
戴震:“《山鬼》六章,通篇皆为山鬼与己相亲之辞,亦可以山鬼自喻,盖自吊其与山鬼为伍,又自悲其同于山鬼也。歌辞反侧读之,皆其寄意所在。此歌与《涉江》篇相表里,以此知《九歌》之作,在顷襄复迁之江南时也。”(《屈原赋注》)
马茂元:“山鬼即山中之神。称之为鬼,因为不是正神。……篇中所说的是一位缠绵多情的山中女神,必然有着当地流传的神话作为具体依据,当非泛指。” (《楚辞选》)
谭介甫:“《河伯》《山鬼》为一偶,本来山与河是相对的,那么,鬼与伯也是相对的吗?《河伯》内容是说齐、楚使臣间的交际和别离,而《山鬼》虽多言楚事,但其间也言使齐事,还有一处提及齐国和齐王,已可见此两篇自有相同之点。……《山鬼》列在最后,多叙屈原和怀王君臣间的离合。”(《屈赋新编》上集)
作者简介
屈原(约前340—约前278),战国时期楚国政治家,中国最早的大诗人。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号灵均。学识渊博,初辅佐楚怀王,任三闾大夫、左徒。主张对内举贤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因遭贵族排挤,被流放沅湘流域。后因楚国政治腐败,首都郢被秦攻破,既无力挽救,又深感政治理想无法实现,遂投汨罗江而死。他写下了《离骚》《天问》《九章》《九歌》等许多不朽诗篇。其诗抒发了炽热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表达了对楚国的热爱,体现了他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和为此九死不悔的精神。他在吸收民间文学艺术营养的基础上,创造出骚体这一新形式,以优美的语言、丰富的想象,融化神话传说,塑造出鲜明的形象,富有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对后世影响很大。其传世作品,均见汉代刘向辑集的《楚辞》。
苏轼和王弗、王闰之、王朝云三位夫人
苏轼的一生,政治上是失意的,但是却有三位夫人陪伴他终其一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苏轼的文学成就也有她们的“一半”。这三位夫人便是结发之妻王弗、继室王闰之和侍妾王朝云。 苏轼与王弗 说到王弗,不能不使人想到苏轼在密州时写的一首词《江城子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是苏轼为亡妻王弗写的一首悼念词,被后人誉为“千古第一悼亡词”。苏轼为什么写这首词,而且写得如此感人?这要从岷江河畔的中岩寺说起。 中岩有座书院,青神乡贡进士王方执教时,好友苏洵把儿子苏轼送到中岩书院读书。苏轼聪明好学,王方喜爱在心,欲选为乘龙块婿。 中岩风景绝佳,寺下有一绿潭。每有人在池边击掌,鱼儿便从岩下游出。当时王方邀文人雅士为绿潭题名。或曰“戏鱼池”,或曰“观鱼塘”。不是过雅,就是太俗。苏轼最后展出他的题名“唤鱼池”,众人叫绝。苏轼正得意之时,王方的女儿王弗也使丫鬟从瑞草桥家中送来题名。红纸上,秀美的字迹跃然而出“唤鱼池”三字。众人惊叹,真是“不谋而合,韵成双璧”! 一天,苏轼与同窗到瑞草桥为老师祝寿而醉倒在老师家中。一觉醒来,天色已晚,独自漫步后院,师妹王弗正临窗梳头。苏轼顿生爱慕之心,便从怀里摸出从山上采来的一簇飞来凤花,轻轻投进窗去。王弗一惊,把那簇浓香阵阵的花苞贴在胸前……后来,王方请人做媒,将王弗许配苏轼。至和元年(1054),19岁的苏轼娶16岁的王弗。这就是“唤鱼联姻”的千古佳话。 婚后,王弗随苏东坡去京城相伴,夫唱妇随,恩恩爱爱,卿卿我我。王弗常伴苏轼书房陪读,“终日不去”。苏轼偶有遗忘,王弗能从旁提示。有时苏轼问其典籍故事,她也能“皆略知之”。 春天,苏东坡和王弗去放风筝,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夏天,苏东坡和王弗去赏荷花,才子佳人,其情深深; 秋天,苏东坡和王弗去拾枫叶,夫妻同心,其爱浓浓; 冬天,苏东坡和王弗去看梅花,两情依依,其景美美。 苏东坡对王弗说:“如果时间能停留,让我们天长地久,那该有多好!” 苏轼本性善良,固守着“世间无恶人”的信条。而王弗则时时不忘提醒他“江湖险恶”、“人心叵测”。26岁的苏轼担任凤翔府签判时,家中常有客人来访。王弗躲在屏风后听察苏轼和客人谈话,帮助苏轼辨别哪些人可推心置腹,交为朋友;哪些人口蜜腹剑,须提高警惕,以免受其害这就是“屏后听语”的故事。 “忽如一夜风云变,惊起鸳鸯生死隔”。治平二年(1065)五月,王弗不幸病逝京师,时年27岁。苏轼依父亲之言,“于汝母坟茔旁葬之”,从京城护送妻子灵柩回到老家,并在山坡上栽下三万棵青松——这该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景啊?又要植多长时间每种一棵又是什么心情呢?今人动辄送上玫瑰,即使999朵玫瑰吧,又怎能胜过这三万棵苍翠的青松呢?玫瑰易凋,青松长翠啊! 十年后,苏轼在山东密州做知州。一天夜晚,梦回中岩,醒来伤感不已,想到自己在宦海中的浮浮沉沉,又想起了温柔多情、娴雅贞淑的爱妻王弗,热泪纵横,天人永隔,情何以堪?于是,以文人的浪漫和超人的执著,写了这首《江城子·记梦》,向爱妻表达一份感天动地的情意。诗人用朴实无华、近似白话的语言,虚实相间,轻重结合,全无雕琢痕迹,却情真意远,韵味醇厚,回味无穷,令人倍感沉痛。 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曾用“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来评赞此词。读此词,似乎让读者看到字字都浸透着血泪、听到作者锥心裂肺的恸哭之声。自此以后,苏轼诗词中开始大量涌现“衰”、“老”、“早生华发”、“须髯稀疏”之类的词语,可见他的哀伤程度。难怪当今有位痴迷苏轼的美女读者说道:“来生嫁给苏东坡,哪怕历尽千年的情劫”。 苏轼与王闰之 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熙宁元年(1068),即王弗逝世后第三年嫁给苏轼。王闰之是进士王介之之女,能以11岁的年龄差距,给姐夫做填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苏轼人品和文采的仰慕。 王闰之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家庭妇女,她对姐姐所生的儿子苏迈和自己后来所生的苏迨、苏过,“三子如一”,视同己出。 王闰之陪伴苏轼前后共25年。其间,苏轼受到革新派的排挤,远离京城,从杭州通判到密州、徐州、湖州三地知州,怀才不遇,漂泊不定;侍妾王朝云还比较年幼,王闰之便成了支撑家庭生活的贤内助。更使人感动的是,她陪伴苏轼度过“乌台诗案”这段最难熬的日子和被贬黄州后的最艰苦的生活。 苏轼“乌台诗案”被捕入狱,王闰之惊怖之下,担心那帮小人还会从诗文中找出苏轼的罪状,于是便把苏轼的诗稿焚毁了。这件事也成了千百年来喜欢苏轼的人们心中一个永难弥补的遗憾。 苏轼被贬黄州时,从知州降为团练副使,从“从五品”降为“从八品”,仅有很少的4500文薪俸。王闰之便把它分成30串挂在房梁上,每天取1串以供家用。如有结余,放在大竹筒里,用以卖酒招待客人。苏轼在《后赤壁赋》写道:“有客无酒,有酒无肴……归而谋诸妇。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这个“妇”不是别人,正是王闰之。陈季常七次到黄州造访苏轼,也都靠王闰之操办吃住。她还和苏轼一起采摘野菜,赤脚耕田,变着法子给苏轼解闷。有时,孩子在苏轼面前牵衣哭闹,苏轼就像找到了“出气筒”一样,倾刻暴发出来,大骂孩子“傻”!闰之便开导说:“你怎么比小孩还痴,为什么不开心点呢?我弄点菜给您饮酒解闷就好了!”苏轼听后有所感愧,就把这件事写进诗里。患难夫妻,相濡以沫,何其感人! 王闰之虽然没有王弗那么具有政治才能,也没有王朝云那么聪明,在苏轼的熏陶下,也能触景生情,说一些含有诗情画意的话来。一天晚上,堂前梅花盛开,月色如洗,苏轼与朋友在花下饮酒。她脱口而出:“春月胜如秋月,秋月令人凄惨,春月令人和悦。”苏轼大喜:“你说的话真是诗家语言!”于是写了一首《减字木兰花》: 春庭月午,摇荡香醪光欲舞。步转回廊,半落梅花婉娩香。轻云薄雾,总是少年行乐处。不似秋光,只与离人照断肠。 被贬黄州是苏轼一生创作的丰收期。当今人们常说,“一位成功男人的背后,一定有位贤内助”!在黄州苦涩艰辛的岁月中,有这样的贤内助,对苏轼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安慰。 元佑八年(1093)8月,苏轼再度启用的第八年,46岁的王闰之在陪伴苏轼25年之后染病去世。苏轼哀伤至极,写下了感天动地的《祭亡妻文》: “呜呼!妇职既修,母仪甚敦。三子如一,爱出于天。 从我南行,菽水欣然。汤沐两郡,喜不见颜。 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须,弃我而先! 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干。旅殡国门,我实少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 这里,苏轼再次提到“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无奈天不假年,闰之竟然先他而去。“谁在家门里等我归来?谁往田亩里给我送饭?一切都已无法兑现,我的泪水已经流干!”哭诉之后,依照旧例,东坡将老妻的灵柩寄在国门之外的僧舍之内,并立誓:“将来惟有与你同穴而葬,才能履行一同归去的诺言!” 死后百日,他请大画家李龙眠画了十张罗汉像,献给妻子的亡魂。苏轼死后,苏辙将其与王闰之合葬,实现了祭文中“惟有同穴”的愿望。 苏轼与王朝云 有资料说,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时,“纳王朝云为侍妾”。 这件事,后人还根据《燕石斋补》中所说,王朝云乃杭州“名妓”,苏轼“爱幸之,纳为常侍”云云,附会成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 一日,苏轼与几位文友同游西湖。这时,丽日普照,波光潋滟,湖光山色,犹如仙境。宴饮时招来歌舞班助兴。悠扬的丝竹声中,数名舞女浓妆艳抹,长袖徐舒,轻盈曼舞。而舞在中央的王朝云又以其艳丽的姿色和高超的舞技,引人注目。舞罢,众舞女入座侍酒,王朝云恰好转到苏东坡身边。此时,她已换了另一种装束:洗净浓装,黛眉轻扫,朱唇微点,素衣净裙,清丽淡雅,楚楚可人。突然,天气突变,阴云蔽日,山水迷蒙。湖山佳人,相映成趣,苏轼灵感顿发,挥毫写下了传颂千古的西湖绝唱《饮湖上初晴后雨》: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浓装淡抹总相宜。 其实,史实并非如此。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九月初,苏轼接到“移知密州”的诰命,离杭前“王朝云来归”。 归者,归附也。一个小女孩来归附即将远行的苏轼,若不是孤儿,就必定是父母养之不起,实出于无奈而已。 当时,苏轼已经三十九岁,王朝云只有十二三岁。“纳为妾”之说,恐怕是文人墨客的附会、艳词了。细想想,也确实不合情理。 从苏轼的作品和有关资料上看,王朝云确是个聪敏的女子,长大后非常“懂得”苏轼,苏轼也十分钟爱朝云。在三位夫人中,苏轼为王朝云写的诗最多,对王朝云的评价也是极高的。他在《惠州荐朝云疏》中说:“有侍妾王朝云,一生辛勤,万里随从。”又在《朝云墓志铭》中说王朝云“敏而好义,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如一。” 元丰六年(1083),21岁的王朝云在黄州曾为苏轼生下了一子。苏轼想起昔日名躁京华而今却“自渐不为人识”,感慨之极,为儿子取名苏遯。遯者,隐藏起来而不让人知道踪迹也。苏轼为儿子取这个名字,反映了被贬后的思想变化。因此,他还作了一首自嘲诗: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唯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没有想到,10个月后,这个孩子在金陵夭折了。自此以后,王朝云再没有生育,成为她一生的遗憾。直到去世前,她还常为此伤心流泪。 苏轼流放惠州启程前,曾动员年纪尚轻的王朝云回南方。朝云不肯,始终随侍其身傍,成了苏轼后半生的生命支柱。苏轼在《朝云诗序》中写道:“予家有数妾,四五年间,相继辞去,独朝云者随予南迁”,过着“门薪馈无米,厨灶炊无烟”的清苦生活。她还开菜园,躬身耕种,缝补浆洗,克勤克俭,为东坡分忧解愁,任劳任怨。苏轼能在极度艰难困苦的处境下挺过来,这与王朝云的照顾、体贴是密不可分的。可惜,绍圣三年(1096)7月,朝云得了一种烈性传染病,不幸身亡,年仅三十四五岁。 朝云死后,苏轼将她葬在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并在墓上筑六如亭纪念她。亭柱上镌有一副楹联: 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 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这副楹联还包含着一个流传至今的故事——“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见识’。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坡捧腹大笑。” “不合时宜”四字是苏轼对自己一生的概括;“惟有”句说明她们不仅是患难夫妻,而且是心灵相通的知音。正因为“不合时宜”,也就只能“独弹古调”了。“倍思卿”句,表明苏轼对朝云的深深思念之情。 苏轼还为王朝云撰写一副挽联,其中“六不”和“六如”则进一步寄托着他对朝云的哀思: 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不垢不净 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 前一句出自《心经》,后一句出自《金刚经》。从这副对联中不难看出,苏轼一方面希望爱妻能够像佛家所说的那样“不生不灭”,一方面也为自己在佛经中找到精神上的解脱。这是何等凄婉的心境!自此,苏东坡一直鳏居未娶。 遗憾的是,王朝云与苏轼只有夫妻之实,而无夫妻之名,也就是说苏轼并没给王朝云以“妻”或“夫人”的名份。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苏轼与王弗是恩爱夫妻,其感情可谓之“清纯”,与王闰之是患难夫妻,其感情可谓之“厚醇”,而与王朝云是濡沫夫妻,其感情则可谓之“相知”了。尽管他们的一生充满了“悲欢离合”、“阴晴圆缺”,但是他们都给世人留下了最美好、最珍贵、最恒久的精神财富和道德遗产,让后人“取之无禁,用之不竭”,享之无尽也。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