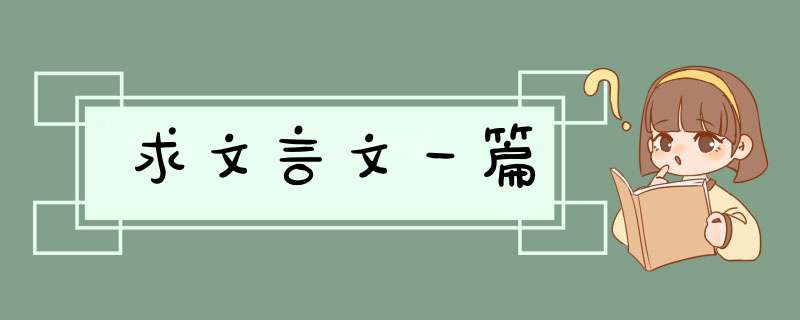
周易参同契
卷上
乾坤者,易之门户,众卦之父母。坎离匡郭,运毂正轴。牝牡四卦,以为橐
龠。覆冒阴阳之道,犹工御者准绳墨,执衔辔,正规矩,随轨辙,处中以制外,
数在律历纪。月节有五六,经纬奉日使。兼并为六十,刚柔有表里。朔旦屯直事,
至暮蒙当受。昼夜各一卦,用之依次序。既未至晦爽,终则复更始。日辰为期度,
动静有早晚,春夏据内体,从子到辰巳。秋冬当外用,自午讫戌亥。赏罚应春秋,
昏明顺寒暑。爻辞有仁义,随时发喜怒。如是应四时,五行得其序。
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者,乾坤之象也;设位者,列阴阳配合之
位也。易谓坎离,坎离者,乾坤二用。二用无爻位,周流行六虚。往来既不定,
上下亦无常。幽潜沦匿,变化于中。包囊万物。为道纪纲,以无制有,器用者空,
故推消息,坎离没亡。言不苟造,论不虚生,引验见效,校度神明,推类结字,
原理为征。坎戊月精,离己日光。日月为易,刚柔相当。土旺四季,罗络始终。
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禀中宫,戊己之功。
易者,象也。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穷神以知化,阳往则阴来。辐辏而轮
转,出入更卷舒。易有三百八十四爻,据爻摘符,符谓六十四卦。晦至朔旦,震
来受符。归斯之时,天地构其精,日月相掸持。雄阳播玄施,雌阴化黄包。混
沌相交接,权舆树根基。经营养鄞鄂,凝神以成躯。众夫蹈以出,蝡动莫不由。
于是仲尼赞鸿蒙,乾坤德洞虚,稽古当元皇,关雎建始初。冠婚气相纽,元年乃
芽滋。
圣人不虚生,上观显天符。天符有进退,屈伸以应时。故易统天心,复卦建
始萌。长子继父体,因母立兆基。消息应钟律,升降据斗枢。三日出为爽,震受
庚西方。八日兑受丁,上弦平如绳。十五乾体就,盛满甲东方。蟾蜍与兔魄,日
月气双明,蟾蜍视卦节,兔魄吐精光。七八道已讫,屈折低下降。十六转受统,
巽辛见平明。艮直于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东北丧其明。节尽相禅与,
继体复生龙。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终。七八数十五,九六亦相应。四者合三十,
阳气索灭藏。象彼仲冬节,草木皆摧伤。佐阳诘商旅,人君深自藏。象时顺节令,
闭口不用谈。天道甚浩广,太玄无形容。虚寂不可睹,匡郭以消亡。谬误失事绪,
言还自败伤。别序斯四象,以晓后生盲。
八卦布列曜,运移不失中。元精眇难睹,推度效符征。居则观其象,准拟其
形容。立表以为范,占候定吉凶。发号顺节令,勿失爻动时。上察河图文,下序
地形流,中稽于人心,参合考三才。动则依卦变,静则循彖辞。乾坤用施行,天
下然后治。
可不慎乎,御政之首。管括微密,闿舒布宝。要道魁杓,统化纲纽。爻象内
动,吉凶外起,五纬错顺,应时感动。四七乖戾,誃离仰俯。文昌统录,诘责
台辅,百官有司,各典所部。日合五行精,月受六律纪。五六三十度,度竟复更
始。原始要终,存亡之绪。或君骄溢,亢满违道;或臣邪佞,行不顺轨。弦望盈
缩,乖变凶咎,执法刺讥,诘过贻主。辰极受正,优游任下。明堂布正,国无害
道。
内以养己,安静虚无。原本隐明,内照形躯。闭塞其兑,筑固灵株。三光陆
沉,温养子珠。视之不见,近而易求。黄中渐通理,润泽达肌肤。初正则终修,
干立末可持。一者以掩蔽,世人莫知之。上德无为,不以察求;下德为之,其用
不休。上闭则称有,下闭则称无;无者以奉上,上有神德居。此两孔穴法,金气
亦相须。
知白守黑,神明自来。白者金精,黑者水基。水者道枢,其数名一。阴阳之
始,玄含黄芽。五金之主,北方河车。故铅外黑,内怀金华;被褐怀玉,外为狂
夫。金为水母,母隐子胎。水者金子,子藏母胞。真人至妙,若有若无。仿佛大
渊,乍沉乍浮。进退分布,各守境隅。采之类白,造之则朱。炼为表卫,白里贞
居。方圆径寸,混而相拘。先天地生,巍巍尊高。旁有垣阙,状似蓬壶。环匝关
闭,四通踟蹰。守御固密,阏绝奸邪。曲阁相连,以戒不虞。可以无思,难以愁
劳。神气满室,莫之能留。守之者昌,失之者亡。动静休息,常与人俱。
是非历脏法,内视有所思。履斗布罡宿,六甲次日辰。阴道厌九一,浊乱弄
元胞。食气鸣肠胃,吐正吸外邪。昼夜不卧寐,晦朔未尝休。身体日疲倦,恍惚
状若痴。百脉鼎沸驰,不得清澄居。累土立坛宇,朝暮敬祭祀。鬼神见形象,梦
寐感慨之。心欢而意悦,自谓必延期。遽以夭命死,腐露其形骸。举措辄有违,
悖逆失枢机。诸术甚众多,千条有万馀。前却违黄老,曲折戾九都。明者省厥旨,
旷然知所由。勤而行之,夙夜不休。服食三载,轻举远游。跨火不焦,入水不濡。
能存能亡,长乐无忧。道成德就,潜伏俟时。太乙乃召,移居中洲。功满上升,
膺箓受图。
火记不虚作,演易以明之。偃月法鼎炉,白虎为熬枢。汞日为流珠,青龙与
之俱。举东以合西,魂魄自相拘。上弦兑数八,下弦艮亦八。两弦合其精,乾坤
体乃成。二八应一斤,易道正不倾。铢有三百八十四,亦应卦爻之数。
金入于猛火,色不夺精光。自开辟以来,日月不亏明。金不失其重,日月形
如常。金本从月生,朔旦受日符。金返归其母,月晦日相包。隐藏其匡郭,沉沦
于洞虚。金复其故性,威光鼎乃熺。
子午数合三,戊己号称五。三五既和谐,八石正纲纪。呼吸相含育,伫思为
夫妇。黄土金之父,流珠水之子。水以土为鬼,土镇水不起。朱雀为火精,执平
调胜负。水盛火消灭,俱死归厚土。三性既合会,本性共宗祖。巨胜尚延年,还
丹可入口。金性不败朽,故为万物宝。术士服食之,寿命得长久。土游于四季,
守界定规矩。金砂入五内,雾散若风雨。薰蒸达四肢,颜色悦泽好。发白皆变黑,
齿落生旧所。老翁复丁壮,耆妪成姹女。改形免世厄,号之曰真人。
胡粉投火中,色坏还为铅。冰雪得温汤,解释成太玄。金以砂为主,禀和于
水银。变化由其真,终始自相因。欲作服食仙,宜以同类者。值禾当以黍,覆鸡
用其卵。以类辅自然,物成易陶冶。鱼目岂为珠,蓬蒿不成槚。类同者相从,
事乖不成宝。是以燕雀不生凤,狐兔不乳马;水流不炎上,火动不润下。
世间多学士,高妙负良材。邂逅不遭遇,耗火亡货财。据按依文说,妄以意
为之。端绪无因缘,度量失操持。捣治羌石胆,云母及矾磁。硫黄烧豫章,泥汞
相炼冶。鼓下五石铜,以之为辅枢。杂性不同类,安肯合体居。千举必万败,欲
黠反成痴。侥幸讫不遇,圣人独知之。稚年至白首,中道生狐疑。背道守迷路,
出正入邪蹊。管窥不广见,难以揆方来。
若夫至圣,不过伏羲。始画八卦,效法天地。文王帝之宗,结体演爻辞。夫
子庶圣雄,十翼以辅之。三君天所挺,迭兴更御时。优劣有步骤,功德不相殊。
制作有所踵,推度审分铢。有形易忖量,无兆难虑谋。作事令可法,为世定此书。
素无前识资,因师觉悟之。皓若褰帷帐,瞋目登高台。火记六百篇,所趣等不殊。
文字郑重说,世人不熟思。寻度其源流,幽明本共居。窃为贤者谈,曷敢轻为书。
若遂结舌瘖,绝道护罪诛。写情著竹帛,又恐泄天符。犹豫增叹息,俯仰缀思虑。
陶冶有法度,未可悉陈敷。略述其纲纪,枝条见扶疏。
以金为堤防,水入乃优游。金计有十五,水数亦如之。临炉定铢两,五分水
有馀。二者以为真,金重如本初。其三遂不入,火二与之俱。三物相含受,变化
状若神。下有太阳气,伏蒸须臾间。先液而后凝,号曰黄轝焉。岁月将欲讫,毁
性伤寿年。形体为灰土,状若明窗尘。捣治并合之,持入赤色门。固塞其际会,
务令致完坚。炎火张于下,昼夜声正勤。始文使可修,终竟武乃陈。候视加谨慎,
审察调寒温。周旋十二节,节尽更须亲。气索命将绝,体死亡魄魂。色转更为紫,
赫然成还丹。粉提以一丸,刀圭最为神。
推演五行数,较约而不繁。举水以激火,奄然灭光明。日月相薄蚀,常在晦
朔间。水盛坎侵阳,火衰离昼昏。阴阳相饮食,交感道自然。名者以定情,字者
缘性言。金来归性初,乃得称还丹。吾不敢虚说,仿效圣人文。古题记龙虎,黄
帝美金华。淮南炼秋石,玉阳加黄芽。贤者能持行,不肖毋与俱。古今道由一,
对谈吐所谋。学者加勉力,留念深思惟。至要言甚露,昭昭不我欺。
卷中
乾刚坤柔,配合相包。阳禀阴受,雄雌相须。须以造化,精气乃舒。坎离冠
首,光耀垂敷。玄冥难测,不可画图。圣人揆度,参序元基。四者混沌,径入虚
无。六十卦周,张布为舆。龙马就驾,明君御时。和则随从,路平不邪。邪道险
阴,倾危国家。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谓万乘之主,处九重之室,发号
出令,顺阴阳节,藏器待时,勿违卦月。屯以子申,蒙用寅戌,馀六十卦。各自
有日,聊陈两象,未能究悉。立义设刑,当仁施德,逆之者凶,顺之者吉。按历
法令,至诚专密,谨候日辰。审察消息,纤芥不正,悔吝为贼。二至改度,乖错
委曲,隆冬大暑,盛夏霜雪,二分纵横,不应漏刻,风雨不节。水旱相伐,蝗虫
涌沸,群异旁出,天见其怪,山崩地裂。孝子用心,感动皇极,近出己口,远流
殊域。或以招祸,或以致福,或兴太平,或造兵革。四者之来,由乎胸臆。动静
有常,奉其绳墨。四时顺宜,与气相得。刚柔断矣,不相涉入。五行守界,不妄
盈缩。易行周流,屈伸反覆。
晦朔之间,合符行中。混沌鸿蒙,牝牡相从。滋液润泽,施化流通。天地神
明,不可度量。利用安身,隐形而藏。始于东北,箕斗之乡。旋而右转,呕轮吐
萌。潜潭见象,发散精光。昴毕之上,震出为征。阳气造端,初九潜龙。阳以三
立,阴以八通。故三日震动,八日兑行。九二见龙,和平有明。三五德就,乾体
乃成。九三夕惕,亏折神符。盛衰渐革,终还其初。巽继其统,固济操持。九四
或跃,进退道危。艮主进止,不得逾时。二十三日,典守弦期。九五飞龙,天位
加喜。六五坤承,结括终始。韫养众子,世为类母。上九亢龙,战德于野。用九
翩翩,为道规矩。阳数已讫,讫则复起。推情合性,转而相与。循据璿玑,升降
上下。周流六爻,难可察睹。故无常位,为易宗祖。
朔旦为复,阳气始通。出入无疾,立表微刚。黄钟建子,兆乃滋彰。播施柔
暖,黎蒸得常。临炉施条,开路正光。光耀渐进,日以益长。丑之大吕,结正低
昂。仰以成泰,刚柔并隆。阴阳交接,小往大来。辐辏于寅,运而趋时。渐历大
壮,侠列卯门。榆荚堕落,还归本根。刑德相负,昼夜始分。夬阴以退,阳升而
前。洗濯羽翮,振索宿尘。乾健盛明,广被四邻。阳终于巳,中而相干。姤始
纪序,履霜最先。井底寒泉,午为蕤宾。宾服于阴,阴为主人。遯世去位,收敛
其精。怀德俟时,栖迟昧冥。否塞不通,萌者不生。阴伸阳屈,没阳姓名。观其
权量,察仲秋情。任畜微稚,老枯复荣。荠麦芽蘖,因冒以生。剥烂肢体,消灭
其形。化气既竭,亡失至神。道穷则反,归乎坤元。恒顺地理,承天布宣。玄幽
远渺,隔阂相连。应度育种,阴阳之元。寥廓恍惚,莫知其端。先迷失轨,后为
主君。无平不陂,道之自然。变易更盛,消息相因。终坤始复,如循连环。帝王
承御,千载常存。
将欲养性,延命却期。审思后末,当虑其先。人所禀躯,体本一无。元精云
布,因气托初。阴阳为度,魂魄所居。阳神日魂,阴神月魄。魂之与魄,互为室
宅。性主处内,立置鄞鄂。情主营外,筑固城郭。城郭完全,人物乃安。爰斯之
时,情合乾坤。乾动而直,气布精流。坤静而翕,为道舍庐。刚施而退,柔化以
滋。九还七返,八归六居。男白女赤,金火相拘,则水定火,五行之初。上善若
水,清而无瑕。道之形象,真一难图。变而分布,各自独居。类如鸡子,黑白相
符。纵广一寸,以为初始。四肢五脏,筋骨乃俱。弥历十月,脱出其胞。骨弱可
卷,肉滑若铅。
阳燧以取火,非日不生光。方诸非星月,安能得水浆。二气玄且远,感化尚
相通。何况近存身,切在于心胸。阴阳配日月,水火为效征。耳目口三宝,闭塞
勿发通。真人潜深渊,浮游守规中。旋曲以视听,开阖皆合同。为己之枢辖,动
静不竭穷。离气内营卫,坎乃不用聪。兑合不以谈,希言顺鸿蒙。三者既关键,
缓体处空房。委志归虚无,无念以为常。证难以推移,心专不纵黄。寝寐神相抱,
觉悟候存亡。颜容浸以润,骨节益坚强。排却众阴邪,然后立正阳。修之不辍休,
庶气云雨行。**若春泽,液液象解冰。从头流达足,究竟复上升。往来洞无极,
怫怫被容中。反者道之验,弱者德之柄。耘锄宿污秽,细微得调畅。浊者清之路,
昏久则昭明。世人好小术,不审道浅深。弃正入邪径,欲速阏不通。犹盲不任杖,
聋者听宫商。没水捕雉兔,登山索鱼龙。植麦欲获黍,运规以求方。竭力劳精神,
终年无见功。欲知服食法,事约而不繁。
太阳流珠,常欲去人。卒得金华,转而相因。化为白液,凝而至坚。金华先
唱。有顷之间,解化为水。马齿琅玕,阳乃往和,情性自然。迫促时阴,拘蓄禁
门。慈母育养,孝子报恩。严父施令,教敕子孙。五行错王,相据以生。火性销
金,金伐木荣。三五与一,天地至精。可以口诀,难以书传。子当右转,午乃东
旋。卯酉界隔,主客二名。龙呼于虎,虎吸龙精。两相饮食,俱相贪并。遂相衔
咽,咀嚼相吞。荧惑守西,太白经天。杀气所临,何有不倾。狸犬守鼠,乌雀畏
鹯。各得其功,何敢有声。
不得其理,难以妄言。竭殚家产,妻子饥贫。自古及今,好者亿人。讫不谐
遇,希有能成。广求名药,与道乖殊。如审遭逢,睹其端绪。以类相况,揆物终
始。五行相克,更为父母。母含滋液,父主禀与。凝精流形,金石不朽。审专不
泄,得为成道。立竿见影,呼谷传响。岂不灵哉,天地至象。若以野葛一寸,巴
豆一两,入喉辄僵,不得俯仰。当此之时,虽周文揲蓍,孔子占象,扁鹊操针,
巫咸扣鼓,安能令苏,复起驰走。
河上姹女,灵而最神。得火则飞,不见埃尘。鬼隐龙匿,莫知所存。将欲制
之,黄芽为根。物无阴阳,违天背元。牝鸡自卵,其雏不全。夫何故乎,配合未
连。三五不交,刚柔离分。施化之精,天地自然。犹火动而炎上,水流而润下,
非有师导,使其然也。资始统政,不可复改。观夫雌雄,交媾之时,刚柔相结,
而不可解。得其节符,非有工巧,以制御之。若男生而伏,女偃其躯,禀乎胞胎。
受元气初,非徒生时,著而见之。及其死也,亦复效之。此非父母,教令其
然。本在交媾,定制始先。
坎男为月,离女为日。日以施德,月以舒光。月受日化,体不亏伤。阳失其
契,阴侵其明。晦朔薄蚀,掩冒相倾。阳消其形,阴凌灾生。男女相须,含吐以
滋。雌雄错杂,以类相求。金化为水,水性周章。火化为土,水不得行。故男动
外施,女静内藏。溢度过节,为女所拘。魄以钤魂,不得*奢。不寒不暑,进退
合时。各得其和,俱吐证符。
丹砂木精,得金乃并。金水合处,木火为侣。四者混沌,列为龙虎。龙阳数
奇,虎阴数耦。肝青为父,肺白为母,肾黑为子,心赤为女,脾黄为祖。子五行
始,三物一家,都历戊己。刚柔迭兴,更列分部。龙西虎东,建纬卯酉。刑德并
会,相见欢喜。刑主杀伏,德主生起。二月榆落,魁临于卯。八月麦生,天罡据
酉。子南午北,互为纲纪。一九之数,终而复始。含元虚危,播精于子。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雄不独处,雌不孤居。玄武龟
蛇,蟠虬相扶。以明牝牡,竟当相须。假使二女共室,颜色甚姝,令苏秦通言,
张仪结媒。发辨利舌,奋舒美辞,推心调谐,合为夫妻。弊发腐齿,终不相知。
若药物非种,名类不同。分刻参差,失其纲纪,虽黄帝临炉,太乙执火,八公捣
炼,淮南调合。立宇崇坛,玉为阶陛,麟脯凤腊,把籍长跪,祷祝神只,请哀诸
鬼,沐浴斋戒,冀有所望。亦犹和胶补釜,以硇涂疮,去冷加冰,除热用汤,飞
龟舞蛇,愈见乖张。
卷下
惟昔圣贤,怀玄抱真。服炼九鼎,化迹隐沦。含精养神,通德三元。津液腠
理,筋骨致坚。众邪辟除,正气长存。累积长久,变形而仙。忧悯后生,好道之
伦。随傍风采,指画古文。著为图籍,开示后昆。露见枝条,隐藏本根。托号诸
名,覆谬众文。学者得之,韫椟终身。子继父业,孙踵祖先。传世迷惑,竟无见
闻。遂使宦者不仕,农夫失耘,商人弃货,志士家贫。吾甚伤之,定录此文。字
约易思,事省不繁。披列其条,核实可观。分两有数,因而相循。故为乱辞,孔
窍其门。智者审思,用意参焉。
法象莫大乎天地兮,玄沟数万里。河鼓临星纪兮,人民皆惊骇。晷影妄前却
兮,九年被凶咎。皇上览视之兮,王者退自改。关键有低昂兮,害气遂奔走;江
淮之枯竭兮,水流注于海。天地之雌雄兮,徘徊子与午。寅申阴阳祖兮,出入复
终始。循斗而招摇兮,执衡定元纪。
升熬于甑山兮,炎火张设下。白虎唱导前兮,苍液和于后。朱雀翱翔戏兮,
飞扬色五彩。遭遇罗网施兮,压之不得举。嗷嗷声甚悲兮,婴儿之慕母。颠倒就
汤镬兮,摧折伤毛羽。漏刻未过半兮,鱼鳞狎鬛起,五色象炫耀兮,变化无常主。
潏潏鼎沸驰兮,暴涌不休止。接连重叠累兮,犬牙相错距。形如仲冬冰兮,琅玕
吐钟乳。崔嵬而杂厕兮,交积相支柱。阴阳得其配兮,淡泊而相守。青龙处房六
兮,春华震东卯。白虎在昴七兮,秋芒兑西酉。朱雀在张二兮,正阳离南午。三
者俱来朝兮,家属为亲侣。本之但二物兮,末而为三五。三五并为一兮,都集归
二所。治之如上科兮,日数亦取甫。先白而后黄兮,赤黑达表里。名曰第一鼎兮,
食如大黍米。
自然之所为兮,非有邪伪道。山泽气相蒸兮,兴云而为雨。泥竭遂成尘兮,
火灭化为土。若檗染为黄兮,似蓝成绿组。皮革煮成胶兮,麹糵化为酒。同类易
施功兮,非种难为巧。惟施之妙术兮,审谛不诳语,传与亿世后兮,昭然自可考。
焕若星经汉兮,昺如水宗海。思之务令熟兮,反覆视上下。千周灿彬彬兮,万遍
将可睹。神明或告人兮,心灵乍自悟。探端索其绪兮,必得其门户。天道无适莫
兮,常传与贤者。
圆三五,寸一分,口四八,两寸唇,长尺二,厚薄均。腹齐三,温坐垂。阴
在上,阳下奔。首尾武,中间文。始七十,终三旬。二百六,善调匀。阴火白,
黄芽铅。两七聚,辅翼人。赡理脑,定升玄,子处中,得安存。来去游,不出门。
渐成大,情性纯。却归一,还本原。善敬爱,如君臣。至一周,甚辛勤。密防护,
莫迷昏。途路远,复幽玄。若达此,会乾坤。刀圭沾,静魄魂。得长生,居仙村。
乐道者,寻其根。审五行,定铢分。谛思之,不须论。深藏守,莫传文。御白鹤
兮驾龙鳞,游太虚兮谒仙君,受天图兮号真人。
参同契者,敷陈梗概,不能纯一。泛滥而说,纤微未备,阔略仿佛。今更撰
录,补塞遗脱。润色幽深,钩援相逮。旨意等齐,所趣不悖。故复作此命三相类,
则大易之情性尽矣。大易情性,各如其度。黄、老用究,较而可御。炉火之事,
真有所据。三道由一,俱出径路。枝茎华叶,果实垂布。正在根株,不失其素。
诚心所言,审而不误。
会稽鄙夫,幽谷朽生。挟怀朴素,不乐权荣。栖迟僻陋,忽略利名。执守恬
淡,希时安宁。宴然闲居,乃撰斯文。歌叙大易,三圣遗言。察其旨趣,一统共
论。务在顺理,宣耀精神。神化流通,四海和平。表以为历,万事可循。序以御
政,行之不繁。引内养性,黄老自然。含德之厚,归根返元。近在我心,不离己
身。抑一毋舍,可以长存。配以服食,雄雌设陈。挺除武都,八石弃捐。审用成
物,世俗所珍。罗列三条,枝茎相连。同出异名,皆由一门。非徒累句,谐偶斯
文。殆有其真,砾硌可观。使予敷伪,却被赘愆。命参同契。微览其端,辞寡意
大,后嗣宜遵。委时去害,依托丘山。循游寥廓,与鬼为邻。化形而仙,沦寂无
声。百世一下,遨游人间。敷陈羽翮,东西南倾。汤遭厄际,水旱隔并。柯叶萎
黄,失其华荣。吉人相乘负,安稳可长生。
参同契者,辞隐而道大,言微而旨深。列五帝以建业,配三皇而立政。若君
臣差殊,上下无准,序以为政,不致太平。服食其法,未能长生。学以养性,又
不延年。至于剖析阴阳,合其铢两,日月弦望,八卦成象,男女施化,刚柔动静,
米盐分判。以易为证,用意健矣。故立为法,以传后贤。推晓大象,必得长生。
强己益身,为此道者,重加意焉。
一
了解一个民族,不能不了解其鬼神观念。说到底,人生事不就是生与死生前之事历历在目,不待多言;死后之事则因其神秘莫测、虚无缥缈,强烈地吸引着每一个民族的先民们。“鬼之为言归也”(《尔雅》)。问题是活蹦乱跳的“人”,归去后还有没有感觉,还能不能活蹦乱跳,这实在让人放心不下。据说,当子贡向孔子请教死人有知无知时,孔子的回答颇为幽默:“欲知死人有知将无知也,死徐自知之,犹未晚也。”(刘向《说苑》)可惜世上如孔子般通达的人实在不多,“无事自扰”的常人,偏要在生前争论这死后才能解开的谜。
在一般民众心目中,“鬼”与“神”是有很大区别的。祸害人间,故对之畏惧、逃避,驱赶其出境;后者保佑人间,故对之崇敬、礼拜,祈求其赐福。“畏”与“敬”、“赶”与“求”本是人类创造神秘异物的两种心理基因,只不过前者坐实为“鬼”,后者外化为“神”。这样,“鬼”、“神”仿佛有天壤之别,由此引申出来的各种词汇也都带有明显的情感趋向。“鬼域”与“神州”不可同日而语;君子必然“神明”,小人只能“鬼黠”;说你“心怀鬼胎”、“鬼鬼祟祟”,与说你“神机妙算”、“神姿高彻”根本不是一回事。只是在强调其非人间或非人力所能为这一点上,鬼、神可以通用。比如“鬼工”就是“神工”,“神出鬼没”与“鬼使神差”中鬼神不分。至于“文化大革命”中使用频率最高的“牛鬼蛇神”,更是把鬼神一锅煮了。
也有努力区分鬼、神的哲人,着眼点和思路自然与一般民众不同。汉代的王充以阴阳讲鬼神,称“阴气逆物而归,故谓之鬼;阳气导物而生,故谓之神”(《论衡》)。宋代的朱熹则赋予鬼、神二名以新义,将其作为屈伸、往来的代名词,全无一点宗教意味:“气之方来皆属阳,是神;气之反皆属阴,是鬼。午前是神;午后是鬼。初一以后是神;十六以后是鬼。草木方发生是神;凋落是鬼。人自少至壮是神;衰老是鬼。”(《朱子语类》)如此说神鬼,已失却神鬼的本来意义:天下万事万物都是神鬼,神鬼也就没有存在价值了。
我之不想区分神、鬼,并非鉴于哲人的引申太远和民众的界说模糊,而是觉得这样说起来顺些。本来人造鬼神的心理,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根本无法截然分开。说近的,现实生活中多的是“以鬼为神”或者“降神为鬼”,鬼、神的界限并非不可逾越。说远的,先秦典籍中“鬼神”往往并用,并无高低圣俗之分,如《尚书》中的“鬼神无常享”、《左传》中的“鬼神非人实亲”、《礼记》中的“鬼神之祭”,以及《论语》中的“敬鬼神而远之”等。先秦时代的鬼、神,似乎具有同样的威力,也享受同样的敬畏与祭祀。再说,详细辨析鬼神观念的发展变化,并加以准确的界定,那是学者的事。至于文人的说神道鬼,尽可不必过分认真,太拘泥于概念的使用。否则,文章可能既无“神工”也无“鬼斧”,只剩下一堆大白话。也就是说,如果是科学论文,首先要求“立论正确”,按照大多数经过科学洗礼的现代人的思路,自然最好是宣传无神论,或者大讲不怕鬼的故事。可作为文艺性的散文,则鬼神不分没关系,有鬼无鬼也在其次,关键在“怎么说”,不在“说什么”。只要文章写得漂亮,说有鬼也行,说无鬼也行,都在可读之列。有趣的是,大多数有才气有情趣的散文,不说有鬼,也不说无鬼,而是“疑鬼神而亲之”―――在鬼神故事的津津乐道中,不时透出一丝嘲讽的语调。或许,坚持有神鬼者和一心辟神鬼者,都不免火气太盛、教诲意识太强,难得雍容自适的心态,写起散文来自然浮躁了些。
二
周作人在《谈鬼论》中曾经说过,他对于鬼故事有两种立场不同的爱好,一是文艺的,一是历史的(民俗学上的)。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还应加上第三种立场的爱好:现实政治斗争的。从艺术欣赏角度谈鬼、从民俗学角度谈鬼,与从现实斗争角度谈鬼,当然有很大不同。不应该单纯因其角度不同而非此即彼或者扬此抑彼,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以对其有所褒贬。只是必须记得,这种褒贬仍然有社会学的、民俗学的和文艺学的差别。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来说,生活实在太紧张太严肃了,难得有余暇如周作人所吟咏的“街头终日听谈鬼”。这就难怪周氏《五十自寿诗》一出来,就引起那么多激进青年的愤怒。现实中的神鬼为害正烈,实在没有心思把玩鉴赏。于是,作家们拿起笔来,逢神打神,遇鬼赶鬼。虽说鬼神不可能因此斩尽杀绝,毕竟尽到了作家的社会责任。
后人或许不理解这个时代的作家为什么热衷于把散文写成“科普读物”,甚至提出了“了解鬼是为了消灭鬼”这样煞风景的口号,比起苏东坡的“姑妄听之”,比起周作人的“谈狐说鬼寻常事”,未免显得太少雅趣。陈独秀的话部分解答了这个问题:“吾国鬼神之说素盛,支配全国人心者,当以此种无意识之宗教观念最为有力。”(《有鬼论质疑》)致力于社会进步的现代中国作家,不能不请科学来驱鬼―――即使明知这样做没有多少诗意。是的,推远来看,鬼神之说挺有诗意,“有了鬼,宇宙才神秘而富有意义”(许钦文《美丽的吊死鬼》)。可当鬼神观念纠缠民心,成为中国发展的巨大障碍时,打鬼势在必行,作家也就无权袖手旁观,更不要说为之袒护了。清末民初的破除迷信、八十年代的清算现代造神运动,都是为了解放人的灵魂。如此巨大的社会变革,从人类发展史来看,不也挺有诗意吗―――当然,落实到每篇文章又是另一回事。
文人天性爱谈鬼,这点毋庸讳言。中国古代文人留下那么多鬼笔记、鬼诗文、鬼小说和鬼戏曲,以至让人一想就手痒。虽说有以鬼自晦、以鬼为戏、以鬼设教之别(刘青园《常谈》),但谈鬼可自娱也可娱人,我想,这一点谁也不否认。李金发慨叹:“那儿童时代听起鬼故事来,又惊又爱的心情!已不可复得了,何等可惜啊!”(《鬼话连篇》)之所以“不可复得”,因为接受了现代科学,不再相信神鬼。倘若摒弃鬼神有利于社会进步,那么少点“又惊又爱”的刺激,也不该有多大抱怨。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世纪的文人尽管不乏喜欢谈鬼说神的,可大都有所克制,或者甚至自愿放弃这一爱好的原因。
三十年代中期,《论语》杂志拟出版“鬼故事专号”,从征文启事发出到专号正式发排才十五天时间,来稿居然足够编两期,可见文人对鬼的兴趣之大。除周作人此前此后均曾著文论鬼外,像老舍、丰子恺、梁实秋、李金发、施蛰存、曹聚仁、老向、陈铨、林庚、许钦文等,都不是研究鬼的专家,却也都披挂上阵。好多人此后不再谈鬼,很可能不是不再对鬼感兴趣,而是因为鬼神问题在二十世纪中国,基本上是个政治问题,而不是文化问题。要不打鬼,要不闭口,难得有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小品心态”。也就三十年代有过这么一次比较潇洒而且富有文化意味的关于鬼的讨论,余者多从政治角度立论。不说各种名目的真真假假的“打鬼运动”,即使编一本《不怕鬼的故事》或讨论一出鬼戏,都可能是一场政治斗争的讯号或标志。这么一来,谈神说鬼成了治国安邦的大事,区区散文家也就毋庸置喙了。勉强要说也可以,可板起面孔布道,笔下未免滞涩了些。
三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李商隐的《贾生》诗,曾令多少怀才不遇的文人感慨唏嘘。时至二十世纪,再自命“贾生才调更无伦”者,也不敢奢望“宣室求贤访逐臣”了。即便如此,不谈苍生谈鬼神,还是让人胆怯乃至本能地反感。古代文人固然甚多喜欢说鬼者,知名的如苏轼、蒲松龄、纪昀、袁枚等,可据说或者别有怀抱、或者寄托幽愤。今人呢今人实际上也不例外,都是兼问苍生与鬼神。正当“鬼故事专号”出版之际,就有人著文捅破这层窗户纸,诉说不谈国事谈鬼事的悲哀,结论是“客中无赖姑谈鬼,不觉阴森天地昏”(陈子展《谈鬼者的悲哀》)。
茶棚里高悬“莫谈国事”的告示,可并不禁止“白日说鬼”;报刊中要求舆论一律,可也不妨偶尔来个“鬼话连篇”。无权问苍生,只好有闲谈鬼神,这是一种解释;无权直接问苍生,只好有闲假装谈鬼神,这又是一种解释。中国现代作家中无意于苍生者实在太少,故不免常常借鬼神谈苍生。鲁迅笔下“发一声反狱的绝叫”的地狱里的鬼魂(《失掉的好地狱》),老舍笔下无处无时不令人讨厌的“不知死的鬼”(《鬼与狐》),周作人笔下“附在许多活人身上的野兽与死鬼”(《我们的敌人》),还有李伯元笔下的色鬼、赌鬼、酒鬼、鸦片烟鬼(《说鬼》),何尝不是都指向这“清平世界朗朗乾坤”清人吴照《题〈鬼趣图〉》早就说过:“请君试说阎浮界,到底人多是鬼多”
不管作家意向如何,读者本来就趋向于把鬼话当人话听,把鬼故事当人故事读,故不难品味出文中隐含的影射、讽喻或者根本就不存在的暗示与引申。即使把一篇纯属娱乐的鬼故事误读成意味深长的政治寓言也不奇怪,因为“鬼世界”本就是“人世间”的摹写与讽喻。正如曹聚仁说的:“为鬼幻设计殿阎罗,幻设天堂地狱,幻设鬼市鬼城,也是很可哀的;因为这又是以人间作底稿的蜃楼”(《鬼的箭垛》)。一般地说,“牵涉到‘人’的事情总不大好谈,说‘鬼’还比较稳当”(黄苗子《鬼趣图和它的题跋》)。但也有例外,说鬼可能最安全也可能最危险,因为鬼故事天生语意含糊而且隐含讽刺意味。当社会盛行政治索隐和大众裁决,而作者又没有任何诠释权时,鬼故事便可能绝迹。谁能证明你的创作不是“影射现实发泄不满”“鬼”能证明吗
还有另外一种说鬼,不能说无关苍生,但确实离现实政治远些,那就是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出发,借助鬼神的考察来窥探一个民族的心灵。不同于借鬼神谈苍生,而是谈鬼神中的苍生,或者说研究鬼中的“人”。这就要求多一点理解,多一点同情,多一点文化意味和学识修养,而不只是意气用事。周作人说得好:“我不信人死为鬼,却相信鬼后有人,我不懂什么是二气之良能,但鬼为生人喜惧愿望之投影则当不谬也。”(《鬼的生长》)虽说早在公元一世纪,哲学家王充就说过鬼由人心所生之类的话:“凡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论衡》)。但是,王充着眼于破有鬼论,周作人则注重鬼产生的文化心理背景,两者仍有很大差别。在理论上,周作人谈不上什么建树,他所再三引述的西方人类学家来则等对此有更为精细的辨析。不过,作为一个学识颇为渊博的散文家,认准“鬼后有人”,“听人说鬼实即等于听其谈心”(《鬼的生长》),在中国古代典籍中钩稽出许多有关鬼的描述,由此也就从一个特定角度了解了“中国民族的真心实意”。经过周氏整理、分析的诸多鬼故事,以及这些谈论鬼故事的散文小品,确实如其自称的,是“极有趣味也极有意义的东西”。至于这项工作的目的与途径,周作人有过明确的表述:“我们喜欢知道鬼的情状与生活,从文献从风俗上各方面去搜求,为的可以了解一点平常不易知道的人情,换句话说就是为了鬼里边的人。”(《说鬼》)代代相传的辉煌经典,固然蕴藏着一个民族的灵魂;可活跃于民间、不登大雅之堂的鬼神观念及其相关仪式,何尝不也代表一个民族心灵深处的隐秘世界前者历来为学者所重视,后者在思想史研究上的意义尚未得到普遍的承认。当然,不能指望散文家作出多大的学术贡献,可此类谈神说鬼的散文确实引起人们对鬼神的文化兴趣。借用汪曾祺的话,“我们要了解我们这个民族”(《水母》),因此,我们不能撇下鬼神不管。在这方面,散文家似乎仍然大有可为。
四
本世纪初,正当新学之士力主驱神斩鬼之时,林纾翻译了“立义遣词,往往托象于神怪”的莎士比亚的戏剧和哈葛德的小说。为了说明专言鬼神的文学作品仍有其存在价值,林纾列出两条理由,一为鬼神之说虽野蛮,可“野蛮之反面,即为文明。知野蛮流弊之所及,即知文明程度之所及”(《〈埃及金塔剖尸记〉译余剩语》);一为政教与文章分开,富国强兵之余,“始以余闲用文章家娱悦其心目,虽哈氏、莎氏,思想之旧,神怪之托,而文明之士,坦然不以为病也”(《〈吟边燕语〉序》)。用老话说,前者是认识意义,后者为文学价值。
三十年后,梁实秋再说莎士比亚作品里的鬼,可就只肯定鬼是莎氏戏剧中很有用的技巧,而且称“莎士比亚若生于现代,他就许不写这些鬼事了”(《略谈莎士比亚作品里的鬼》)。或许一般读者还没有真正摆脱鬼神观念的束缚,还很难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客观考察鬼神的产生与发展,故文学作品不宜有太多鬼神。说起古代的鬼诗、鬼画、鬼戏、鬼小说来,作家们大致持赞赏的态度,可一涉及当代创作,则都谨慎得多,不敢随便表态。“如果是个好鬼,能鼓舞人们的斗志,在戏台上多出现几次,那又有什么妨害呢”这话说得很通达。可别忘了,那是有前提的:“前人的戏曲有鬼神,这也是一种客观存在,没有办法可想。”(《有鬼无害论》)也就是说,廖沫沙肯定的也只是改编的旧戏里的鬼神,至于描写现代生活的戏里能否出现鬼神,仍然不敢正面回答。
这里确实不能不考虑中国读者的接受水平。理论上现代戏也不妨出现神鬼,因那只是一种可供选择的艺术技巧,并不代表作家的思想认识水平,更无所谓“宣传迷信”。可实际上作家很少这么做,因尺度实在不好把握。周作人在谈到中外文学中的“僵尸”时称,此类精灵信仰,“在事实上于文化发展颇有障害,但从艺术上平心静气的看去,我们能够于怪异的传说的里面瞥见人类共通的悲哀或恐怖,不是无意义的事情”(《文艺上的异物》)。反过来说,倘若不是用艺术的眼光,不是“平心静气”地欣赏,鬼神传说仍然可能“于文化发展颇有障害”。了解二十世纪中国读者的整体文化水平以及中国作家普遍具有的启蒙意识,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作家们对当代创作中的鬼神问题举棋不定、态度暧昧。直到八十年代中期,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至于为什么鬼神并称,而在这个世纪的散文中,却明显地重鬼轻神,想来起码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原因:一是鬼的人情味,一是散文要求的潇洒心态。不再是“敬鬼神而远之”,民间实际上早就是敬神而驱鬼。现代人对于神,可能崇拜,也可能批判,共同点是走极端,或将其绝对美化,或将其绝对丑化,故神的形象甚少人情味,作家落笔也不免过于严肃。对鬼则不然,可能畏惧,也可能嘲讽,不过因其较多非俗非圣亦俗亦圣的人间味道,故不妨对其调笑戏谑。据说,人死即为鬼,是“自然转正”,不用申请评选;而死后为神者,则百年未必一遇。可见鬼比神更接近凡世,更多人味。传说里鬼中有人,人中有鬼,有时甚至人鬼不分;作家讲起此类鬼而人、理而情的鬼故事来,虽也有一点超人间的神秘色彩,可毕竟轻松多了。而这种无拘无束的宽松心境,无疑更适合于散文小品的制作。
对于鬼神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作家们虽一再提及,其实并没有认真的研究。老舍也不过说说鬼神可以“造成一种恐怖,故意的供给一种人为的哆嗦,好使心中空洞的人有些一想就颤抖的东西――神经的冷水浴”(《鬼与狐》);而邵洵美分析文学作品中使用鬼故事的“五易”,则带有嘲讽的意味(《鬼故事》)。如果说这个世纪的散文家在研究文艺中的鬼方面有什么值得注意之处的话,一是诸多作家对罗两峰《鬼趣图》的评论,一是鲁迅对目连戏中无常、女吊形象的描述。“这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爱的无常”(《无常》),这“大红衫子,黑色长背心,长发蓬松,颈挂两条纸锭”,“准备作厉鬼以复仇”的女吊(《女吊》),借助于鲁迅独特的感受和传神的文笔,强烈地撼动了千百万现代读者的心。这种鬼戏中的人情,很容易为“下等人”领悟;而罗两峰的《鬼趣图》和诸家题跋,则更多为文人所赏识。现代作家未能在理论上说清鬼诗、鬼画、鬼戏的艺术特色,可对若干以鬼为表现对象的文艺作品的介绍评析,仍值得人们玩味―――这里有一代文人对鬼神及“鬼神文艺”潜在而浓厚的兴趣。
周代鬼神之说兴盛。
鬼神:中国 宗教观念和哲学术语。《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古代祭祀之礼,有天神、人鬼、地祇之分。人鬼又称为“人神”,即鬼神,指死去的祖先。如《周书·金滕》记周公旦语:“多才多艺,能事鬼神。”后凡人死,认为其 灵魂不死,则称为鬼神。如《左传·昭公七年》记载郑子产语,以人死后,其“魂魄”犹能作怪为鬼。墨子亦说:“有人死而为鬼者”(《墨子·明鬼下》)。《礼记·祭法》则说:“人死曰鬼。”凡此皆以鬼神为人格神,认为人死后,其灵魂能给人以祸福。
战国时代,一些哲学家以“精气”解释灵魂,鬼神又有了新的涵义。《管子·内业》说:精气“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以人体内的精气离开形体,在天地间流动为鬼神。《周易·系辞上》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郑玄注说:“精气谓之神,游魂谓之鬼。”此种观点,以鬼神为精气变化的形态,其人格神的涵义,较为淡薄,但仍有某种神秘的性质。《礼记·祭义》吸取了精气说,以人死,其体魄归于地为鬼,其气发扬于上为神,认为此气仍有知觉,能享受人间的祭祀。《礼记·郊特牲》则说:“鬼神,阴阳也。”又以魂气归天为神,为阳;以体魄归地为鬼,为阴,以阴阳二气之性质及其变化解释鬼神。但同样认为祭祀鬼神可以获福。《礼记》中的鬼神说,仍承认鬼神有意志,保留了人格神的涵义。
到汉代,无神论者王充批判地吸取了《礼记》中的鬼神说,提出“阴气逆物而归,故谓之鬼;阳气导物而生,故谓之神”(《论衡·论死》)。认为人死无知,鬼神只是阴阳二气生化万物的性能,否认有人格神的性质。郑玄注《礼记·乐记》,以物死有所归为鬼,物生有所信为神,亦取此义。晋韩康伯注《周易·系辞》文,吸取了上述气有归伸说,以精气聚而成物为神,聚极则散为鬼,并以“聚散之理”,解释“鬼神之情状”。宋张载于《易说》中,又批判地吸取了韩康伯说,称气聚显而成物为神,气散隐而为变为鬼。其在《正蒙·太和》中又说:“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认为阴气主屈为鬼,阳气主伸为神,将鬼神视为气运动变化的两种形式,并说:“鬼神之实,不过二端而已。”“二端”,指阴阳二气。张载此说,不仅否定了鬼神的人格神的性质,而且扬弃了其灵魂的涵义,鬼神成了表达气往来屈伸的哲学术语。其后,朱熹亦说“鬼神只是气,屈伸往来者气也”(《朱子语类》卷三)。此种鬼神说,为宋明清多数易学家和哲学家所采纳。
鬼神 拼音:guǐ shén 解释 (1)鬼与神的合称。 《易·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礼记·仲尼燕居》:“鬼神得其飨,丧纪得其哀。” 孔颖达 疏:“鬼神得其飨者,谓天神人鬼各得其飨食也。”唐 韩愈 《原鬼》:“无声与形者,鬼神是也。”清 姚衡 《寒秀草堂笔记》卷三:“夫古人作书垂后……亦鉴及后人之无赖,故徐引其机,以待有心者之自为觉悟,庶不蹈妄传之戒,为鬼神所忌耳。” (2)泛指神灵、精气。 《史记·五帝本纪》:“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 张守节 正义:“鬼之灵者曰神也。鬼神曰山川之神也。”《史记·五帝本纪》:“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 张守节 正义:“天神曰神,人神曰鬼。又云圣人之精气谓之神,贤人之精气谓之鬼。” (3)偏指鬼;死去的祖先。 《左传·昭公七年》:“今君若步玉趾,辱见寡君……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贶矣,何蜀 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实嘉赖之,岂唯寡君?”《孝经·感应》:“宗庙致敬,鬼神著矣。” 唐玄宗 注:“事宗庙能尽敬,则祖考来格。” (4)指形体与精灵。 《礼记·礼运》:“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 孔颖达 疏:“鬼谓形体,神谓精灵。《祭义》云:‘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必形体精灵相会,然后物生。” (5) 古代指天地间一种精气的聚散变化。 《易·系辞上》:“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 韩康伯 注:“尽聚散之理,则能知变化之道。” 孔颖达 疏:“物既以聚而生,以散而死,皆是鬼神所为,但极聚散之理,则知鬼神之情状也。”后世哲学家多以阴阳之变、气的往来屈伸解释“鬼神”。汉 王充 《论衡·论死》:“鬼神,阴阳之名也。阴气逆物而归,故谓之鬼;阳气导物而生,故谓之神。”《礼记·中庸》:“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 程颐 章句:“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 张子 曰:‘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愚谓以二气言,则鬼者阴之灵也,神者阳之灵也。以一气言,则至而神者为神,反而归者为鬼,其实一物而已。”《朱子语类》卷三:“鬼神只是气,屈伸往来者气也。”
《孙子兵法》
孙武
始计第一
孙子曰: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
曰法。道者,令民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危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之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作战第二
孙子曰:
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军罢马,甲胄矢弓,戟盾矛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①杆一石,当吾二十石。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故兵贵胜,不贵久。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注:
①:“忌”加“艹”头。
谋攻第三
孙子曰:
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
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①□②,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
拔者,此攻之灾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
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故曰:知己知彼,百战不贻;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
注:
①:[车贲]。
②:“温”字“氵”旁换“车”旁。
军形第四
孙子曰:
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
称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
兵势第五
孙子曰:
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①投卵者,虚实是也。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时是也。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故善战者,其
势险,其节短。势如扩弩,节如发机。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注:
①:“瑕”的“王”旁换“石”旁。
虚实第六
孙子曰:
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出其所必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必攻也。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
必救也;我不欲战,虽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之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而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哉!故曰: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候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
军争第七
孙子曰:
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和而舍,莫难于军争。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军争为利,军争为危。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
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和为变者也。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悬权而动。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之金鼓;视不相见,故为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民之耳目也。民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故夜战多金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人之耳目也。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无击堂堂之陈,此治变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遗阙,穷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
九变第八
孙子曰:
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合。泛地无舍,衢地合交,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九变之利,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行军第九
孙子曰:
凡处军相敌,绝山依谷,视生处高,战隆无登,此处山之军也。绝水必远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渡而击之利,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客,视生处高,无迎水流,此处水上之军也。绝斥泽,唯亟去无留,若交军于斥泽之中,必依水草而背众树,此处斥泽之军也。平陆处易,右背高,前死后生,此处平陆之军也。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流至,欲涉者,待其定也。凡地有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远之,敌近之;吾迎之,敌背之。军旁有险阻、潢井、蒹葭
、小林、□①荟者,必谨覆索之,此伏奸之所处也。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众树
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条达者,樵采也;少而往来者,营军也;辞卑而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奔走而陈兵者,期也;半进半退者,诱也;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见利而不进者,劳也;鸟集者,虚也;夜呼者,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旌旗动者,乱也;吏怒者,倦也;杀马肉食者,军无粮也;悬□②不返其舍者,穷寇也;谆谆□③□③,徐与人言者,失众也;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先暴而后畏其众者,不精之至也;来委谢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
,必谨察之。兵非贵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卒未亲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故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素不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
注:
①:“翳”加“艹”头。
②:[垂瓦]。
③:[讠翕]。
地形第十
孙子曰:
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阳,利粮道,以战则利。可以往,难以返,曰挂。挂形者,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敌虽利我,我无出也,引而去之,令敌半出而击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若敌先居之,盈而勿从,不盈而从之。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若敌先居之,引而去之,勿从也。远形者,势均难以挑战,战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凡兵有走者、有驰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乱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灾,将之过也。夫势均,以一击十,曰走;卒强吏弱,曰驰;吏强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敌怼而自战,将不知其能,曰崩;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将不能料敌,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曰北。凡此六者,败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隘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于主,国之宝也。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
之半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故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
九地第十一
孙子曰:
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轻地,有争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泛地,有围地,有死地。诸侯自战其地者,为散地;入人之地不深者,为轻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为争地;我可以往,彼可以来者,为交地;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众者,为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为重地;山林、险阻、沮泽,凡难行之道者,为泛地;所由入者隘,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吾之众者,为围地;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是故散地则无战,轻地则无止,争地则无攻,交地则无绝,衢地则合交,重地则掠,泛地则行,围地则谋,死地则战。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敢问敌众而整将来,待之若何曰:先夺其所爱则听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主人不克,掠于饶野,三军足食。谨养而勿劳,并气积力,运兵计谋,为不可测。
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尽力。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
,深入则拘,不得已则斗。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
禁祥去疑,至死无所之。
吾士无余财,非恶货也;无余命,非恶寿也。令发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
卧者涕交颐,投之无所往,诸、刿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
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敢问兵可使如率然乎
?曰可。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而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
马埋轮,未足恃也;齐勇如一,政之道也;刚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
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
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民不得虑。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
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
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
九地之变,屈伸之力,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
凡为客之道,深则专,浅则散。去国越境而师者,绝地也;四彻者,衢地也;
入深者,重地也;入浅者,轻地也;背固前隘者,围地也;无所往者,死地也。
是故散地吾将一其志,轻地吾将使之属,争地吾将趋其后,交地吾将谨其守,
交地吾将固其结,衢地吾将谨其恃,重地吾将继其食,泛地吾将进其途,围地吾将
塞其阙,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
故兵之情:围则御,不得已则斗,过则从。
是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
不用乡导,不能得地利。四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国,
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
己之私,威加于敌,则其城可拔,其国可隳。
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
之以害,勿告以利。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
败。
故为兵之事,在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是谓巧能成事。是故政举
之日,夷关折符,无通其使,厉于廊庙之上,以诛其事。敌人开阖,必亟入之,先
其所爱,微与之期,践墨随敌,以决战事。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
敌不及拒。
火攻第十二
孙子曰:
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积,三曰火辎,四曰火库,五曰火队。
行火必有因,因必素具。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
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火
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火发而其兵静者,待而勿攻,极其火力,可从而从之,不
可从则上。火可发于外,无待于内,以时发之,火发上风,无攻下风,昼风久,夜
风止。凡军必知五火之变,以数守之。
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不可以夺。
夫战胜攻取而不惰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惰之,非
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攻战。合于利而
动,不合于利而上。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说,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
。故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用间第十三
孙子曰:
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
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
情者,不仁之至也,非民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
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
,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故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
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乡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
;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闻知之而传于敌间也;生
间者,反报也。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贤不能用
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间事未发
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兼死。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
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敌间之来间我者,因而
利之,导而舍之,故反间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乡间、内间可得而使也;因
是而知之,故死间为诳事,可使告敌;因是而知之,故生间可使如期。五间之事,
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间,故反间不可不厚也。
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
,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