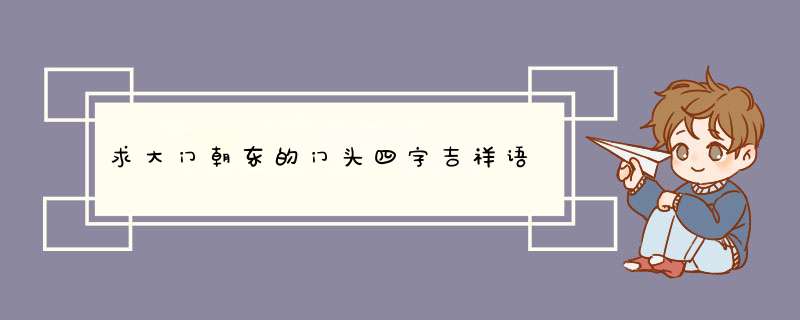
大门朝东的门头四字吉祥语如下:
云岚福气
舒华布实
日月澄晖
华堂聚和
时和景泰
竹苞松茂
万事如意
福寿即来
五谷丰登
四季呈祥
向阳门第
纳福迎祥
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欣欣向荣
时和岁好
年年大发
岁岁有余
万象皆春
四季平安
吉祥语是具有吉祥意义用于向他人或自己表示祝福的词语,具有祝福性、超前性、时代性、民族性。在言语交际活动中,具有动力功能、安慰功能,可以调节人际关系、塑造人物形象和反映时代特色等。
吉祥语的形式有语素或词、短语、句子等。句子形式的吉利语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愿辞(祝词),愿辞是指在某些特殊场合使用的句子形式的吉利话。常用的吉祥语素或吉祥词有“福”、“禄”、“寿”、“喜”、“财”、“吉”等。例如“福”字,人们在过大年的时候会在庭院里单独张贴一张大大的“福”字,并且还把这“福”字倒着贴,寓意“福到了”。
这些单独的吉祥语素一般是在特殊场合下单独张贴使用,口头上很少单独说,在口头表达的时候,人们习惯于将他们与其它语言成分组成吉祥词语,如带“喜”字的可以组成“喜酒”、“喜筵”、“有喜”、“抬头见喜”、“双喜临门”等。
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按照《序志》所提示,可分为三大部分:一是《原道》至《辨骚》五篇为“文之枢纽”;二是《明诗》至《书记》二十篇为“论文叙笔”;三是《神思》至《程器》二十四篇为“割情析采”。这只是刘勰对全书主要轮廓的说明,其具体安排还有以下情况:第一、二部分之交的《辨骚》,既有列入“枢纽”的必要,又与《明诗》以下“论文叙笔”各篇有相同的性质。“论文叙笔”的二十篇(加《辨骚》为二十一篇),一般称为“文体论”,其中又分“文”与“笔”两个部分:由《辨骚》到《哀吊》的九篇属“论文”,由《史传》至《书记》的十篇为“叙笔”,间于这两类之中的《杂文》和《谐隐》两篇,则兼属“文”、“笔”两类。“割情析采”的二十四篇,又可分为创作论和批评论两个部分:《神思》至《总术》的十九篇是创作论,《才略》、《知音》、《程器》三篇为批评论。创作论与批评论之间的《时序》、《物色》两篇,也兼有创作论和批评论的性质。最后一篇《序志》是全书序言。根据《文心雕龙》的这种结构体系,下面拟从“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创作论、批评论四个方面分别介绍。
首先讲“文之枢纽”,重点探讨《文心雕龙》全书的总论及其理论体系
(一)
“枢纽”不等于总论,这是首先要明确的。关于《辨骚》篇属上属下的长期争论,主要就是混淆了“枢纽”和总论的性质。所谓总论,应该是贯穿全书的基本论点,或者是建立其全部理论体系的指导思想。从这个理解来看,不仅《辨骚》,《正纬》也同样不具备总论的性质。所谓“枢纽”,也是关系全书的关键问题,不首先解决,就将影响和不利下面的论述。如《正纬》,因为儒家经典在东汉时期被纬书搅混了,不首先“正纬”,就会影响到在全书中贯彻“宗经”的基本观点。所以,“正纬”不过是为“宗经”扫清道路,并未提出什么总论性的论点。《辨骚》论骚体,实为“论文叙笔”之首。刘勰之所以把《辨骚》篇列为“文之枢纽”,有两个重要原因:一、“论文叙笔”共二十一篇,在全书中所占分量是很大的;而全书的理论结构,又是在这二十一篇的基础上,来总结文学理论上的种种问题;也就是说,刘勰是首先分别探讨各种文体的实际创作经验,再由此提炼出一些理论问题来。因此,整个“论文叙笔”部分,都是为后半部打基础。这样,可以说“论文叙笔”的二十一篇,都具有论文之“枢纽”的性质。但不可能把二十一篇全部列入“文之枢纽”中去。把“论文叙笔”的第一篇《辨骚》列入“文之枢纽”,也正表明刘勰对整个“论文叙笔”部分的重视。二、《楚辞》是儒家经典之后出现最早的作品,即所谓“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并且《楚辞》又是“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在文学发展史上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也就是说,《楚辞》在儒家经典与后世文学作品之间,具有“枢纽”的作用。
由此可见,《正纬》和《辨骚》虽列入“文之枢纽”,但并不是《文心雕龙》的总论。属于总论的,只有《原道》、《征圣》、《宗经》三篇。其中《征圣》和《宗经》,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就是要向儒家圣人的著作学习。因此,刘勰的总论,只提出两个最基本的主张“原道”、“宗经”。
“原道”的基本观点,上面已经谈到了。这里要进一步研究的是:刘勰提出“自然之道”的意图和“征圣”、“宗经”的关系如何?《原道》的最后一段已讲到这个问题:
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在《原道》的讨论中,曾有人提出:“刘勰的《原道》,完全着眼在文上。”73这个意见是不错的,论者正看到了刘勰写《原道》篇的真正意图。如前所述,“自然之道”作为刘勰论文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指万事万物必有其自然之美的规律,这是刘勰论证一切作品应有一定文采的理论根据。他不仅认为文采“与天地并生”,甚至断言:“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情采》)可见,文章应该有文采,在刘勰看来是天经地义的。刘勰论文而首标“原道第一”,其用意就在于此。他虽然崇拜儒家圣人,却认为圣人也必须本于“自然之道”,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以说,从伏牺到孔子,“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这里的“神理”亦即“道心”,就是“自然之道”,圣人只有本于“自然之道”,研究“自然之道”,才能写成文章,完成教化作用。圣人的著作其所以能鼓动天下,刘勰认为,就因为他们的著作“乃道之文也”。这就表明,必须要有符合“自然之道”的文采,其著作才能产生巨大的艺术力量;而圣人的作用,只在于能掌握“自然之道”,能很好地发挥“自然之道”的作用,所以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这就是“自然之道”和圣人的关系。
对“道”和“圣”的关系,上述理解是“自然之道”和儒家圣人(主要指周、孔)的关系。最近出现一种新的理解是:“道(佛道)沿圣(孔子)以垂文(儒家之经),圣(孔子)因文(儒家之经)而明道(佛道)。”74“道”不等于“佛道”,前已略及。这种“道圣”关系的新说,主要基于对“玄圣创典,素王述训”的如下新解:
“玄圣”(佛)创《佛经》之典,孔子述“玄圣”所创之佛典为儒家之六经,故孔子之所述为“训”。
此说的关键在于对“玄圣”的解释,论者“肯定”是“指佛言而无疑”,实则大有可疑。其说主要根据有三:一、宗炳的《答何衡阳书》、孙绰的《游天台山赋》中说的“玄圣”是指“佛”;二、《庄子》、《后汉书》、班固、何承天等虽用到“玄圣”,但“注家皆不得其确解”;三、刘勰之前的宗炳、孙绰,刘勰之后唐初的法琳,均以“玄圣”专指佛,处于其间的刘勰也是佛徒,不能不也是指佛75。这些理由是很难成其为理由的。宗、孙之文,“玄圣”指“佛”是不错的,却无法证明刘勰所说的“玄圣”也指“佛”。道理很简单,“玄圣”二字与“佛”也好“儒”也好,都没有必然联系,各家都可用以指自家的远古之圣。仅以刘勰一家来看:《史传》篇的“法孔题经,则文非玄圣”,不是佛而是孔;甚至同一篇《原道》,“光采玄圣,炳耀仁孝”,岂能说使“仁孝”焕发光彩的“玄圣”是“佛”?上二例只能指孔,而“玄圣创典”的“玄圣”却并非指孔,但也不指“佛”(详下)。同一人,同一篇的“玄圣”尚各有所指,怎能据宗、孙的“玄圣”判定刘勰的“玄圣”必同指一物?前面说过,佛入东土之后,为了宣传效果,往往借用儒、道的一些概念和词汇。怎能把宗、孙等借用道家与儒家早已运用的“玄圣”一词,来反证儒道的概念源于佛家呢?
《庄子·天道》和班固《典引》都用过“玄圣”,论者却以为“注家皆不得其确解”。纵使不得确解,也不能证明“玄圣”即“佛”,何况并非未得确解?成玄英注《庄子》的“玄圣、素王”为“老君、尼父是也”,“玄圣”指“老君”,“素王”指“尼父”,这怎是“泛指”,怎么不确呢?至于班固《典引》等文中的“玄圣”二字,说“均是泛指‘老君、尼父者也’”,那就不知何据了。李善注《典引》:“玄圣,孔子也”76;李贤注《后汉书》中所录《典引》:“玄圣,谓孔丘也。《春秋演孔图》曰:‘孔子母征在,梦感黑帝而生,故曰玄圣。’”77这都是很明确的。
第三条理由就无待细辨了,论者自己所列《上白鸠颂》的作者何承天、《后汉书》的作者范晔,都是孙绰之后、与宗炳同时、略早于刘勰的人,范晔在《王充(等)传论》中说的“玄圣御世”,是无法解为不“御世”的“佛”的,何承天则是宋初著名的反佛者,岂能颂佛为“玄圣”?“能不能说偏偏处于中间的刘勰”不用“玄圣”指“佛”,也就很清楚了。
“玄圣创典”一句的“玄圣”所指何圣,要从刘勰的具体用意来定。他的原话本来讲得很明确:
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
如把这几句中的“玄圣”解为“佛”,上二句又作何解释呢?要是不割断上二句,则只能理解为“玄圣”指“风姓”,“素王”指“孔氏”,这就能顺理成章,勿劳旁搜博证。要求旁证,也应于《原道》本篇求之:
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
这四句不正是上四句最好的注脚吗?“风姓”即伏牺。相传伏牺画八卦,演而为《易》,孔子作《十翼》以解释,这就是“翼其终”了,“述训”正指孔子的“翼其终”,“创典”则是伏牺的“画其始”了。所以,“玄圣创典”不是佛主创典,而是伏牺创典。如此,孔子要“述训”的,也就不是什么“《佛经》之典”,“圣”与“道”的关系,就不是儒家之圣和佛家之道的关系了。
(二)
至于“原道”和“宗经”两种基本观点的关系,这还须首先弄清“征圣”、“宗经”的观点之后才能说明。
《征圣》主要讲征验圣人之文,值得后人学习,即所谓“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宗经》则强调儒家经典的伟大,是“文章奥府”、“群言之祖”,因此,建言修辞,必须宗经。其中许多对儒家著作的吹捧,大都是言过其实的,什么“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完全是唯心的、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儒家经书是“衔华而佩实”的典范等等,除《诗经》中的部分优秀作品外,大多数儒经都是不堪其誉的。
但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刘勰为什么要强调“征圣”、“宗经”,他的用意何在。《通变》中说:“矫讹翻浅,还宗经诰。”这个用意,《宗经》中也明确讲到了:“建言修辞,鲜克宗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刘勰就是针对楚汉以后日益艳侈的文风,而大喊大叫“征圣”、“宗经”,企图以此达于“正末归本”的目的。从这一方面来看,“征圣”、“宗经”的观点虽有它的局限,但也是未可厚非的。
刘勰从文学要有益于封建治道的思想出发,企图使文学作品对端正君臣之道以及在整个军国大事中发挥作用,在当时就必然要反对“离本弥甚”的浮华文风,而强调“正末归本”。“离本”的原因是“去圣久远”,文学创作“鲜克宗经”,则“归本”的途径,他认为就是“征圣”、“宗经”。对于挽救当时“讹滥”的创作倾向,刘勰从当时的思想武库中所能找到的唯一可用的武器,也就只有儒家经典了。佛道思想在齐梁时期无论怎样盛行,它既没有提出文学创作方面的什么理论主张,也没有儒家思想那种“根柢盘深,枝叶峻茂”的雄厚基础,而最根本的原因,还在只有儒家思想,才过问世俗,才取积极入世的态度;也只有儒家经典,才更有利于为封建治道服务。正如前引孙绰所说:“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耳。”范泰和谢灵运也有这种说法:“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必求灵性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78佛经是用“普度众生”、解救人类灵魂之类为“指南”来动人的,至于“济俗为治”,处理世俗政教,怎样统治人民,一般佛徒就无意过问,而认为理所当然是儒家的事了。这也说明,《征圣》、《宗经》中虽然极力吹捧儒经,对于笃信佛学的刘勰并不矛盾。
更值得注意的,是《征圣》、《宗经》的具体内容。刘勰论文,当然不仅仅是打儒家的旗号,他写《文心雕龙》时积极入世的态度,也决定了他确是以浓厚的儒家思想来评论文学的。但刘勰毕竟是一个文论家,而不是传道士;《文心雕龙》也毕竟是一部文学评论,而不是“敷赞圣旨”的五经论。所以,即使在《文心雕龙》中最集中、最着力推崇儒家圣人及其著作的《征圣》、《宗经》中,并没有鼓吹孔孟之道的具体主张。在《文心雕龙》全书中,刘勰对忠孝仁义之类也有一些由衷的肯定和宣扬。如《程器》篇肯定“屈贾之忠贞”,“黄香之淳孝”;《指瑕》篇说“左思《七讽》,说孝而不从,反道若斯,余不足观矣”。《诸子》篇评商鞅、韩非的著作“弃仁废孝,轘药之祸,非虚至也”等等。这说明,儒道思想在刘勰的文学评论中,是占有重要地位的,这种思想使他形成一定的偏见,严重地影响了他的文学观点。但这个方面并不是《文心雕龙》的主要任务,刘勰既不是在一切问题上都从维护儒家观点出发,也没有把文学作品视为孔孟之道的工具而主张“文以载道”。
举一个具体例子来看。战国初墨家学说盛行的时候,“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以至到了“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79的严重程度,孔、墨两家发生一场尖锐、激烈的斗争。这场与孔、墨两家存亡攸关的重要斗争,刘勰是不会不知道的。他对这场斗争的态度如何呢?《奏启》篇曾有所议论:
墨翟非儒,目以豕彘;孟柯讥墨,比诸禽兽。……是以世人为文,竞于诋诃,吹毛取瑕,次骨为戾,复似善骂,多失折衷。若能辟礼门以悬规,标义路以植矩,然后逾垣者折肱,捷径者灭趾,何必躁言丑句,诟病为切哉!
对于“世人为文”以善骂为能的现象,刘勰是极为反感的。他主张“辟礼门”、“标义路”,定规矩,对有违“礼门”、“义路”的文章,就要砍他的手,断他的足!这就严然是一副凶象毕露的卫道者的面孔了。“礼门”、“义路”出自《孟子》80,礼、义之教,也正是儒家的主要教义,这似乎很能说明刘勰对儒家的态度了。但从他所举“躁言丑句”的具体例子,联系当年儒墨之战的具体背景来看,刘勰的用意就值得研究了。那种“复似善骂”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孔门“亚圣”孟轲和墨翟的破口大骂。墨翟骂儒家是猪,孟轲骂墨翟是禽兽。刘勰呢?认为这些都是“吹毛取瑕”,都是“躁言丑句”,一概加以批判。他不仅没有在这场关系儒家命运的大战中站在儒家立场指责墨家,也不仅是认为两家都不该大骂,且用《孟子》的话来批评孟子。很难认为这是刘勰立论的疏忽,误以《孟子》批判了孟子;更难说这是刘勰对孟子的有意嘲讽。刘勰的这段论述,只能证明他是从论文出发,不是从宗派出发;他反对的是“为文”中的破口大骂,关心的是文之利弊,而不是儒家宗派。
《征圣》、《宗经》两篇所论,和上述刘勰对儒家的态度是一致的。这两篇对儒家著作虽然作竭力的吹捧,也全都是从写作的角度着眼的。刘勰所强调的,主要是儒家圣人的著作值得学习。如说圣人之文“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或“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等,都是讲圣人的文章在写作上有各种各样的好处,堪为后人学习的典范。这一思想讲得最集中的,是《宗经》篇提出的“六义”:
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
这就是刘勰所论学习儒家经典的全部价值,也是他主张“征圣”、“宗经”的全部目的。学习儒家经典来写作,他认为就有情深、风清、事信、义直、体约、文丽六大好处,这就是他要归的“本”。“六义”的提出,其针对性也很明确,就是当时文学创作中出现的:诡、杂、诞、回(邪)、芜、*,这就是刘勰要正的“末”。所以,刘勰“征圣”、“宗经”的主张,主要就是企图纠正当时文学创作中形式主义的倾向,使之“正末归本”。
(三)
明确了“征圣”、“宗经”的基本观点,我们就可进而探讨它与“原道”的观点有何关系了。“原道”是注重自然文采而反对过分的雕饰,主要属于形式方面,《原道》中对内容方面还没有提出什么主张,这就不能构成全面的文学观点。要挽救当时“饰羽尚画,文绣鞶帨”(《序志》)的创作趋向,只以“原道”的主张,也是无能为力的。“征圣”、“宗经”主要是针对当时“将遂讹滥”的文风,为了“正末归本”而提出的,重点是强调“情深”、“风清”、“事信”等内容方面,而反对“诡、杂、诞、回、芜、*”等弊病。对一般文章的写作,以“征圣”、“宗经”为指导思想是可以的;作为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来看,只强调内容的纯正、反对形式的*丽,对文学艺术的特点没有正面的主张,对必不可少的文采没有一定的理论根据,则《文心雕龙》就将循着“征圣”、“宗经”的观点写成一部“五经通论”,而不可能成为一部文学理论。这就是刘勰论文要首标“原道”,而又强调“征圣”、“宗经”的原因,也是他的总论只有这两个基本观点的说明。“原道”和“宗经”的结合,就构成《文心雕龙》完整的基本观点。
“原道”和“宗经”实际上是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提出的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基本文学观点。虽然“道心惟微”,自然之道是十分深微奥妙的,但“圣谟卓绝”,因此,可以“因文而明道”。而儒家经典其所以值得后人学习,刘勰认为主要就是它体现了自然之道。这样说,显然是为其论文找理论根据。儒家的周孔之文,未必是自然之道的体现者;儒家的经典,也未必有刘勰所说的那些典范意义,这都是很明显的。我们要看到的是,除了在当时突出强调“征圣”、“宗经”有一定的必要性外,刘勰这样讲,如果不是仅仅借助儒家的旗号,至少是反映了他自己的某些观点:或者是被刘勰所美化了的儒家经典,在他看来真是如此;或者是他以为在当时要提出较有力量的、全面的文学观点,必须强调这两个方面。我们要注意的,主要是后一种意义,也就是以“原道”和“宗经”相结合所表达的刘勰对文学艺术的基本主张。因为他在实际上是这样做的,并以此贯彻于《文心雕龙》全书。我们从这里就可清楚地看到:刘勰首先树立本于自然之道而能“衔华佩实”的儒家经典这个标,不过是为他自己的文学观点服务。“衔华而佩实”,是刘勰的《原道》、《征圣》、《宗经》三篇总论中提出的核心观点;所以他说:“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要有充实的内容和巧丽的形式相结合,这就是文学创作的金科玉律,这就是刘勰评论文学的最高准则。
这一基本观点,是贯彻于《文心雕龙》全书的。在“论文叙笔”部分,论骚体中提出“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辨骚》);评诗歌,则强调“舒文载实”(《明诗》);论辞赋,就主张“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诠赋》);对“情采芳芬”(《颂赞》)、“华实相胜”(《章表》)、“志高而文伟”(《书记》)、“揽华而食实”(《诸子》)的作品,予以肯定和提倡;对“或文丽而义睽,或理粹而辞驳”(《杂文》)、“有实无华”(《书记》)、“华不足而实有余”(《封禅》)的作品则给以批评。
至于创作论和批评论部分,刘勰用“割情析采”四字来概括其总的内容,更说明他是有意着眼于华和实、情和采两个方面的配合来建立其文学理论体系的。创作论部分,如结合“体”和“性”(《体性》)、“风”和“骨”(《风骨》)、“情”和“采”(《情采》)、“熔”和“裁”(《熔裁》)等进行论述,这些篇题都是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来命名的。刘勰认为:“立文之道,惟字与义。”(《指瑕》)又说:“万趣会文,不离情辞。”(《熔裁》)“情”与“义”指内容方面,“字”与“辞”指形式方面,作品不外由这两个方面组成,创作的具体任务,也就是如何“舒华布实”,怎样安排好内容和形式的问题。所以,刘勰在《情采》篇把正确处理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称为“立文之本源”。创作论中虽然讲修辞技巧的较多,也都是围绕着如何运用种种表现手段服务于内容来论述的。如讲对偶,要求“必使理圆事密”(《丽辞》);论比喻,主张“以切至为贵”(《比兴》);论夸张,要求“辞虽已甚,其义无害”(《夸饰》)等。
文学创作是作者有了某种情志然后通过文辞形式表达出来;文学批评与此相反,是通过形式进而考察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刘勰就根据这一原理建立了他的文学批评论:“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知音》)因此,他认为文学批评的基本途径,就是“沿波讨源”,即从作品所用的体裁、文辞等形式方面,进而考察作品的内容,以及这些形式能否很好地表达内容。这和刘勰论创作的基本观点完全一致,仍然是从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这个基本点出发,要求作品既有充实的内容,又有完美的表现形式。因此,刘勰的作家论,也是肯定在创作上“文质相称”、“华实相扶”(《才略》)的才能,而不满于“有文无质”(《程器》)、“理不胜辞”(《才略》)的作者。
以上情形,不仅说明“原道”和“宗经”相结合的基本观点是贯穿于《文心雕龙》全书的;同时也说明,“衔华佩实”是刘勰全部理论体系的主干。《文心雕龙》全书,就是以“衔华佩实”为总论,又以此观点用于“论文叙笔”,更以“割情析采”为纲来建立其创作论和批评论。这就是《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概貌,也是其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
1 有关门的四字成语
有关门的四字成语 :
五花八门、
程门立雪、
分门别类、
闭门造车、
左道旁门、
不二法门、
满门抄斩、
开门揖盗、
门庭若市、
开门见山、
双喜临门、
关门大吉、
扫地出门、
自立门户、
关门打狗、
班门弄斧、
破门而入、
书香门第、
得意门生、
门当户对、
吃闭门羹、
一门心思、
将门虎子、
布鼓雷门、
城门鱼殃
2 求大门朝东的门头四字吉祥语大门朝东的门头四字吉祥语如下:
1云岚福气
2舒华布实
3日月澄晖
4华堂聚和
5时和景泰
6竹苞松茂
7万事如意
8福寿即来
9五谷丰登
10四季呈祥
11向阳门第
12纳福迎祥
13国泰民安
14风调雨顺
15欣欣向荣
16时和岁好
17年年大发
18岁岁有余
19万象皆春
20四季平安
21东风解冻
22春日载阳
23春盈四海
24梅开五福
25百业兴旺
26五谷丰登
27春和景丽
3 关于门的四字成语 疯狂猜成语中的过屠门而大嚼 屠门:肉店。比喻心里想而得不到手,只好用不切实际的办法来安慰自己。
倚门倚闾 闾:古代里巷的门。形容父母盼望子女归来的迫切心情。
相门有相 宰相门里还出宰相。旧指名门子弟能继承父兄事业。
侯门似海 王公贵族的门庭像大海那样深遂。旧时豪门贵族、官府的门禁森严,一般人不能轻易进入。也比喻旧时相识的人,。
长戟高门 门庭高大,门内列戟。形容旧时显贵人家的威仪。
筚门闺窦 筚门:柴门;圭窦:上尖下方的圭形门洞。形容穷苦人家的住处。
祸福无门 无门:没有定数。指灾祸和幸福不是注定的,都是人们自己造成的。
高门大户 高门:旧时指富贵之家;大户:声势显赫的家族。有钱有势的人家。
屠门大嚼 屠门:肉店。比喻心里想而得不到手,只好用不切实际的办法来安慰自己。
分门别户 分、别:分辨、区别;门:一般事物的分类;户:门户。指在学术上根据各自的格调或见解划清派别,各立门户。
遁迹桑门 指避开尘世而出家为僧。桑门,即沙门。
剪发杜门 剪发:剪掉头发,指削发为僧。杜门:闭门。剪发为僧,闭门不出。
杜门自绝 杜门:关门不出;绝:断绝。闭门不出,将自己与外界隔绝。
进退无门 前进无路,后退无门。形容处境十分困难,进退两难,无处容身。
闭门思愆 指关起门来自我反省。同“闭合思过”。
荜门圭窦 筚门:荆竹编成的门,又称柴门。常用以喻指贫户居室。
闭门读书 关起门来在家里读书。原意是独自学习,而不与别人切磋。后也用以形容专心埋头苦读。
改换门闾 闾:里巷的门。改变门第出身,提高家庭的社会地位。
杜门屏迹 指隐居不出。同“杜门晦迹”。
筚门圭窬 同“筚门闺窦”。柴门小户。喻指穷人的住处。
啊啊
4 门口什么的四字成语没有 门口什么 的四字成语,门 开头的成语如下:
门不停宾 宾:宾客。门外不停留客人。形容勤于待客。
门当户对 旧时指男女双方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情况相当,结亲很适合。
门到户说 到各家各户宣传解说。
门户之见 门户:派别;见:成见。因派别不同而产生的成见。
门禁森严 指 机关门口的警卫极严密。
门可罗雀 大门之前可以张起网来捕麻雀。形容十分冷落,宾客稀少。
门闾之望 指父母对子女的想望。
门墙桃李 门墙:指师长之门;桃李:比喻后进者或学生。称他人的学生。
门生故吏 故吏:过去的吏属。指学生和老部下。
门庭若市 门前和院子里人很多,象市场一样。原形容进谏的人很多。现形容来的人很多,非常热闹。
门外汉 指外行人。
门无杂宾 家中没有闲杂的人来作客。形容交友谨慎。
门不夜关 形容社会安宁,风气良好。
门不夜扃 形容社会安宁,风气良好。同“门不夜关”。
门单户薄 指家道衰微,人口不昌盛。
门殚户尽 指全家死亡。
门户之争 宗派之间的争论。
门阶户席 门里门外的地方。形容到处,随处。
门堪罗雀 形容十分冷落,宾客稀少。同“门可罗雀”。
门可张罗 形容十分冷落,宾客稀少。同“门可罗雀”。
门生故旧 指学生和旧友。
门衰祚薄 门庭衰微,福祚浅薄。
门庭赫奕 门庭:指家庭社会地位。赫奕:盛大。形容人地位、名声显赫。
门庭如市 门:家门;庭:庭院;如:像;市:集市。门前像市场一样。形容来的人很多。
门无杂客 家中没有闲杂的人来作客。形容交友谨慎。同“门无杂宾”。
5 农村大门四字词语 有好的象征运气的门字的四字成语
书香门第、
左道旁门、
程门立雪、
门可罗雀、
班门弄斧、
门当户对、
门庭若市、
开门见山、
闭门造车、
鲤鱼跳龙门、
不二法门、
五花八门、
鱼跃龙门、
开门揖盗、
双喜临门、
遁入空门、
朱门绣户、
开门七件事、
各人自扫门前雪、
关门打狗、
将门虎子、
清水衙门、
布鼓雷门、
分门别类、
过屠门而大嚼、
歪门邪道、
车马盈门、
侯门似海、
政出多门
6 门的四字成语大全详细
踢断门槛:因跑得太勤、太快,把人家的门槛都踢断。讽刺那些溜须拍马的走狗们
摆龙门阵:闲谈,聊天,讲故事 详细»
满门抄斩:投没财产,杀戮全家 详细»
傍门依户:傍:依傍,靠着;门、户:家。依靠在别人门庭上。指依赖别人,不能自立 详细»
硬撑门面:装体面,假充上流。保持高等或中等阶级社会地位的风度、架子或门面 详细»
硬门槛子:比喻不易克服的困难 详细»
船到桥门自会直:桥:桥梁。比喻事先不必多虑,问题自会得到解决 详细»
船到桥门自然直:桥:桥梁。比喻事先不必多虑,问题自会得到解决 详细»
鸿门宴:鸿门:地名,今陕西临潼东北。指不怀好意的宴请或加害客人的宴会 详细»
黄门驸马:黄门:宫庭禁门,后成为官署名;驸马:转指皇帝女婿。汉代掌管皇帝出行车马的官。指依靠婚姻而上的人 详细»
寄人门下:寄:依靠。寄居在别人家中。比喻依附别人生活 详细»
粉饰门面:粉饰:打扮,装饰。比喻只把外表装饰得很美观 详细»
旁门歪道:指不正经的东西 详细»
热门货:指好销的货 详细»
贼走关门:比喻事故发生后才采取措施 详细»
独门独户:单独一家 详细»
鬼门关:迷信传说中的阴阳交界的关口。比喻凶险的地方 详细»
将门出将:将门:世代为将帅的人家。指将帅家门出将帅 详细»
前进无路,后退无门:形容处境非常困难 详细»
单门独户:一个院里只住一户,也指一院一户的住宅 详细»
丧门星:爱争吵的人。比喻带来灾祸或者晦气的人 详细»
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秀才:指儒生。指有知识的人待在家里,也能知晓天下的事情 详细»
远门近枝:比喻远亲近亲 详细»
走后门:比喻通过托情或利用职权等不正当的途径谋取通融或利益 详细»
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指好事不容易被人知道,坏事却传播得极快 详细»
名门望族:名门:豪门。高贵的、地位显要的家庭或有特权的家族 详细»
自报家门:戏曲演员一出场先把角色的姓名、家世、来历介绍给观众。指作自我介绍 详细»
半夜敲门不吃惊:比喻没有做过什么亏心的事,心里很踏实 详细»
半夜敲门心不惊:比喻没有做过什么亏心的事,心里很踏实 详细»
灭门之祸:灭:消灭;门:家,家族。满门老少皆被诛灭的灾祸 详细»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不吃惊:平生:有生以来;亏心:违背良心。从来没有干过违背良心的事,即使夜半人敲门也。 详细»
方便门:方便:便利。佛教语,指引人入教的门径,后指给人便利的门路 详细»
开后门:比喻利用职权给予他人某些不应有的方便和利益 详细»
大祸临门:临:光临。即将发生大灾祸 详细»
大门不出,二门不进: 详细»
广开门路:指尽量想办法开辟多种渠道 详细»
门户开放:开着门或像是开着门做某事。也指在对外关系中减少限制,让外国人进入本国进行某些活动 详细»
三过家门而不入:指夏禹治水的故事,比喻热心工作,因公忘私 详细»
一登龙门:龙门:传说鲤鱼跃过龙门就变成龙。指一时间飞黄腾达 详细»
一登龙门,身价十倍:忽然得到荣耀,从而身价倍增 详细»
装门面:表面伪装 详细»
丧门神:指专管死丧哭泣的凶神,比喻给人带来晦气的人 详细»
吃闭门羹:羹:流汁食品。比喻串门时,主人不在家,被拒绝进门或受其他冷遇 详细»
闭门谢客:指不接待客人 详细»
熟门熟路:熟悉门径,了解情况,很有经验。 详细»
善门难开:善门:为善之门。旧指一旦行善助人,许多人都会来求援,凡无法应付了。 详细»
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比喻每人只管自己的事,不管别人的事。 详细»
各人自扫门前雪:比喻不要多管闲事。 详细»
挨门挨户:挨:按照顺序。按照住户的顺序一家也不漏。同“挨门逐户”。 详细»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富贵人家酒肉多得吃不完而腐臭,穷人门却在街头因冻饿而死。形容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
刘勰的文学思想
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一、强调文学的美质,这是与当代文学风气一致的。缺陷也同当代文人一样,是单纯地以华丽为美。二、主张宗经,提倡雅正,在原则上排斥一切离经叛道的文学,这是一种保守的文学观念。但在对待具体作品的时候,态度并不那么褊狭。尤其在以后的各篇中,并没有以是否雅正的标准随意否定有成就的作家与作品。三、应当注意到,刘勰所说的“宗经”,是指以儒家经典为典范,而不是要求把文学作为阐发儒家之道的工具。他还是承认文学有抒发个人感情的作用。这同后世极端的载道文学观还是有很大区别。四、联系刘勰对六朝文学的批评,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是离异于儒道,包括思想感情不够纯正、艺术风格诡奇轻艳等等,二是有单纯追求辞采而缺乏充实的感情的现象。这些批评有些是正确的(如对后者),有些仍有些守旧倾向(如对前者)。但不管怎么说,以返归经典作为文学发展的出路,总是弊大于利。 作为“文之枢纽”的五篇,其意一在赋予文学以哲学本质上的说明,同时也由此赋予文学以崇高的意义,这一种理论上的努力,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在建立一种规范的、雅正的,同时又富于美感的文学准则,在这里,作者采取了折衷的态度,也反映出矛盾的心态。
刘勰的文学发展观
文学形式、文章风格,总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并且总是“染乎世情”,“系乎时序”,“崇替在选”,适应时代需要的。辞赋的发展和演变也是这样:楚辞演变为汉赋,某些辞赋又演变成骈文……。
辞赋作品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辞赋家的才华、气质和学识。《才略》篇则是刘勰叙述文学家才华史的篇章。兹就其中有关辞赋作家的部分介绍给读者。汉初曾经劝说刘邦崇尚文化,提出“能在马上得天下,岂能在马上治天下”口号的陆贾,“首发奇采,赋《孟春》而选典诰,其辩之富矣”;文帝时“贾谊才颖,陵轶飞兔,议惬而赋清”;枚乘、邹阳,“膏润于笔,气形于言矣”;司马相如自小喜爱读书,“师范屈宋,洞人夸艳,致名辞宗;然核取精意,理不胜辞,故扬子以为‘文丽用寡者长卿’,诚哉是言也”,意即司马相如注重文辞的夸饰,而影响了他的赋作的思想性;王褒善于辞赋的结构,“以密巧为致,附声测貌,泠然可观”;扬雄注重辞赋的思想性,“辞气最深,观其涯度幽远,搜选诡丽,而竭才以钻思,故能理赡而辞坚矣”,刘勰比较欣赏扬雄那种文辞与思想性俱佳的才略;刘勰在《才略》中叙述了自屈原、宋玉、荀子以下至东晋末约80位辞赋作家的才华和特点。可以说《才略》篇是一部简明的辞赋作家史。
虽然刘勰没有明确论述辞赋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但他有几处论断,足以为我们引为辞赋史阶段划分的依据。比如:《时序》篇曰:“爰自汉室,迄至成哀,唯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辞赋史的阶段划分可以有多种标准,改朝换代、最高统治者的爱好与否、作品的内容和思想性、作品的形式等等,都可以作为依据,而刘勰以辞赋形式为标准。《时序》篇还说:“然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华实所附,斟酌经辞,盖历政讲聚,故渐靡儒风者也。降及灵帝,时好辞制,造羲皇之书,开鸿都之赋,而乐松之徒,招集啷陋,故杨赐号为驩兜,蔡邕比之俳优,其余风遗文,盖蔑如也。”我们知道,西汉、东汉的辞赋显然属于两个不同的阶段,刘勰在这里不是简单地以改朝换代为划分依据,而是以辞赋的内容、思想性、风格作为依据的;而且指出东汉从光武帝至灵帝为一个阶段,献帝的建安时代为另一个发展阶段。事实上刘勰也曾指出,西汉的辞赋也可以划分两个阶段,《才略》篇云:“然自卿渊已前,多役才而不课学;雄向已后,颇引书以助文;此取与之大际,其分不可乱者也。”如果说《时序》篇的两处论述并非直接关系到辞赋的阶段划分的话,那么这一段论述则是非常直接地专论辞赋史阶段划分的。西汉辞赋从汉初到王褒为一个发展阶段,扬雄、刘向所处的时代则为另一个阶段。整个两汉时代的辞赋,刘勰以为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诠赋》篇是辞赋发展的专门史;《时序》篇是文学的时代史(以时代为序列,但不是编年史,因为不以年代为序列),其中包含了辞赋的时代史;而《才略》篇则为辞赋作家的历史。从不同的角度总结辞赋发展的历史,是刘勰对辞赋学研究的一大贡献。
传统修辞学分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方面:消极修辞包括语音修辞——讲究平上去入、阴阳清浊、音节对应、叠字双声、合辙押韵;语汇修辞——在同义近义词语中,作适合语境的意义选择与搭配选择、作适合感情和语体的色彩谐调选择;语法修辞——在同义表达中,对句式的长短整散、主动被动、肯定否定、常式变式、陈疑祈叹等作最适合语境的恰当选择;篇章修辞——文章的酝酿构思、选材布局、情感事理、风格详略、修改评析等。积极修辞——特指经过长期修辞实践而形成的固定而公认的修辞格。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这两方面都有精当而深刻的论述,尤其对消极修辞的论述,不仅论及文章技巧,而且深入到心理活动和思维规律与语言生成关系的层面,不仅当时直至今天也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汉字以建筑式方形结构为独立个体单位,一个个体单位为一个音节,音节又多具备阴阳上去不同调值,这种特点,为汉语语音修辞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语音修辞方面,刘勰没有沿习名人沈约的“八病说”,而着重提出了“飞沉”问题、“双声叠韵”问题。
在《神思》中,刘勰就提出了“寻声律而定墨”的主张,在《声律》中又说:“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意思是字调有阴阳清浊平声仄声之分,词之声韵之中有双声叠韵之别。(当时平仄之说,故以飞沉言之。此前借用音乐术语宫商角徵羽指称声调高低。《文镜秘府论》讲到调声三术:指出宫商是平声,徵是上声,羽是去声,角是入声,上去入是仄声。此处飞指阴清,平声;沉指阳浊,仄声)阴阳清浊之字,应平仄穿插交替,若连用仄声,就有声气沉沉欲断之觉,若连用平声,又有声气升飏飘飘不降之感。(如曹植《美女篇》: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潘岳《悼亡诗》: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而双声叠韵之词,必须连用,若两词之间插入他字,或将一词分用于相邻两句,则会造成“吃文”——拗口的毛病。这确为卓见,诸多绕口令不都是故意运用这种穿插而造成“必睽”之“吃文”嘛。一旦产生了这种毛病,则须“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则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矣。”刘勰认为,作韵易而选和难——异音相从谓之和——平仄声调配合得当叫和谐,同声相应谓之韵——相应位置上同韵字遥相呼应叫押韵。足见刘勰不但非常重视而且准确把握了汉字汉语的语音特点,对语音修辞在理论上作出了可贵贡献。如何用韵,《章句》有论:“若乃改韵从调,所以节文辞气,……然两韵辄易,则声韵微躁,百句不迁,则唇吻告劳妙才激扬,虽触思利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无咎。”折中的主张,是符合声韵运用美学的。
在语汇修辞方面,刘勰提倡慎重遴选词语。
《指瑕》凡举用词四疵,皆碍美文。——陈思之文,群才之俊也,而《武帝诔》云:‘尊灵永蛰’;《明帝颂》云:‘圣体浮轻’,浮轻有似于蝴蝶,永蛰颇疑于昆虫,施之尊极,岂有当乎!——以指称微小虫豸之词而施于尊长,确属搭配对象失误。
潘岳为才,善于哀文,然悲内兄,则云感口泽,伤幼子,则云心如疑。礼文在尊极,而施之下流,辞虽足哀,义斯替矣。——感口泽只能用来唁念辞世的母亲,心如疑只能用来悲悼故去的父亲,——潘岳用其哀挽同辈和小辈,分属词义运用错误、搭配对象错误,又是感情色彩分配失当。
所举另两种瑕疵,有左思反对孝道的思想错误和崔瑗把虞舜误比不出名的李公,虽属思想和比类之误,然毕竟要通过遣辞用语表现出来,归为语汇修辞亦非不当。
语汇修辞中,还涉及用字,刘勰在《炼字》提出用字“四要则”:……是以缀字属篇,必须拣择: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诡异,生辟险怪之字,如汹呶;联边,相同偏旁之字,如峥嵘;重出,同字相犯即同一个字在句中重复使用;单复,字形肥瘠笔画多寡。——仔细想来,均有道理:读文时遇诡异之字,犹赤足行于怪石每现之途,必耗神费力坏心绪;联边相集,如寄寓客家牢守寒窗空寂寞,迷途远避退还莲迳返逍遥之类,也会呆板乏目;重出之弊,字之音形无不单调乏味;字形肥瘠笔画多寡如若不加调配,则会或失之于纤疏,或失之于垒重。无怪刘勰叹曰:故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为难也。
语法修辞部分,刘勰在《章句》中提出了要按内容安排章句和按情韵安排章句的主张。按内容,要“控引情理,送迎际会”即根据表达的情理,有时枝蔓扶疏旁征博引,有时紧扣题旨不蔓不枝;据情韵,则“若夫章句无常,而字有枚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裕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刘勰主张,句式的选择上,用长用短,或长短穿插,整散结合,完全要符合情韵需要,情韵急,少音节短词句,情韵缓,可用舒曼之长句,情韵起伏跌宕,则可长短并用整散结合,以收荡气回肠之效。
刘勰修辞美学最为璀璨的部分,在篇章修辞。
重涵养,立风格。《体性》之体,文章体貌,《体性》之性,人之性情,《体性》即论文章风格和作者个性的关系。文有“八风之议”即穷列文章八种风格——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又据不同标准分为四组:思想内容——雅与奇反,情理义蕴——奥与显殊,题材表达——繁与约舛,体象气韵——壮与轻乖。凡为文者,均望尽快形成自己独特风格,刘勰指出文章风格和作者涵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而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性情所烁,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有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由是观之,文如其人,理应不错。作者的内心情理外化为语言文章,作者的才学、气质、性情、习惯所陶染而成的个性,必然盈溢为文章风格。因此,要熔铸自己独特文风,必须注重修养才学,涵性怡情完善个性品质。无怪刘勰在《神思》中提倡“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也只有如是,才有助于文章风格的形成。
文章有风格,更有风骨,才煽情动人,辞采焕然。什么是风骨呢?“《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ch o悲愤)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简言之,风就是充盈于作品中的情志和才气,是感化的根本力量。骨则是切中肯綮、言简意赅、恰如其分、流畅和谐的语言。风骨指向了感人才情和生动语言的修辞美学。要使文章含风树骨,则须“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刘勰还进一步指出有无风骨对文章的不同效果:“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徵也。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相如赋仙,(作《大人赋》)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如是观之,白居易“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之论,与刘勰风骨之议,均为至言也!
感人的才情和生动的语言固然重要,但一定要为情而造文,而不要为文而造情。要写真情实话,不要假意虚言。“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刘勰之论,对匡正无病呻吟、言不由衷、矫揉造作、空假俗媚之流,不啻当头棒喝警钟长鸣。
重熔裁,明隐秀。文章长短、内容详略、语意显隐、精警庸凡,亦为文之必虑。《熔裁》指出:“规范本体谓之熔,剪裁浮辞谓之裁。裁则芜秽不生,熔则纲领昭畅。”简言之,熔是炼意,提炼中心,裁是炼辞,锤炼语言。因为“凡思绪初发,辞采苦杂,心非权衡,势必轻重。”所以,刘勰提出了“三准论”——“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赊于终,则撮辞以举要。然后舒华布实,献替节文(献:可,替:否。即根据需要调节文字),绳墨以外,美材既斫,故能首尾圆合,条贯统序。若术不素定,而委心逐辞,异端丛至,骈赘必多。故三准既定,次讨字句。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三准论”提出了写好文章的三部曲、三准则:首先根据情理确定文章体裁;其次分析素材遴选典型题材;再次简言要义提纲挈领。然后加工润色,处理详略,条贯首尾,敲定全文。
语意显隐、精警庸凡,义涉隐秀。《隐秀》云:“夫心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ch ng)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今日言之,隐即弦外余音,秀即篇中警语。文章浅白直露固无余香满口,通篇俗语庸言亦难振聋发聩。文有余音,犹“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润”;篇纳秀语,似月依日而夜明,树沾春而林翠。
文章秀句,或自出锦心,或得益援引。《事类》认为:无论“引古事而莫取旧辞”的化用暗引,也无论“取旧辞万分之一”的择要精引,还无论“颇酌诗书传记”的综采博引,只要是为“以其据事类义,援古证今”,则无可指责。而《指瑕》认为:“若掠人美辞,以为己力”,则“宝玉大弓,终飞其有。全写则揭箧,傍采则探囊。然世远者太轻,同时者为尤矣。”由是观之,刘勰并非反对引用,而是反对抄袭。引用乃明借,旨在助己之文,抄袭是明抄,旨在当己之章。全抄无异开箱抢劫,小抄亦如掏腰绺窃,抄袭前代的贼味稍轻,同代相窃则堪堪致罪了。
透过鉴赏论的有关内容,也可看出刘勰篇章修辞的观点。他在《知音》中指出鉴赏作品要从两大方面六项内容入手,提出了“六观说”——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即体裁情志),二观置辞(即铺饰辞采),三观通变(即通古变今适应时代)四观奇正(即语言态势是雅正通畅还是奇诡怪诞),五观事义(即据事类义,指典型题材)六观宫商(即调声协律,安排语调辞气)。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以上六观,位体、通变、事义属于作品内容,置辞、奇正、宫商属于作品形式。从上论看出,只有从内容到形式作通盘考虑,这六个方面都熨烫妥帖恰到好处,才可以使文章“譬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
在积极修辞即辞格的运用方面,刘勰也予以了诸多观照。《丽辞》专讲对偶,将对偶分成相容的两组四种——以内容分,言对、事对为一组;以意义分,正对、反对为一组。言对事对各有反正,两组互相包容。在具体运用方面,刘勰指出“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迭用奇偶,节以杂佩,乃其贵耳。”
刘勰生活在殊重骈俪的时代,本人又对其青眼有加,一部洋洋大观的《文心雕龙》,通体骈俪为文,足证其爱。故所倡之法,可谓独得神髓,深谙三昧——骈散间出,方显错综之美,长短杂用,乃有灵动之活。
《夸饰》专讲夸张。刘勰没有像今天这样从形式上将夸张分为扩大式、缩小式、串前式等加以研究,而是抓住夸张得是否合乎事义情理这一关键,将夸张分为两类并指出其不同效果:“然饰穷其要,则心声蜂起,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如果夸张得合情理得神髓,就会引起强烈共鸣,反之,就会违背事实不合情理。
今天,我们如果面对这样的夸张——“麦秸粗粗像大缸,麦芒尖尖到天上。一片麦壳一片瓦,一粒麦子三天粮。秸当柱,芒当梁,麦壳当瓦盖楼房,楼房顶上写大字,社会主义大天堂。”“玉米稻子密又浓,遮天盖地不透风。就是卫星掉下来,也要弹回半空中。”——谁能不深切地感到刘勰所论,切中要害而又至关重要呢!
此外《比兴》讲到比喻,《事类》讲到引用,都有不刊之论。兹不赘述。
刘勰能在距今1500余年之遥,提出这如许之多的至今难超其苑囿的精辟修辞理论实为难能可贵。其修辞之论,既有理性的阐释,又有言证、事证,既涉文章内容形式,又关作者思维、气质、涵养、才情。他能从美才、美德、美情与美辞美文的关系方面,阐释情动而辞发、因内而符外的修辞美学观,他承认“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辞必巧丽”,尽管当时还没有堂皇的辩证唯物主义之说,然而在今天看来,这完全符合这种观点。在这种观点指导之下,他从内容决定形式的认识出发,建立了系统的剖情析采理论,他从历史唯物主义和现实唯物主义的认识出发,提出了“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种选择继承、据时创新的修辞观,这种服务于时代的“时文”修辞观,时至今日,也是必须遵循的一条修辞美学原理。 《文心雕龙》体大思精,深文周纳,拙文仅就修辞而蜻蜓点水,掠影浮光。若成引玉之砖,亦幸遂微愿矣。
刘勰《文心雕龙》的创作目的是反对当时文风的「浮诡」、「讹滥」,纠正过去文论的狭隘偏颇。它在文学批评史上的突出贡献是:
①初步建立了文学史的观念。他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终归要受到时代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他在《时序》篇中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并在《时序》、《通变》、《才略》诸篇里,从上古至两晋结合历代政治风尚的变化和时代特点来探索文学盛衰的原因,品评作家作品。比如他说建安文学「梗概而多气」的风貌,是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而形成;东晋玄言诗泛滥,是由于当时「贵玄」的社会风尚所决定。注意到了社会政治对文学发展的决定影响。不仅如此,他还注意到了文学演变的继承关系。并由此出发,反对当时「竞今疏古」的不良倾向。这些都是十分可贵的。
②分析论述了文学创作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关系,主张文质并重。在《风骨》篇里,他主张「风情骨峻」;在《情采》篇里,他强调情文并茂。但在二者之间,他更强调「风」、「情」的重要,他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坚决反对片面追求形式的倾向。
③从创作的各个环节上总结了经验,提出了应该避免的失败教训。他指出,在创作上,作家「神与物游」的重要,强调了情与景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化。他还指出,不同风格是由于作家先天的才情、气质与后天的学识、习染存在着差异的结果。针对当时「近附而远疏」、「驰骛新作」的风气,他提出了继承文学传统的必要,论述了文学创作中「新」、「故」的关系。此外,他对创作中诸如韵律、对偶、用典、比兴、夸张等手法的运用,也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④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在《知音》篇里,他批评了「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各执一隅之解」的不良风尚,要求批评家「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六观」的批评方法:一观位体,看其内容与风格是否一致;二观置辞,看其文辞在表达情理上是否确切;三观通变,看其有否继承与变化;四观奇正,看其布局是否严谨妥当;五观事义,看其用典是否贴切;六观宫商,看其音韵声律是否完美。这在当时是最为全面和公允的品评标准。
《文心雕龙》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的发展史上具有巨大的奠基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是一份十分宝贵的遗产,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理论工作者越来越多的注意和重视。在中国,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注释、翻译著述颇多。现存版本有影元至正本、《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本,另有今人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等。
1 文章修辞方面
传统修辞学分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方面:消极修辞包括语音修辞——讲究平上去入、阴阳清浊、音节对应、叠字双声、合辙押韵;语汇修辞——在同义近义词语中,作适合语境的意义选择与搭配选择、作适合感情和语体的色彩谐调选择;语法修辞——在同义表达中,对句式的长短整散、主动被动、肯定否定、常式变式、陈疑祈叹等作最适合语境的恰当选择;篇章修辞——文章的酝酿构思、选材布局、情感事理、风格详略、修改评析等。积极修辞——特指经过长期修辞实践而形成的固定而公认的修辞格。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这两方面都有精当而深刻的论述,尤其对消极修辞的论述,不仅论及文章技巧,而且深入到心理活动和思维规律与语言生成关系的层面,不仅当时直至今天也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汉字以建筑式方形结构为独立个体单位,一个个体单位为一个音节,音节又多具备阴阳上去不同调值,这种特点,为汉语语音修辞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语音修辞方面,刘勰没有沿习名人沈约的“八病说”,而着重提出了“飞沉”问题、“双声叠韵”问题。
在《神思》中,刘勰就提出了“寻声律而定墨”的主张,在《声律》中又说:“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意思是字调有阴阳清浊平声仄声之分,词之声韵之中有双声叠韵之别。(当时平仄之说,故以飞沉言之。此前借用音乐术语宫商角徵羽指称声调高低。《文镜秘府论》讲到调声三术:指出宫商是平声,徵是上声,羽是去声,角是入声,上去入是仄声。此处飞指阴清,平声;沉指阳浊,仄声)阴阳清浊之字,应平仄穿插交替,若连用仄声,就有声气沉沉欲断之觉,若连用平声,又有声气升飏飘飘不降之感。(如曹植《美女篇》: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潘岳《悼亡诗》: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而双声叠韵之词,必须连用,若两词之间插入他字,或将一词分用于相邻两句,则会造成“吃文”——拗口的毛病。这确为卓见,诸多绕口令不都是故意运用这种穿插而造成“必睽”之“吃文”嘛。一旦产生了这种毛病,则须“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则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矣。”刘勰认为,作韵易而选和难——异音相从谓之和——平仄声调配合得当叫和谐,同声相应谓之韵——相应位置上同韵字遥相呼应叫押韵。足见刘勰不但非常重视而且准确把握了汉字汉语的语音特点,对语音修辞在理论上作出了可贵贡献。如何用韵,《章句》有论:“若乃改韵从调,所以节文辞气,……然两韵辄易,则声韵微躁,百句不迁,则唇吻告劳妙才激扬,虽触思利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无咎。”折中的主张,是符合声韵运用美学的。
2语汇修辞方面
在语汇修辞方面,刘勰提倡慎重遴选词语。
《指瑕》凡举用词四疵,皆碍美文。——陈思之文,群才之俊也,而《武帝诔》云:‘尊灵永蛰’;《明帝颂》云:‘圣体浮轻’,浮轻有似于蝴蝶,永蛰颇疑于昆虫,施之尊极,岂有当乎!——以指称微小虫豸之词而施于尊长,确属搭配对象失误。
潘岳为才,善于哀文,然悲内兄,则云感口泽,伤幼子,则云心如疑。礼文在尊极,而施之下流,辞虽足哀,义斯替矣。——感口泽只能用来唁念辞世的母亲,心如疑只能用来悲悼故去的父亲,——潘岳用其哀挽同辈和小辈,分属词义运用错误、搭配对象错误,又是感情色彩分配失当。
所举另两种瑕疵,有左思反对孝道的思想错误和崔瑗把虞舜误比不出名的李公,虽属思想和比类之误,然毕竟要通过遣辞用语表现出来,归为语汇修辞亦非不当。
语汇修辞中,还涉及用字,刘勰在《炼字》提出用字“四要则”:……是以缀字属篇,必须拣择: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诡异,生辟险怪之字,如汹呶;联边,相同偏旁之字,如峥嵘;重出,同字相犯即同一个字在句中重复使用;单复,字形肥瘠笔画多寡。——仔细想来,均有道理:读文时遇诡异之字,犹赤足行于怪石每现之途,必耗神费力坏心绪;联边相集,如寄寓客家牢守寒窗空寂寞,迷途远避退还莲迳返逍遥之类,也会呆板乏目;重出之弊,字之音形无不单调乏味;字形肥瘠笔画多寡如若不加调配,则会或失之于纤疏,或失之于垒重。无怪刘勰叹曰:故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为难也。
语法修辞部分,刘勰在《章句》中提出了要按内容安排章句和按情韵安排章句的主张。按内容,要“控引情理,送迎际会”即根据表达的情理,有时枝蔓扶疏旁征博引,有时紧扣题旨不蔓不枝;据情韵,则“若夫章句无常,而字有枚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裕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刘勰主张,句式的选择上,用长用短,或长短穿插,整散结合,完全要符合情韵需要,情韵急,少音节短词句,情韵缓,可用舒曼之长句,情韵起伏跌宕,则可长短并用整散结合,以收荡气回肠之效。
3篇章修辞方面
刘勰修辞美学最为璀璨的部分,在篇章修辞。
重涵养,立风格。《体性》之体,文章体貌,《体性》之性,人之性情,《体性》即论文章风格和作者个性的关系。文有“八风之议”即穷列文章八种风格——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又据不同标准分为四组:思想内容——雅与奇反,情理义蕴——奥与显殊,题材表达——繁与约舛,体象气韵——壮与轻乖。凡为文者,均望尽快形成自己独特风格,刘勰指出文章风格和作者涵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而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性情所烁,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有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由是观之,文如其人,理应不错。作者的内心情理外化为语言文章,作者的才学、气质、性情、习惯所陶染而成的个性,必然盈溢为文章风格。因此,要熔铸自己独特文风,必须注重修养才学,涵性怡情完善个性品质。无怪刘勰在《神思》中提倡“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也只有如是,才有助于文章风格的形成。
文章有风格,更有风骨,才煽情动人,辞采焕然。什么是风骨呢?“《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ch o悲愤)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简言之,风就是充盈于作品中的情志和才气,是感化的根本力量。骨则是切中肯綮、言简意赅、恰如其分、流畅和谐的语言。风骨指向了感人才情和生动语言的修辞美学。要使文章含风树骨,则须“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刘勰还进一步指出有无风骨对文章的不同效果:“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徵也。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相如赋仙,(作《大人赋》)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 如是观之,白居易“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之论,与刘勰风骨之议,均为至言也!
感人的才情和生动的语言固然重要,但一定要为情而造文,而不要为文而造情。要写真情实话,不要假意虚言。“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刘勰之论,对匡正无病呻吟、言不由衷、矫揉造作、空假俗媚之流,不啻当头棒喝警钟长鸣。
重熔裁,明隐秀。文章长短、内容详略、语意显隐、精警庸凡,亦为文之必虑。《熔裁》指出:“规范本体谓之熔,剪裁浮辞谓之裁。裁则芜秽不生,熔则纲领昭畅。”简言之,熔是炼意,提炼中心,裁是炼辞,锤炼语言。因为“凡思绪初发,辞采苦杂,心非权衡,势必轻重。”所以,刘勰提出了“三准论”—— “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赊于终,则撮辞以举要。然后舒华布实,献替节文(献:可,替:否。即根据需要调节文字),绳墨以外,美材既斫,故能首尾圆合,条贯统序。若术不素定,而委心逐辞,异端丛至,骈赘必多。故三准既定,次讨字句。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三准论”提出了写好文章的三部曲、三准则:首先根据情理确定文章体裁;其次分析素材遴选典型题材;再次简言要义提纲挈领。然后加工润色,处理详略,条贯首尾,敲定全文。
语意显隐、精警庸凡,义涉隐秀。《隐秀》云:“夫心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ch ng)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今日言之,隐即弦外余音,秀即篇中警语。文章浅白直露固无余香满口,通篇俗语庸言亦难振聋发聩。文有余音,犹“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润”;篇纳秀语,似月依日而夜明,树沾春而林翠。
文章秀句,或自出锦心,或得益援引。《事类》认为:无论是“引古事而莫取旧辞”的化用暗引,也无论“取旧辞万分之一”的择要精引,还无论“颇酌诗书传记”的综采博引,只要是为“以其据事类义,援古证今”,则无可指责。而《指瑕》认为:“若掠人美辞,以为己力”,则“宝玉大弓,终飞其有。全写则揭箧,傍采则探囊。然世远者太轻,同时者为尤矣。”由是观之,刘勰并非反对引用,而是反对抄袭。引用乃明借,旨在助己之文,抄袭是明抄,旨在当己之章。全抄无异开箱抢劫,小抄亦如掏腰绺窃,抄袭前代的贼味稍轻,同代相窃则堪堪致罪了。
评析
透过鉴赏论的有关内容,也可看出刘勰篇章修辞的观点。他在《知音》中指出鉴赏作品要从两大方面六项内容入手,提出了“六观说”——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即体裁情志),二观置辞(即铺饰辞采),三观通变(即通古变今适应时代)四观奇正(即语言态势是雅正通畅还是奇诡怪诞),五观事义(即据事类义,指典型题材)六观宫商(即调声协律,安排语调辞气)。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以上六观,位体、通变、事义属于作品内容,置辞、奇正、宫商属于作品形式。从上论看出,只有从内容到形式作通盘考虑,这六个方面都熨烫妥帖恰到好处,才可以使文章“譬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
在积极修辞即辞格的运用方面,刘勰也予以了诸多观照。《丽辞》专讲对偶,将对偶分成相容的两组四种——以内容分,言对、事对为一组;以意义分,正对、反对为一组。言对事对各有反正,两组互相包容。在具体运用方面,刘勰指出“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迭用奇偶,节以杂佩,乃其贵耳。”
刘勰生活在殊重骈俪的时代,本人又对其青眼有加,一部洋洋大观的《文心雕龙》,通体骈俪为文,足证其爱。故所倡之法,可谓独得神髓,深谙三昧 ——骈散间出,方显错综之美,长短杂用,乃有灵动之活。
《夸饰》专讲夸张。刘勰没有像今天这样从形式上将夸张分为扩大式、缩小式、串前式等加以研究,而是抓住夸张得是否合乎事义情理这一关键,将夸张分为两类并指出其不同效果:“然饰穷其要,则心声蜂起,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如果夸张得合情理得神髓,就会引起强烈共鸣,反之,就会违背事实不合情理。
今天,我们如果面对这样的夸张——“麦秸粗粗像大缸,麦芒尖尖到天上。一片麦壳一片瓦,一粒麦子三天粮。秸当柱,芒当梁,麦壳当瓦盖楼房,楼房顶上写大字,社会主义大天堂。”“玉米稻子密又浓,遮天盖地不透风。就是卫星掉下来,也要弹回半空中。”——谁能不深切地感到刘勰所论,切中要害而又至关重要呢!
此外《比兴》讲到比喻,《事类》讲到引用,都有不刊之论。兹不赘述。
刘勰能在距今1500余年之遥,提出这如许之多的至今难超其苑囿的精辟修辞理论实为难能可贵。其修辞之论,既有理性的阐释,又有言证、事证,既涉文章内容形式,又关作者思维、气质、涵养、才情。他能从美才、美德、美情与美辞美文的关系方面,阐释情动而辞发、因内而符外的修辞美学观,他承认“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辞必巧丽”,尽管当时还没有堂皇的辩证唯物主义之说,然而在今天看来,这完全符合这种观点。在这种观点指导之下,他从内容决定形式的认识出发,建立了系统的剖情析采理论,他从历史唯物主义和现实唯物主义的认识出发,提出了“时运交移,质文代变”,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种选择继承、据时创新的修辞观,这种服务于时代的“时文”修辞观,时至今日,也是必须遵循的一条修辞美学原理。 《文心雕龙》体大思精,深文周纳,拙文仅就修辞而蜻蜓点水,掠影浮光。若成引玉之砖,亦幸遂微愿矣。
《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共十卷,五十篇,分上、下部,各二十五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个主要部分。上部,从《原道》至《辨骚》的五篇,论 “文之枢纽”,阐述了作者对文学的基本观点,是全书的纲领和理论基础。从《明诗》到《书记》的二十篇,以“论文序笔”为中心,每篇分论一种或两三种文体,可称是文体论。下部,从《神思》到《物色》的二十篇,以“剖情析采”为中心,重点研究有关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是创作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等四篇,从不同角度对过去时代的文风,作家的成就提出批评,并对批评方法进行专门探讨,可称是文学史论和批评鉴赏论。下部的这两个部分,是全书的精华所在。最后一篇《序志》说明自己的创作目的和全书的部署意图。《文心雕龙》从内容上说虽然分为四个方面,但理论观点首尾一贯,各部分之间又互相照应,体大思精,具有严密的体系,在古代文学批评中是空前绝后的著作,是我国文学理论遗产的瑰宝,对于我们现在从事于文学创作、文艺批评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研究由上古至南齐以前我国文学的发展,更是不可或缺的依据,值得我们重视和好好研究。其成就是杰出的、空前的、是举世公认的。
然而,由于刘勰身名未显,当时的学术界还不大知道他,《文心雕龙》问世后,这部心血的结晶却得不到文坛的重视,名流的首肯。当时沈约名高位显,在政界和文化界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刘勰想首先取得他的承认,却没有机会接近他。一次,刘勰把书背着,像一个卖书的小贩似的,在大路边等着沈约。当沈约坐车经过时,便拦住了他。沈约好奇地把《文心雕龙》拿来阅读,立即被吸引,认为此书“深得文理”(《南史·刘勰传》),大加称赏。后来又常常把《文心雕龙》放在几案上随时阅读。经过沈约的称扬,刘勰的名气才大起来,《文心雕龙》终于在士林中传播开来。同时,三十八岁的刘勰,也告别了居留十多年的定林寺,“起家奉朝请”,踏上了仕途。
刘勰所撰《文心雕龙》五十篇,是我国古代第一篇文学批评著述。他主张文学作品应有“风骨”(充实的内容)、华美的形式(文采),并提出文学批评的六条标准(“六观”)及其必须具备的修养,系统阐述先秦以来文学批评理论,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