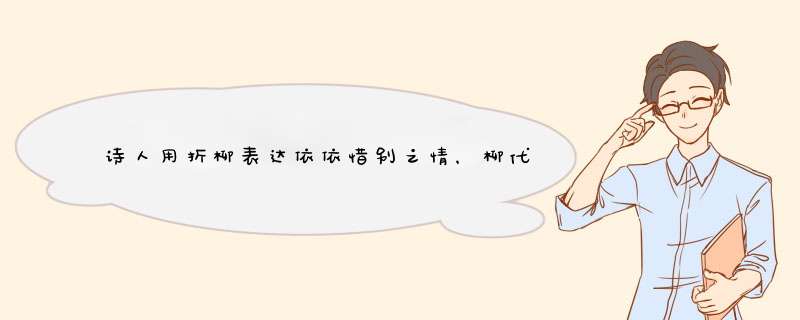
诗歌中的“柳”字有丰富的内涵。
柳意象是中国诗歌中出现频率极高而蕴含极丰富的植物意象,是一种蕴含着集体无意识的原始意象,积淀着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情趣,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和中国文学的特有风貌。柳意象的形成亦是如此,它发轫于《诗经》,形成于六朝,盛行于唐宋。柳意象在六朝形成的原因可从从别离、相思、乡思、时间意识等方面审视。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之中的吟咏,杨柳飘扬春风荡。影响了历代的诗人,“杨柳依依”也被历代诗人所钟爱,“浮云玉叶君不知,思君惜去柳依依”(萧子显《燕歌行》)“桂华殊皎皎,柳絮亦霏霏”(刘孝绰《校书秘书省对雪咏怀》);“杂桂还如月,依柳更疑星”(陈后主叔宝《宴光璧殿咏遥山灯诗》);“春心自浩荡,春树柳攀折。共此依依情,无奈年年别”(江总《折杨柳》);“含露桃花开未飞,临风杨柳自依依” (隋炀帝杨广《四时歌·东宫春》)等。柳的意象,已潜移默化的进入诗人的心灵,当诗人创作时,它便涌上心头。
柳的字面意思再明白不过,诗人的创作中却往往不是引用其中的字面意思。民间有“折柳赠别”风俗的影响。六朝时期社会动荡,人生离别也就成了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柳与人之间已具备“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情况下,人们就非常乐意把柳当作情感的寄托物和负载体。亲朋别离,折下一条细柳枝,什么话都不说,便表达了送者对离别者恋恋不舍的挽留之情,也希望离别者不论走到哪里,都要像柳那样成活发达,随遇而安,更希望能把故友的绵绵情丝永远留在心里,早日归来。
乐府诗云“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便是书写离别行旅之苦,路边折枝相送,表达恋恋不舍的心情。“幽幽桂叶落,驰道柳条长。折荣疑路远,用表莫相忘”(顾野王《芳树》)。“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隋杂曲歌辞《送别诗》),“渭城朝雨悒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王维(送元二使安西》) 等,或希望远行人早日归来,或希望友谊长存,即使在很远的地方也不要忘记。汉代出现了第一首专门反映折柳送别的《折杨柳行》,六朝时则有30多首,还出现了《月节折杨柳》这样十三首连在一起的组歌,并由乐府歌词发展到文人的专门创作。六朝时仅梁就有刘邈、简文帝萧纲、元帝萧绎等人写了《折杨柳》。也许折柳赠别更合六朝文人高雅飘逸的心态,故而反映折柳赠别的诗在六朝大量产生。
至于为何形成“折柳赠别”,当时还有折梅赠别的习俗。贺彻《赋得长笛吐清气诗》中的“柳折城边树,梅舒岭外林”是互文,意思是城边的柳树梅树被折来送别,只有岭外的梅柳才能舒适地生长。陆凯《赠范晔诗》中“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则是折梅表离别之情的名句。但折梅赠别远不及折柳赠别繁盛,这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柳比梅种植普遍得多,便于就地取材;二是柳枝弱,枝条长而下垂,容易攀折。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原因让柳成为诗人词客的常选意象。
“柳”与“留”、“丝”与“思”、“絮”与“绪”谐音。中国人善于使用谐音表达情感,柳及其相关物的这种谐音便易于成为表达情感的媒介,这在诗歌中大量存在。“垂丝被柳陌”(卢思道《赠刘仪同西聘诗》)、“悬丝拂城转”(岑之敬《折杨柳》)、“柳絮时依酒,梅花乍入衣”(梁元帝萧绎《和刘上黄春日诗》)等都可以有谐音双关之意。何况“,柳”还有聚之意《周礼天宫》“柳毂”注疏:“柳者诸色所聚。”《释名·释丧制》“柳车”注疏:“柳,聚也,众饰所聚,亦其形偻也。”“聚”也就是留聚的意思。
柳意思诗人生活环境中的常见之物,易于入诗。“无心插柳柳成荫。”不管是屋前“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陶渊明《拟古诗》),还是园边“折柳攀场圃,负绠汲潭壑”(鲍煦《秋夜诗》);不管是路边“桃林方灼灼,柳路日瞳瞳”(梁简文帝萧纲《乐府上之回》),还是水边“柳条恒拂岸,花气尽薰舟”(梁元帝萧绎《赴荆州泊三江口诗》)、“垂柳覆金堤,蘼芜叶复齐”(隋炀帝杨广《昔昔监》)都有柳树垂拂。诗人看的多了,也就容易引起他们的感情波动,成为了他们的审美意象。贺知章“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专为咏柳所作诗句,最能表现此点。
落絮游丝亦有情”(杜甫《白丝行》)。柳还具有独特的表现性。““杨柳青青着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垂柳枝条的形状、方向和柔软性本身就传递了一种被动下垂的表现性。柳丝柔长,象征情意绵绵;纷舞不定的柳絮又与游子飘零、分离时的离情别绪飞扬合拍;柳枝下垂,跟感慨离别时的人们那压抑低回的情态同构。柳的这种独特表现性使其具有独特审美性,让柳看上去便有了一种自然的“悲哀”。柳永“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秦观“西城杨柳弄春柔,动离忧,泪难收。”韦庄“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其中字里行间尽是无尽悲凉之情,以柳之意象渲染哀情,只使得悲哀之情更显几分悲哀。
柳是春天之物,其荣枯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岁月流逝的沧桑之感。这样,柳不仅具有离别相思、乡思等象征喻义,而且还具有时间象征喻义。陆游“梦断香销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 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岁月流逝,四十年物是人非,沈园之中的老柳见证了岁月变迁之中无尽的沧桑与悲凉,是过往岁月的见证,是时间的喻义。“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陆游:《钗头凤》) ,“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李白:《春夜洛城闻笛》) ,悠悠岁月之中,无尽变换无尽离别无尽悲欢,唯有依依垂柳做了那岁月的忠诚见证。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漫漫历史长河之中,柳以它无与伦比的特性,为无数文人骚客所喜爱所推崇。柳以它丰富的情感以及文化底蕴,使之足以表明意象在诗歌之中的灵魂作用。
折杨柳歌辞《乐府诗集》收入横吹曲辞梁鼓角横吹曲,共五首,内容相贯,主要为征人临行之际与其情人相互赠答之词。折杨柳是古代送别的习俗,送者、行者常折柳以为留念。
第一首是写“行客”告别亲友远行之际,“上马”理当挥鞭启程,可他却“不捉鞭”,反而探身去折一枝杨柳。柳者,留也,在古代习俗中是作为惜别的象征。这一细节,正表现出其依依惜别的心情。而此时更传来了悠悠长笛之声,岂不更令人怅惘,别情难抑!诗前三句纯用叙事代抒情,不明言离愁,而巧妙地用“柳枝”、“长笛”象征离情的事物意象作垫衬,逼出最后一句“愁杀”两字。
第二首中,“愁不乐”点出与“郎”经常离别,故女子大发奇想,希望成为心上人的马鞭,终日伴随情郎身边。诗蕴藉有致,颇带南方吴声西曲的柔情;但又颇有不同,“愿作郎马鞭”的痴想就明显带有北方器物的特征。诗以刚健之笔抒温婉之情,于爽健之中寓缠绵之情致。
第三首是写放马的情形。马不戴羁,人扛马鞍,人随马走,然后提出疑问“何见得马骑”,怎么不见你骑马呢。远离故乡前夕,作者的心情是沉重的,对未来充满了迷惑与不解。
第四首诗写征人遥望漫漫征程,对此行怀有隐忧。此诗应当注意两点:(一)作者当是北方少数民族,或为鲜卑,或为其他,虽已难深究,但其显然习惯于北方大漠生涯,来到中原沃土为时未久。故“遥望”之际,对“杨柳郁婆娑”之中原景物倍觉新鲜。“郁婆娑”三字十分传神,令人想见垂柳成行、依依摇曳之美景。此种景物描写,在北歌中极为罕见。(二)此诗当原用北族语言,经过汉译。“虏家儿”者,即出诸汉人译笔,北方民族断不会用此贬词自称。至于诗中透露出其时南北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信息,亦值得重视。
第五首诗是写一场激烈的马赛前的情景。赛马场上,人强马壮,跃跃欲试。作者不禁感叹:健儿要获胜,必须依靠骏马;但快马要显示出其善奔,亦须依靠骑术高明的健儿。两个“须”字,突出了人马互相依赖的重要关系。“跸跋黄尘”,动人心魄,展示出万马奔腾的壮阔景象。这是作者的揣想之辞,故云“然后”才能决一雌雄。诗有议论,有描写,场景阔大,给人一种阳刚的美感。
通过学习古代诗文,我们发现:在中国古代,每当行人远离,送行者往往折柳相送,以表惜别之情、祝福之意。这种独特的送别方式在文人墨客中颇为流行,为原本落寞惆怅凄凉伤感的离别场面平添了几分浪漫色彩。一般认为,“折柳送别”发端于西周初期,而《诗经》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则被视为首开了咏柳寄情、借柳伤别的先河。到了汉代,“折柳送别”渐成风气,记录汉代京师长安社会生活的《三辅黄图》云:“霸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折柳送别”有固定的送别地点及具体的折柳内涵,标志着这一送别形式的定型与成熟。到了唐代,由于实行科举制度和边疆战争频繁,普通庶民为追求功名,或远离家乡以文求仕,或远赴边塞建功立业,“折柳送别”之风大盛,成为时人送行饯别的主要方式,所谓“杨柳东门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者,应为离别多”。多情浪漫的唐代诗人将其作为诗歌中的特定意象,引诗入词反复吟咏。如权德舆《送陆太祝》诗:“新知折柳赠,旧侣乘篮送。”同时,情感表达也从抒发离别之苦拓展到了表现离别双方的相思之痛。如李白《宣城送刘副使入秦》:“无领长相思,折段杨柳枝。”那么,古人为什么会采用这种别具一格的送行方式?“折柳送别”的原始意蕴究竟何在呢?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探讨,历来不乏其人,然终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有以下几种主要观点:一、礼俗说有人从古代的丧葬礼俗中加以解释,认为古人用柳来制作丧车丧具,是借用柳的再生功能,表现了活着的人对逝者生命再生的企盼和愿望;再由“死别”转向“生离”,柳成为现实生活中人们远行或亲友分离时,寄托生命长在、生命平安这一类朴素愿望的吉祥物。二、生命说有人从生物学角度予以阐述,杨柳易活,生命力旺盛,以柳入诗,寄寓祝福,希望远行之人能很快适应异乡的水土,健康地生活,随遇而安,能够很快地融入当地的人群中,一切顺遂。正如清朝褚人获在《坚瓠广集》卷四中所说:“送行之人岂无他枝可折而必于柳者,非谓津亭所便,亦以人之去乡正如木之离土,望其随处皆安,一如柳之随地可活,为之祝愿耳。”这一说法便有了深刻的哲理性和更高的文化品位。三、文化传承说有人认为最早的渊源应该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几句古诗。这诗句来自《诗经》,而且是名句。“杨柳依依”表达了战士出征前怀家恋土的离情别绪,为后来的的送别诗奠定了文化基调。《诗经》作为五经之一,其深广的文化传承作用是不容怀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折柳送别”实际是一种文化传承。四、介之推说有人认为“折柳”、“插柳”源于寒食节习俗。南北朝时期梁宗懔撰《荆楚岁时记》记载:“江淮间寒食日,家家折柳插门。”家家户户门前插柳,是为了纪念春秋时晋国大臣介之推的。据说他力保国君重耳出逃19年,割股作汤,忠心耿耿。后来重耳作了国君却把他遗忘了,他与老母在绵山自耕自织为生,最后被大火烧死在山中的枯柳树下。人们插柳,是怀念介之推追求政治清明之意。从这个角度来看,折柳便有了纪念、怀念之意,成为后世“折柳送别”之滥觞。五、谐音说有人从音韵学方面给予解释,认为古人注重谐音表意。“柳者,留也。”这样,柳的这种谐音便易于成为表达情感的媒介。折柳相送,是表达依依惜别的深情。况且,那随风飘舞千丝万缕的柳枝与“剪不断、理还乱”的离愁别绪是何等吻合,柳丝飘荡与游子飘泊的情状又何其相似,以柳相送,自然合情合景。六、信仰说现代学者追溯出“折柳送别”的起源乃是蕴涵着“树神崇拜,生殖信仰”的观念,认为柳在中国文化中被视为就有祛邪扶正的神异力量,是被推崇敬奉的神树,同时也是生殖重版的象征,后来逐渐演化为了送别形式。以上种种观点,虽然丰富发展了“折柳送别”的文化内涵,却使得这一送别形式的原始意蕴愈加变得扑朔迷离、真伪难辨。笔者认为,任何习俗的产生形成都来源于人们的生产生活,是那个时期人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具体表现。正如郭于华在《民间社会与仪式国家——一种权力实践的解释》一文中所说,“民间仪式主要是作为生存的技术而存在的,其遵循的是一种生存的逻辑。”追根溯源,“折柳送别”的起源亦应来自人们的生产生活。我们因此认为:“折柳送别”滥觞于西周初期的“禁烟改火”制度,源自古人对火的崇拜,是现实生活在习俗中的具体反映。众所周知,火在人类进程史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它使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蒙昧时代,增强了人类的体质,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本领,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同时,火所酿成的巨大灾难,给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的极大损害,又使古人对火产生一种畏惧之感。这种既敬且惧的复杂心理表现在生活上,就出现了对火的崇拜和用火的禁忌。据专家考证,曾有过很长一段时期,周人是以火星作为示时星象,安排生产和生活的。那时候,天上的火星和人间的火,被想象为有着某种神秘关系。仲春时节火星昏见东方之时,被认为是新年的开始,此时有一套隆重的祭祀仪式。仪式之一便是熄灭去年薪火相传下来的全部旧火,代之以重新钻燧取出的新火,为新的一年生产和生活的起点,其名目叫做“改火”——《论语_阳货》“钻燧改火”讲的就是此事。新火未至,就禁止人们生火,这是当时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周礼_秋官_司煊氏》云:“中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在周代时还专设官职,名曰司_氏,是主持火禁的官,负责仲春的改火,他摇着木铎通知人们熄火,三天后再给人们带来新火。古代钻木取火讲究四季要用不同的木。《论语集解》马融曰:“周书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_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钻火各异木,故曰‘改火’。”与春相关的是榆、柳之木。春季正是将士出征、游子远行的多发时节,将用于改火后的柳枝新火赐于行人以避祸祈福保留火种,方便征人生活,温暖游子身躯自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为了保证火种不致半道熄灭,就须折柳相送,以备路途不时之需。这应是“折柳送别”的原始起源。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人们对火的认识日趋理性客观,钻木取火保留火种已非生活必需,对火的崇拜、保留火种的原始意蕴就逐渐淡化。后人沿用了其送别的意义,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折柳送别” 的习俗,并且对其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也有了不同的理解。赠火的古老传统即使在唐宋仍留有余绪。韩翊“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唐王朝赐火的情况。据唐末李绰《辇下岁时记》载:“清明日取榆柳枝火以赐近臣。”《宋朝事实类苑》亦有记载:“唐时唯清明以榆柳之火以赐近臣戚里。本朝因之,唯赐辅臣、戚里、帅臣、节察三使、知开封府、枢密直学士、中使,皆得厚赐,非常赐例也。”我们注意到其中赐火的时间与材质同西周时期的“禁烟改火”完全吻合。“以榆柳之火以赐近臣戚里”也充分证明赐火之说并非笔者妄加揣测,实乃古亦有之。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折柳送别”与“禁烟改火”乃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只不过此时赐火的主体与对象发生了变化,赐火已成为统治者的特权,是封建贵族独享的殊荣,一般的平头百姓则与之无缘。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折柳送别”与“禁烟改火”源出一辙,但其社会功用却大相径庭。综上所述,“折柳送别”与“禁烟改火”同出于西周,且选用的材质亦有雷同之处,其中的联系似乎很难用“巧合”一词解释。而且,从“折柳送别”习俗的产生发展轨迹看,它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现实生活需要到情感寄托表现的演变过程,而这个过程是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及人类认知水平的。来源:当代商报
此夜曲中闻折柳”。这一句的修辞很讲究,不说听了一支折柳曲,而说在乐曲中听到了折柳。这“折柳”二字既指曲名,又不仅指曲名。折柳代表一种习俗,一个场景,一种情绪,折柳几乎就是离别的同义语。它能唤起一连串具体的回忆,使人们蕴藏在心底的乡情重新激荡起来。
是突出诗人思乡之情,李白这首诗写的虽然是闻笛,但它的意义不仅仅限于描写音乐,更重要的是还表达了对故乡的思念,这才是这首诗感人的地方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