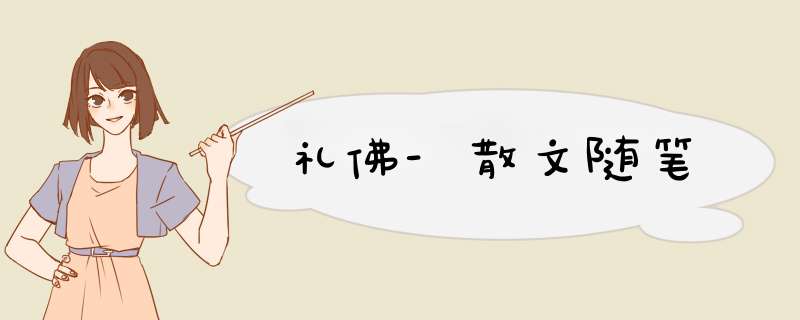
进入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坐上观光车,顺着盘曲的山道上行。一路的近山突兀,远山逶迤;一路的苍翠满眼,清风拂面;更有一路的车来车往,行人络绎。
距山顶约一公里,到达停车场,我们下车徒步登山。一家人停停走走,大约花了半小时,终于远远望见一尊偌大的佛像屹立山顶。
走到广场,瞻观音佛像,须极力仰视。佛像高达33米,由999块3300多顿花岗石雕刻而成。菩萨端坐须弥莲座之上,头戴宝冠,身着天衣,左手持净瓶于胸腹,右手结成无畏之印。
广场上人头攒动,烟雾弥漫。不管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是面若桃花的**,亦或是黧黑的青壮之汉,莫不手持香火,或望佛祷告,或闭目祈福,亦莫不是一脸虔敬满怀寄望。
敬完香火,我便去读刻写在佛像底座之上的般若波罗蜜心经: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佛经的意思说,宇宙间的一切,包括日月星辰、天地山河、花鸟虫鱼以及我们的发肤身体,都是有形有相的,我们身体的感受、思想、行为、意识(所谓受想行识),却是无形无相的,这些外在的有相和内在的无相蕴合一起,就是色。
而无论是外在的有相或内在的无相,都是因缘合和成的,是没有独立自性实体的空幻,所以佛说色与空没有两样,色本身就是空,空也是色。举例说一块有相的布,是由纱线纺织而成的,但纱线本身不是布;纱线要靠棉花来纺成,棉花本身又不是纱线;棉花不能自有,要靠种子;种子不能自种,要靠人工天时地肥等等。布是由天时地肥种子人工众多因缘和合而成的,布本身不过是一个空幻的名称而已。所以布这个色体不过是一个无自性的'空幻的不实之体,所谓色即是空,但也不是绝对的空,而是有着众多因缘的空,这个空中也有色,是谓空即是色。又举例说一人睡在夏天的凉席上甜美至极,无我无心。忽而被蚊虫叮咬而醒,心便有了叮咬的觉得。这个无相的觉得之色便是由我身与蚊虫集合的因缘而起,是一个因缘而生的无形的空幻,但这个色空也不是绝对的空,里面有着我与蚊虫的因缘。
佛经说,有着受想行识和色身的我们由四大合和而成。地成就了我们的毛发和骨肉,水成就了我们的血液和分泌,火成就了我们的体温,风成就了我们的呼吸。而我们因有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而生出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来,又因眼根贪色、耳根贪声、鼻根贪香、舌根贪味、身根贪细滑、意根贪乐境,贪且不知满足而又生嗔、痴,从而使人生长出无数的烦忧堕入苦海。
佛与肉眼凡胎的我们区别在于佛是参透一切的,知道一切皆是镜中花一般的不实之相,放下一切所有,得了了然自在。而我们却把一切空幻看作实在,企盼唯我所有,终究得到的只是满心的挂碍。
似懂非懂地默念着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从庞大的佛像底座上拾级而下,走远了,抬起头,再看观音佛像,便从她极静的眼中和慈悲的面容上看出一丝笑意来。佛笑我心中满满,不知放下,反来求取,许下种种的心愿。
在观音山顶礼完佛,小憩,而后随着接踵的香客沿着极陡的石阶下行。
观音在身后,在头顶,仿佛随我而来,驻进心里。
我的老家静静地躲藏在皖西南的山水弯蜒里,一屋一落,依山就势,临溪而守,出门便是峰峦叠翠,淙淙流水,田陌铺陈。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家已不偏远,延伸不绝的水泥路打通了一座座山村与外界的阻隔,而现代文明则悄然改变了这里的一切,特别是网络、智能终端等互联设备的普及,正肆意重塑着千百年来传统、羞怯的村民人格和生活方式。
嬗变与重塑似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是近年来,几近消失的一座座规模不一的山间佛寺又忽而慢慢地寻址重建开来,清晨夜幕下人声去后,小桥流水,风鸣狗吠,已然掩不住远山深处的寺院钟鼓声。
往拜的,阅尽冷暖、潮息湖平的老人有之,上老下幼、艰难疲惫的中年有之,守望安逸、相夫哺子的农妇有之,踌躇功名、备试应考的少年有之,更难分成功失意者,乡下城里人,贤达与卑微。
这突如其来的回归,除了印证佛与追求感官刺激、物质享受和成功胜算为动力的现代文明角逐中,佛赢得一线云天,佛光觅着情色物欲的喧嚣和网络风潮的浸润,再次似无意间于芸芸世俗里掘开根茎一块,沙土一捧,便蔓得一枝叶绿,流放瓣瓣花香,也留给人无尽的疑惑和不解。
以我的老家为例,佛寺的回归,除了有禅宗之乡人文底蕴的依托,人们对快节奏现代生活相伴而来的压力、焦虑、迷惘和浮躁的反思与自省,而佛何曾发出安顿灵魂的呼唤?
“佛”自印度传来中土已有2000余年,不同年代,虽或荣或弱,却总能绵延佛学、佛教与佛法之间,流于或乱或治、或张或合、或聚或散、或炫或涩的历史轴卷与人声犬色当中。繁荣也罢,衰弱也好,佛从不喜急于色;静听质疑,笑受笃信,佛亦向来低眉不语。
人生最惨莫于前无生机、退无活路,而人生最绝望莫于叫天不应、呼地不灵。那可叫无处着力又无地躲藏,挣扎只多了一地鸡毛。
即使这等落魄,一脸苦相地走进佛堂,跪一地虔诚,点一柱清香,听到的是跪拜者倾诉不止,上香人许愿诤诤,佛却永远化一尊泥胎,无非光华照人亦或不着浮饰。谁问佛,佛都不语,从未开口许诺。
走出佛堂苦相虽未彻去,笑意已悄然聚集,对命运逆转的生机与期翼早如孩童溺食般涂得满脸花色。是佛法无边还是人心本来宽广?亦或世间从来都是祸福相倚,迷茫时只需心灵深处的一句自我对话,便可再一次坚定求人不如求己的信念?厄难过去,时境反转后,再来跪拜,语无论次地谢恩再谢恩,而佛仍端如泥胎,悄然不语。
我不止一次惊叹佛的定力,佛的不语,佛不为却不经意间化腐朽为神奇。
佛为梵文 Buddha的音译“佛陀”的简称,意为“觉者”。不问出身,也不管是渐悟,还是顿悟,佛曰开悟即成佛。但自古得道佛、法、僧,哪一个不是曾经享尽人间浮华或尝遍世间苦难?人人皆可成佛岂非诳语?细一思量,这实乃俗人的执着,佛哪里说过这样的话,分明是我们人借了佛的名头。
修佛次第虽分“信、解、行、证”诸阶段,但佛却最讲无得。修佛、学佛不过是一次又一次启发智慧的起止转承。参佛似乎永远只在路上。
坚持悟道者,不见得都能获有万种般若智慧,但总会在对“我”、对“世界”、对“我的世界”认知中应缘证得一丝一缕或一粒一尘的智慧无碍。就算历史重来,亦是高手有居庙堂之上,也总在民间如繁星簇拥,不是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也许,世间本无佛。佛只凝结了对智慧造极的期许,在于修知行之慧,从不求神通之果。享尽浮华者可,尝遍苦难者可,凡俗微卑者谁说不可呢?去问佛吧,佛微笑,仍不语。
佛法强调万物本空,“色”虽道尽一切有形质的斑斓,但万物皆为因缘所生,并非本来实有,其当体是“空”。所以,佛曰“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人生过往,既然一切皆空,自无烦恼,却岂不了无生趣?一切从小我出发,烦恼又必自在自生,内心亦会因自我自闭而终究还是无趣。不是有多少实现了个人成功,却失去了人生方向?!然,得亦是空、失亦是空,成亦是空、败亦是空,何须生忧惧,又何来得喜而失悲?
这才有大我境界,才有家国情怀,才有格、致、正、诚、修、齐、治、平,才有“视天下人为子女,视子女为天下人”。易经强调生命价值在于“参赞天地之化育”,佛法讲普渡芸芸众生于绵延。两个不同的古老民族,两种不同的文化范式,在对人生大义的取舍上竟出奇的一致。
离“杀盗*妄酒”五戒是修佛,净“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远“色声香味触法”六尘也是修佛;出家受戒是修佛,俗家居士也是修佛;行德政、布王道是修佛,结善缘、施德行也是修佛,起一善念是修佛、去一恶念也是修佛,困顿后的呐喊是修佛、执妄后的沉静也是修佛。可谓一念一菩提、一善亦佛陀,一级石阶短,千重楼阁空。
当年南怀谨老先生在峨嵋山闭关三年,下山时,一和尚问他大藏经都全部读完了,怎不出家?南老先生以诗作答:不二门中佛法僧,聪明绝顶是无能。此生不上如来坐,收拾河山亦要人。大隐于市、活跃于朝,你能说南老先生不是修佛?向佛求证,佛还是微笑,依然不语。
《坛经》中云:“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议论不已。惠能进曰:‘非风动,非幡动,仁者心动’。”上乘无心,住于清静,不见有空,不见有色,一切真如,所以非风动,非幡动,仁者心动。下乘有心,住于有无是非,见色见空,非空即色,非色即空,起心动念皆是妄见,故一僧说风动,一僧说幡动。
一千个人眼里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人眼里更会有一千个“我”、一千个“世界”、一千个“我的世界”,心中自然住着一千尊不同的“佛”。你不是我,焉知我开悟没有、如何开悟,又开悟或多耶或少耶?
若不信,仍可去问佛,佛断然不变的是微笑,一贯的是不语。
于我,所谓散文就像一个朱漆的镂空雕花托盘,精致的明黄缎子上散落着龙眼大小的粉红珠子,流光异彩、高贵非凡,远远地看,你就已经为它的绝美喝彩。走近了,忽又发现,原来每颗夺目的珠子之间又有细细的银线连缀,游丝断缕,却又坚韧异常。珠子本就娇贵明艳,可落了单儿,一无氛围托衬,二无同类相拥,人只道它名贵,却没了它的气派;就像皇帝出游,前呼后拥的皇家华盖和御辇才会让平民百姓敬畏。穿过珠子的银线才是整个托盘的精髓,就如乡里野人一样,怕的不是皇帝,而是皇帝手里的权利。
这是好的散文,我的散文只是茶余饭后的嚼料。
我本无茶缘。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茶和佛是一样的道理,佛有佛缘,茶有茶缘;佛有佛禅,茶有茶禅。
只是我是个地道的“茶家门外汉”,到十二三岁的时候,对茶叶的认识还停留在“茉莉花茶”的初级阶段,而且看着小卖铺中“茉莉一级”、“茉莉特级”的标识,还以为世间的茶叶就仅此两种而已。尔后年纪再大两岁,看到家里若有亲朋来,老爸都以“毛尖”宴之,于是,对茶叶的认知又上升了一个高度,自以为是地和朋友炫耀:“毛尖”“毛尖”顾名思义就是“长着小白毛的茶叶尖”。在此期间还听说了龙井、碧螺春之类的茶叶,可一种叫“银毫”的茶叶的出现,又混淆了我自定义的关于“毛尖”的概念。
想起小时候,真是有趣。我们初中的数学老师为人严厉、不苟言笑,最痛恨学生上课睡觉,也因此练就了一手“弹指粉笔”的好功夫。我从小就头疼数学,考试卷上“全线飘红”的大叉已经让我饱尝老师“严厉关怀”的眼神,又怎么敢在上课的时候打瞌睡,让脑袋起大包呢?可是天知道,那索然无味的数学课有多么令人想躲入梦乡,可是我不敢。只好每天都带一大壶酽酽的茶水,随时灌入胃里,以提精神。此举果然有效,至少老师不会再以上课睡觉的理由来责骂我60分以下的成绩了。只是在很久以后的某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牙根有些偏黄,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时候“驴饮”浓茶的下场?
大学后,上铺的姐妹来自苏州,我们常常沏点碧螺春,靠在窗台上,以无限向往的神情极力远眺,被舍友笑骂“附庸风雅”。那个时候,因为喜极了碧螺春的清香,跑到图书馆去查阅关于碧螺春的历史,才知碧螺春产于碧螺山而得名,其色如螺黛,其味如兰麝,其细如蚕眉。固有吓煞人的别称。清代朱琛的《洞庭东山物产考》就有有关碧螺春的记载:“洞庭山之茶,最著名为碧螺春。树高二三尺至七八尺,四时不凋,二月发芽,叶如栀子,秋花如野蔷薇,清香可爱。实如枇杷核而小,三四粒一球。根一枝直下,不能移植,故人家婚礼用茶,取从一不二之义。”
毕业上班头一次和客户吃饭,去的就是一个茶馆。逋入店门便洞若世外,有汩汩的清泉绕脚而过,典雅古朴的方桌立于假山脚畔,一支《渔舟唱晚》若有若无宛如来自缥缈洪荒,款款摇曳的茶女、店内喃喃细语的品茗人以及充斥弥漫在整个茶屋的茶香,我仿佛进入世外桃源,胸间烦恼逐一涤荡,四肢百骸畅快淋漓。与客户的会谈通畅而欢快,高额的茶费竟然也付得心甘情愿,一扫商场购物锱铢必较的心态。
细细算来,我的生活里很多事情竟然和茶有着莫大的关联,我亦是有茶缘的人啊,只是相比与别人的茶缘来说,我的俗气点罢了。扰扰红尘中,浊物有酒,清物有茶,亦是大快人心之事。
其实,我在很久以前并不知道我喜欢银杏,因为它总被人们忽视。直到有一天我成为了阿掖山卧佛寺院内的银杏,看着我飘逸的叶片,完美的骨骼,我才开始为自己感动。
● 一切都是缘分,冥冥之中,前世、今生、来世早又注定和安排。
一千多年前,我本是被遗忘深山的银杏,孤独寂寞,无人问津。我佛慈悲,不忍看到我就此沉寂,了却一生,特派唐朝大将尉迟敬德僧翻山越岭,将我的种子从深山带出,带到阿掖山卧佛寺,跟随佛主,修炼佛法。
佛主对我怜悯,不仅将我的根深植于泥土,还给我浇水,看着我发芽,渐渐长成小树。可惜我的身体太脆弱了,初到卧佛寺,面对一切陌生的环境,并不适应,经不住自然的挑战。当时阿掖山卧佛寺佛法没有普及,山上树木,少之又少。一阵白杨风吹过,黄沙滚滚,我的身体瞬间被狂风从土里提起来,倒在一旁,奄奄一息了。
但佛主已经知晓我的痛苦,特意设法解救我。第二天早上,天微亮,就有一个小和尚缓缓地从我跟前走过。他看到我倒在地上的躯体,奄奄一息,毫无生机。他似乎落泪了,停留了很久,轻轻地将我从地上扶起来,并抱在怀里,嘴里念念有词。然后快速去厨房找了一把铲子,温柔地再次将我种下,他天天给我浇水,天天和我说话,直到师傅叫他他才不快地离开。遇见就是缘分,本以为自己活不成了,没想到奇迹地复活了。我感激,感谢佛主的恩赐,感谢小和尚的善心。
小和尚的照顾下,我渐渐长大了,枝繁叶茂,并和小和尚成为真挚的朋友。我喜欢秋天,秋天我的叶很美,那时小和尚总是在我树下玩,凉爽的秋风吹着我的树干,不一会儿,我的叶开始飘荡起来,转瞬间便可以改变地上所有景色的容貌。小和尚坐在的树底下,在洒满金**的叶子上,翻开翻去,抱写我的树干,似乎在和我玩捉迷藏,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整个秋天,我每天静静地听着风声,听着小和尚那响起“沙沙”悦耳的足音,听着他对我的呼喊,美妙极了。我和小和尚天天待再一起,我们喜欢听钟声,更喜欢大雪的清晨,看千里冰封的景象。我为成为一棵树而高兴,小和尚天天来找我说话,我一点也不孤独,反而成长了许多。
我喜欢听小和尚讲关于寺庙的一切,也喜欢听他念经,听他说卧佛寺以外的事。有时候我也跟着他念,“阿弥陀佛”,只是他好像听不见,我也不伤心,只要有他在就好了。
●时间匆匆,转眼好多年过去,小和尚变成了大和尚,我经过风雨洗礼也渐渐长高了。
有一天,有一高僧云游到卧佛寺,巡游四周,站在我身边看了很久。离别时赠语:“寺若香火千年旺,需卧佛一尊,头当沉香木、体宜檀香木。”小和尚决然只身江南化缘,我悄悄掩泪,至此以后,只剩下我一棵孤独的银杏,每天听钟声,悟禅语,默念心经,颇感无聊。小和尚知道我孤独,怕我伤心,在临走时,和我聊了很久,我们泪雨相别,没想到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还从山下移开一株小银杏,说让他成为我的朋友,代替他为我做伴。
小和尚走了,我每天过得昏昏噩噩,佛主知道我的苦衷,也拿我没办法。新植来的银杏,脾气暴躁,有事没事摇摇晃晃,弄得我头晕,让我心烦。
我不想理那株银杏,除非他主动给我说话,要不然我不想将就。没有小和尚的卧佛寺,很安静,没有孩童的笑声,没有车水马龙,没有高楼大厦,有的只是凄凉,只是孤独的明月和星辰。但这里的静,我很喜欢。广阔无边的宁静铺展在我的眼前,时间,好像走的很慢很慢。这里远离繁杂的人世,还可以望明月,品花香,看野草睡觉,看另一株银杏打盹,还算可以。
夜静了,卧佛寺所有生灵都已经熟睡,只有我还醒着。小和尚走的这些年,还是觉得空落落的,十八年我没见到他,十分为他担心,不知道他现在如何了。我每天为他在佛前祈祷,静静念着他交给我的佛经,希望佛主护他平安,能快快归来。
听佛主讲,小和尚在云贵一带化得沉香、檀香二木。木重路遥,运作艰难,无奈之际,适遇一商船北归,遂告求捎回。没想到人心难测,商人见物现私欲,途中将沉香、檀香偷偷换出,后又买通官府,栽赃小和尚借钱不还,捉拿进县衙施以重刑,已经奄奄一息了。听到这些,我一晚上都没有入眠,默念佛经,只祈求小和尚快快好起来。
小和尚终于回到卧佛寺,已经变成了老和尚,心如死灰,面如泥土一样难看。小和尚再也没有来院子里看我,但我知道他的苦衷。失木、遭打、又毁清誉,气得他六神离宫,三焦失衡,后来就一病不起了。每天小和尚的房间人来人往,每个人都面色难看,纷纷叹息,掩泪而泣。看到这些,我也非常害怕,担心小和尚离我而去。
小和尚还是离开了,我哭了很久,旁边的银杏每天安慰我,后来也哭了,我们成为了好朋友。苍天有眼,一切皆有定数,十八年后,小和尚再次转世,成了县令。他亲审此案,严惩奸商,追回佳木,小和尚陈冤得雪,并选能工雕塑卧佛,沉香为头,檀香作体,供于大殿。
看到卧佛寺名声大作,膜拜者络绎不绝,我心里高兴,感激小和尚的无私和大爱。
●春去秋来,几度黄昏,不知过了多少年,我和旁边的银杏话题多了起来。我们谈佛学,谈禅语,听风声,感悟四时变化,不再提起小和尚,怕彼此心里伤心。
“是日已过,命则随减。”我已经不再年轻,已经来到阿掖山卧佛寺多年,看惯了世间繁华,看惯了人情世故,看惯了悲欢离合。可佛主还是放心不下我,常常为我担心。他想考验我,而我则欣然接受。作为一株有灵性的银杏,不只是风景树,而应该经历人生劫难,就算站也应该站成永恒。
一棵平凡的树,也可以过得不平凡。我向佛主祈求,愿意接受他的考验,哪怕刀片火海我也愿意,但佛主还是心太软,太心疼我了,时时护着我。
一切注定,该来的劫难,谁也无法阻挡。元代初期,一个没有风的夜晚,天空没有一颗星星,卧佛寺庙惨遭遇百年不遇的大火。火从厨房开始,一点点蔓延,直到包围整个卧佛寺。刹那间,僧房毁于一旦,僧众纷纷死去,眼看就要烧到我的身前,火高达树米,我没有慌张,用心念起了佛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佛主慈悲,看到了一切苦难,天下起了大雨,大火被浇灭,佛主金身卧佛像还在。但卧佛寺还是有些破败了,后来在明代,清初,山贼纷纷涌入寺庙,破坏寺庙,我都险些被砍伐。还好在清朝时期,进行了大翻修,一切都变得好起来,我也变老了。
历经千年,历经数次劫难,能活下来,都是我佛的关怀。念过去,回不去,而后遥遥无期。看着高达二十九米的身躯,,而心已经疲惫,万事越来越力不从心,我旁边的银杏树也高二十八米,常常有人来合围,他倒是很乐观。
我应该知足,千年而幸存。看着自己挺拔的树干,枝繁叶茂,超然物外,亭亭云表,树冠覆盖整个寺院,傲然俯视卧佛寺,给人以古朴幽静之感,我是高兴。看到身上挂满了人们祈福的布条,飘扬的风中,我能感受到莫有的知足和心安。还有什么抱怨呢?还有人喜欢就好。
一切都是命。能成为佛前的银杏,要修炼多世才有这样的机会。我是幸运的,不快不慢,刚好赶上。本以为有一天我的落叶掉光,我就化为一片泥土,长卧卧佛寺,低吟着壮烈的悲哥离去,以报佛主的知遇之恩。没想到,却一直活到现在,见证世俗人生,欣赏花开花落。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我虽然已经衰老,但问心无愧于天下。我虽不愿迎合任何一个人,但我知道众生的疾苦。我知道我的责任,再弱小,也应该做出一份奉献。我给烦恼的人一片绿意,我给画家一片意境,我给作家一片诗意。我静静听着佛主教诲,叶儿为伴清风为友,哪怕被世人遗忘,我也无怨无悔。
●根植千年,看淡一切,现在的我只求一片宁静。喜欢看庙堂缥缈的云雾,喜欢僧客厢房里那一方独有的清净。
我天天诵经,时时念佛,我喜欢寺庙古旧的青瓦,我喜欢一只鸟停留的片刻。我喜欢看天南海北的人涌入卧佛寺,看他们膜拜,听他们虔诚,祈福,这也是一种幸福,更是缘分,需要珍惜。
虽然很多人都会忘记后院的我。可是,我不在意,我懂得人们的匆忙,总会有走近我得那一天。作为树,一尘不染的树,我有灵性的,我飘逸,我洒脱。晨钟暮鼓别人听着空渺,而我觉得他们就是乐音。氤氲香雾纵然迷离,而他梦让我内心清如溪水。无论我有多么渺小,无论我多么孤独,但我真的欢喜寺庙那一方清净,一缕清香。
我感激上天,感激佛主,让我来到阿掖山卧佛寺,并成为一棵千年老树。我享受“一花一天堂,一沙一世界”的时光,我陶醉烟雨,喜悟禅理,我向往空渺宁静的意境,向往来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一扫大地浊气,让我心间永远纯净。
佛前银杏,是对时错,我没有追问。更多的时候,是安心,没有机会漫步在斜阳的山径,踩着落叶踏步远方,可不后悔,既来之则安之,站立在天地间,守望阿掖山,贴近卧佛,我的精神,我的灵活将永恒。
路过一个街道,看到熟悉的风景,便会凝神许久,那无法拒绝的心动和会意,如春天枝桠上冒出的嫩绿,丝丝润着心,暖着眸。想起你,是一种花落书香的暖,沉浸在心仪的文字里,感知着生命的另一个春天,那种灵魂与字韵的融合,是一种无以言表的感动。你,如天空洁白的云朵,亦如心底深处的一轮明月,一丝清风过,便是风动梨花落的草香绵延。
行走在路上,生活里的磨砺很多,在一定时候,人需要这种孤独,只有孤独才会在自检中使自己残缺的灵魂得到丰盈。每个人用自己激情澎湃的心灵去解读生命,这种感情他们并不排斥,并且对此非常的享受和喜欢,乐在此中。
感恩入怀,一种平和的情愫在血液中缓缓流淌,云卷云舒,去留无意,花开花落,不再黯然神伤。如此境界,仿似置身于云水禅心之境,一念清幽,何惧风雨,细细品味时光的静好,不言山高水远,只念风过留香。
缘分与爱情相依并存。佛说,人生如梦,是因为人生存在不可知的未来。梦如人生,是因为有梦才存在生活的欲望。注定的相识,有时也如这春天花开的声音,给人带来清脆悦耳般的欢欣,其实,听一场花落,更是另一番意境。
更多 情感 、故事、精彩哲理 美文
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生活哲理 美文
这是台湾诗人散文家席幕荣的诗啊,她是蒙古王爷的后裔,后来在解放前随家人到台湾了。
这首诗是诗集《时光九篇》(大概是)中的一首,叫“一棵开花的树”。
一棵开花的树
如何让你遇见我
在我最美丽的时刻
为这
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
求佛让我们结一段尘缘
佛於是把我化做一棵树
长在你必经的路旁
阳光下
慎重地开满了花
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
你走近
请你细听
那颤抖的叶
是我等待的热情
而当你终於无视地走过
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
朋友啊
那不是花瓣
那是我凋零的心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