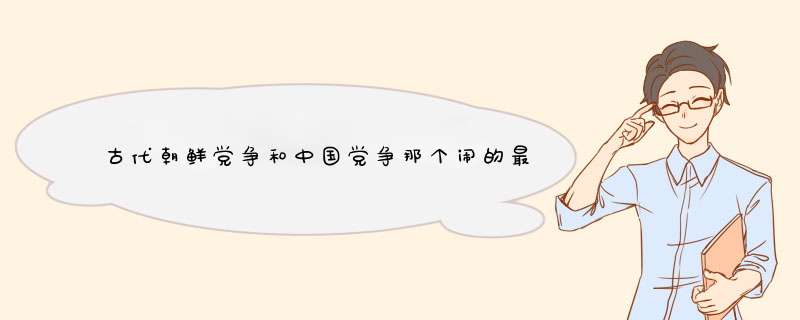
高丽国的皇帝不是太软弱了,而是因为他们的国家一直在实行的制度和中国魏晋南北朝类似属于世家政治,国内的主要官职被世家大族把持,而且后党外戚这个特殊团体始终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国王的废立这些大臣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君臣之间的关系属于三足鼎立。
毛泽东看到的世界,和溥仪看到的世界差别很大,前者代表着了穷苦阶级,后者则代表着权贵阶级。
但二人也有相同的地方,都做过国家的最高首脑,都要面对各部门的政务。
1962年,毛泽东举行家宴邀请溥仪,毛主席问对方:“你当皇帝的时候,怎么对待下面的大臣呢?”
溥仪面对这个问题,又该如何回答呢?他自认为是罪人,回忆当年的龙椅生涯,又会作何感想呢?
而本期文章要带来的内容,便是溥仪被特赦之后,在北京的生活。
关于此事的详细经过,要从1959年9月14日说起,毛泽东发文章谈特赦战犯,时间点选得是国庆十周年。
当时,国内政治环境空前稳定,而监狱里的一些战犯,确实已经改恶从善,例如血债累累的王耀武,已经从蒋介石的刽子手,蜕变为战犯所的学习委员。
再有就是,战犯所当中有一批死硬分子,始终不肯接受改造,倘若特赦一批人的话,便可分化类似于黄维那样的顽固派。
毛泽东的文章经广播传到各地,而在辽宁抚顺战犯所,大家坐在广播旁边,聚精会神地听着特赦,生怕错过任何一个字儿。
随着广播的声音落下,众人先是陷入沉思,紧接着便是雷鸣一般的掌声和呼喊。
一直喊得累了、嗓子哑了、欢呼才逐渐停下,这是高墙生活当中,听到的最好消息之一。
战犯所的众人,总算是看到了出去希望,相互讨论着会首先特赦谁……谁要是能提前出狱,可别忘了寄点东西回来。
而那些学习不积极的人,如今是满脸的懊悔,早知能特赦的话,肯定专心致志地改造。
有个大下巴的落后分子,红着眼睛闹事说:“如果放就全都放!”
当时五十四岁的溥仪,看到有人欢呼雀跃,也有人怒目争论,他自己则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不想跟大家唇枪舌战,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下场,极有可能是牢底坐穿。
溥仪认为,特赦肯定轮不到自己,可树欲静而风不止,他不想参加讨论,别人却在讨论他……
就拿那个大下巴的战犯来说,有骂他不可能会被特赦,他反击说:“ 除非剩下溥仪!如果不剩溥仪的话,就不会剩我! ”
言外之意则是,溥仪肯定不会被特赦,而他特赦的时间,会排到溥仪的前面。
这也能从侧面看出,抚顺战犯所的众人,认为溥仪的罪恶最大,即使被特赦也应该是最后离开高墙的人。
溥仪枕着众人的议论,睡了整整一夜,早晨醒来去打饭,突然接到通知,说是副所长要跟他谈话。
溥仪则转身去了战犯所的办公室,而那位副所长见了溥仪,则让他谈一谈对特赦的看法……
按照溥仪的描述,他在战犯所能学习到很多做人的道理;如果离开了战犯所,因为父母已经去世了,亲人也很难理解他,也就无法学到很多做人的道理。如果真获得了特赦,对于他来说,等于是获得了重新做人的资格。
以上这番话,说得非常委婉,即感激了战犯所的改造,也表达了想获得特赦的想法。由此可见溥仪经过退位、复辟、伪满、赴苏……等等经历之后,变得更加圆滑。
溥仪在战犯所呆了十年,按照他的总结来说,弄清了这世界的是是非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比那个被诅咒的旧 社会 ,强了不知多少。
他说自己前半生看不起人民,所以必然会走向毁灭,即使靠着军阀和日寇,获得一点点的地位,也必然会走向崩溃。
到了新时代,溥仪明白了哪一边是对的,就应该站到哪一边。
过了两个月,副所长再次找溥仪谈话,问题跟上次一模一样,让溥仪谈一谈特赦……
溥仪则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说战犯所谁谁表现得很好,言外之意无非是,他们应该获得特赦。
副所长笑了笑,话锋一转说:“ 如果特赦有你,你如何想呢? ”
溥仪笑着说:“不可能。”
谈话结束之后,溥仪回到自己的床铺上,脑子里想着的,全都是特赦的事情,内心开始幻想自己能否走出高墙,沐浴新时代的阳光,去某个单位任职,哪怕是去医院做助理。
总之,溥仪也想获得特赦,离开战犯所,去拥抱新的生活。
溥仪一整晚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想的都是特赦。天亮之后去集合,看到大厅里挂起了红色的横幅,写着: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
刹那间,溥仪内心很紧张,连呼吸都火辣辣的,他渴望获得人民的批准,希望走出战犯所重新做人。但他又想到,特赦大概率轮不到自己。
大厅里很安静,溥仪能听到大家心跳的声音,首长登台讲话,随后是最高法的负责人上台,宣读特赦名单。
最高法的同志,念出了一个长长的名字:爱新觉罗·溥仪!
刹那间,溥仪因为太激动,所以跳着就往台前去,而最高法的同志,则宣读了毛泽东的特赦令。
大致意思就是,溥仪被关押了十年,经过国家的审查,思想改造积极,参加劳动热情,符合党中央提出的战犯改恶从善之规定……
特赦令才念了大半,溥仪已经嚎啕大哭,心里想着的是,感谢祖国把他改造成了人。
溥仪离开战犯所,乘火车去北京,这是溥仪第一次跟老百姓坐在一起,如今他成了亿万群众当中的一份子,这正是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场景。
溥仪看到火车上,大家相互让座,天南地北的群众,相互亲切问候着。
溥仪之前还担心出狱之后没有亲人,如今彻底把心放在了肚子里,因为新 社会 的群众,落地都是兄弟。
溥仪自幼读圣贤书,二古代圣贤对美好 社会 的描述,历经千年之后总算成了现实,甚至比墨子和孟子描述得更加美好。
溥仪到了北京,一晃三十五年过去了,早已物是人非。
妹妹和妹夫去车站接人,见了溥仪的时候喊了一声大哥,溥仪听到亲人的声音,当场就哭了出来。
早晨起床,溥仪看到有人扫大街,心想着过去帮忙,却因为不熟悉路,扫到了别人家里。
本以为会被批评,却被热情邀请进屋喝茶,溥仪万万没想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能好到这种程度。
北京的清晨,带给溥仪巨大的震撼,人人争做光荣榜样,人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
再也不是旧 社会 麻木不仁的模样,不仅城市焕然一新,群众的精神状态比朝阳更加火热。
对比晚清来说,这里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按照冯玉祥的回忆,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达官显贵早就准备好八面旗帜。看到个子矮的来了,就举起膏药旗,说是大日本的“顺民”,看到个子高的来了,就说是大德国的顺民。
至于那些准备两三面旗子的,按照冯玉祥讽刺的说法,可能是凑不够八块布。
八国联军当中,数日本人最为残暴,老百姓被外国人肆意欺辱。尤其是年纪大的老人,会被强行拉走当做搬运工;而老人的儿子去救父母的时候,外国人便借机故意制造争端,殴打中国年轻人取乐。
再看今朝新时代,中国人在***的领导下,真正站了起来!
溥仪在北京越逛越兴奋,身边的妹妹和妹夫,累得是腰酸腿疼,连连喊着停下来休息休息。
可溥仪他本人却意犹未尽,因为新时代带给他的冲击太大了,当年 社会 的乱象好似噩梦,如今新时代蓬勃向上勃勃生机。
溥仪回想三十五年前离开北京的时候,处处都是破败的景象,如今城市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让他心情非常激动,所以就忘记了劳累,总想去更多的地方看看。
溥仪坐公交车的时候,看到大家都给老弱妇孺让座,他也赶紧为一位妇女让座,妇女连说不用,因为她是售票员。
溥仪见了功德林获特赦的一众国民党江铃,义务做了解说员,和大家一起游览名胜古迹。
以往破败的故宫,如今已经焕然一新,皇家子弟倒卖的文物、以及溥仪亲手倒卖的很多文物,又重新回到了这里,供群众参观。
溥仪被分配到植物园工作,他看附近的民兵训练热情,所以也主动报名参加,即使对方不肯收超龄民兵,他也要在工作之余,和大家一起训练。
民兵队长无奈,只能接受这个大龄民兵,队长跟大家想的一样,认为溥仪工作可能不行,可大家都想错了,溥仪对每一项工作都很认真,虽然事情往往办得不理想,但事事都用心。
在日常生活当中,年轻人围着溥仪叽叽喳喳问个不停,大家都很喜欢这位和蔼的“瘦老头”,性格幽默爱开玩笑,所以成了好朋友。
溥仪在跟大家相处的时候,从外表来看他是很开心的,甚至嘻嘻哈哈的,跟年轻人谈皇宫趣事。
但每当提起家人,溥仪眼角却暗藏着一抹伤感,按照他本人的说法,家人死得死离得离,所以生活倍感孤独。
1962年春节,溥仪接到通知,去中南海参加毛泽东的家宴。
说是宴会,菜式则非常简单,都是辣椒和苦瓜之类的小菜,喝的则是葡萄酒。
获邀的除了溥仪之外,还有多位政界和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大家相聚一堂。
毛泽东为了调节气氛,所以他在颐年堂见到了溥仪的时候,还幽默地开了个玩笑,把溥仪说成是当年的顶头上司。
众人落座之后,毛泽东为溥仪夹菜,毛主席说:“我们湖南人最喜欢吃辣椒,叫做‘没有辣椒不吃饭’,所以每个湖南人身上都有辣椒味。”
溥仪拿起筷子,夹起了碗碟里的辣椒炒苦瓜,一口吃下去的时候,出了满脸的汗,由此可见他日常喜欢清淡的食物。
在政治方面,毛泽东问起了溥仪写的自传(当 时尚 未公开发表),毛主席显然想得更多,如果末代皇帝的自传能在国内外广泛传播,会影响到诸多国民党高官,尤其是海外华人。
以往按照 历史 惯例,溥仪会被推出去砍头,甚至是五马分尸,又或者像李煜那样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
可旧 社会 已经被彻底打碎,新中国的宽大政策,给了溥仪重新融入集体的机会。
毛泽东希望海外的国民党高官,以及被西方媒体蛊惑的海外华人,能认识到真实的新中国,并加入到新中国的建设当中。
毛泽东看过溥仪写的自传,他认为溥仪写得过于拘谨,总是以罪人的角度落笔,总想着检讨曾经的罪恶,连他本人都看不下去,读一半都难,更何况是海外华人呢?
毛主席认为,这样并不能反映出真实的 历史 ,毕竟自传应该主要写人生经历,不能总想着认罪悔过。
溥仪听完了毛泽东的建议,他全都记在了心里。
聊完了溥仪的自传之后,毛泽东一边吃饭一边问:“你当皇帝的时候,怎么对待下面的大臣呢?”
溥仪回答说:“清朝时我太小了,由叔父载沣摄政,张勋复辟那年也还不懂事,往后到了伪满,实际还是傀儡……”
的确,溥仪登基的时候,还是个吃奶的孩子,甭说管理大臣了,他连朝中官员的名字都不会写,载沣则把持朝政,跟北洋袁世凯争权夺利。
溥仪十多岁那年,张勋辫子军开 历史 倒车,强行把溥仪推上龙椅,当时大事小事也都是张一手操办。
至于后面的伪满洲国,溥仪人虽然长大了,但犹如笼中鸟一般,听到的、看到的、乃至于吃到的……都要听日本人的安排,更别提管理官吏了。
纵观晚清、复辟、以及“伪满”三大时期,溥仪犹如是一片枯叶,被 历史 的浪涛推来推去,很少有真正管理官吏的机会。
溥仪直到被关押在抚顺战犯所,才彻底认清日寇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恶,他在回忆录当中,对此有过长篇的描述。
而毛泽东听完了溥仪的一番话,目光扫过饭桌的众人,笑着对溥仪说:“今天在座的几位中,还是数你最年轻哟!”
毛泽东谈起溥仪的生活,得知这位前朝皇帝早已经离婚,于是鼓励对方再次组建家庭。
溥仪经历过失败的婚姻, 历史 的包袱太重了,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获得了毛泽东的支持之后,他再次打开了心扉,去追寻自己的爱情。
溥仪的意中人,是一位明教李淑贤的姑娘,在医院里做护士工作。他为了获得李的好感,所以每天都精心打扮一番。
据李淑贤的回忆,溥仪对她的爱,是发自内心的,是真挚又热情的。
俩人一起游览了北京的名胜古迹,聊了很多的悄悄话,溥仪敞开心扉向李淑贤,而李淑贤经过慎重的考虑,接受了末代皇帝的这份爱。
在五一劳动节的前一天,溥仪以一位劳动者的身份,跟护士李淑贤举行了婚礼,正式走到了一起。
婚礼发言的时候,溥仪以劳动者的身份宣布,他跟李淑贤成立了幸福的小家庭,成为大家庭的一份子。
根据溥仪回忆录的描述,1962年多喜临门,获得了体面的职位,成立了一个真正的家庭,人生翻开了新的篇章。
他说:“我永远不能忘记我的新生是怎样得到的。”
两年后,溥仪的自传出版发行,也就是那本著名的《我的前半生》一书,很快就轰动国际,成了那年的畅销书。
举例来说,末代“代总统”李宗仁,在美国看了溥仪的自传,也萌生了回国的想法,年纪大了总想着落叶归根。
李宗仁回国带来的轰动,比溥仪的自传更大,而他回国的原因有很多,例如妻子重病、中国掌握核武器、想念国民党老朋友……而溥仪的自传,同样是原因之一。
海外的国民党高官,从溥仪的自传当中,看到了新中国的宽大政策。
当末代“代总统”李宗仁,回国见到了末代皇帝溥仪,谈起了《我的前半生》那本书,他说:“你的大作,对我启发很大。”
溥仪毕竟做过皇帝,虽然在北京任职的时候,能拿到一百多块钱工资,但朋友实在是太多了,再加上他本人不善理财,所以生活颇为拮据。
毛泽东得知此事,于是把自己的稿费,分出了一部分给溥仪,免得前朝皇帝饿肚子,传出去让人笑话。
溥仪后来进入政协任职,他对工作很认真,对家庭倾尽真心,最喜欢参观红色老区,虽然说他改不了粗心的性格,但也绝没有**里演绎的那样“夸张”。
1967年9月底,溥仪身患重病,跟妻子李淑贤最后一次长谈,他回顾自己的这一生,犯过太多的错误,身为封建王朝的统治者,能获得国家的改造,归宿还是很好的。
溥仪有感于时日无多,没能为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所以对人民有愧;没能为家庭做出更多的贡献,所以对妻子李淑贤有愧。
10月17日凌晨,溥仪因病医治无效,在医院永远闭上了双眼,带着对妻子的不舍,离开了人间。
时间一晃,到1995年,河北省易县的“华龙皇家陵园”的开发商找到李淑贤,希望把溥仪的骨灰能移到易县这边的陵园,并且会专门为李淑贤和谭玉玲修建墓地。
李淑贤答应了那个开发商,于是去北京的八宝山迁出溥仪骨灰,移葬到了易县。
可让人感到失望的是,两年后李淑贤去世,骨灰却葬到了别处,另外谭玉玲也没有葬到易县。
以至于溥仪的墓碑,孤零零竖在易县的墓地,没能跟妻子黄泉相伴……
他这一生是孤独的,也是充满波折的,在不同的年纪遇上袁世凯、孙中山、冯玉祥、日本人、斯大林……事事小心谨慎,能体面的活着,就已经是最大的幸运。
“穷不与富斗富不与官斗”,这句话在清朝乾隆年间,还要加上五个字:“汉不与满斗”。所谓《官场斗》(又名《满汉斗》)只是评书或单口相声而已,借给刘墉几个胆子,也不敢跟和珅斗,他见了和珅就得下跪磕头,那倒是真的。
在和珅眼里,他需要忌惮的公爵以下满汉文武大臣只有三个,这其中当然不包括刘墉和纪晓岚。事实上按照正史记载,和珅根本就不在刘墉和纪晓岚,甚至还有点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在乾隆朝,刘墉最大的官职是工部尚书署理直隶总督、协办大学士,直到嘉靖二年,在被任命为体仁阁大学士。刘墉一生没当过军机大臣,按照雍正以后“大学士不入军机不为真宰相”的惯例,刘墉就是驼背称呼啦圈,也没资格被称为“宰相刘罗锅”。
纪晓岚名气虽然大,但是很遗憾,他连假宰相都不是,因为他一辈子也没当过正牌大学士,直到嘉靖十年,纪晓岚才在临终前被授予协办大学士称号,一天“中堂”都没当过。
清朝大学士被称为“中堂”,那是有典故的:清朝实行皇帝直管下的六部制,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一部有一满一汉两位尚书。满尚书地位高能力差,汉尚书地位低本事强,此消彼长就成了平起平坐。两个尚书经常闹别扭甚至在部里吵架打架,弄得手下一帮郎中、员外郎无所适从。
为了给各部满汉尚书拉架,皇帝让大学士每人监管一个部,召开部务会议的时候,大学士居中而坐,满汉尚书一左一右,隔着大学士就掐不起来了。大学士因为居中而坐,所以被称为“中堂”。
清朝的大学士,同一时间最多只有六个(中和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乾隆年间撤中和殿大学士而新增体仁阁大学士,形成了三殿三阁制),最少的时候只有一两个,给满汉尚书拉架的工作,由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承担,比如胤禛胤祥都曾管过某一部。
和珅不但是一人监管数部的文华殿大学士(从乾隆五十一年到嘉庆四年),而且在乾隆四十八年受封一等男爵,五十三年晋升三等忠襄伯,嘉庆三年,和珅晋封一等忠襄公。
虽然位极人臣,但是和珅在朝堂上也有惹不起的人物,比如和硕和亲王弘昼、固山贝子福康安。
弘昼和福康安跟乾隆都是实在亲戚,弘昼是乾隆最疼爱的弟弟,福康安是乾隆最亲近的小辈(疑似比侄子还亲),和珅还没上班,弘昼就没了(乾隆三十五年薨,三十七年和珅入宫当侍卫),不管和珅是几等公爵,见了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都是要下跪磕头的。
清朝的皇室之外有九级爵位,分别是超一品公、侯、伯,正一品子、正二品男、三品轻车都尉、四品骑都尉、五品云骑尉、七品恩骑尉,和珅一上班就是三品官(世袭三等轻车都尉),刘墉的父亲刘统勋虽然很受乾隆器重,但是却连个男爵都不是,刘墉自然也就没有恩荫世袭的爵位,也就是一个白丁,唯一能享受的待遇,就是不用参加乡试,可直接以“恩荫举人”的身份参加会试。
刘墉尚且如此,纪晓岚就更不用说了,他的前辈连个当道台的都没有,所以虽然考试成绩跟刘墉差不多(刘墉二甲第二,纪晓岚二甲第四),但是升迁却比刘墉慢得多。
在乾隆执政期间,刘墉和纪晓岚都不敢跟和珅发生正面冲突,一个是地位相差悬殊,再一个就是乾隆跟谁关系好,满朝文武都知道,聪明甚至有些圆滑的刘墉纪晓岚才不会没事找事儿去触霉头。
和珅也很聪明,他早早受封超品伯爵,最后还得到了异姓大臣的最高爵位(不算福康安,因为福康安算不算异姓大臣只有乾隆等少数人知道),但是他绝不与真正的八旗贵胄叫板,所谓和珅训斥王子贝勒,那都是小说家言,和珅奉承还来不及呢。
无人问津
wú rén wèn jīn
[释义] 津:渡口。没有人来问渡口。比喻无人过问。
[语出] 晋·陶渊明《桃花源记》:“南阳刘子骥;高尚人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正音] 津;不能读作“jūn”。
[辨形] 津;不能写作“今”。
[近义] 置之不理
[反义] 门庭若市
[用法] 用来形容受冷落;没有人再来尝试或过问某件事、某种东西。一般作宾语。
[结构] 兼语式。
[例句]
①那些书皮五光十色的侠怪小说;渐渐变得~。
②这座山太险峻;据说从来~。
在“江陵取爱”的超公事件中,又有一个年轻人在法庭上被打。此人如飞蛾扑火,铁了心要得罪丞相和皇上。他叫邹元标,名叫二站,是江西吉水人。
这个人从小就是神童。《明史》说自己“九岁,知道《五经》”。而他也没有成为一个年轻、聪明、平庸的人。他在去考试的路上一路绿灯。万历五年,22岁高中进士。在“五十少进士”的科嘉时代,这个年龄年轻得让人眼红。这真是一个繁荣的马蹄病。
这一年,朝臣们争论张的父亲死后是否应该回家,邹纲“放了布朗”。一般的考试都是在春天举行,叫做“春蔚”,而张的父亲就死在那年秋天。这时,邹元标是“刑部关正司”,也就是说,他还是一个掌管事务的秀才。用现在的话说,他是一个刚分配到国家机关的实习生,还没有定级转正。
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官方新人,按照一般的想法,一定是在享受热闹。还轮不到你来挑战国家大事。但邹金石是个有强烈使命感和道德感的年轻人。说他是那个时代的愤青也不为过。
这个初生牛犊不怕虎,写了一封非常有力的弹劾张的奏章,指出了“夺情”的悖论。写完了,我准备去法院交上去。刚刚遇到吴中行等人被法院打了。——当着所有朝廷官员的面敲打朝廷,就是为了杀鸡给猴看。眼见首辅上疏弹劾终结,一般人都会知难而退,而邹元标却激起了更多的斗志。吴中行被朝廷打完,就拿出奏疏,委托太监转发。他怕人家知道是骂张不敢送上来,谎称是请假条,塞钱给太监。这样,皇位只有在天上才能听到。
与吴中行、赵用贤、艾木和沈思孝相比,年轻而充满活力的邹元标说话毫不避讳。他说张是“有才华的,但学术。”虽然一个人的野心太大,不能为己所用,甚至有几句话戳中了人心。他抓住了圣旨中的一句话,皇帝要求官邸保留官制。皇帝说,保留张的原因是:“我还没有完成学业,我的志向还没有确定。老师一走,我之前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邹元标反问道,幸好张担心他父亲的死,他才能留下来。如果他不幸死于任上,陛下的学识最终会不会失败,他的志向最终会不会不确定?并进一步发挥张说的建议,“世上有不平凡的人,再做不平凡的事。”如果他不屑于把为父亲奔丧当成一件平常的事,他不知道一个人只能遵从节操的方式,然后叫人。现在有这样一个人,他活着的时候父亲不回家照顾他,他死了父亲也不回家参加他的葬礼。他还告诉世人,他是一个不平凡的人,世人要么认为他是疯子,要么认为他是猪一样的畜生。这是一个非凡的人吗?
不管谁对谁错,都像是人身攻击。皇帝和张看到这种疏,都义愤填膺,远远超过他们对前四疏人的痛恨。照例是朝廷官员,远戍,打得比吴中行四人还狠。
一个在朝廷没有多少人脉的见习生,被勒令挨打,没人敢求饶。惩罚他的圣旨,就像今天的白话一样浅显易懂:“邹元标是个狂躁可恨的家伙,只是他以前没有看到圣旨里的大讨论,所以只是照着艾穆的样子做。以后他再疯,就要遵守祖先法度的重典。"
我想是因为皇帝和张故意给一个台阶下,或者是因为他们觉得不妥而没有杀他。但是原谅活着的罪行是很难的。这个无知的学员比前几个受伤最深。后来有人记录了邹元标幕僚的详细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宫廷幕僚,其中的学问太大了。在法庭殴打过程中,邹元标两股分开,左脚放在右大腿下,所以受伤面积比两条大腿并拢的面积大很多。在法庭殴打完毕,将奄奄一息的邹元标抬出后,有人剥下一块黑羊皮,用药物包好,裹在他的屁股上,让这块肉再生。毕竟年轻,充满活力。从那时起,邹元标就被禁用了。阴天的时候,他的腿肯定疼,走不顺畅。
因为明朝的官员经常被打官司,所以他们探索出了这样一种急救打官司的方法:当他们受重伤时,狱吏迅速剥下一块羊皮,盖在伤者的屁股上。受伤后,上面有一个印记,叫“羊毛皮”。据莱文考证,经常有尴尬搞笑的事情。那时候县令的权威很重,老百姓闯了他的道,可以当街打屁股。可是有时候,你看你的裤子,如果是“羊毛皮”,就不敢随便打板子了。这样的人说不定哪天又被利用了,官位肯定比县长还大,还会报复。所以县长遇到“羊毛皮”就特别警惕。
邹元标驻军贵州都匀卫——。如今,贵州南部的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已经够偏远了。这样的人对张的仇恨一定是刻骨铭心的。
张死后被清算,反国家之一的当然受到重用。不久他惹怒了皇帝,皇帝让他回家呆三十年。在此期间,他作为林东人民的领袖之一而闻名于世。万历皇帝死后,才当了一个月皇帝的太常皇帝也随他而去。木匠皇帝天启即位,他被召回,官至年左都帝国最高监察官。此时,邹元标这个当年的愤青,面对林东人和其他派系,正在争夺道德制高点,互相批判。他提倡“和谐”。他说,现在当权的人不是选择人才和能力,而是赶走人才,说三道四的官员也不能心平气和,而是另立门户。所以,最重要的是朝臣齐心协力。他在《尚书》中说,“与人谈世界的人,都是偏颇的,执着于生活,执着于生命,委身于我。谁也不认识谁了,灾难移向了国家。”
所以有人觉得奇怪,说他刚做官的时候,爱恨情仇那么清楚,不欺软怕硬。为什么他老了还得过且过?他认为自己已经失去了年轻时的正直。邹元标笑道:大臣不同于官员。官员的职责是减少风。作为大臣,如果不是原则问题,就要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国家制度。怎么能像少年一样冲动急躁?
万帝废了张的官爵和谥号。到了熙宗时,大明已经千疮百孔,百病缠身。这才让大家感受到张这个不平凡的人的难得。在的再三恳求下,皇帝下令为张平反,恢复他的名字,并把被剥夺的官爵谥号还给了张家。
因迁怒于张而差点丧命的愤青到了官邸,已是年近古稀。在即将走上漫漫人生路的时候,他已经完全理解了张当年的记录,这也许是一个愤青走向成熟的必然。可惜,这种认识晚了四十年。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