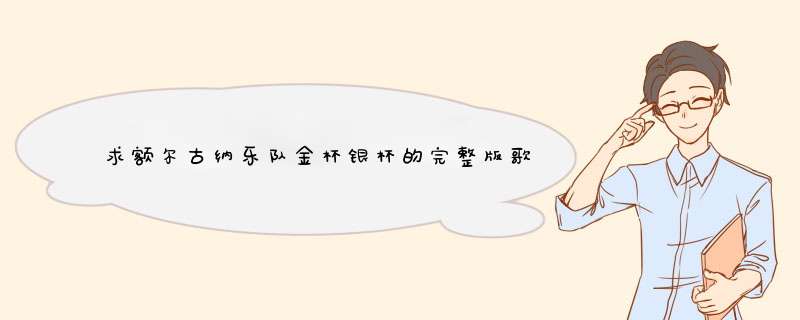
额尔古纳乐队歌曲大全在线听免费,百度网盘下载资源:
4k16
简介: 额尔古纳乐队由那日苏、玛希巴图、包玉民和王猛于2001年7月组成,组合经历了两次人事变动,2009年,乐队推出全新EP《信念》,犹如凤凰涅槃,重新出发。
额尔古纳乐队歌曲大全在线听免费,百度网盘下载资源:
4k16
简介: 额尔古纳乐队由那日苏、玛希巴图、包玉民和王猛于2001年7月组成,组合经历了两次人事变动,2009年,乐队推出全新EP《信念》,犹如凤凰涅槃,重新出发。
这是一个90岁的鄂温克女人的自述,她近百年的人生经历,折射出鄂温克族近百年的发展历程。这个民族在森林中生活,信奉萨满,因驯鹿觅食而搬迁、游猎。他们在自然的恩惠与折磨下生存,他们遭遇了日侵,他们经历了,最后,在所谓先进文明的“侵袭”下,他们不得不在游牧与定居之间游荡。不过,这是一部女人的书,似乎应该荡气回肠的历史,在迟子建的笔下,在“我”的口中,是一个个普通人的生活,自然、生动、诗意、悲情……
人与自然
故事由“我”的诞生开始,“我”出生在寒冬,有一个姐姐也出生在严冬,但因狂风掀了母亲生产用的希楞柱,姐姐受了风寒,出生两天后就死了。自然赋予鄂温克人一切,也会不时残酷地收回它的恩惠,“我”的父亲林克死于雷电,姐姐列娜、第一任丈夫拉吉达在风雪中永远地睡眠,第二任丈夫瓦罗加被熊揭开了脑壳。
即使自然很无情,但鄂温克人并不愿意离开森林。可是现代文明在“侵袭”,伐木工进驻森林,铁路公路伸进深山,动物四处逃散。鄂温克人下山定居,依旧的游牧生活又将他们带回森林,定居点激流乡最终成为一座空城。只是人心开始浮躁,有的年轻人甚至走上歧途,如孙子沙合力因盗伐天然林被判刑三年;外孙女索玛不停地与不同的男人幽会,然后不停地流产,无法出嫁。为了孩子们,女儿达吉亚娜筹建了新的定居点布苏,可是“我”觉得他们终有一天还是会回到山林里。
人与人
在人与自然的大主题下,人与人的故事是这本书最吸引人的地方。里面有数段美丽的爱情。如母亲达玛拉,在年轻时与兄弟俩相遇,兄弟俩都爱上了这个美丽的姑娘,就以射箭一决胜负,最终林克成了达玛拉的丈夫,而伯父尼都萨满孤独终生。在林克去世后,尼都萨满再次追求达玛拉,可是弟媳不能嫁哥哥这一族规,扼杀了两人的爱情,也让两人的生命日渐枯萎。
而姑姑依芙琳的爱情则是一场悲剧。她嫁给了不爱她的坤德,怨恨充斥其一生,她甚至讨厌自己的儿子金得,认为金得如坤德般懦弱。她为儿子安排了一场婚事,金得反抗不得,上吊自杀了。坤德令依芙琳再次怀孕,可是依芙琳千方百计地让自己流产了。
人与神
鄂温克人信奉萨满。在小说中,萨满确实具有神力,能呼风唤雨,救人性命。可是萨满也为身上的神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妮浩继承了尼都萨满的衣钵,可是妮浩每救一个人,就要失去自己一个孩子。但是身为萨满,她的职责就是救命,即使是有罪的“马粪包”和偷吃驯鹿的少年,她也要穿上神衣,跳神救之。最后,妮浩为祈雨救火而死。
茅盾文学奖如此评价此书:这部“家族式”的作品可以看作是作者与鄂温克族人的坦诚对话,在对话中她表达了对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坚持信仰、爱憎分明等等被现代性所遮蔽的人类理想精神的彰扬。
另一段:
刊登在2005年第六期《收获》上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是生活在黑龙江省的女作家迟子建的新作。小说通过一位九旬老人、鄂温克最后一位酋长的女人的独有经历,向我们传递和叙述了一个家族乃至一个民族的悠久历史和人脉传承。额尔古纳河的左岸曾是这个民族的故乡,额尔古纳河的右岸,更是积淀着无穷的森林宝藏以及深厚绵长的民族文化和情感。那种神奇、神秘的力量,那份清澈、深沉的挚爱,似一曲古老的民族赞,又似一曲哀伤的历史晚唱,不由地令人想起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幅少数民族的苍凉历史画卷,更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优秀现实作品。
上部 清晨
我有九十岁了。我们这个乌力楞只剩下我和安草儿了,他们都离开大山去那个叫布苏的地方定居了。听着刷刷的雨声,看着跳动的火光,我特别想跟谁说说话。
我是个鄂温克女人,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我出生在冬天,父亲林克,母亲达玛拉,除了死于风寒的姐姐,我还有一个姐姐列娜,一个弟弟鲁尼。父亲非常清瘦,是个爱说爱笑又爱枪的人,他能用连珠枪捕获到森林中最大的动物堪达罕。我伯父尼都,是我们乌力楞的族长,他还担任着萨满,也就是巫师或者部落和氏族的精神领袖。尼都萨满和父亲一点也不像亲兄弟,很胖,不喜欢人们说笑或谈论女人,据说他只在我出生那天,因前夜梦见一只白鹿而对我的降生无比欣喜,喝了很多酒,还跳舞跳到火塘里去了。我爱去他的屋子,那里不光住人,还住着神,被称为“玛鲁”的神,统统装在一只圆形皮口袋里,大人们出猎前,常常要在神像前磕头,这使我好奇。
听依芙琳姑姑说,额尔古纳河的左岸是我们的故乡,三百多年前,俄军侵入,挑起战火。这使我对铁匠伊万的蓝眼睛妻子娜杰什卡曾充满敌意。伊万是我伯祖父的儿子,娜杰什卡则是俄商从左岸带到右岸金矿当的,是伊万凭着一双打铁的大手,把她从俄商那里带了出来。
我第一次看见父亲和尼都萨满发生冲突,正是那年打灰鼠的最好季节。尼都萨满说这一带灰鼠少了要搬迁,父亲不同意,因为母亲生下的女孩没有存活且因失血过多不能再受风寒。尼都萨满冷笑着说,你不让她生孩子就不会失去孩子,气急败坏的父亲揍了尼都萨满。我第一次听到母亲责备父亲自私。那次迁移途中,姐姐列娜骑在鹿上瞌睡而倒下冻死。商人罗林斯基带来了一面小圆镜,这是他带给列娜的礼物!我摘下它,珍藏至今。那年冬天,父母亲很伤心,直到春天,我身体里往外流血,母亲脸上才有了红润和笑影,她抱着我对父亲说,我们的小乌娜吉长大了。
那年,瘟疫持续了两个多月,雨季来的时候,父亲林克为了赶在秋末驯鹿交配前换回驯鹿,在经过一片松林时被雷电击中而亡。父亲带走了母亲的笑声,尼都萨满却好像变了一个人,他爱说话了。他将吃山鸡时拔下的羽毛缝成了一条裙子。母亲穿着显得无比端庄和高贵,可我咬着牙冷冷地说,像只大山鸡,依芙琳也故意地在人多的时候提起林克,母亲哭了,每逢雨天总是跑到林子中寻找什么,等她打着寒战回来的时候,尼都萨满就会唱起来,那声太哀愁了。
日本人来了,那一年蓝眼睛的娜杰什卡带着儿子吉兰特和女儿娜拉逃回了额尔古纳河左岸,把孤单的伊万推进深渊;还有我嫁人了。
中部 正午
正午了,雨还在下,安草儿往火塘里添了几块木柴。如果说我是一棵经历了风雨却仍然没有倒下的老树,那我的儿孙们就是我树上的枝桠……。
我和拉吉达结婚了,我在追寻娜杰什卡迷路时遇到拉吉达的,他长得和我父亲相像,母亲很喜欢他,母亲送我的新婚礼物是一团火,那是她和父亲结合时外公送的,母亲一直没让火熄灭。那个瞬间我抱着母亲哭了,觉得她那么可怜和孤单。我生儿子维克特时,依芙琳给我讲了父亲、尼都萨满与母亲之间的故事。原来兄弟俩同时喜欢上爱笑爱跳舞的达玛拉,爷爷只好让兄弟俩连着比武,最后一刻林克赢了。从此尼都萨满行为怪异。我想,尼都萨满在最后时刻也许是不心看林克失望的目光才放弃的吧?
维克特三岁的时候,弟弟鲁尼娶了妮浩,母亲在欢庆婚礼的篝火灰烬旁,穿着那条羽毛裙子,跳着舞永远地走了。尼都萨满为母亲主持葬礼的时候唱了一支送葬,“滔滔的血河啊,请你架起桥吧,……”声中,让我看到了尼都萨满对母亲深深的爱。
我又有了儿子安道儿。尼都萨满衰老了,他为了保全乌力楞,用最后的舞蹈治愈了日本军官吉田的腿伤,和达玛拉一样的走了。
拉吉达做了新的族长。这期间,日本人成立了“关东栖林训练营”,凡十四岁以上的山上猎民都必须接受训练。那晚驯鹿未归,营地的女人们跪在玛鲁神面前,祈求神保佑驯鹿。拉吉达他们从训练营获准回来骑马去找驯鹿,回来时已冻死在马背上。我看到僵硬的拉吉达时昏了过去,醒来时,我的肚子已经空了,早产的死婴是个女婴。
后来,我们推选了伊万做新的族长,当伊万从日本人的东大营逃走以后,我们又选了鲁尼做族长。春天的时候,妮浩生下一个男孩,鲁尼给他取名果格力。
三十一年,我们乌力楞出了两件大事,一个是妮浩做了萨满,妮浩披挂着的是尼都萨满留下的神衣;另一个是依芙琳强行为儿子金得定下婚期,一直喜欢妮浩的金得便在婚礼后吊死在树上,妮浩萨满在同一天为同一个人既婚礼又葬礼。
这年秋天,我用伊万打铁场艳丽细腻的泥土当颜料,开始在岩石上画画,额尔古纳河右岸已经风化的岩石,呈现出一片血色岩画;这年秋天,妮浩生下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儿,取名交库托坎,是百合花的意思。
维克特长大了,他跟着鲁尼学会了射箭。安道儿也长高了,能和果格力一起玩耍了。这年夏天,山上“黄病”流行,日本人取消东大营的训练,不让猎民下山了,我丈夫的家人仅他十三岁的弟弟拉吉米手里握着父亲遗留的口弦琴木库莲活了下来。我把他接了过来。这年冬天,妮浩帮助别人除病,自己的儿子果格力则从树上摔下死了。几年后,她为救别人使得女儿交库托坎也撞上马蜂窝而死。妮浩唱起神,我问为什么?妮浩说,天要那个人去,我把他留了下来,自己的孩子就要顶替他去那里。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了,我在寻找拉吉米的贝尔茨河畔遇见了瓦罗加,他是一个氏族的酋长,小时候学过汉语。当他带着拉吉米出现在我前面,向我求婚的时候,我幸福地晕厥过去了。那时候,妮浩又生下一个儿子,取名耶尔尼斯涅,也就是黑桦树的意思。在我的婚礼上,伊万回来了。
下部 黄昏
希楞柱里黯淡了,雨停了,安草儿一手提着水桶,一手握着一束紫菊花进来,我把花插在桦皮花瓶里……。
我和瓦罗加完美地融合在一起,1946年的秋天生下女儿达吉亚娜,瓦罗加非常喜欢她,常坐在火塘边给她念诗。那时候伊万已穿上军装,他告诉我们,开始对逃窜到山里的土匪大清剿。依芙琳叹气以后没有铁匠了,依芙琳的话让我想起保存下来的画笔,我在贝尔茨河一条支流旁的白色岩石上,画了一面印有火样纹的神鼓和七只驯鹿仔,这是我和岩石之间的一个秘密。
1950年成立了供销合作社。拉吉米在供销社边上的客栈马厩里拣回一个可爱的女孩,瓦罗加给她起名叫马伊堪,伊堪是"圆舞"和"篝火舞"的意思,拉吉米当她宝贝,说长大了也不给别人当媳妇。1955年,妮浩懂事的儿子耶尔尼斯涅十岁了,他被瓦罗加讲的天鹅故事感动,说要是我的额尼遇险,我也愿像那只丑天鹅一样,替她去死。后来,黑桦树一样挺拔的耶尔尼斯涅真的替母亲妮浩挡住灾难而被河水卷走。
儿子维克特和柳莎结婚了,安道儿也快到结婚年龄了,看着英姿勃勃的两个儿子,我蓦然明白,在我的生命之灯中,还残存着前夫拉吉达留下的灯油,瓦罗加虽然为我注入了新的灯油,但他点燃的其实是一盏灯油半残的旧灯。
1959年,为我们盖起了几栋木刻楞,几个氏族的人开始不定期地在那里居住。变得衰老的伊万回到地方上,他对瓦罗加说,山林以后怕不会安宁了,林业工人要进山伐木,铁道兵也要修建铁路了。瓦罗加建议把达吉亚娜送到学堂上学,说有了知识,才会看到世界的光明。可我觉得光明就在河流旁的岩石画上。
山外饥荒有所缓解,我们度过了相对平静的两年时光。19年夏天,妮浩又生下一个男孩,方脸宽额,哭声响亮,鲁尼给孩子起名马克辛姆,很多年后妮浩去世,马克辛姆举止怪异,我们知道他也要成为萨满了。
死亡的阴云再次凝聚到我们乌力楞的上空。我的小儿子安道儿走了,他鹿哨吹得太好,又穿着野鹿皮缝制的衣服,哥哥维克特一枪打过去,难以置信地打在安道儿的脑壳上。
派人来动员我们去激流乡定居。有人来请瓦罗加作激流乡的乡长,瓦罗加指着我说,她不下山,我这个酋长就得陪着。那年冬天,大兴安林大规模,森林中的灰鼠减少了,逃到额尔古纳河的左岸去了。瓦罗加一天天老了,我们再也没有风声的了。
达吉亚娜婚后生下女儿依莲娜。没想到我与孙女的第一次见面竟在伊万的葬礼上,伊万当年因为一本军事地图被当作苏修特务而受尽折磨,伊万临死前对维克特说,把我土葬,头朝额尔古纳河的方向。
1974年,瓦罗加在送放映队回林场的路上遭遇黑熊,为了保护放映员,最后一位酋长也走了。两年后,因误伤了弟弟安道儿再也没振作起来的维克特,也酗酒过度死亡。
依莲娜看见我的岩画惊叹石头也可以画画。进入八十年代,三十岁的马伊堪有了私生子,可在孩子断奶后却跳崖死了。原因据说是不管谁向漂亮的马伊堪求婚,领养她的拉吉米都一口回绝,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悲剧。为此,拉吉米哭瞎了双眼。
山中的林场和伐木工人越来越多,动物越来越少。时间过得飞快。依莲娜从美术学院毕业,她结婚又离婚;除了画画外喜欢和驯鹿呆在一起,时间长了又嫌山里寂寞。1998年初春,两个林业工人吸烟乱扔烟头引起山中大火,妮浩最后一次披挂上神衣,唱完了她生命中最后一支神后倒在了雨水中。"额尔古纳河啊,你流到银河去吧,干旱的人间"
依莲娜看着妮浩祈雨的情景,说一定要把那激荡人心的瞬间画下来,她画着画着就哭出声来,直到进入新世纪的那年春天,才完成自己的画卷。那个晚上,依莲娜喝了酒走出家门,第二天人们在贝尔茨河下游看见她的尸体。我在依莲娜上岸的地方找到一块白色岩石,为她画了一盏灯,希望她在没有月亮的黑夜漂游时,找到方向。我知道,那是我一生画的最后一幅岩画了。我的泪水沁在岩石上,就好像为它注入了灯油。
尾声 半个月亮
天黑了,故事快讲完了,我真担心他们所去的布苏又会成为一座歇脚的客站。……月亮升起来了,是半轮,它莹白如玉,像喝水的小鹿。月亮下面,是通往山外的路,我落泪了,因为我分不请天上人间了。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描述我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的长篇小说。它以一位年近九旬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夫人的自述,展开了这个民族近百年的顽强坚守和文化变迁过程。
它让很多人知道了东北地区有鄂温克这个民族,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鄂温克族人口数为30875人。鄂温克人与驯鹿为伍,死后会举行风葬,他们对于火是十分敬畏的不能往火里吐口水,不能往火里扔不干净的东西。
“达西离开后,玛利亚突然病了,她吃什么都吐,虚弱得起不来了。所有人都认为玛利亚活不长了,只有伊芙琳,她说玛利亚以后不会在给驯鹿锯茸的时候见着鲜血流泪了。谁都明白,伊芙琳认为玛利亚怀孕了。”
“春天快到的时候,她的肚子大了,脸也变得圆润了,看来伊芙琳的判断是对的,从此她和哈谢的脸上就总是挂着笑容。”
——节选自《额尔古纳河右岸》
繁衍生息,有人出生就有人去世。小姨2006年生下大女儿彤彤后,此后一直没法怀孕。红霞阿姨说过小姨去过江西、贵阳等多地求医。大概是2018年的1月,爷爷是突然去世的。当年年底11月小姨就生下了第二胎是个男孩。那一年她已经38岁了,可以预见小姨妈是在爷爷去世后怀孕的,命运这个东西有时候是很奇妙的。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鄂温克人信奉萨满教,他们敬畏自然与恶劣环境搏斗。鄂温克人意外的死亡率很高,醉死、雷劈死、熊抓死、水淹死。少数民族往往是有信仰的,他们有自己的民规法约。我们对于未知事物要保持敬畏之心。
浅谈一下这部作品的启示。
十多年前在苗岭市读初中,就问班上的同学:“你知道苗族是谁的后代吗?”
“蚩尤。”
没错,苗族是蚩尤的后代。
那个时候读书一个班七成以上都是苗族,汉族在苗岭才是“少数民族”。截止2016年苗岭市的常住人口是5431万人,有苗、汉、侗、仫佬、畲、布依、水、彝、壮、瑶、满、回、蒙古、景颇、佤、黎、东乡、纳西、仡佬、京、朝鲜、土家、白、傣、藏、拉祜、维吾尔等民族和革家、西家等待定民族。这些民族中,仫佬族、苗族、汉族、畲族及革家、西家是世居民族。少数民族人口为360686人,占全市总人口的7536%,其中苗族人口2835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633%。
黔东南州的一些景点借助短视频,肇兴侗寨、西江千户苗寨、镇远古城等景观其实已经让更多人熟知了。有时候人是很矛盾的,既希望家乡的一些好的东西能够为人所知,但不希望商业化太严重,以至于回来变得陌生。
芒果台的《爸爸去哪儿》的第三季的第九期节目,选在湖南绥宁大园苗寨拍摄。若论规模肯定是西江千户苗寨比它大,但是大园苗寨是湖南的呀。《江山如此多娇》的主要取景地是张家界永定区,成龙的《绝地逃亡》在在广西程阳平定村取景。
文学作品、影视剧去表现少数民族特色跟现实相比其实是有差距的,现实中的少数民族说的是他们自己民族语言。首先来说他们的普通话没那么好,脸也没那么白白净净。
一群人来一个苗寨,穿少数民族服装、拍摄取景、学习银饰制作、做酸汤、腌鱼。找一些演员来演绎,难道你就把人刻画出来了吗?摄制组最多就呆几个月而已,获得的信息是有限的。
没看过《山海情》这部电视剧,单单本剧启用了大量西北籍演员,符合这部剧的定位。剧组在服化道上的用心程度可见一斑了。《阿浪的远方》**中的小演员们为了演绎人物是专门学了苗族歌曲的。《十八洞村》片尾出现的那位穿着民族服饰被杨懒踩脚后跟的女人,一看妆容太精致,眼神不够清澈,肯定不是农村人呀。《铁道游击队》中的芳林嫂在河边洗衣服,镜头切到两只细嫩的手留着长长的指甲。说老实话农村妇女砍柴、喂鸡、喂猪、种菜,手是不可能留长指甲的。那么这个人物就跟现实有差距呀,她没有生活气息呀,跟普通老百姓有距离呀。
文学作品也好、影视作品也好,你尽管去刻画了一个以前少有人知的领域或者人群。你的作品是不是贴近了人物,应该让被演绎的那一群人来说,他们才有发言权。
有些在城市生活几十年的作家,没有长期生活在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环境浸*。比方一个人去了苗寨采风,住了一段时间感受到了民族特色,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身心受到了洗礼。所以回去创作了一部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描写苗族百年沧桑的变幻。
好比一个城市人去了苗寨穿戴上了银饰服装,拍了一组照片。很好看,有民族特色。然后你把照片发到了社交网络,大家纷纷点赞。但是她不会做酸汤、不会打谷子、不会做蜡染、不会说苗话。也不能要求她会这些。
你的东西可能只是拥有了外壳,内核呢。可能只是借助了高超的写作技巧,披上了少数民族的外衣而已。
方言、民俗、服饰、建筑等民族文化特色,特别希望有那种出生苗寨土生土长的人,能把自己听到的传说看到经历的事物写下来。为这个民族的发展留下文字。
写作不喜欢虚构,没有触摸过的东西写起来还是觉得那么不自在。
说到一件生活小事,工地门口的山脚下有棵板栗树。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就谈到了要去摘板栗,还是很多人不知道板栗的果实是从刺球里剥出来的。因为在城市生活的人买板栗都是炒制好的,纸袋子装着吃。没有经历过打板栗的那种过程,街上卖板栗打的招牌都是说野生板栗,板栗很大一颗。真正的野生板栗其实最大只有人的拇指那么大,且山高路远采摘极其困难。
你没有体验的东西做到感同身受是基本是很难的,老一辈人珍惜粮食。你让现在年轻人告诫他不要浪费粮食,他不一定做得到,他知道浪费粮食不好,当干果、水果、辣条、薯片占据了他的胃口你觉得他还能吃去一碗米饭吗。因为他们没有饿过肚子,对于饥饿没有深刻的体会。如果你插秧、给秧田赶水、打谷子,知道白花花的大米是怎么来的。一斤大米两三块一斤呀,你就会觉得好便宜呀。
反而你对年轻人说:“你说你出门要戴口罩呀。”
他肯定会戴呀。
你让农村的老头老太戴口罩他多半不会,疫情一般情况下去不了偏远山区。
在生活中积累了一定的生活经验,再去看一些文学作品。说老实话那一代经历特殊时代苦难的作家的文学作品,确实是很厉害。说两个细节:《农民帝国》蒋子龙,孕妇吃炒熟的豆子,一喝水胀死了。莫言《丰乳肥臀》,一位女生也是因为吃豆饼,大量喝水也被胀死。在此介绍下传统工艺的锔瓷,当时锔瓷不仅仅是为了修复瓷器,其本身也成为一种装饰。甚至有人会将原本品相完好的瓷器装上黄豆,再倒入水,用“胀死牛”的方法将瓷器撑裂,然后锔出特定的图案来,以此来把玩。说明豆类遇水要膨胀,佐证作家是有丰富生活经验的人,想张贤亮、冯骥才、古华等人都是在农村待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觉得他们的文艺作品更容易打动人,尤其是生活细节的刻画。
你在一个地方呆个几个月就写出一部作品,跟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十多年写出的东西能一样吗,你所接受的信息不一样呀。
文字对自身的意义来说希望借助文字去记录生活的感受、自己内心的想法。名利对一个知识分子没有多大的意义。
今年以来对阅读文学作品变挑剔了,以后大概率不会写长篇。最多写中篇,因为生活经验的匮乏。在现实中要多获取生活经验,比如多和工人师傅交谈呀,这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这也是我们对于文学作品的态度,有些作品吹得天花乱坠。自己去读也就那么一回事了,并不是说我们与主流价值相悖以显得自己的与众不同。
仍认为迟子建是个人很喜欢的一位作家,她是东北地区的一张文化名片。
现在画能卖了,在经济社会。好像画家就能赚钱了,这孩子都送去画画,培养那么多画家,出来那么多画院,养那么多画家,全世界没有,我没有看到哪个世界上养那么多画家。我们的国家还很穷的,需要养的东西很多,为什么要养那么多画家?画家是怎么来的?画家是苦难中出来的,他感觉到人生的酸甜苦辣,他有种感受,这种的感受啊,他用这种才华,变成艺术品。不管是美术、音乐和文学这样的东西是十分珍贵的。是人类文化的了不起的回报,这样子是创造这个东西来的。不可能有很多才华的人,而且讲穿了艺术没有职业。
——吴冠中先生八十九岁时接受采访时谈话。
吴冠中老先生的这段话适用于在文学、书法、美术、音乐上等领域,相当于指导思想。
2021年3月11日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