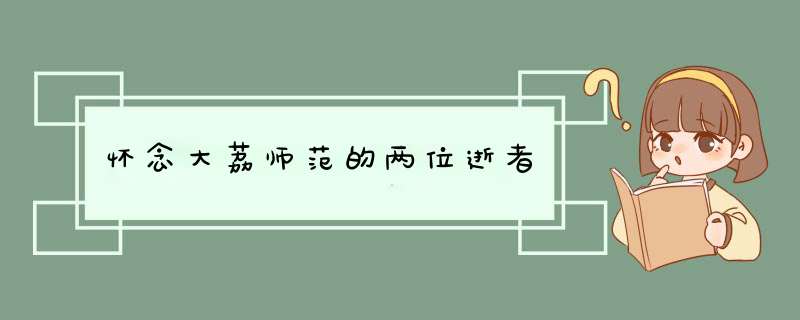
温文尔雅的季英奋老师走了,享年85岁。高大魁梧的吕建华师傅紧跟着也走了,还不到70岁吧!短短一个月左右,大荔师范的两位老先生相继离去,永别在这明媚的春天里,让人痛感遗憾。从此后,两张曾经熟悉的面孔再也见不到了,但他们的名字却永远刻在大师人的心底。
季老师当过学校的教务主任、工会主席,门生遍布东秦大地,故交旧友甚多,原本以为他去世后,会有很多的官方或私人纪念文章发出,但我一直没有见到,不觉有点诧异。有朋友问我,你写过那么多缅怀大师故人的文章,为何迟迟不写季老师?我怯怯地说,他是领导,轮不上我写吧!如今,听到吕师的噩耗,痛定思痛,还是一并追忆和他们相处的日子,表达一下自己的哀悼之情,愿逝者安息。
在我的印象中,季老师这个人很受同事尊敬。他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模样,戴一副眼镜,虽然两鬓染霜,但头发梳理的一丝不乱。衣服也穿的整洁干净,稳重淡雅。言谈举止,谦恭有度,慎思敏行,有古君子的风范。
工会主席,这个位置,其实就是一个清水衙门。无权无势,只是做一些为大家排忧解难,扶危济困,化解矛盾,凝聚人心的事,经费不多,琐事不少。季老师不辞辛苦,勤力亲为,活动比赛、婚丧嫁娶的事情自然少不了他,为大家操过心的人自然不能被人忘。
92年我初到师范,便参加了元旦越野赛,这是季老师领着工会牵头组织的,线路是从学校沿着大华路跑过洛河桥一段后,又折返回来。那时候,大荔县各界对大荔师范举行的活动还很支持,沿途好像有人维持秩序,学生也在路旁摇旗呐喊助威,冬日严寒,我竟跑的热汗淋漓,成绩不错,至少是教工组前四名,这恐怕是我一生中最好的越野成绩了!最难忘的是,凯旋时,季老师他们在校门口热烈欢迎的场景。人头攒动,掌声如雷,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为我们喝彩,为新年祝福。那段岁月,学生们朝气蓬勃,学校也充满了活力。可惜,以后,这些活动渐渐少了,大家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我结婚哪一年,还没有婚庆公司,我一个外地年青人,婚事的前前后后还多亏季老师的全力扶助。他精心安排了几个人给我帮忙,让我感激不尽。团委书记张学义给我管事,当时他不过是三十不到的小伙子,年轻有为,才华横溢,没想到的是,他日后会成为傲视文坛的鲁迅研究专家。季老师主持,他对我表达了真诚的祝福和热切的期望,温馨之言,如春风拂面,让我一生感怀。汪忠印,王云侠,任葆华……还有数学组的年轻老师忙前忙后,鼎力相助,让我顺利完成了这一人生中的大事。
当年大师传统,一家有事,全校上阵,九十年代,大荔酒风最烈,喝酒划拳最有看头,酒令如水珠飞溅,又似机关枪喷涌,手势变换快如闪电,却又神出鬼没。好一番斗智斗量,不醉不休,让我见识了东府人的豪爽与真诚。后来的每一次聚会,觥筹交错,谈笑风生,不敢说响彻云霄,起码是声震屋宇,让人回味无穷。
最让我们佩服的是季老师的淡泊宁静。他退休后,毅然将校内的单元房退还,回归乡下。在很多人挤破脑袋想进城的时候,他却两袖清风还故里,过上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黄河”的田园生活。当时我们还为他惋惜,他又不缺钱,干吗把房子退了,留着将来也能住呀!也许他是为没有房子的人着想,境界不同的人,自然理解不了。他的字写的好,独树一帜,颇有名气,也没听说他卖过字。退隐后他几乎没来过学校,家里有事也没打扰过大家。我只在十几年前在大门口见过一次,他风尘仆仆,远远的叫我的名字,走近握手,没有忘了我,也没有一点生分,让我感动。
吕师则身高八尺,体格健硕,相貌堂堂,颇有威严。虽然他只是一个工人,做过学生灶上的厨师,当过家属院的门卫,如一颗螺丝钉,哪里需要,就在哪里上。不论是学校委派的什么工作,他都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他学历不高,但读书不少,知道的更多,有学识,有思想,嘴里常常冒出文绉绉的词藻,语出惊人,让我自叹不如。他对人间百态见解独到,却也为此常生闷气,世间不平事多了,又有谁能奈何?叹惋之余,他有点落寞了。
其实我是先认识他儿子的,那是92年的盛夏,我在暑假中报到,天气炎热,在校园溜达。不知谁告诉我,开水灶旁有个澡堂,今天2点后开门,我欣欣然去,结果只有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他很大方,和我交谈起来。告诉我,他叫元元,他爸在灶上做饭,他妈在学校开了个理发店,他在附近的村小上学,然后给我说起了学校的一些人和事,当然他是从他爸嘴里听到的。我初到大荔,只觉得这小孩大荔话说的有趣,叙事清晰,不觉聊了很多,他最后竟对我说“叔,我一看你就是个好人”,吓我一跳,不过这句话也让我铭记于心,时时提醒自己要当一个好人。以后的日子,和这一家人也多有接触,一直保持着很友好的关系。
只是可惜,吕师还是走的有点匆匆,听说季老师追悼会的那一天,他还在场,好好的,怎么说走就走!还记得炎炎夏日,家属院门口,他坐在一把小椅子上,敞着短袖,露着背心,摇着蒲扇,眼睛盯着一个个出出进进的行人,遇到陌生人,他会很严肃的盘问,一本正经不亚于公事公办的警务人员。有时和我们聊天、辩论,他常常有点悲观,叹一口气,面容严肃,即使笑,也带有点涩味。他的生活负担相对我们比较重,毕竟两个孩子要养,妻子也是临时工,他心气也高,我觉得他属于一类有志难酬,怀才不遇的人物,没办法!时运如此,人不得不向生活低头呀!
逝者已去,生者还要活下去,现在想想,郑板桥的“难得糊涂”颇有道理,人生不过是一个过程,不论是工会主席,还是普通工人,只不过角色不同,每个人既是演员,也是观众,有些事看破了,也就看淡了,有些人看不透,也就忘了吧。戏完了,剧终了,一切都化作了云烟。
“馄饨”,意取“浑全”“圆满”之意,代表了人们深深的祝福。新婚夫妇走丈人家,要带十二个花馄饨,取“成双成对”“圆圆满满”之意。评论是常有的,二嫂三姨,四婶五婆,看着馄饨指指点点,啧啧称赞:“你看,秀儿家的馄饨蒸得多好,皮薄周正棱棱花,圆皙圆皙(漂亮),这婆婆是个人才儿。”瞧,馄饨可撑起了婆家的脸面哟!设若谁家的馄饨捏的不皙,女人们会嘲笑说:“某某家,山蛋蛋,蒸哈馍馍没沿沿。
渭南政法网(通讯员 苏蒙) 随着时代的发展,以“按揭”、“分期付款”、“花呗”等形式购买自己暂时无力全款支付的房屋、车辆乃至奢侈品已经屡见不鲜,但是,订立婚约时约定的彩礼也能“分期付款”吗?近日,大荔法院双泉法庭便受理了这样一起婚约财产案件。
三四年前,原告小伙经人介绍与被告姑娘相识,确立恋爱关系后,两家人在媒人的协调下很快见面达成婚约,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在随后的相处过程中,两人常因购房等琐事发生矛盾,最终未能走到一起。2019年初,小伙以婚约财产纠纷将姑娘及其父亲告上法庭,要求二被告退还彩礼5万、三金首饰等共计八万余元。
受理案件后,承办人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虽然双方就无法结婚的事实均无异议,但关于彩礼的数额却各执一词。被告坚持认为在订婚时,原告仅支付了彩礼6600元及一份“千里挑一”,而原告则认为订婚时给付了6600元和1001元没错,但双方约定的彩礼是5万元,由于原告家条件较差,所以剩余彩礼是在订婚后陆续给付,现在5万元已经全部给付了被告,被告则又反驳称在订婚后的相处过程中,原告是给过钱不假,但该钱是双方恋爱时的必要支出,而非彩礼。
由于双方意见差距较大,承办人决定在开庭查明事实的基础之上,再于庭后进行调解。庭审中,男、女方的媒人均出庭作证,两人均表示在订婚宴上,双方是有彩礼总额5万元,先给6600元,其余在婚前陆续支付的约定。原告也提供了其通过银行卡、微信等向被告转账的记录。庭审结束后,承办人再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首先将男方的全部转账记录进行统计,随后再将其中数额为“1314”、“521”等具有典型示爱、赠与性质的款项剔除,最终,在明晰数额的基础上,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被告一次性返还原告彩礼36000元并履行,案件得到圆满处理。
在山西的四大戏曲文化中,蒲剧占了一席之地。蒲剧也是山西文化中最古老的一种,它的历史悠久,蒲剧的脸谱是全国有名的,它的流星地一般在山西南部。你对于山西的蒲剧了解多少呢?下面的山西文化为您带来更多的蒲剧信息,一起来看看吧。
蒲剧又称蒲州梆子,当地人通称乱弹戏,是一种古老的汉族民间戏曲艺术。因兴于山西晋南古蒲州(今山西运城永济)一带而得名。蒲剧在清代乾隆时期外省称“乱弹”、“晋腔”、“山陕梆子腔”等;嘉庆、道光以后,又称“山西梆子”;陕西称:东路戏,山西省北、中部称“南路戏”;晋南当地则习惯称“大戏”或“乱弹”。
蒲剧约形成于明代嘉靖年间。山西省汉族戏曲剧种之一,它是“山西四大梆子”中最古老的一种。流行于山西南部各县和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自治区的部分地区。蒲州地处黄河中游,其大庆关渡口毗连山西、陕西,最古代南方丝瓷通往西北的交通要道,商业兴隆,经济文化繁荣,为戏曲的发展、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金元时期,这里金院本、元杂剧的演出极为盛行;明清以来,又是梆子、乱弹活动的重要基地,故素有“戏曲之乡”之称。
临汾地区有许多古代戏剧活动遗迹,例如临汾市的魏村元代牛王庙戏台、东羊戏台和王曲元代戏台等,造型逼真,表情丰富,再现了我国古代的戏剧艺术。这些实物史料证明,晋南地区戏剧活动历史悠久。蒲剧唱腔高昂,朴实奔放,长于表现慷慨激情、悲壮凄楚的英雄史剧,又善于刻划抒情剧的人物性格和情绪。一说胚胎于晋南和陕西东部民间的锣鼓杂戏(陕西称“跳戏”);一说为北曲遗响,同山、陕民歌小曲、典艺结合的“弦索调”,至明中叶受青阳腔(清戏)影响后演变而成。
山西蒲州与陕西同州(大荔)﹑朝邑﹐河南陕州(陕县)﹑灵宝﹐地处黄河中游﹐居黄河激流南下而折流向东的三角地带﹐彼此隔河相望﹐长期以来有着经济﹑文化的密切交往﹐其风俗习惯﹑语音﹑方言也大体相同。明末清初﹐这一带已有“乱弹”流行。孔尚任于康熙四十六年所作《平阳竹枝词·乱弹词》可为证。当时的平阳乱弹演技已有相当水平,曾博得康熙帝的赏识。其旦角葵娃的“花梆子”小步非常出色,受到孔尚任的赏识。康熙至乾隆时,北京观众也称蒲剧为“西调”、“西秦腔”、“勾腔”。咸丰、同治后,又多以“山梆子”称之(见清吴长元《燕兰小谱》、近人王芷章《腔调考源》)。所谓“山陕梆子”,当时泛指山西晋南的蒲州梆子和陕西的同州梆子。两地仅一河之隔,语言相近,风俗习惯相同,又有大庆亲渡口毗连一体,艺人相互搭班演出,历来无艺界。乾隆年间秦腔名旦申祥麟曾渡黄河“由蒲州售技至太原”(清严长明《秦云撷英小谱》)。嘉庆年间北京有“山陕班”演出,直到光绪、宣统年间,蒲州和同州艺人仍有在北京搭梆子班演唱的,如名须生郭宝臣和白长命合演《鞭打芦花》。故京﹑津﹑直隶(河北)一向谓之“山陕梆子”。此外﹐他们还有过共同组班南下﹐在湖北襄阳老河口演戏的经历。
山陕梆子对各地梆子腔剧种的形成﹐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其后两个剧种始逐渐分道发展。分别以蒲州和同州命名的蒲州梆子与同州梆子虽为两个剧种﹐但实同源于此。它们唱腔相似﹐戏路相通﹐今天虽各有不同发展变化﹐然两地艺人均自称为“乱弹”。蒲剧传统剧目有本戏、折戏500多个,题材上至远古,下至明清,有文有武,风格多样。传统剧目有《薛刚反朝》、《三家店》、《窦娥冤》、《意中缘》、《燕燕》、《西厢记》、《赵氏孤儿》等,新编历史剧有《白沟河》、《港口驿》,现代戏有《小二黑结婚》等。其中《窦娥冤》已摄制成影片。
抗战时期﹐部分蒲剧艺人聚集在陕北延安南区合作社组成蒲剧班﹐曾演出《正气图》等。解放战争时期﹐太岳区的翼城解放剧团曾演出现代戏《赤叶河》等。在西安有晋风社﹑唐风社。此外﹐在晋南也有班社坚持演出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後﹐蒲剧得到迅速发展﹐晋南﹑豫西﹑陕北等地相继成立的蒲剧团共有40多个。其中以山西晋南蒲剧院(今临汾地区蒲剧院和运城地区蒲剧团的前身)最具有代表性﹐主要名演员有王秀兰(小旦)﹑阎逢春(须生)﹑张庆奎(须生)﹑杨虎山(二净)﹑筱月来(小生)﹐主要乐师有车林娃(鼓板)﹑车太娃(板胡)等。又有编剧﹑导演﹑音乐﹑舞美工作者共同参加艺术创作和革新工作。整理改编的传统剧目有《薛刚反朝》﹑《三家店》﹑《窦娥冤》﹑《意中缘》﹑《燕燕》﹑《西厢记》﹑《赵氏孤儿》﹑《周仁献嫂》﹑《贩马》﹑《杀驿》﹑《出棠邑》﹑《破洪州》﹑《少华山》﹑《麟骨床》﹐新编历史剧有《白沟河》﹑《港口驿》,现代戏有《小二黑结婚》等。其中《窦娥冤》已摄制成影片。想流传在山西晋南。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