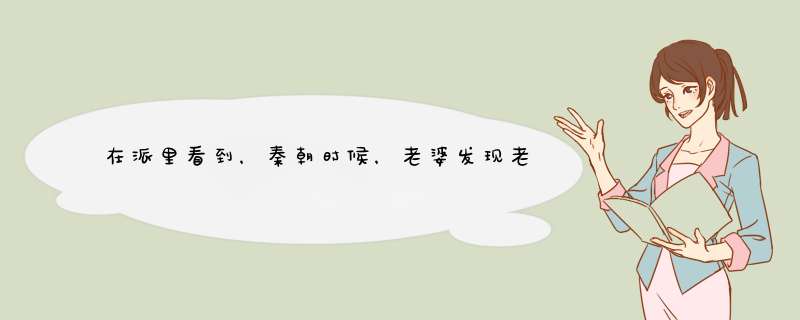
秦朝的确很有意思 我来简单介绍一下秦朝的婚姻与继承。
秦律规定结婚只有到官府登记才有效,未经登记的婚姻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而丈夫休妻也同样必须报官登记。
有关夫妻的权利义务关系,秦律虽然也维护男尊女卑和夫权,但因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小,因而能对夫权有所限制,对妻子人身权利的保护也超过汉以后的历代王朝,比如,秦律一方面要求妻子忠于丈夫,另一方面也规定丈夫通奸有罪。“夫为寄豭,杀之无罪。” 还有秦简《法律答问》“妻悍,”丈夫也不得随意殴打,否则将被处刑。
史书上没有关于秦始皇册立皇后的时,只记载了他后宫的嫔妃非常之多,其中为人们所知道的有两个,一个是公子扶苏的母亲郑妃,另一个胡亥的母亲胡姬。
嬴政出生于赵国都城邯郸,后回到秦国,前247年,13岁时即王位,前238年,平定长信侯嫪毐的叛乱,之后又除掉权臣吕不韦,开始独揽大政。
重用李斯、王翦等人,自前230年至前221年,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完成了统一中国大业,建立起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秦朝。
扩展资料:
秦朝在统一后不久就频繁的大兴土木,尽管其中一部分工程如长城灵渠是利国利民的,但生产力仍遭到极大破坏,秦始皇三十一年,一石米就卖到了一千六百钱,民众苦不堪言,因此秦朝二世而亡也就不奇怪了。
历代都宣扬秦始皇残暴不仁,如焚书坑儒、大建阿房宫、长城、骊山墓等等。但从考古看来,”焚书“是有的,但是好在所焚的书在咸阳宫和民间多有副本,可惜的是周王室存放的珍贵史籍没有副本,也被付之一炬从此绝迹。
“坑儒”是后世的说法,《史记》中记载为坑杀术士,但同时也提到“诸生皆诵法孔子”,也就是说这些术士和儒生算是一类的。
一、唐朝婚姻制度的概述
(一)唐朝婚姻制度概况
唐朝的婚姻制度主要包括婚姻的缔结、婚姻的解除和婚姻的限制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婚姻的缔结方面,《唐律》规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和传统的“六礼”程序是成立婚姻的必要条件,并规定了“报婚书”、“有私约”等成立婚姻的具体条件。在婚姻的解除方面,唐朝解除婚姻关系有两种方式:强制离婚与协议离婚。前者分为“断离”与“出妻”,协议离婚即“和离”。根据《唐律》规定,官府断离的情形主要有两种,一是“嫁娶违律”或“违律为婚”,二是出现“义绝”的情况,这些由官府强制解除其婚姻关系。在婚姻的限制方面,主要包括缔结婚姻的限制和解除婚姻的限制两方面的内容。《唐律》禁止结婚的情形主要是“嫁娶违律”和“违律为婚”,《唐律》关于解除婚姻的限制任然是传统的“三不去”。另外唐律允许寡妇自愿再婚和纳妾。
(二)唐朝婚姻制度的特点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盛唐时期社会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法律健全,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唐朝的一派繁荣景象使唐朝的婚姻制度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即包容性和开放性。
第一,唐朝婚姻制度的包容性
经历了南北朝以来的民族大融合和民族同化,各民族在风俗习惯上相互承认和接受,民族之间彼此通婚的现象也相对增多,唐政府的最高统治者李氏家族出身关陇军事贵族,流淌着鲜卑族的血液,是胡汉通婚的融合体,虽受儒家伦理纲常的熏陶,但在实际生活中受礼法的限制却不像后朝那样严密。其统治集团的重臣长孙无忌、宇文融等都是汉化很深的鲜卑族人,阿史那杜尔、李光弼等高级将领也都是其他少数民族,唐初的统治者具有远大的政治韬略,对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持开明、包容的政策,民族之间的包容性呈现出一派新的景象,民族间的通婚增多,婚姻习俗相互影响,对礼教形成一定的冲击,使人们的思想观念趋于开放。
第二,唐朝婚姻制度的开放性
在唐朝,由于受民族大融合的影响,关于婚姻的礼教相对松弛,人们的婚恋思想相对开放,现实生活中女性的地位有所提高,贞操观念相对淡薄。唐朝离婚较为常见、再嫁不为失节,正如有学者所言,唐人“似乎不懂得如何去掩饰和压抑自己的欲望和追求,相反,他们要让这种欲望正常的表现出来。”在唐朝,和离,寡妇改嫁,一定程度上的自由择偶,纳妾为法律所明文允许,使唐朝的婚姻制度呈现出历史上少有的开放性特点。
二、唐朝缔结婚姻的制度
(一)实质要件
唐朝缔结婚姻的实质要件包括“一夫一妻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同姓不婚”等。
第一, 缔结婚姻关系要遵循“一夫一妻制”。
所谓一夫一妻制,也称“个体婚制”或“单偶婚制”,是由一男一女结成稳定配偶关系的婚姻形式,它是在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度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后世一直沿用。在封建时代的上层社会,一夫一妻制更多的表现为一夫一妻多妾制,唐朝的婚姻制度也不例外。唐令规定贵族官僚除正妻外,侧室也各分等级:凡亲王可有孺人2人(相当于正五品官阶)、媵10人(相当于正六品官阶);郡王以及一品官可有媵10人(相当于从六品官阶);以下递减,至五品官可有媵3人(相当于从八品官阶),六品官以下至庶人的侧室就只能称之为妾,没有官阶身份。《唐律疏议·户婚律》规定:“有妻者不得重娶妻,违者徒一年”、“不得乱妻妾位,违者处徒刑”。
第二,缔结婚姻关系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唐律》确认父母及尊长的主婚权。在中国传统婚姻制度中“男不自专娶,女不自专嫁,必由父母,须媒妁”,“男女无媒不交”。秦朝以后这些礼制规范被以法律形式确认父母意志是子女成立婚姻的必要条件。唐朝规定:“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定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又规定“诸嫁娶违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在唐朝,父母还可以强迫守寡的女儿改嫁。《唐律》也维护“媒妁之言”在缔结婚姻关系中的地位。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媒,谋也,谋合二姓者也”,“妁,酌也,斟酌二姓者也”。可见,媒妁就是成就男女婚姻关系的媒介,《豳风·伐柯》说:“娶妻如何,匪媒不得”,唐律已正式将媒人规定为婚姻成立的法定要件,《唐律疏议》卷13“为婚妄冒”条疏议云:“为婚之法,必有行媒。”《唐律疏议·名例律》篇中也有“嫁娶有媒”的规定,可见媒人是成立婚姻关系不可缺少的条件。《唐律·户婚律》中“嫁娶违律条”规定:“诸嫁娶违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媒人各减首罪二等。”由此可见,媒人在成立婚姻关系中处于重要地位,需要承担仅次于主婚人的法律责任。
第三,缔结婚姻关系须遵循“同姓不婚”的原则。
中国自古同姓不为婚,这一原则同样为唐律所秉承,《唐律疏议》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同宗共姓,皆不得为婚。”但对于同宗异姓,因“祖宗迁易,年代浸远,疏源析本,罕能推详”,而“不在禁例”。另外,原本同姓,被皇家赐予他姓,众所共知者,属在禁之例;对音同字异之姓,如“杨”与“阳”之类,都不得为婚。唐朝禁止同姓为婚,是为防止辈份混乱,维护礼所倡导的伦理道德。
(二)形式要件
唐朝缔结婚姻关系的形式要件主要有:“报婚书”、“有私约”和“六礼”程序等。
所谓“婚书”是指双方尊长以书面形式提出和答应订立婚姻关系。《唐律疏议》卷13“许嫁女辄悔”条:“许嫁女已报婚书者,谓男家致书礼请,女氏答书许讫”,“辄悔者,杖六十”,并且“婚仍如约”。男家自悔无罪,仅不能追回聘财,可见婚书对男女双方的约束是不平等的。
所谓“私约”是男女双方尊长缔结婚姻关系的口头协议,包括对对方生理或其他方面一些缺陷的认可,《唐律疏议》对私约作了解释:“约,谓先知夫身老、幼、疾、残、养、庶之类。老幼,谓本约相校倍年者;残疾,谓状当三疾肢体不完;养,谓非己所生;庶,谓非嫡子及庶、孽之类。以其色目非一,故云‘之类’。皆谓宿相谙委,两情具惬,私有契约,或报婚书,如此之流,不得辄悔,悔者杖六十,婚仍如约。”
唐朝缔结婚姻关系仍然遵循传统的“六礼”程序。《唐律疏议》说:“妻者,传家事,承祭祀,既具六礼,娶则二仪”,“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属合法婚姻,说明六礼仍是唐朝结婚的必经程序。所谓“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的第一个程序是“纳采”,传统的纳采是指男家委托媒妁以雁为礼物,向女家求婚,《仪礼·士昏礼》:“昏礼,下达纳采,用雁。”第二个程序是“问名”,指男家请媒妁求取女方姓名、生辰等情况,向宗庙卜问婚配吉凶。第三个程序是“纳吉”,即男家将卜问所得吉兆通知女家,《仪礼·士昏礼》:“宾执雁,请问名;主人许,宾人授。”唐朝的纳吉主要是将“报婚书”送达女家,女家答书许讫。第四个程序是“纳征”,即男家向女家送交聘财,正式订婚,《仪礼·士昏礼》孔颖达疏:“纳征者,纳聘财也。征,成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唐高宗时曾规定不同官品缴纳不同数量的聘财,庶人则以礼而行。第五个程序是“请期”,即请定婚期,择取吉日成婚,《仪礼·士昏礼》:“请期用雁,主人辞,宾许告期,如纳征礼。”最后一个程序是“亲迎”,即成婚之日,男方亲自前往女家迎娶。《诗经·大雅·大明》:“大邦有子,天之妹,女有阙祥,亲迎于渭。”经过“六礼”程序,男女双方缔结的婚姻得以正式成立。
(三)缔结婚姻的限制
《唐律》禁止结婚的情形主要有两类,一是“嫁娶违律”,二是
“违律为婚”。另外又有不得先奸后娶等规定。
第一,嫁娶违律。唐律规定的嫁娶违律的情形主要包括居父母丧嫁娶,居夫丧嫁娶,祖父母、父母犯死罪被囚禁而嫁娶等三种。根据“礼”的规范,在为父母服丧期间嫁娶是“不孝”,为丈夫服丧期间自行改嫁是“不义”。《唐律疏议·户婚律》卷13“居父母夫丧嫁娶”条:“诸居父母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妾减三等。各离之。知而共为婚姻者,各减五等;不知者,不坐。”《唐律疏议·户婚律》卷13“父母被囚禁嫁娶”条:“诸祖父母、父母被囚禁而嫁娶者,死罪,徒一年半;流罪,减一等;徒罪,杖一百。祖父母、父母命者,勿论。”《唐律疏议·户婚律》卷13“居父母丧主婚”条:“诸居父母丧,与应嫁娶人主婚者,杖一百。若与不应嫁娶人主婚,得罪重于杖一百。”很明显,唐律关于嫁娶违律的规定,体现了礼法的结合,是忠孝思想在婚姻制度上的体现。
第二,违律为婚。唐律规定的违律为婚的情形主要包括同姓为婚、五服以内亲属为婚、良贱为婚、与逃亡妇女为婚、监临官与监临女为婚,妄冒为婚以及恐吓、强娶为婚等。
《唐律疏议》规定五服以内亲属不得为婚,“缌麻以上,以奸论。若外姻有服属而尊卑共为婚姻者,及娶同母异父妹妹,若妻前夫之女者,亦各以奸论。其父母之姑、舅、两姨妹及姨,若堂姨、母之姑、堂姑,己之堂姨及再从姨、堂外甥女、女婿姊妹,并不得为婚姻,违者各杖一百,并离之。诸当为袒免亲之妻,而嫁娶者,各杖一百;缌麻及舅甥妻,徒一年;小功以上,以奸论。”唐律禁止五服以内亲属为婚,目的是为防止道德沦丧,维护礼制。
为维护等级制度,唐律禁止良贱为婚。《唐律疏议》卷14《户婚下》说:“诸杂户不得与良为婚,违者杖一百;官户娶良人女者亦如之,良人娶杂户女者亦如之,良人娶官户女者加两等。”唐朝实行“当色为婚”制度,即要求门当户对,《唐律疏议》卷14“杂户官户与良人为婚”条曰:“其工、乐、杂户、官户,依令‘当色为婚’,若异色相娶者,律无罪名,并当‘违令’。既乖本色,亦合正之。”
《唐律疏议》卷14“娶逃亡女”条规定:“诸娶逃亡妇女为妻妾,知情者与同罪,至死者减一等。离之。即无夫,会恩赦免罪者,不离。”《唐律疏议》卷14“监临娶所监临女”条规定:“诸监临之官,娶所监临女为妾者,杖一百;若为亲属娶者,亦如之。其在官非监临者,减一等,女家不坐。即枉法娶人妻妾及女者,以奸论加二等;为亲属者,亦同。行求者,各减二等。各离之。”
妄冒为婚指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如身份、年龄等而为的婚姻,为唐律所禁止。《唐律疏议》卷13“为婚妄冒”条规定:“诸为婚而女家妄冒者,徒一年;男家妄冒,加一等。未成者,依本约;已成者,离之”。恐吓、强娶为婚亦为唐律所禁止,《唐律疏议·户婚律》卷14“违律为婚”条规定:“诸违律为婚,虽有媒娉,而恐吓娶者,加本罪一等;强娶者,又加一等。被强者,止依未成法。即应为婚,虽已纳聘,期要未至而强娶,及期要至而女家故违者,各杖一百。”长孙无忌对“强娶者”解释曰:“谓以威若力而强娶之。”此外,唐令规定不得先奸后娶,“假令,先不由主婚,和合通奸,后由父母等立主婚已讫后,先奸通事发者,纵生子孙犹离之耳。常赦所不免,悉赦除者,不离。唐令犹离者非。”这一规定出于维护礼制的目的,对家庭和社会稳定具有一定作用。
三、唐朝解除婚姻的制度
(一)强制离婚
唐朝的强制离婚分为“断离”与“出妻”两种方式。所谓“断离”是指官府强制解除婚姻关系的行为。《唐律》规定,在两种情况下,由官府断离,第一种情况是“嫁娶违律”或“违律为婚”,第二种情况是出现“义绝”的情形。有关“嫁娶违律”和“违律为婚”的情形上文已有详述,这里不作重复。所谓“义绝”是指夫妻双方对一定范围内的亲属有杀伤、殴打、骂詈、通奸等情形,以及妻子谋害丈夫的情形。《唐律疏议·户婚》解释曰:“夫妻义合,义绝则离”,并以此作为这项规定的根据。《唐律疏议·户婚》规定了“义绝”的具体情形:“(夫)殴妻之祖父母、父母及杀妻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或“妻殴詈夫之祖父母、父母,杀伤夫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及与夫之缌麻以上亲,若妻通奸及欲害夫者。”或“夫妻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自相杀者”。出现“义绝”的情形,由官府强制解除婚姻关系,并给予双方一定处罚,《唐律疏议·户婚》“义绝离之”条规定:“诸犯义绝者离之,违者,徒一年。”
所谓“出妻”是指男方单方面休弃妻子的行为。唐朝仍然沿用传统的“七出”作为丈夫强制离婚理由,《大戴礼记·本命篇》中有“妇有七出:不顺父母,去;无子,去;*,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妻子犯“七出”之条,男方即可提出休妻,无需官府判决,只要作成文书,由父母和证人署名,即可解除婚姻关系。唐律则规定凡妻子犯无子、*佚、不事姑舅、口舌、盗窃、嫉妒、恶疾之一者,由丈夫强制离异。
(二)协议离婚
协议离婚又称“和离”、“两愿离”,指男女双方自愿解除夫妻关系的行为。《唐律·户婚》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可见,唐朝法律是允许夫妻双方自愿离婚的,但需要双方达成协议书,作为解除婚姻关系的凭证,敦煌文书中就有载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的和离协议书。在我国古代,唐律首创了“和离”制度,这是唐朝政治开明在法律上的一个体现,这对减轻妇女因婚姻关系造成的痛苦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三)解除婚姻的限制
唐律对解除婚姻的限制主要也是传统的“三不去”。《大戴礼记·本命篇》中说:“妇有三不去:有所取无所归,不去;有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唐律疏议·户婚律》认为“三不去者”,谓“一经持姑舅之丧,二娶时贱后贵,三有所受无所归。”“诸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徒一年半;虽有七出,有三不去出之者,杖一百,追还合。若犯恶疾及奸者,不用此律。”可见如果妻子未犯“七出”或虽犯“七出”但有“三不去”情形之一的,不得随意休妻,否则要受到处罚,但如果妻子犯“恶疾”及“奸”则“虽有三不去,亦在出限”。
“三不去”是对男子随意解除婚姻关系的一种限制,对于稳定婚姻关系,减少社会问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体现了儒家仁义精神和礼制对法律的影响。
四、对唐朝婚姻制度的几点思考
(一)体现了礼法结合的法律文化
礼法关系是唐律中最重要的一种关系,唐律“一准乎礼,而得古今之平”,礼法结合的法律文化在唐朝婚姻制度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在唐律中,婚姻的缔结、解除、惩治违律为婚和罪名的设立等都渗透了礼的因素。例如,在婚姻缔结过程中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遵循“六礼”程序、;婚姻解除中的“七出”、“三不去”;违律为婚中“同宗共姓,皆不得为婚”,“诸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妾减三等,各离之。知而共为婚姻者,各减五等;不知者,不坐。若居期丧而嫁娶者,醉杖一百,卑幼减二等,妾不坐。”“诸有妻者,更娶妻者,徒一年,妾减一等”又规定:“诸以妻为妾,以婢为妻者,徒二年。以婢为妾者,各正还之。”以上这些规定或者直接移用礼教规范,或者体现礼的精神,体现了唐朝礼法结合的法律文化。
(二)体现了妇女法律地位的提升
在唐朝妇女的地位有所提升,这在整个封建时代是罕见的。唐朝妇女受束缚较少,“一女不事二夫”等贞节观念较为淡薄,也无“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而且出现“男到女家成婚”和“夫从妻居”的现象。在婚姻制度上,唐律除规定“三不去”外,和离、改嫁、再婚均为法律所明文允许。以再婚为例,唐朝允许寡妇再嫁,贞观元年二月四日诏令:“孀居服纪已除,并需申以婚媾,令其好合……其鳏夫年六十、女年五十以上,及妇虽尚少,而有男女,及守志贞洁,并任其情,无老抑以嫁娶……鳏寡数量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唐律疏议》规定“诸夫丧服除而欲守志者,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强嫁之者,徒一年;期亲嫁者,减二等,各离之。女追还前家,娶者不坐”。唐朝以诏令的形式允许并鼓励寡妇再嫁,并把寡妇数量的减少作为地方官吏政绩考核标准的一个方面,其目的是促进人口的增长,发展经济,但实际上对正统妇女贞节观念也是一种冲击,有利于唐朝社会风气的开放,体现了妇女地位的提升。
(三)体现了民族文化的互化融合
唐朝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唐朝的最高统治者李氏家族出生于关陇贵族,是胡汉融合的产物,既受少数民族文化习俗的影响,又深受儒家伦理的影响,因此在对待民族文化的问题上较为开明,各民族之间的习俗相互影响,反映在婚姻关系上,表现为民族间互通婚姻的现象增多,婚姻习俗相互影响,互相承认和接受,这些又促进了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与融合;在此背景下,儒家的伦理纲常受到一定的冲击,礼教相对松弛,世风开放,贞操观念淡薄,这些都是民族文化互化融合的表现。
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唐朝的婚姻制度由于受封建礼教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但其中不乏一些良法美制,有利于稳固封建家庭秩序。科学总结我国唐朝的婚姻制度,借鉴其合理之处,吸收其经验教训,以期对健全我国当代婚姻制度能有所启示。在建设我国当代婚姻制度的过程中,唐朝婚姻制度的包容性与开放性特点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它启示我们不仅要借鉴我国古代婚姻制度的合理成分,还要借鉴国外有关婚姻制度方面的先进立法经验,针对我国多民族,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情,要注重婚姻制度的灵活性,允许一些变通性的规定;唐朝婚姻制度强调保护妇女权益和尊老爱幼、家庭和睦、亲情和谐的传统美德,在当代对我们坚持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下的和谐婚姻制度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1、
一般来说,古代女性在15岁到19岁结婚,而男性在15岁到20岁结婚。《礼记》是孔子编的,大致反映了以往的社会习俗。它的规定是“男人二十冠而字”“女人…十有五年发夹”,可以结婚。秦以前也有宽容的时尚,没有硬性规定。后来,秦汉模式的农业封建中央集权国家开始干涉个人生活,妇女超过年龄不结婚,受到惩罚。一开始有男权社会的风格,后来专制集权压过一切,干脆连男女都罚。
2、
秦朝以前的结婚年龄在《礼记》中有描述。根据《礼记曲礼》,人生十年,学习。二十天弱,冠。三十天强,有房间。”可见,在秦朝及以前,男子20岁时被称为“弱冠年”。儿子20岁时,父母在家庙里为儿子举行成人礼,把垂直头发盘成发髻,戴上帽子,这叫行冠礼。
3、
战国齐桓公令:男三十,女十五。
战国越王勾践令:男二十,女十七。
汉惠帝令:女十五。
晋武帝令:女十七。
北周武帝令:男十五,女十三。
唐太宗贞观令:男二十,女十五。
唐玄宗开元令:男十五,女十三。
宋仁宗天圣令:男十五,女十三。
宋宁宗嘉定令:男十六,女十四。
宋司马光《书仪》:男十六,女十四。
宋朱曦的《家礼》:男十六,女十四。
明太祖洪武令:男十六,女十四。
清清《大清通礼》:男十六,女十四。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