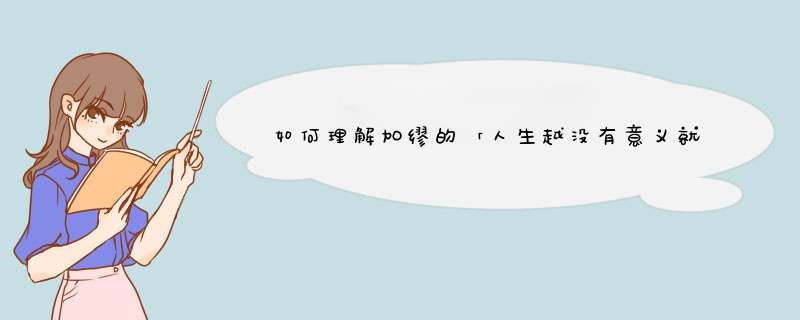
先说一种观点,“意义”本身是一种对身份的认同。我们看很多巨贾富商们,他们都是锦衣玉食,开劳斯莱斯,吃山珍海味,出入各种五星级宾馆。我们怎么评价他们,我们评价这些人的时候都会说:“这些人做的事情没有意义”。我们会认为救死扶伤,读书,提高自己才是有意义的。其实呢,假如你有100亿,你会不会买劳斯莱斯,会不会住五星级宾馆,会不会吃山珍海味,当你的一句话可以决定一个项目启动与否的时候,你会不会收贿受贿,当你说一句话周围的人都会围着你转的时候,你还不会做到兼听则明,你可以说你现在可以做到,但是你真的可以做到,为什么我们看很多官员都一样的毛病,为什么当官的好像都有几个情妇,难道他们不知道这是没有意义吗?原因很简单,因为上层人士不需要通过所谓的“意义”来获得自身的认同和价值,每天的各种欲望的满足(在我们看来毫无意义)就足以让其快乐的过完一生。
搜狐网
被全世界抛弃的民族:拒绝任何的国家与法律,终生不离沙漠
回答于2022-11-03

阿尔贝·加缪曾在《沙漠》里展信而抒:“生活或多或少是’表达’的反义词。如果相信托斯卡纳大师们的看法,那就是三重见证:在沉默中、火焰里和静止中见证。”
沙漠的魅力在于静默,云与沙都凝滞不动,于是时间无法留下痕迹,沙漠便选择了停驻,在停驻里你我得以直视自己的生活。
但沙漠的寂静是燃烧的,它的火焰烧在地心,千年沸沸而不绝,于是这份沉默便成了倔强,就像在沙漠中游历了千年的贝都因人,他们被世界抛弃,便也抛弃了世界,在荒漠之中自给自足。
民族驱逐,流亡惨死
大多数的贝都因人因为长时间的居无定所,渐渐地逃到周边国家融入其中,成为阿拉伯地区老百姓中的一员。
仍然在以他们本民族生活方式生活的纯正贝都因人,散布在北非和西亚一带的沙漠中,零零散散也有十万余人。

贝都因人曾经是整个阿拉伯地区中最富饶而且科技发展水平最高的民族,巅峰时期的民族力量几乎能够建立贝都因王朝。
然而随着更强大势力的扩张,再加上周围各方势力的联合绞杀,贝都因王朝抵抗住了埃及的侵略,躲开了古罗马的追杀,但最终还是难以逃脱奥斯曼帝国的占领。
在帝国的铁蹄之下,贝都因人难逃伤害,在最后一次贝都因的朝圣途中,被奥斯曼围追堵截在一处峡谷之中,几经困兽犹斗,两万贝都因人死于饥饿与战斗,不堪重负的贝都因民众只能屈服。
为了维持民族的延续,贝都因人不得不分开求生存。

一部分贝都因人投降于奥斯曼王朝,为了慰藉帝国统治下各民族的反抗情绪,奥斯曼颁布了分领土地的政策惠及各民族势力。
但帝国执行力明显不足,缺乏文化基础与文明制度的国家不足以长治久安,过了不久奥斯曼帝国土崩瓦解,这部分贝都因人开始再寻出路。
另外一小部分贝都因人,在被奥斯曼帝国势力残害之中逃出生天,潜入北非地区的大沙漠中安家落户。
他们在绿洲之间穿行,以氏族为单位,四处谋生以讨生计。
奥斯曼帝国陨落后,贝都因人又逃到叙利亚等中东与西亚地区,甚至有的小部分人逃到了高加索山脉附近常居。

流亡逃窜,居无定所
贝都因人被奥斯曼帝国的苛捐杂税搞得分崩离析,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再次出现,贝都因人立下了永不背弃的族规:“不承认氏族以外政权与法律”。
一战前后,贝都因人在土耳其一带聚集的氏族被征集应召入伍,同另一方的英军势力展开较量。
土耳其一方将贝都因军队立于整支部队的最前线,但当英军来袭之时,贝都因人先手投降,带领英军直取土耳其老巢,也算是报了奥斯曼帝国的课税之仇。
也正因此事贝都因人成名,被称为“哈马得之剑”。

一战结束后,贝都因人开始了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
在世人眼中的贝都因人都是向往自由的浪漫主义者,但真实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贝都因人被全世界所遗弃,若不是没有落脚之地,谁又愿意整日漂泊落地无根呢?
战争过去后,大量的贝都因人聚集流亡,形成势力,对于阿拉伯周边地区的具有很大的潜在威胁,于是在阿拉伯等国的强迫之下,一部分贝都因人“自愿”融入这些国家,过起平凡而安定的生活,也渐渐的放弃了自己贝都因民族的身份。
但仍然有一批人数可观的贝都因人游走于北非与西亚一带的沙漠地区,形成了一支极端独立并且排斥一切外部势力的游击力量。

这也是能够维持住本民族长久存在,同时不被其他国家文化吞并同化的唯一方法。
长时间的与外界文化隔离,也使得外部文明对于他们贝都因民族更加的不包容,甚至否定这个民族与政权的存在。
他们更像是行走在撒哈拉沙漠的幽魂,来无影去无踪,不与真实存在的国家与文明相融合,只是为了生存漫无目的地走在茫茫荒野之中。
人们常说他们是崇尚自由而又不愿被法条制度约束的民族,但于他们自己而言,不过是被时代与世界遗弃的天之孤儿而已,没人在意他们的存在,更没有人会阻挠他们存在。
漂泊于漫天黄沙是他们别无他法的唯一出路。

极度排外,不易接近
因长达几个世纪的不与外界文明接触,贝都因民族的内部文化已经处于对外部的一切接触都抗拒的程度。
再加上其武装力量不可小觑,成为了荒漠上最危险而又最神秘的势力之一。
一名曾经接触过贝都因人的人声称,在贝都因人的民族文化中,所有外来的势力都是不好的,他们语言自成一派,风俗自成一派,婚姻更是内部嫁娶。
不用说与外面通婚,就连最简单的肢体接触都有可能演变为惨烈的大战。
在北非的沙漠地区,贝都因人就算见到人种同根同源的阿拉伯人也会严肃抗拒,不予交流,但奇怪的是部分氏族对待东亚面孔却会喜笑颜开。

传说是一个氏族在沙漠中遇到风暴险情,适逢中国探险队才侥幸逃脱危险,因此对于中国东亚一带有着难以言喻的好感。
但传说只是传说,这条新闻在中国境内并没有报道传出,不过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也确实能让许多难以接触的文明展开交流的渠道。
现如今算得上是贝都因民族的人不算少数,大多数都是散在各个城镇之间,隐姓埋名重新生活。
但最为纯正的西亚北非沙漠中的“幽灵”,依然步履坚定的走在下一个绿洲所指示的导向标中。
长时间失去所依赖的家园,他们对于流离失所的环境习以为常,为了维持民族与自己文明的存在,他们如此流浪也是无可奈何。

他们的文明就如刘慈欣《流浪地球》中的地球一样,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不复存在,因此我们孤独的穿行在无边无际的银河荒漠中,寻找着下一个能够生存下去的环境,为了维持文明延续再无他法。
贝都因人穿行在黄沙下,亦如地球穿行在银河间。
他们知道自己曾经的家在哪,但他们同时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那个家园。
他们只能不停地流浪,带着文明流浪,一路孤独地前行,相对封闭与孤立的条件正是他们维持文明不受侵害的最好方法。

在一片苍茫的黄之间,他们是唯一鲜活存在,孤立于世界秩序,而又自成秩序。文明是孤独的,丹心碧透,汗青写满,照不过国境半米;但文化应当是开放的,孺子笔墨,文章三百,远播西洋千里。
贝都因民族的文明是应当延续的,但论到文化却是固步自封,清湖空池,无源头活水,早晚是死潭终了。
漫步在茫茫荒野,望向沙丘点点,回头低声叹息,问何以为家?为首者轻点脚下:“但行此程,莫问西东。”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阅读原文
属于秋天的专属浪漫
就醒来,读书,写长长的信,在林荫路上不停地挪徊,落叶纷飞。----里尔克《秋日》
世界上美好的东西不太多,立秋傍晚从河对岸吹来的风,和二十来岁笑起来要人命的你。
——《下雨和见你》宋小君
树林传来揉叶子的声音,那是秋天的手指。阳光把墙壁刷暖和了,夜将它吹凉。——简媜
秋日薄暮,用菊花煮竹叶青,人与海棠俱醉。——林清玄《温一壶目光下酒》
秋天是第二个春天,每片叶子都是一朵花。——加缪
秋天短到没有,你我短到不能回头。——冯唐
这一看似矛盾的说法,并非加缪狡猾的“辩证法”,而是说,反抗表面上看起来是否定之物,“其实它表现了人身上始终应该捍卫的东西,因而十足地成为肯定之物”。譬如一个奴隶,当他向主人说“不”时,他是一个反抗者。但同时,他又是一个说“是”的人,因为当他反抗时,他事实上肯定了主人与奴隶界限的存在。一个真正的反抗者,并非从奴隶变成新的主人。肯定与否定共存,才真正构建出反抗的价值,也就是人存在的价值。 加缪首先梳理和反驳了两种“反抗”:“形而上的反抗”和“历史上的反抗”。从历史上看,第一波有力的反抗是由几个时髦的文学人物完成的。首先是萨德,这位极端的反抗者发出最刺耳的“不”。 虽然27年的牢狱生涯都未让他产生妥协的思想,他却一边向世界要求着“绝对的”,一边用单调的摧毁着世界的“是”。“世界残酷地对待他,他也残酷 地回敬世界。”浪漫主义诗人波德莱尔创造了一种“美学”,艺术成为唯一的道德。然而这是一种奇特的否定美学,他们放浪形骸,却又与个人主义的享乐 主义脱不开干系。洛特雷阿蒙和兰波是花花公 子美学的继承者。加缪对作为诗人的兰波充满敬意,“令人赞美的大诗人,他的时代最伟大的诗人,闪电般的权威,这就是兰波。”但一联想到这位诗的魔法师、 通灵者自哈拉尔的来信中大谈金钱与收益,围着肚子的腰带里永远带着八公斤黄金,你就再也轻松不起来了。“难道这就是我们推荐给年轻人的神话般的英雄吗?” 加缪在总结“历史上的反抗”时说,历史上大部分反抗行为,最终都堕落为“革命行动”。革命无非就是杀人,无论是奴隶的骚乱、农民的起义,还是乞丐们的战 争、土包子的反抗,都遵循着一个“以命抵命”的等价原则。斯巴达克斯起义即是这样一个典型。斯巴达克斯带领角斗士们揭竿而起,驰骋于整个意大利,当神圣的 罗马城墙遥遥在望时,这支奴隶军队却停了下来,随即后撤,退回到他们最初出发的西西里。为什么要后撤?加缪说:“倘若这个城被毁,那么用什么来代替它 呢?”要知道,正是怀着对正义的渴望,怀着因受伤害而变得疯狂的爱,才使这些不幸的人们坚持到此时。但面对众神的原则,面对伟大的罗马城,他们退却了。他们本希望得到的是“平等的权利”,他们想成为与主人一样的人。如果奴隶军团攻陷了罗马城,他们以前的主人就会沦为他们的奴隶。所谓胜利,只不过是颠倒一下位置,杀更多的人。退却的斯巴达克斯开始溃败。他让人把一个罗马民吊在十字架上,让手下人明白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而他自己则不断的往前冲,希望遵循等价原则,与指挥罗马军团的克拉苏同归于尽。他始终也没能靠近克拉苏,却死在同为奴隶的雇佣兵的刀剑之下。一个罗马民的死,最终换来的是从卡普亚到罗马的大道旁竖起的六千个十字架。 以“革命”为关键词,加缪还考察了自年以来的历次革命运动。他不仅批驳了圣茹斯特的“断头台风格”,认为正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首先解开了断头台的缆绳(“以往属于上帝的一切此后都交给了凯撒。”),并对历史上一切革命的行为和“高尚的杀人者”展开批判。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反抗者的“不”与“是”的平衡一旦被破坏,反抗就会演变为与杀人的循环游戏。而一切现代革命,最终都会带来一个普遍杀人的时代:年革命带来的是拿破仑,年革命使斯大林上台,年代的意大利让墨索里尼掌握了,魏玛共和国招致的统治…… 真正的反抗者必须回到“不”与“是”的平衡上来。反抗既是一种生命的尊严,也是一种生命的创造。但任何反抗都不是简单地说“不”,因为仅仅说“不”,可能会沦为新的与非正义。“之所以存在反抗,是因为谎言、非正义与部分地构成了反抗者的生存状况。他若要坚持反抗,则要下决心完全不杀人与说谎,永远不同意一切杀人与的行动。他也不能让自己杀人与说谎。”也就是说,反抗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存在而去杀人,相反,是为了“创造我们现在的存在而活着,并让他人活着”。 在《反抗者》的最后一章,加缪提出了一种“南方思想”,这也是他的核心思想:一种与阴暗、暴戾的欧陆精神相对的地中海思想。加缪从小就在阿尔及尔的乡下长 大,那里的每一个街角都能看到大海,到处都有鸟儿拍打翅膀的声音,人也极具自然的美感,就像生活在健康的古希腊世界一样。加缪一直自视为一个乡下人,一个 外省人,一个与奥古斯丁和普罗提诺为邻的地中海人。他喜欢古希腊文化中静态的一面。如果说欧陆精神是被黑格尔和的精神现象学与历史辩证法所控制,那 么地中海思想就是沐浴着柏拉图和圣奥古斯丁的精神之光。“南方思想”是明净的、节制的、均衡的;是人道的、乐观的、理性的。 ————————————————————————————————————— 它可以意味着“这类事情持续得太久了”,“到此为止还可以,再超过就不行了”,“你走得太远了”,也许还意味着“有个界限是不可逾越的”。总之,这个 “不”肯定了一条界限的存在。从反抗者的某种感情中也可以发现这一界限的想法。这种感情就是他要将其权利扩展于这个界限之外,但越过此界限即有另外一种权 利约束他。因而,反抗行动同时也就是对视之为不可容的侵犯予以斩钉截铁的拒绝。朦胧地相信他有一种正当的权利。更确切地说,反抗者这时怀有他享有“…… 权利”的印象。从某种程度上说,反抗者若未怀有自己是理直气壮的这种感情,便不会有反抗。正由于此,反抗的奴隶同时既说“不”又说“是”。他在肯定上述界 限的同时,也肯定他所怀疑的一切,并想使之保持在这个界限之内。他固执地表示自己身上有某种东西“值得……”,要求人们予以关注。他以某种方式表明自己受 到的不能超过他认可的程度,以这种权利来对抗他的命令。 人厌恶对自己的侵犯。同时,在一切反抗中,他都完全坚持自己身上的某种意愿,因而必然坚信一种价值判断,在危难时仍坚定不移。直到此时,他保持缄默,陷入绝望之中,虽对不公正的境况仍加以接受。缄默,会令人认为他不进行判断,一无所有,而且在某种情况下他的确一无所求。绝望同荒诞一样,一般说来,对一切皆进行判断,并渴求之。而在具体情况下,却毫无判断,一无所求。沉默便清楚地表明这一点。然而,他一旦开口讲话,即使是说“不”,便表明他在判断与渴求。反抗者,从该词词源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他在主人的鞭笞下昂然行进,进行反抗,以自己所赞成的一切对抗自己不赞同的一切。并非一切价值观念都会引起反抗。但是一切反抗行动都不言而喻地以一种价值观念为依据。是否至少会涉及一种价值观呢? 从反抗行动中产生了意识的觉醒,不论它是何其朦胧。他突然意识到人身上有某种东西应该是属于自己的,哪怕这种情况为时短暂。这种自主性直到此时尚未为他所真正感觉到。在进行反抗之前,奴隶受了一切压榨。他那时甚至对主人的命令往往俯首帖耳,完全驯从,尽管这些命令比如今招致他拒绝的命令更应激起反抗。他对之逆来顺受,也许内心并不愿接受,但他更关心的是眼前的利益,而尚未意识到他的权利,于是保持缄默。当他失去耐心而变得焦躁时,便开始对以往接受的一切采取行动。这种冲动其实以往经常出现。奴隶在拒绝主人令人屈辱的命令时,同时便否定了他自己的奴隶地位。反抗行动使他比单纯的拒绝走得更远,甚至超出了为其对手确定的界限。如今要求以平等的身份对待自己。这种难以遏制的最初的抗争逐渐使人与抗争融为一体,使其一言一行均表现出抗争。他想让人们尊重他身上的这个部分,并将其置于其余一切之上,钟爱它胜过一切,甚至生命。这个部分对他说来成为至高无上的财富。奴隶以前处于委曲求全的境地,现在一下子要求获得“一切”,否则便“什么也不是”。他的觉悟随着反抗而苏醒。 人们看到,这种觉悟既想得到尚且相当模糊的一切,又想到了“什么也不是”,这表示有可能为此“一切”而牺牲自己。反抗者想成为一切,完全拥有他突然意识到的这笔财富,希望人们承认他身上的这笔财富并向它致敬,否则他便一无所有,也就是说,最终被支配他的力量剥夺一切。他如果被夺去他称之为的神圣事物,便会接受死亡这最终的结局。宁愿站着死去,而不跪着偷生。 根据某些卓越的作者的见解,价值“往往代表着从事实走向权利,从所渴望的事物走向合乎要求的事物(一般说来通过普遍渴望的事物)”。我们看到,从反抗争取权利是显然的。同样发生着“必须如此”走向“我要求如此”。不仅如此,还出现了一种概念,即为了今后共同的利益而超越个人。非“一切”即“一无所有”,这表明,反抗尽管产生于人具有极其严格的个人特性,却与流行的见解相反,令人对个人这一概念产生疑问。倘若个人在反抗中接受了死亡,并且终于为此死去,这表明他是为了超出个人命运的利益而牺牲的。他宁肯死亡而不愿否定他所捍卫的权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将这种权利置于他自己之上。他于是以价值的名义而行动,这种价值观念尽管依然模糊,他至少感觉到它对他与所有的人是共同的。人们看到,一切反抗行动所包含的这种观念使其超越了个人,它使个人摆脱了孤独状态,为其行动提供了合理性。存在于一切行动之先的这一观念驳斥了历史上的哲学,这些哲学认为价值观念是在行动的最后才获得的。注意到这一点是重要的。对反抗的至少令人怀疑存在有人的天性,而希腊人即这样认为。它与当代思想的见解也是相反的。既然自己身上无任何永恒的东西可以保持,为何要挺身反抗?奴隶起而反抗是为了同时代所有的人,因为他认为,这种命令否定了他身上的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不仅属于他自己,也是所有的人共同享有的,甚至包括侮辱与他的人在内。 有两个事实可以支持这一判断。人们首先会注意到,反抗行动从本质上讲不是自私的行为。无疑,它含有某些自私的考虑。但人们反抗的既是,也是谎言。此外,尽管反抗者有这些顾虑,但他怀着最强烈的情绪,豁出了一切,未保留任何东西。他为自己争取的是尊重,但也认为整个人类都理应如此。 其次应注意到,反抗并不仅仅产生于被者身上,当人们看到他人成为的受害者时,也会进行反抗。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他将别人看成是自己。应该明确指出,这并非一种心理上的认同,并非在想象中感到自己受到了侵犯。相反,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自己受到侮辱时并未反抗,而看到他人受到痛仰的侮辱却难以容。者在苦役犯监牢看到同伴受到鞭笞时,为进行而自杀。这足以说明上述见解。问题也不在于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当我们看到自己视为对手的人们遭受不公平时,也会产生反抗的情绪。这仅仅是由于有共同的命运。个人所捍卫的价值因而不仅属于他个人。这种价值是由所有的人形成的。人在反抗时由于想到他人而超越了自己。从此观点看来,人的互助性是天生的。只不过在当前的情况下,这种互助性是在镣铐中产生的。 反抗与怨恨 只要将由一切反抗所推断出的这种价值与怨恨之类完全否定的概念进行比较,即可明确其肯定的方面。塞勒便曾对怨恨的概念下过定义。的确,反抗并不仅仅是要求讨还某种东西的行为。怨恨被塞勒明确地定义为自我毒害,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萎靡不振。相反,反抗激励生命,帮助他摆脱现状,使静止的死水波涛滚滚。塞勒本人着重强调怨恨的消极方面,他注意到怨恨在女子的心理中占有很大位置。她们沉溺于渴望与占有。相反,论及反抗的起源时,有条原则便是活动过多与精力饱满。塞勒不无道理地说,妒羡极大地激起怨恨。人们妒羡自己所没有的东西,而反抗者则保卫已拥有之物。他不仅仅索要他不拥有或被剥夺的财富,而且他的目标是让人承认他拥有的东西。几乎在所有情况下,他认为这种东西比他所可能妒羡的东西更重要。反抗并不是现实主义的。依然按照塞勒的看法,怨恨在一个有力的或软弱的人物身上变成勃勃野心或尖酸刻薄。不过对这两种情况说来,人们都愿意成为与现在不同的另一个人。怨恨总是在自怨自责。相反,反抗者在最初的行动中,拒绝人们触及他的现状。他为其人格的完整性而斗争。他首先所追求的不是征服,而是要人接受。 最后,怨恨似乎乐于看到它仇恨的对象遭受痛苦。尼采与塞勒看到这种感情的一个绝妙例证,特杜利安在其著作的一个段落中告诉读者,天上幸福的人们最大的快乐是观看罗马帝国的皇帝们在地狱中煎熬的景象。诚实的人们观看有人被处死时也会产生这种快乐。相反,反抗原则上仅限于拒绝屈辱,而并不要求屈辱他人。只要其人格得到尊重,它甚至愿意尝受痛苦。 人们因而不理解塞勒何以将反抗精神与怨恨绝对地等量齐观。他对人道主义(他视之为人类的爱之非教形式)中的怨恨的批评也许适用于人类的理想主义的某些形式,或者恐怖的技术。这种批评若指向人对现状的反抗则是错误的。这种反抗使个人为捍卫一切人的共同尊严挺身而出。塞勒想指出,人道主义中含有憎恨世界的因素。人们一般地热爱人类,并不一定要热爱特殊的人。在某种情况下,这是正确的。当人们想到,他认为人道主义由宾萨姆与卢梭代表时,便会更好地理解塞勒的见解。然而,人们之间彼此的爱并非完全来之于利益的算计或对人类本性的信任,再说,这种本性只是理论上的说法。面对功利主义者与爱弥尔的家庭教师,有种逻辑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伊凡·卡拉马佐夫身上加以体现。可适用于反抗行动与形而上的反抗。塞勒通晓这一点,从而将其概括为下面的论断:“世上的爱并不太多,只能将其施加于人而不会施加于他物。”即使这种说法是真实的,它所表露出的绝望也不应该受到蔑视。事实上,他低估了卡拉马佐夫的反抗震撼人心的性质。相反,伊凡的悲剧产生于他虽有太多的爱,却没有爱的对象。由于这种爱无处发泄而上帝又被否定,人们于是决定以慷慨大度的同伙的名义把爱重新倾注于人类。 总之,我们至此所论述的反抗行动中,人们并非由于心灵贫乏而选择一种抽象的理想,也不是出于无谓的要求。人们渴望自己身上不能归之为思想的那些东西得到重视,这是只对生命有用的那一部分。难道这就是说任何反抗都没有怨恨的因素吗?并非如此。在仇恨的年代,我们看到相当多的这种情况。然而,我们应当从最广泛的角度来理解这个概念,否则会曲解它。就此而言,反抗在各方面都超越了怨恨,希思克利夫在《呼啸山庄》中提出,他看重爱甚于上帝,只要能与钟情的女子结合在一起,即使下地狱也无妨。这不仅是他受屈辱的青春在呼喊,也是整个一生惨痛的遭际的流露。同样的情绪使爱卡特说出令人惊愕的离经叛道的言辞:他宁愿同耶稣一道进入地狱,而不愿生活在没有耶稣的天国。这就是爱的流露。与塞勒相反,人们不能过分强调反抗行动中的肯定因素,这一因素使它与怨恨区别开来。反抗不创造任何东西,表面上看来是否定之物,其实它表现了人身上始终应该捍卫的东西,因而十足地成为肯定之物。 反抗的意义 然而,这种反抗以及它传达的价值难道不是相对的吗?随着时代与文化的变迁,人们进行反抗的理由的确在改变。显然,印度的贱民,印加帝国的武士,中非的原始人或最初的,他们进行反抗的动机并不是相同的。人们甚至以极大的可能性断言,反抗的概念对于这些确定的情况是没有意义的。然而,一个希腊奴隶,一个农奴,一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骑兵队长,一个摄政时期的巴黎绅士,一个二十世纪初的知识分子以及一个当代工人。即使他们反抗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毫无疑问,其反抗皆具有正当性。换句话说,反抗的问题只是在西方思想的范围内获得了确切的含义。倘若我们同塞勒一样注意到,在极其不平等的社会(印度的种姓制度),或相反在绝对平等的社会(某些原始社会),反抗思想都是难以表现出来的,我们的看法更加明确。社会中,惟有理论上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极大的不平等,才有可能出现反抗精神。因而反抗问题只在我们西方社会的范围中有意义。于是可以断言,这个问题是与个人主义的发展有关的,如果我们不会由于前面的见解而反对这个结论的话。 从塞勒的论述中所能得出的结论就是:在我们的社会中,从的理论方面来说,人们对人的概念意识在增强,而从这种的实际状况来看,却远远不能令人满意。事实上的并未随着人们意识的增强而成比例地增加。由此可得出下面的结论:反抗是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并已觉醒的人们的行动。但我们决不能说反抗仅仅涉及个人的权利。相反,从上面已经指出的互助性来看,反抗表现出人类在其生存活动中对自身的意识越来越广阔。事实上,印加帝国的平民或印度的贱民并未提出反抗的问题,因为在他们提出此问题之前,它已按照传统得到解决,答案是神圣不可触及的。在由神统治的世界中,之所以不存在反抗的问题,是因为人们从未想到要提出这个问题,它已经一了百了的得到一切答案。形而上学为神话所替代,再无任何诘问,有的只是永恒的答案与诠释,它们可能是形而上学的。然而,在人们进入由神统治的领域或从中走出来之后,便出现了诘问与反抗,这样他们便会欣欣然地进入与出来。反抗者只存在于进入神的领域或从中走出来之后。他致力于要求一种尊重人的体制,一切答案都应该是符合人性的,也就是说要合乎理性地表述出来。从这时起,一切诘问,一切言论,无不成为反抗,而在神的领域,一切言论皆是感恩行为。可以这样说,人的思想只有两个可能的世界,神的世界(用教的语言说就是圣宠的世界)与反抗的世界。此世界的消失即彼世界的出现。尽管另一世界出现是,其形式令人困惑。说到此,我们又涉及“一切”或“一无所有”。反抗问题的现实性仅仅由于某些社会今天想要远离神的领域。我们如今生活在非神圣化的时代。当然,人不能归结为反抗。但今天的历史以及其种种争论迫使我们不得不说,反抗是人的生存的基本方面之一。这就是我们历史的现实。我们除非逃避现实,否则便应该从反抗中找到我们的价值。当人们远离神及其绝对价值后,可以找到行为准则吗?这正是反抗要提出的问题。 我们已经可以确定在反抗的范围内所产生的朦胧的价值。现在我们应该思考,在当代的反抗思想与行动的各种表现形式中是否可以重新找到这种价值。若可以找到的话,则应该弄清其内容,但在继续探讨之前,应该注意到这种价值的基础是反抗本身。人类的互助性建立在反抗行动的基础之上,而反抗行动反过来又从这种互动关系中找到自己的根据。我们因而有理由说,任何反抗若意欲否定或摧毁这种互助性,则再不能称为反抗,实际上它此时已与同意杀人的行为无异。同样在神的领域之外,这种互助性只有在反抗的层面方可获得生命。反抗思想的真正意义即在于此。人为了生存一定要反抗,但这种反抗不应越过自身所发现的一个界限,这就是人们聚集在一起才开始生存。反抗的思想因而不能摆脱记忆:它永远处于紧张之中。当我们考虑它的行为与业绩时,应该思忖它是否忠于最初的崇高原则或者相反,它是否由于倦怠或冲动而忘记了崇高原则,沉迷于专制或者奴役。 这就是用反抗思想对世界的荒诞性与表面的荒芜开始进行深入思索而取得的最初进展。在荒谬的经历中,痛苦是个人的,一进入反抗行动,痛苦则成为集体的,成为众人的遭遇,一种具有奇特性思想最初的进展因而就是承认所有的人都有这种奇特性,而人类现实从整体上说由于远离这种思想与世界而受苦。使单独一人痛苦的疾病成为集体感染的瘟疫。我们每天所遭受的苦难中,反抗所有的作用犹如“我思”在思想范畴中所起的作用一样。它是第一个明显的事实,然而这个事实使人摆脱了孤独状态。它使所有的人都接受了第一种价值。我反抗,故我们存在。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