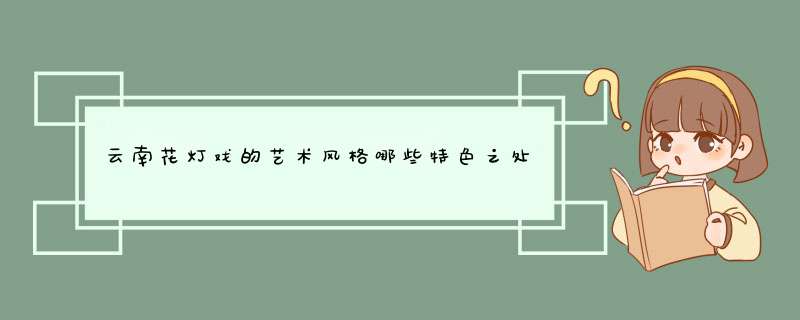
云南花灯戏作为花灯戏的一个分支,有着许多自己的艺术特色,尤其是它的表演形式、花灯的歌舞、花灯的音乐都有着独特的艺术特点和魅力。
云南花灯戏的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演出方式遍地撒,也就是演出不择地方。早期的花灯演出曾被称为过街灯、院坝灯、坝坝灯,非常自由随便,演出的班子也容易凑,所以花灯戏班在开始时,被称之为逗凑班。
二是贴近生活。花灯观察与表现生活的角度比起许多大型剧种与生活的距离也要近得多,因此它的内容男女老幼都懂,演唱的技艺也容易学会。在民间有俗语和顺口溜说:
头上梳鬏的会听,脚上糊牛屎的会唱。说我们的事,打我们的卦,唱我们的歌,用我们的帕。
云南花灯戏这种采取近距离对待生活的表现手法,使花灯的生活气息比较浓厚,它所反映的农村生活和市民生活古朴天真,关注农村及市民生活,体现了花灯观察生活别具慧眼的特点。这一特点适应了人们直率真情的表达。
三是花灯的音乐兼收并蓄了许多民歌小调,形成了许多支派。花灯有史以来就在云南广大汉族及少数民族杂居区广为流行,由于受到各地方言土语、风俗民情、音乐曲调的影响,形成了昆明花灯、玉溪花灯、楚雄花灯、建水花灯等许多支派。
昆明花灯较多地保留了明清小曲,玉溪花灯的本子戏比较多,楚雄花灯吸收了许多民歌小调,建水花灯的音乐和唱词、道白,他们都与当地彝族的民间语言及艺术有关系。另外,花灯的音乐多半是小调,音节规整、轻快、跳跃,有很强的动感,这与花灯剧载歌载舞的特点是一致的。
四是花灯音乐曲调的来源相当广泛。从搜集到的上千首曲调中可以看到,花灯的音乐曲调一部分源于明清小曲,大量的是源于民歌小调,还有的是从云南扬琴、宗教音乐及民族音乐中吸收的。
此外,还有一些是从兄弟省市的剧种中移植的。由于花灯吸收了多种来源的曲调,加上自己特有的演唱习惯、润腔方法,再结合花灯舞蹈、戏剧节奏及云南的方言土语,使花灯音乐具有了多样性与统一性相结合的特征。
五是云南花灯歌舞表演多。首先是载歌载舞,无论大戏小戏,花灯舞在剧中都占有较大比重,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一套表演方式。同时,为了很好地表现情节、人物,舞蹈中还有许多从生活中提炼的舞蹈动作。比如《夫妻打鱼》剧中的玉花扇划步、鲤鱼穿江,《乡城亲家》剧中人物何大发的跺蹲乌龙伸腿等。
在云南花灯表演中,歌舞占了很大比重。花灯的“歌”包括唱和打岔两部分,很少说白。“打岔”就是有韵的说白。老灯中很少有不押韵的道白,因此歌和舞就很容易在节奏上统一起来。
除了上述这些特点外,云南花灯的音乐是它区别于其他剧种的主要标志之一。
云南花灯音乐的结构短小,多为上下句或四个乐句组成的单乐段。音乐的节奏鲜明,流动性较强,乐句之间很少有较大的停顿,多从板上起句,在眼上落句。速度一般为中速或小快板,情绪明快、活泼、潇洒,旋律优美。云南花灯音乐的调式多为徵调式和羽调式,其次是宫调式和商调式,以五声的乐曲为主。
云南花灯的伴奏乐器有胡琴、月琴、三弦、笛子等,后来又增加了琵琶、扬琴等民族乐器,有的地方还使用了某些少数民族乐器。
云南花灯的剧目也有自己的特点。其剧目大约有200多个,分为花灯歌舞、花灯小戏与花灯大戏3类。较有影响的剧目有《探干妹》、《游春》、《刘成看菜》、《闹渡》等。云南花灯戏演出的许多剧目,都具有朴素单纯、健康明朗的民间艺术特色,充满着劳动人民的生活气息。
花灯戏的传统剧目不多,除去灯夹戏时期移植过来的滇剧剧目,共有两百出左右。其中,花灯歌舞剧目有《十大姐》、《大头宝宝戏柳翠》、《踩连厢》等,花灯小戏剧目如《三星贺寿》、《红回门》等。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大力整理传统剧目的同时,还新编了大型花灯戏《依莱汗》等近百个剧目。
云南花灯戏比较有名的代表剧目有《芦花记》、《小二黑结婚》、《金碧坊》、《依莱汗》、《梭椤寨》等,很具有代表性。
《芦花记》又名《鞭打芦花》,是云南花灯戏较早演唱的一个传统剧种,讲述的是孝子闵子骞的故事。闵子骞8岁丧母,后父亲续娶后妻姚氏,并又生下了闵革、闵蒙两个孩子。继母疼爱自己亲生的儿子,对幼小的闵子骞横加虐待,但闵子骞诚实敦厚,毫无怨言。
有一年临近年底,父亲驱牛车外出访友,让3个孩子跟着。闵子骞赶着车,当走到一村庄时,天气骤变,寒风刺骨,子骞战栗不已,手指冻僵,将牛缰绳和牛鞭滑落于地,牛车翻倒在路边的沟地里。
闵子骞的父亲特别生气,以为闵子骞真的像继母所说的那样懒惰,非常生气,拾起牛鞭怒抽闵子骞。不料鞭落处绽露出芦花,芦英纷飞。其父见状,惊奇不已。
这时,饥寒交迫的闵子骞已经晕倒在雪地里,其父撕开子骞的棉衣,见尽是丝絮,这才恍然大悟,知道是后妻虐待闵子骞,忙脱下自己的衣服裹住子骞。返回家中后,其父举鞭抽打后妻,并当场写下休书。
苏醒过来的小子骞却苦苦哀求父亲不要赶走后母,他诚恳地对父亲说:“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
意思是休了后母,自己和两个弟弟有可能落入另一个后母的手里,两个弟弟将来也会像自己一样受苦。父亲听了子骞的话,觉得非常有道理,放弃了休妻之事。继母深受感动,她痛改前非,从此对三个孩子一样看待。
《小二黑结婚》是新中国建立初期,昆明人民花灯剧团成立后排演的反映新生活的剧目。在当时排演时,在花灯的唱腔、表演方式的革新方面,花灯剧团都做了不少尝试。《小二黑结婚》讲述了发生在解放区的故事。
二诸葛和三仙姑是刘家峡的两个有名的人物。二诸葛叫刘修德,抬脚动手都要论个阴阳八卦、黄道黑道。有一年春旱,好不容易下了点儿雨,二诸葛掐指一算说:“今日不宜栽种。”
结果,错过了播种的好时机。不宜栽种就成了二诸葛的忌讳。三仙姑是于福的老婆,整日装神弄鬼,曾经在下神给金旺爹问病时,趁着空子偷偷告诉女儿:“灶上煮的米烂了。”
不巧恰被金旺爹听见。于是,米烂了便成了三仙姑的忌讳。三仙姑当巫婆足有三十年了。她年轻时风流俊俏,公爹看不惯,赶走那群常来耍贫嘴的小青年,媳妇却一病不起,请了神婆才见好。三仙姑从此便设香案下起神来。小青年照旧往来不断。
30年后,三仙姑已人老珠黄,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绣花鞋、镶边裤拢不住青年的心。虽说家中依旧热闹,但大家的心思却只在她儿女小芹身上,三仙姑不免心生嫉妒。
小芹18岁,乖巧伶俐,比她娘当年还漂亮,而人却十分正经,金旺兄弟都曾讨过没趣。
金旺一家是这儿的一窝虎,横行霸道,抗战时就做了不少坏事。打垮溃兵土匪后,村里没人愿意当干部,胡乱选了金旺做村政委员,兴旺做武委会主任,金旺老婆做妇救会主席。兴旺见小二黑有趣好玩,就提名他为青抗先队长。二诸葛不乐意又无可奈何。从此,金旺兄弟更是无法无天。
小二黑是二诸葛的儿子,在反扫荡时打死过两个敌人,人又长得精神,人见人爱。虽没上过学,跟着爹也读了不少《阴阳宅》之类的书。他聪明伶俐,18岁了,大家还把他当小孩儿逗,常说“不宜栽种”的话。小二黑脸上挂不住,见人就躲,再也不信八卦阴阳了。
小二黑和小芹相好已经两三年了,可二诸葛忌讳多,不同意,硬是为儿子收了个八九岁的童养媳。小二黑却不认账。
金旺兄弟对小芹怀恨在心,故意找茬儿,说小芹勾引小二黑,为此召开斗争会,武委会这边斗小二黑,妇救会那边斗小芹。幸得村长是个明白人,说小二黑是出于真情,谈恋爱不犯法,童养媳不算数,这一场争斗才了结。
斗争会后,小二黑和小芹的事便公开了。三仙姑嫉妒小芹,要真是二人结了婚,她跟小二黑就连句笑话也说不得了。于是急急忙忙为小芹找婆家,终于收了一个退伍军官的礼帖,认为了却了一桩心病。小芹哪里肯依,她说:“谁收了人家的东西谁跟人家去!”
说完就去找小二黑商量对策。哪知兴旺等人早有预谋,他们从暗地里跳出来,大喊捉奸“拿双”,并把二人捆了起来。小二黑理直气壮,毫不胆怯。
儿子被捕,二诸葛心神不定,又是占卜又是掐算,悔不该小二黑当什么队长,招此大祸。第二天一早,他便赶往区里,路上得知儿子被放,金旺兄弟被捕在押。来到区里,听说上边允许儿子和小芹结婚,便满心不痛快,说乡间七八岁订婚多着哩,请区长恩典恩典,说他俩命相不对,是一辈子的事。可是,这里是民主政府,新社会主张婚姻自主,他二诸葛不同意有啥用?
三仙姑对女儿并不挂心,直到交通员传她,她才打扮得花枝招展来到区上。她满头首饰、浓妆艳抹,惹得一群妇女指指点点,哈哈大笑。而区长竟把她认作前几天跟婆婆生气的年轻媳妇。偏偏又有人讲出了那“米烂了”的故事,三仙姑羞愧难当,恨不得一头碰死。
小芹当众表示不同意她娘操持的那门亲事。区长吩咐三仙姑把所收的彩礼统统退还。三仙姑只得答应。金旺兄弟被押,人人称快。在群众大会上,村民们纷纷检举二人的罪状。区里根据事实,判处二人15年徒刑。大会后,村干部改选,大家再也不敢投坏人的票了。
三仙姑回来后,对着镜子研究一番,也觉得有点不像话,便改换装束,30年来装神弄鬼的那张香案也悄悄拆去了。二诸葛也在老婆孩子的劝说下,放弃旧业。小芹和小二黑终于结了婚,小两口十分和美,邻居们都说是村里的第一对好夫妻。
卧房里,小二黑学唱三仙姑的“前世姻缘由天定”,小芹则学说二诸葛的“恩典恩典,命相不对”。淘气的孩子们去听房,学会了这两句话,就给两位神仙起了新外号,三仙姑叫“前世姻缘”,二诸葛叫“命相不对”。
《金碧坊》是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创作的新编清装历史剧,演绎了神马、碧鸡的传说。在云南古老的传说中,神马、碧鸡是吉祥、美好的象征。花灯剧《金碧坊》再现了当年老昆明的市井生活,以全新的方式,将金碧坊古老的传说重现在舞台上,且以悬念牢牢抓住观众。
《金碧坊》的故事发生在清康熙年间的1687年。木匠曾石楠立志重建金碧坊,实现民众的心愿,不料横祸飞来,突然成了罪犯。他的表弟潘福来,乘人之危骗取了曾家祖传的图样。知县张廷树心有疑惑,要追查真相,冒着风险为曾石楠做担保使其走出牢狱。知府高志远浮躁轻信,急功近利,委任潘福来当上了重建二坊的主管。还有3个女人搅和在其中,起到或好或坏的作用。
剧中真与假纠缠在一起,正与邪的明里暗里较量,使剧情波澜起伏,悬念丛生,直至最后才一切水落石出。
《梭椤寨》是由云南省花灯剧团创作演出的大型花灯剧,取材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原型。
改革开放之初,云南文山石洞村的彝族妇女任应珍,经过进城卖菜、开办碾米加工企业和兴建采石场而富裕起来。为了报答乡亲,她宣布在村里实行点电灯、碾米、磨面“三不要钱”。但由于种种原因,时隔不到一年,任应珍破产了,又回到文山农贸市场卖菜了。
2008年初,云南省花灯剧团决定采用这个剧本以后,邀请另一位云南本土剧作家马良华加盟对剧本修改加工。马良华与省花灯剧团团长、编导孙晋昆对这个题材作了深入开掘,把该剧的地点从文山移到弥勒阿细人居住的梭椤寨,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展开剧情。
在剧中,创作人员融入阿细人远祖“有猎物,共分割”的遗训,以及阿吉姆从小是孤儿,靠乡亲们哺育成长的身世,阿吉姆致富不忘众乡亲,在村里实行“三不要钱”以后,从县长到村长层层对她加封的情节,赋予该剧较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增强剧情的合理性和阿吉姆这个人物的可信性。
剧中主人公阿吉姆以一己之力,承担了太多的社会责任,终于难以为继。经过反思,阿吉姆最后跪碑谢罪,她用上级奖励的人民币10万元买来桃核苗,建农村生态园,带领乡亲们走上共同致富之路。
总之,云南花灯剧以其突出的地方特色,和唱、念、做、舞中鲜明的民间艺术特色,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它质朴而不矫揉造作,健美而又粗犷,具有十分浓郁的云南地方民族特色。
玉溪花灯以新灯驰名全滇,由一批花灯艺人对老灯彻底改造,推陈出新,创作出一大批新花灯剧目,把老灯由乡间的团场歌舞推向舞台戏剧化,正式成为一个剧种,进而在全省推广普及,以至玉溪花灯成为云南花灯的代表。在 20世纪初年,玉溪经济迅速发展,市民阶层唱花灯日盛。玉溪花灯艺人从滇戏等其他剧种中吸取养分,改造花灯,花灯发生了三大变化:一是创作了一大批新灯剧本;二是花灯进省城昆明,形成专业性质卖票演出;三是出现一批知名的花灯艺人。这三大变化,标志着新灯取代老灯的全面完成。
在新灯中,由玉溪艺人创作的反映农村青年男女爱情与家庭生活的剧目《双接妹》和《出门走厂》,深受农民欢迎。在新灯发展过程中,由滇剧移植或根据善书说唱本改编了《蟒蛇记》、《白扇记》、《金铃记》等大本和连台本戏。演出的地点也由原来的农村院坝广场走向灯楼或饲堂古庙中的戏台。 1938年前后,王旦东等人创作了《张小二从军》、《茶山杀敌》等宣传抗日救国的现代戏,以玉溪花灯艺人为主组成农民救亡灯剧团到昆明及滇西、滇南等部分地区巡回演出,扩大了玉溪花灯在省内的影响。新灯的崛起,吸引了一些滇剧演员参加花灯的演唱,他们有的改唱灯调,有的在演唱移植为花灯的滇剧剧目中仍唱滇剧声腔,也有的花灯艺人学唱滇剧,因而出现了“灯夹戏”的状况。1949年建国前夕,在昆明、玉溪等地作专业、半专业演出的花灯园子就有近10个,年节时临时组合演出的业余灯班就更多。玉溪新灯的发展,以剧目为中心,带动了舞台艺术的发展,在表演上,行当的划分由简单渐趋复杂。一些艺人开始走向专业化,有的在艺术上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较有声望的有佘四(佘永宁)、申六(申国文)。音乐逐渐形成以“道情”、“走板”、“虞美情”、“全十字”、“五里塘”五大调为主的曲牌体系,并开始在艺人中出现风格不同的演唱及表演。 流传在澄江县阳宗小屯村的关索剧,为玉溪地区一个属古老傩戏范畴的剧种。此剧种何时形成,是本地原有还是外地传入,尚待考证。据关索戏老艺人龚向庚提供的情况推断,此剧种可能是外地的一个傩戏支派,在清初顺治年间传入小屯。初为古代用以驱邪逐疫的傩祭舞蹈仪式,后来逐渐从傩舞向着表达故事情节的小戏形式发展。逐渐发展成娱神娱人兼有的古老而独特的戏剧。澄江的傩戏为何以相传为蜀汉大将的关索命名,无文献可考。关索剧的表演特点是不设舞台,不化妆,也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戴上面具(脸壳),穿上服装,带上兵器即可出场表演。行当有生、旦、净三行,而且多以净行为主,角色以面具和服饰区别。演出时无弦索伴奏,全用鼓点(也不正规)指点起落。一般情况是由小军或马童先上场,道说情况以后,即开始各种各样的翻滚动作以吸引观众,继而生角上,在表演中说说唱唱,唱唱打打,没有固定程式(也可能是继承不全),演员可以自由发挥。关索剧的声腔比较复杂,为无弦伴奏,伴唱参杂其间。有说源于高腔,但从某些曲调分析,又杂合当地民歌小调,颂佛唱经的旋律,更为明显的是吸收滇剧腔调。无固定板式,演唱者不受音域节奏的限制,即便同一曲调,各人所唱均有。关索戏曲于年节演出。演出期间,有一套成规仪式贯串始终。如每年演出前的祭药王、练武。正月初一日起开始演出时的按日出巡、踩村、踩街和踩家,每次演出时开头第一个节目必演《点将》,当日演出结束后的辞神,正月十六日全部演出结束后的装戏箱、送药王,均有其固定的程序后要求。
小时候,应该是一直到小学快毕业吧。我很喜欢去看“跳花灯”。“跳花灯”是人去世了,女儿和姐妹(村里人称出钱请人跳花灯的人为”后家”)会请”跳花灯”的人去送死者最后一程,热热闹闹让去世的人走吧。上祭的晚上,会跳很长时间,大概八点一直到十二点吧,“后家”越多,跳的越多越热闹。
在四年级之前不上晚自习,每场花灯都不会落下的,早早做完作业吃完晚饭等着爷爷或者爸爸带我去,去到去世人的家里遇上认识的小伙伴,如果花灯还没开始,就会一起跳皮筋或者丢沙包等着。没遇上周末的话,可讨厌第二天还要早起上课了,爷爷说,明早要早起,回去了。不不,再看一个。一看就到十一点多,第二天早上起不来了。上晚自习后,遇到周末才能去看了,最好的是可以看到结束。
上祭后一天是出殡,出殡也要跳,奶奶领着我,从逝者家开始,一路追着出殡队伍,到绕棺才结束。人很多,跑得慢了,还看不见。还有人卖吃的,我最喜欢吃草莓冰淇淋,可是有些贵,不是每次都买的。
“花灯”是很有民族内涵的东西,在我们村,彝族舞曲最受欢迎,三步弦演的最多,男女一起。印象最深的一出是,男的背着弦子,女的挽着男的手,一起向前,一起退后,步子很有特色,找不到语言去形容。
喜欢看花灯,可能是小时候可以玩的太少了。现在去看花灯的小孩很少了。现在我也不太喜欢看了,今晚舅爷去世了,爸妈要请人跳花灯,跟着去看。就那样想起了那段看花灯的时光。
看到跳花灯的人那样开心,看的人也很开心。小时候的我也是那样开心,就连外祖母去世时,看花灯时我竟也是那般开心,什么都不知道。
现在却开心不起来了。看着跳花灯的场景,想着这个场景以后会出现在爷爷家外公家的院子里,我就害怕。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辈老了,虽说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但是对于自己而言,当面对这样的事时,害怕拒绝,不忍面对。害怕改变,害怕回家以后见不到熟悉的人,熟悉的事。
云南省花灯剧是云南省各地花灯剧的统称。流传于云南全省及贵州的盘县、四川的会理一带。花灯在长期流传中,由于地区不同,先后形成9个支派:昆明、呈贡花灯,玉溪花灯,弥渡花灯,姚安、大姚、楚雄、禄丰花灯,元谋花灯,建水、蒙自花灯,嵩明、曲靖、罗平花灯,文山、邱北花灯,边疆地区花灯。它们彼此大同小异,基本特色相似。
云南花灯戏是一种汉族戏曲剧种。渊源于明代或更早一些时候的民间“社火”活动中的花灯,流行于全省各地和四川、贵州个别地区。 由于各地语音有别和艺人演唱的不同,流行在不同地区的花灯又接受了不同的曲种、剧种或民歌小调的影响,故云南花灯又分有昆明、呈贡花灯,玉溪花灯,弥渡花灯,姚安、大姚、楚雄、禄丰花灯,元谋花灯,建水、蒙自花灯,嵩明、曲靖、罗平花灯,文山、邱北花灯,边疆地区花灯等九个支派。 云南花灯戏演出的许多剧目,都具有朴素单纯、健康明朗的民间艺术特色,充满着劳动人民的生活气息。
明中叶即公元1454年前后,云南杨林人兰止庵曾写过《性天风月通玄记》传奇;清初(1657年)云南人何蔚文写过五个传奇剧本。这是目前已知的云南最早的戏剧创作活动。清康熙年间(1701年)云南开始出现专业戏班,曾有四个戏班在昆明建立乐王庙。
清乾隆年间(1746年)秦腔、石牌腔、楚腔、弋阳腔等传入云南。另据元谋花灯艺人张万育称,元谋花灯相传已有十三代。此外,在花灯的曲调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明清小曲,如挂枝儿、打枣竿等,都是流行与明万历以后直到清初的民间小曲。据此推算,作为一个剧种的花灯,早在明末清初就已具雏形。云南花灯在其发展历史上曾经历了四个阶段。
“灯夹戏”时期。1938年,云南农民救亡灯剧团被迫解散,花灯艺人熊介臣在昆明、玉溪一带教灯、唱灯。1946年熊介臣在昆明庆云茶室连唱三天花灯,受到欢迎,该茶室随后改为花灯园子,成为云南第一个花灯剧场,从此形成固定的职业班社。
为适应职业演出的需要,花灯艺人开始大量移植滇剧剧目,如《四下河南》、《滴水珠》、《朱砂痣》、《狸猫换太子》、《红灯记》、《纱灯记》等,同时进一步学习吸收滇剧的表演程式、服装道具、舞台装置等。这种以花灯曲调唱滇剧剧目的方式,时称“灯夹戏”。
云南花灯音乐
一、省内外大量民歌小调
一部分仍是省外流传的民间小调。较早期传入的如流传南方部分省区的(阳雀调)、(货郎调)、(十二属)等,在花灯中作为小唱、歌舞曲调或戏剧插曲使用。约于清末民初,又有一批小调如流传全国各地的(虞美情)、(烟花告状)、(掐菜苔)、(孟姜女调)等传入,在部分地区被吸收为花灯小唱曲调或戏剧插曲。
另一部分是产生于云南各地的民间小调。如滇西一带广为流传的(朝山调)、(小小葫芦开白花),滇中一带的(出门调)等,被吸收为花灯戏唱腔。滇西的代(赶马调)除曲调外,其故事内容还为花灯戏《开财门》所吸收。再一部分是云南各族的山歌及舞蹈歌。姚安、楚雄一带的汉族山歌(坝子腔)、(倒板腔),彝族山歌(小变腔)等,滇西各地的彝族歌舞曲调(打跳调)、(跳罗)、(傈课灯)等,也被吸收为花灯戏唱腔或歌舞曲调演唱。
云南过去称演花灯为“唱灯”,也称“簸箕灯”,言其在广场围成圆圈演出。历史上,花灯演出多为灯社,会火,逢年过节,迎神赛会就演花灯。元谋的红岗花灯,据说可推到明万历年间(1573-1642年);玉溪花灯,据说也可推到明代。清雍正时,吴应枚在《滇南杂咏三十首》中的一首诗中写道:“呜咽芦笙和口琴,依稀声调杂南音。新腔草竿何许打,莽仗于今尽革心。”原注有“芦坚、口琴,野人乐器;打草竿,曲名,男妇俱能歌。”可知,当时打草竿(即打枣竿)已在滇南一带传唱,并用民族乐器伴奏,且“男妇俱能歌”;“依稀声调杂南音”则反映外来曲子,正处在演变过程中。据有关资料记载,清顺治年问(1644-1661年)昆明附近的花灯歌舞演出,已较普遍。
作为花灯剧,则晚于花灯歌舞。从较早的一些花灯剧目的内容看,可以在清乾隆年间成书的《缀白裘》中找到蓝本。如花灯剧《补缸》、《凤阳花鼓》和《乡城亲家》,分别源于《缀白裘》第6集的《买胭脂》、《花鼓》和《探亲》、《相骂》;而花灯剧《借亲配》、《瞎子观灯》则源于《缀白裘》第11集的《借妻》和《看灯》、《闹灯》。由此推之,作为花灯剧的出现,大约不会早于乾隆时期。因当时正是我国西部的许多民间戏曲兴盛的时候。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