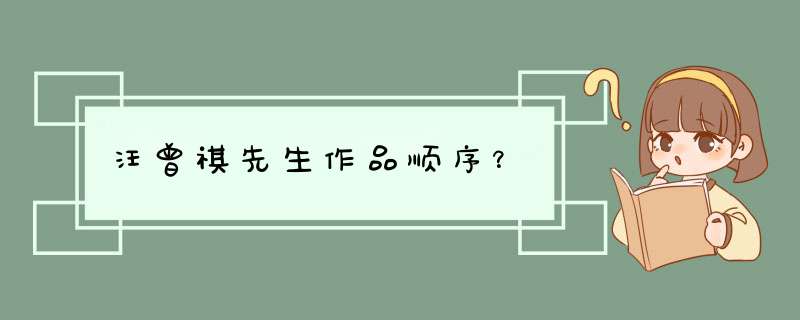
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大学期间,汪曾祺与同学创办校内的《文聚》杂志,并不断在杂志上发表诗歌、小说。
1944年,为生活计,汪曾祺在昆明北郊观音寺的一个由联大同学办的“中国建设中学”当教师,在两年的教学期间,汪曾祺写了小说《小学校的钟声》,重写小说《复仇》。后由沈从文推荐给郑振铎在上海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发表。此外,还写了小说《职业》、《落魄》、《老鲁》等。这期间汪曾祺与同在中国建设中学任教的施松卿相识,并建立了恋爱关系。
1946年秋,汪曾祺由昆明到上海,经李健吾先生介绍,到民办致远中学任教师两年,直到1948年初春离开。这期间,写了《鸡鸭名家》、《戴车匠》等小说。
1948年初春,汪曾祺离开上海到北京,与在北京大学外语系任助教的施松卿会合,临时借住在北京大学。失业半年后,才在北京历史博物馆找到工作。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3月,汪曾祺报名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在武汉被留下来参与接管文教单位,后被派到第二女子中学当副教导主任,干了一年。
1949年4月,汪曾祺的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中的一种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汪曾祺初期作品8篇:《复仇》、《老鲁》、《艺术家》、《戴车匠》、《落魄》、《囚犯》、《鸡鸭名家》和《邂逅》。5月,与施松卿结婚。
1950年,北京市文联成立。汪曾祺从武汉回到北京,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
1954年,汪曾祺创作出京剧剧本《范进中举》,后获北京市戏剧调演一等奖。秋,调离北京市文联,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任《民间文学》编辑。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他因这篇短文受到批评,但并未划定为右派。
1958年夏,被补划为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
1960年,汪曾祺被摘掉右派帽子,结束劳动,暂留农科所协助工作。
1961年春,农科所让汪曾祺到设在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画一套马铃薯图谱,可惜画稿毁于“文革”中。
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年底,汪曾祺调北京京剧团任编剧。
1963年,《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这是汪曾祺的第二个作品集。
1964年,汪曾祺等人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执笔改编同名京剧,由北京京剧团演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观看并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祝贺演出成功。
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久,汪曾祺即因“右派”问题被关进“牛棚”,但1968年迅速获得“解放”。
1970年5月21日,汪曾祺因参与京剧《沙家浜》的修改加工有贡献,而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
1977年,民间文学论文《花儿的格律》发表,这是汪曾祺“文革”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汪曾祺深受鼓舞,创作热情逐渐高涨。
1979年,小说《骑兵列传》在《人民文学》第11期发表,这是汪曾祺在“文革”后发表的第一篇小说。
1980年,小说《受戒》在《北京文学》10月号发表。
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4月,《大淖记事》在《北京文学》发表。这一年汪曾祺的佳作连续发表,小说创作日趋活跃。10月,应高邮县人民政府邀请,汪曾祺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访问。
1982年,汪曾祺新作不断。
1983年,汪曾祺的创作更趋活跃,在全国各地发表小说、散文、评论等近20篇。
1985年,在年初结束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理事。
1987年2月26日,汪曾祺在京入党。4月16日,汪曾祺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云南访问。10月,应安格尔和聂华苓夫妇之邀,汪曾祺赴美国参加国际写作活动,历时三个多月。
1988年,小说无新作,间或发表些散文、随笔。
1989年1月,《北京文学》与台北《联合文学》采取同步行动,同时出汪曾祺作品专辑。
1990年2月24日,汪曾祺写散文《七十抒怀》。
1991年5月,《蒲桥集》由作家出版社再版。
1992年4月,散文集《旅食集》由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
1993年6月,以故乡高邮为背景的小说集《菰蒲深处》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1995年春,应台湾《联合时报》邀请,汪曾祺赴台参加“两岸三边文学问题座谈会”。
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终因抢救无效而不幸去世,终年77岁。
汪曾祺(192035~1997516),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
主要作品
短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异秉》《羊舍一夕》。
小说集:《邂逅集》《晚饭花集》《茱萸集》《初访福建》。
散文集:《逝水》《蒲桥集》《孤蒲深处》《人间草木》《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
艺术小品集,手稿《羊舍一夕》;《汪曾祺:文与画》。
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
剧本京剧:《沙家浜》(主要编者之一)。
京剧:《范进中举》。
扩展资料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傍晚出生于江苏高邮城镇的一个旧式地主家庭。
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贡”。
父亲:汪菊生(1897-1959),字淡如,多才多艺。
生母:姓杨,在汪曾祺三岁的时候因肺病去世;
第一个继母:姓张,后也死于肺病;
第二个继母:姓任,伴随汪曾祺的父亲度过漫长而艰苦的沧桑岁月,汪曾祺对她很尊重。
长子:汪朗
儿子:汪朗,汪明,汪朝
参考资料:
汪曾祺受到沈从文的影响,而很少有人意识到“青出蓝而胜于蓝”。如果就作品的丰富性和成熟度而言,汪曾祺已经将沈从文的审美精神进行了扩展和延伸,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沈从文的价值在于对乡村的抒情性描写和摒弃意识形态的叙事态度,他从梅里美、屠格涅夫等古典主义作家那里汲取营养,开创了中国风俗小说的先河。汪曾祺成功地继承了老师淡化意识形态的叙事态度和诗化、风俗化、散文化的抒情精神,但汪曾祺将沈从文的视角从乡村扩展到市井,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一般来说,对乡村的描写容易产生抒情、诗化意味,在欧洲的文学传统和俄罗斯文学的巨星那里,对乡村的诗意描绘已经有着庞大的“数据库”,在中国文学传统里,虽然没有乡土的概念,但是中国的田园诗歌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山水游记、隐士散文,对乡村的诗意描绘和诗性想像也有着深厚的传统积淀。而对于市井来说,中国文学少有描写,更少诗意的观照。比如《水浒传》,作为中国第一部全方位的描写市井的长篇小说,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水浒传》里的市井很难用诗意来描写,这是因为市井生活和乡村生活相比,有着太多的烟火气,有着太多的世俗味。但生活的诗意是无处不在的,人们常常说不是生活缺少诗意,而是缺少发现诗意的眼睛。汪曾祺长着这样一双能够发现诗意的眼睛,他在生活当中处处能够寻觅到诗意的存在。好多人写汪曾祺印象时,会提到他那双到了晚年依然充满着童趣和水灵的眼睛。眼睛是心灵的外化。汪曾祺那双明亮、童心的眼睛让他在生活中发现了一般人忽略或不以为然的诗意。像《大淖记事》、《受戒》这类带着乡村生活的题材自然会诗意盎然,当然在汪曾祺的同类题材作品中,这两篇的诗意所达到的灵性程度和人性诗意也是同时代作家无人能及的。而在《岁寒三友》、《徙》、《故里三陈》等纯粹的市井题材的小说中,汪曾祺让诗意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当然,或许有人说,描写故乡生活的“朝花夕拾”,容易带着记忆和回忆的情感美化剂,容易让昔日的旧人旧事产生温馨乃至诗意的光芒,因为故乡是人的心灵出发点,也是归宿点。但当你打开汪曾祺的《安乐居》、《星期天》、《葡萄月令》等以北京、张家口、昆明、上海为背景的作品,还是感到那股掩抑不住的人间情怀、日常美感。汪曾祺能够获得不同文化层次、不同地域读者的喜爱,是有道理的。市井,在汪曾祺的笔下获得了诗意,获得在文学生活中的同等地位,而不再是世俗的代名词,而是人的价值的体现。汪曾祺自己意识到这种市井小说的价值在于“人”的价值,他说,“‘市井小说’没有史诗,所写的都是小人小事。‘市井小说’里没有‘英雄’,写的都是极其平凡的人。‘市井小说’嘛,都是‘芸芸众生’。芸芸众生,大量存在,中国有多少城市,有多少市民?他们也都是人。既然是人,就应该对他们注视,从‘人’的角度对他们的生活观察、思考、表现。”可惜这样的文学创造价值被人忽略太久。
就语言的层面而言,沈从文可谓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都是那么的精确和自然。但不难看出,沈从文的小说语言显然带着新文学以来的痕迹,这个痕迹就是西方小说的文体,当然这就造成新文学的文体与翻译的文体形成了某种“同构”。在白话文草创时期,新文学的写作自然会下意识地接受翻译文体的影响,像鲁迅的小说语言和他翻译《铁流》的文体是非常相像的。沈从文在同时代的作家中,是对翻译文体过滤得最为彻底的作家,但毋庸置疑,沈从文的小说语言虽然带着浓郁的中国乡土气息和民间风味,也带着“五四”新文学的革新气息,但读沈从文的作品,很少会去联想到中国的古典文化和中国的文人叙事传统。而汪曾祺比之沈从文,在语句上,平仄相间,短句见长,那种比较欧化的长句几乎没有,读汪曾祺的小说,很容易会想到唐诗、宋词、元曲、笔记小说、《聊斋》、《红楼梦》,这是因为汪曾祺自幼受到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对中国文化的传统有着切身的体验和感受。比沈从文的野性、原生态要多一些文气和典雅。作为中国小说的叙事,在汪曾祺这里,完成古今的对接,也完成了对翻译文体的终结。翻译文体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由来已久,也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诞生,但是翻译文体作为舶来品,最终要接上中国文化的地气。汪曾祺活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历史造就了这样的机会,让人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叙事”。尤其是1978年以后,中国文学面临着重新被欧化的危机,面临着翻译文体的第二潮,汪曾祺硕果仅存地提醒着意气风发一心崇外的年轻作家,“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汪曾祺作为“现代”文学的过来人,在当代文学时期仍然保持旺盛的创作力,他不是那种只说不练的前辈自居的过来人,他的提醒虽然不能更正一时的风气,但他作品的存在让年轻人刮目相看,心服口服。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