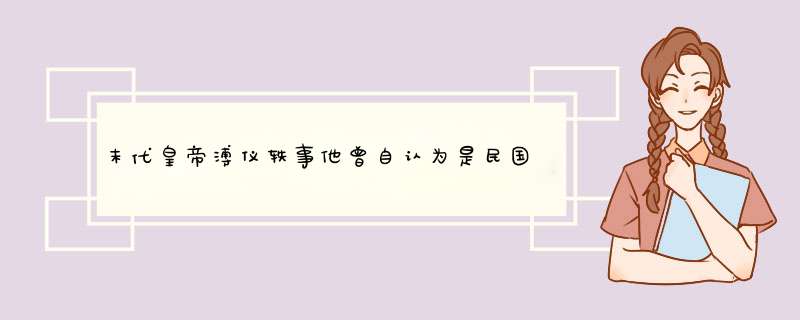
“我是爱新觉罗溥仪,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大的汉奸。今天,我站在祖国庄严的法庭上,指证推行侵略政策、操纵伪满洲国政权、奴役东北人民的日本帝国主义战犯武部六藏和顾海忠。”
1956年6月至7月,最高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沈阳和太原审判了45名日本战犯。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日本战犯在中国的首次审判,45名战犯全部认罪。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拉开了侵华战争的序幕。25年后的1956年6月9日,最高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开始在沈阳审判36名日本战犯。
“日军侵华始于沈阳,止于沈阳。这就是命运。”当时特别军事法庭84岁的书记员全对此表示遗憾。
近日,全和时任特别军事法庭副庭长袁光的女儿袁赛莎接受新京报采访,揭开这段历史。
末代皇帝溥仪当场指认日本战犯。
1956年7月2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中国“末代皇帝”溥仪身穿深蓝色囚服,从法庭西南门缓缓步入法庭。所有的目光和摄影师的镜头都聚焦在他身上,他的囚服号码是“981”。
这是溥仪第一次以战犯和证人的身份出庭。"又高又瘦,脖子很长,戴着黑框眼镜。"这是全第一次见到这位“末代皇帝”。
此时作为证人,他指的是伪满洲国总务厅副厅长顾海忠。
当他在证人席上站稳后,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是爱新觉罗溥仪,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大的叛徒。”
“今天,我站在祖国庄严的法庭上,指证推行侵略政策、操纵伪满洲国政权、奴役东北人民的日本帝国主义战犯武部六藏和顾海忠。伪满洲国各部的日本副部长,各省的副省长,各县的副县长,都是掌握实权的日本人。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操纵和支配网络。”
全安德宇,溥仪的见证,至今印象深刻。作为书记员,他把所有的话都录了下来。
中国自建国以来首次审判日本战犯。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对日本战犯的首次国内审判。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宣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议:审判和处理最后一批关押在中国的日本战犯。时任最高法院刑事庭庭长的钱佳担任最高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庭长,时任解放军军事法庭副庭长的袁光、时任最高法院刑事庭副庭长的朱耀堂担任副庭长,最高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庭8名法官担任审判员。
袁赛莎曾多次听到父亲袁光等参与庭审的长辈说起庭审时的情景。
袁赛沙回忆,父亲和长辈经常提起一个叫张葡萄的老人。那是审判的第一天,张普涛站在证人席上,指控时任日军骑兵旅旅长中将的藤田茂部队在山西安义县上段村杀人放火。在指控过程中,这位62岁的老人气得浑身发抖,流着泪,想跳过桌子扑向藤田茂
据供述,他曾教导下属“杀人比开枪更有效”、“无辜婴儿被杀”在被杀的人中,张葡萄一家也包括在内。
多重意识形态攻势导致战犯认罪。
全回忆说,当这些战犯第一次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时,虽然他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崩溃了,但他们侵犯的思想
1954年3月,根据毛泽东、周恩来“转移干部,重建监狱”的指示,要做好审讯工作,查清他们的犯罪证据,让战犯认罪服法。要改造好他们,不要改造死他们”,最高检察院从中央和各省市有关部门调集366名干部组成东北工作组,专门负责对日本战犯的调查和审判工作。
随后,东北工作组先后赴全国12个省份开展调查取证,查阅卷宗8000余份,提取证人证言26700份。这4314万页的讯问调查取证核实材料,屋里装不下,只好在外面搭帐篷存放。
1954年,中国派人通过日本红十字会向日本的家属讲述战犯的情况。很多家属20多年没有这些人的消息,以为他们都死了。知道他们还活着,他们写信,邮寄东西甚至去监狱探望,希望他们快点坦白。
后来战犯管理所组织战犯看日本**,有原子弹,混血儿,二十四只眼睛。当他们看到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家人都倒下了,看到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沉重后果,他们开始忏悔战争罪行,认为这样的结果是日本的战争造成的。
“当时战犯管理所还带他们参观了丹东水库的建设和鞍钢的钢铁生产。他们逐渐意识到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全安德宇回忆说,不仅如此,根据中央政府“改造日本战犯”的指示,战犯管理所对战犯采取了人道的管理方式。第一,尊重人格,不打不骂;二是照顾生活。长官有小灶,伙食标准由中央定。小官是中灶,下一个是大灶。战犯也可以读书。全认为,正是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和思想上的种种攻势,才使日本战犯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战争罪行。在如山的铁证和意识形态攻势下,这些战犯的思想堡垒开始崩塌。
1950年,在解放军战士的监视下,中国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同犯人一起走下开进站台的一列闷罐火车。溥仪走进洗手间,用刀片割开血管。战犯管理所所长的推门喊叫声把溥仪带回到42年前。当时不足三岁的他,按照慈禧太后的懿旨,进宫登基,当了宣统皇帝。溥仪从小在唯我独尊的环境中长大,孤独而缺少管教。辛亥革命后,他被废除。1922年,溥仪结婚,皇后婉容,淑妃文秀。1924年,做着复辟梦的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到天津做了寓公。1934年,日本吞并中国东北,扶植溥仪当了伪满州国的皇帝,虽然他只是从属于日本关东军的“儿皇帝”。1945年,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溥仪成了苏联红军的囚犯。溥仪押送回国路上的自杀未成,进了战犯管理所。他学会了生活,还学会了解剖自己的思想,改变了唯我独尊的思维方式。1959年,溥仪获特赦回到北京,成为一个公民,过着与普通人一样的生活。1967年,文革中,他冒着生命危险,站出来为当年的管理所所长辩护。同年,溥仪因病谢世。
昨天花了三小时四十分钟把贝托鲁奇的《末代皇帝》看完了。此前还从未完完整整地看完过,觉得太长了。唯一的印象是坂本龙一创作的影片插曲,前阵子在坂本龙一的自传**里也提到了那一段经历,记忆犹新。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时长好像约定俗成似得一般都被设定为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或许考虑到坐在影城里的观众的注意力吧,也可能是其他商业考量就不得而知了。在我很小的时候,对于**还没有明确的概念时,只是觉得它很长,很黑(影院环境的关系)。也是因为近期不能出门,才能看这么个长**,看后感触良多。
开篇第一个人物的出场就让我一下子进入到了**情境中,也就是卢燕(观影后上网查**的相关信息才知道她居然是梅兰芳的干女儿,她和文艺界、演艺界的关系可想而知)饰演的临终前的慈禧太后,以及导演从整体的角度给观众展现的紫禁城,立刻让我觉得这个才是对的;瞬间推翻了我在今天的**电视剧里看到的和紫禁城有关的所有片子的印象。在贝托鲁奇的镜头下,那是个宽阔、距离感十足,又阴森,略显呆板的同时似乎少了些想象中的金碧辉煌的紫禁城,丝毫不让人向往的禁锢之地。这和我以往看到很多国内的清宫戏的观感很不一样,让我第一次会对中国皇族里的生活觉得乏味、苍凉。
**采用双轨时间描述,我也不知道专业术语应该如何描述,一会儿回忆溥仪的童年、少年以及被赶出紫禁城的过往,一会儿就是此刻在战犯营里被“改造” 的此刻。无论从**时长、**语言和结构、拍摄手法、甚至在演员表演上,可能是因为距离,都让我有种“我是个思维上存在巨大困境的人”或“自己的语言体系的狭隘(由于环境和个人共同造成的)”的感觉。它对我来说,极为的不熟悉,不适感,但是是能把我完全吸引过去的不适感,和看一部时下的流行**那种“在自己的范围内”的踏实感截然相反。把不熟悉的历史、从书里看来的历史瞬间拉近,让这段故事在眼前上演,如此之冲击仿佛它能锁住今天观众的思考能力。换句浅白的话说,我们很难用单一或简短的词汇去形容这部**,同样的困惑也围绕在我们该如何形容溥仪这个人物上。就像溥仪这个人,太难比较、太难找到他的位置,甚至将他的呈现合理化也是妄想。
再说说演员。不得不说,尊龙真的是太帅了,我作为一个成年男性都被吸引,无论是贵族气息和落魄贵族的劲儿都刻画的入木三分。溥仪年轻时被摆弄的愤懑、内心满是心虚的贵族气息、被日本人利用后妄想复辟的野心、新中国后被“改造”时期的忍辱感以及通过在狱中看**后得知自己在伪满时期所造成的罪责的歉疚感,作为观众都体会的到。尽管还有其他的好演员,除了彼得·奥图、陈冲和邬君梅,最让我眼前一亮和意外的是坂本龙一饰演的日本特务甘波正彦和英若诚扮演的监狱长。以前只听过这位前文化部副部长的名字,如何如何了得,也知道他是英达的父亲,但看**的时候并不知道。至于坂本龙一,是少见的情况——作曲的同时还参与表演,就像他参与大岛渚的**一样。我很喜欢他现在老年的样子,如他所述,年轻时的他的样貌确实不怎么样,至于是不是招人烦我们作为看客并不知晓。
看这样的**,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处于什么位置,是单纯观众的位置,还是一个读历史的后辈的角度。就比如看主人公溥仪,我们从道理上、情感上或许可能会理解他的焦灼和复杂,但从位置上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他,甚至可以说没人能理解他,如果从艾柯谈“误读”的角度上来说。毕竟不理解才是常态,理解反而是稀有、稀少的。这也是为何我说这样的**对观众是有要求的,因为它会让观众来回摇摆,如果想让自己作为一个认真的观众的话。比如在皇宫外面已经是辛亥革命之后,清朝被推翻了,但作为皇帝的溥仪在“小皇宫”里还被蒙在鼓里,他的表现其内在深层原因是复杂的,是很难让人一下全盘否定的。可能是我的恻隐之心比较重,也没有作为伟人的坚韧和果敢,新中国之势无法阻挡,但我作为观众之一常常会对溥仪产生同情(也不排除潜意识里对尊龙的喜欢)。可是,当影片演到他在东北想要复辟时,同情心又减弱了,但我们也知道他是被日本人利用,复辟又是个梦,甚至是个他自己也知道是梦的梦……一个多么难描述的人啊。
如果我们从所谓的小爱中抽离出来,以今天普遍的人道主义、平民主义的视角来看,一个落魄贵族固然会因他作为时代牺牲品的命运让人唏嘘,但还有那些千千万万的孤苦贫民又将何去何从呢,他们又将怎么说呢?相比于溥仪,他们的一生是注定的悲惨和非自然死亡,只不过**里没有特写而已。诸多的思考会让观众失语。还有一直在服侍溥仪的那个下人,直到他们作为战犯被关在战犯看管所的N年后,这个下人才脱离溥仪,临走时他对溥仪说:“你从来都不了解我”,这是一句振聋发聩的自白,只是被很平和地说出,但在溥仪听来是震撼的,在观众听来也是。好在溥仪1967年因癌症去世了,对他来说,应该不是个很坏的事吧。
这是一部很难说得完、说得清感受的**,简单写一点,聊表寸感。若想有更多的了解,有两本书一定要读:庄士敦(也就是溥仪的洋教师)的《紫禁城的黄昏》和爱新觉罗·溥仪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如果这一篇文章被很多人看到我并不会觉得多么幸运,但如果有人看了**之余又去读了这两本书的话,起码对人和人生有了更为丰盛的理解,这大体来说应该是幸运的。
爱新觉罗·溥仪,清朝最末一代皇帝。前段时间看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从小时候的皇宫生活讲到日本,再讲到特赦。这书是写于1959年特赦之后,有点忏悔录的意思,文中最刺眼的莫过于下面这段:
“自己的文学修养不够,特别是认识水平不高,写出的成品,仍有不少词不达意之处。理解和认识上不深不对,更是难免。我对那些教育了我,帮助了我取得新生的正面人物形象的描绘,未能达其万一,尤其不能满意自己,感到自己笨拙之可气。”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前半生是无一事可及生人,无一言可书史册。这么形容实在有些过头了,对于这位被抱上宝座的傀儡“元首”,身不由己必定更多些。
后来又找出贝托鲁奇的**《末代皇帝》,影片是参照溥仪自传拍的,里面溥仪的前半生不单纯是一个皇帝的历史,更是一个作为皇帝的人的故事。对于历史问题的认识,向来严肃谨慎的中国人认为“讲故事和历史完全是两回事,细节的处理应当尊重历史的真实”。而他眼中的溥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无法摆脱被囚禁命运的生命个体,是成份复杂、面目模糊的一个可以和观众进行心灵沟通的人。
影片原版为英文,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在故宫拍摄的**。故事从1950年冬天开始讲起,清王朝废帝溥仪,作为战犯从苏联被押回中国。此间采用情节穿插手法,断断续续将爱新觉罗溥仪的一生连贯起来。
1908年的一个冬夜,清宫卫队长敲开了醇亲王府的大门,按旨意将3岁的溥仪接进香烟缭绕的坤宁宫,即将咽气的慈禧太后命他即日登基。
太和殿上隆重举行登基大典,溥仪在大臣陈宝琛身上发现了一个装着蝈蝈的小笼子。他对蝈蝈的兴趣显然超过几千名跪在他脚下的文武大臣。
“您是皇帝,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
说罢,大臣将怀中的小笼子献给了溥仪,这幕情景与影片结尾相呼应,直触心房
。
年迈的溥仪花一角钱去了自己曾经的家,此时的故宫已经空无一人,他翻过太和殿的围栏看自己曾经坐过的宝座,这是影片里唯一一次,太阳照满溥仪的整张脸。他沿台阶走上去,却被一个小男孩制止了。
“你不能到那里去!”
“你是谁?”
“我是管理员的儿子,你是谁?”
“我原先是这里的皇帝。”
“你证明给我看。”
满脸皱纹的溥仪蹒跚又轻快地爬上台阶,坐在龙椅上像个怀揣小秘密的孩子一样笑着,并招呼男孩上去。溥仪从龙椅背后掏出了自己五十年前从陈宝琛那里拿来的蝈蝈笼子,仔细地擦了擦,递给男孩。男孩打开盖子,夕阳里,一只蝈蝈爬了出来,抬头,老人已经消失了。
这段从情节到人物情绪,几乎都是超然和虚幻的,也闻不到严峻的历史气息。溥仪的心情也显得非常放松,好像终于卸下历史强加给他的重担,对自己的一生彻底释然;也好像怀念着过去所拥有的荣誉,对时代变迁的妥协。
溥仪无疑是孤独的,虚实结合的尾声也并不完全符合现实。只是已经成为花匠的溥仪,没人知道也没人在乎他曾经是这个国家的皇帝。在历史的洪流前,他们都无能为力,只能谨小慎微地苟活到生命终点降临的那一刻。而在这样剧烈的震荡年代,生命中出现的一切人与爱也不得不重新分散。
正如影片里溥仪与庄士敦告别时的对话:
“How can we say goodbye”
“As we said hello”
1922年,已满16岁的婉容被选入宫,在选皇后一事上,皇帝溥仪第一个圈中者为文绣而非婉容,由于瑾皇贵妃(端康皇贵妃)的阻挠,溥仪才勉强圈点了婉容。
1922年12月1日,婉容与溥仪大婚。至此,婉容成为清朝史也是中国史上最后一位皇后。
百年来,末代皇帝溥仪和婉容大婚之夜的洞房生活,始终是一个未解之谜。
多年后,老太监信修明的一段描述给出了一个较为可信的答案:“钦天监之选择最不相当吉日,近世纪有三错误。穆宗、德宗、宣统三大婚礼。合卺之夜,皆当皇后月事来临,致而皆不圆满,终身不得相近。其为命乎?”
也就是说,同治皇后、光绪皇后再到宣统皇后,在洞房花烛之夜,都恰逢月事来临。三代皇帝大婚之日被同一生理问题困扰,堪称“清宫秘闻”,在几千年的封建宫廷史上也较为罕见!
而从老太监信修明对于这一事情的叙述来看,他则将这一现象归结为三代皇帝的宿命!
那么,溥仪与婉容是如何度过洞房之夜的,溥仪曾经跟最后一个妻子李淑贤说起大婚的经过:“大婚仪式是在夜里举行的。溥仪掀开婉容的大红盖头,看了看,相貌的确不错。他没在坤宁宫睡觉,而是在养心殿和太监一直玩到天亮。”
溥仪是因为已经知晓婉容身体不适,还是因为先前选皇后一事有情绪,总之,他只是看了看相貌不错的婉容,之后去了养心殿与太监一直玩到天亮!
二女共侍一夫,免不了有所猜忌,吃醋,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本不足为奇。可婉容与文秀为此生事,有时竟闹到溥仪面前,让圣上为她们“断官司”,这种现象在以前的宫廷中是不曾有的。溥仪起初还能公平决断,但渐渐地为了减少和婉容的啰嗦,就很少到文秀的宫里去了。就像溥仪自己说的“差不多我总是和婉容在一起,而经常不到文秀所住的地方去。”
该片讲述了中国最后一个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从当上皇帝开始到最终成为一名普通公民之间横跨60年的跌宕一生。
1988年,该片获得第6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摄影、最佳美工、最佳服装设计、最佳剪辑、最佳音响效果、最佳原创音乐等九个奖项。
剧情简介:
1950年的冬天,清王朝废帝溥仪(尊龙饰),作为战犯从苏联被押回中国。火车抵达中苏边境的满洲里火车站后,溥仪认为此去性命难保,便溜进卫生间企图割腕自杀。中国战犯管理所所长(英若诚饰)发现情况有异,急敲卫生间的门,敲门声使溥仪陷入了回忆。
1908年的一个冬夜,清宫卫队长敲开了醇亲王府的大门,按慈禧太后(卢燕饰)旨意把3岁的溥仪接进宫中教养,准备接位。 在香烟缭绕的坤宁宫内,即将咽气的慈禧接见了溥仪,告诉他要即日登基。
在太和殿上隆重举行登基大典时,溥仪在大臣陈宝琛身上发现了一个装着蝈蝈的小笼子。他对蝈蝈的兴趣显然要超过几千名跪在他脚下的文武大臣。登基之后,溥仪成了世界上最缺少管教、也是最孤独的孩子。
溥仪从回忆中惊醒过来。他也被管理所长救起,从此开始了接受审判、接受改造的囚徒生活。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