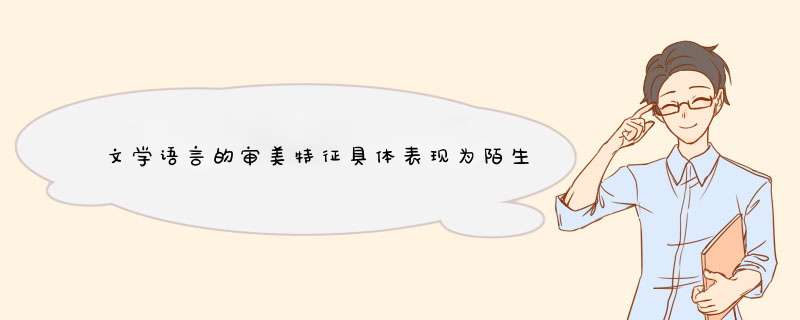
“陌生化”理论,是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的代表,****为什克罗夫斯基。其观点认为文学语言是日常语言陌生化的结果,是“文学性”的具体体现,甚至认为文学的“文学性”只存在于这种艺术处理过的语言中。这种文学性就是陌生化语言本身的看法,显然有些片面。但他们对陌生化语言艺术表现力的强调,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因为,陌生化语言与日常语言不同,它以反常的形式出现,能产生出特别的美学效果。
一、“陌生化”:审美的一个基本原则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何以能使文学成为文学,俄国形式主义者说是语言美使之然,并提出“文学研究的主题不是笼统的文学,而是‘文学性’,就是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的东西。”这里的“文学性”就是指语言的审美功能,它与“陌生化”原则密切相关。例“斜阳在那口大鱼缸边/爬着,看见一只火红的鱼/吞一粒灰色的小石子。”(90后作者高粲)这句诗美在叙述角度的新奇,用鱼的视角来看太阳。太阳爬在鱼缸边。并且透过缸里的水太阳成了小石子。这样把现实中的太阳“异化”,好象从来没有见过,这就是“陌生化”手法。如果我们照直说,斜阳照在鱼缸,小鱼变成了红色,就没有这种新颖感,而不能引起他人的注意。这种把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用一种偏离或反常方式表达出来,从而引起人们注意的手法,就是“陌生化”。在美学理论中又叫“距离产生美”,用于此种手法的语言我们称为陌生化语言,即文学性语言。陌生化为什么会产生美?对此英国著名诗人柯勒律治解释说:给日常事物以新奇的魅力,通过唤起人们对习惯的麻木性的注意,引导他去观察眼前世界的美丽和惊人的事物,以激起一种类似超自然的感觉;世界本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可是由于太熟悉和自私的牵挂的翳蔽,我们视若无睹、听若罔闻,虽有心灵,却对它既不感觉,也不理解。
对“陌生化”原则的表述,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界定为“间离效果”,而中国在审美理念中则是“化腐朽为神奇”,意思都是强调美是一种不同凡俗的陌生的东西。
二、文学语言陌生化的审美特征
陌生化理论对文学审美有着重要意义。就文学语言的“自主性”特点看,其陌生化审美特征主要表现为语言意象的可感性、语言组合的超常性、语言体验的新奇性等方面。
1、语言意象的可感性
审美对象总是依存于感性之中。文学语言的可感性首先来自对语符的直觉,接受者通过对语符的视觉直观,产生感性的审美效应。因此,陌生化语言十分重视文学语言的直观可感,较为常见的手法就是,在描写一个事物时,不用指称、识别的方法,而用一种非指称。仿佛是第一次见到这事物而不得不进行描写的方法。什克洛夫斯基举例说:“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中的陌生化的手法,就是他不直呼事物的名称,而是描绘事物,仿佛他第一次见到这种事物一样;他对待每一事件都仿佛是第一次发生的事件;而且他在描写事物时,不是使用一般用于这一事物各个部分的名称,而是借用描写其它事物相应部分所使用的词。”这种非指称性、非识别性的对事物原本形态的描写方式,在文学作家那里称为是可以“看”的语言,“在文学创作活动中,文学家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看’,没有放弃语言的这一原始特点。”“他能够‘看到’他写的一切,他就是‘看着写的’”。这种可以‘看’的语言,就是一种最原始的直接状态的语言,它保存了诗意的原初本性,因而,也最能体现文学语言的形象性特征。如厨师的菜谱中一碟凉菜,两个去壳的松花皮蛋被称为“小二黑结婚”;一个冷盘,被切碎的猪耳朵和猪舌头被叫作“悄悄话”。这些颇有“文学性”的菜名,因其生动的能指使其充满了审美趣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由所指引起的食欲感。品味这有意味的菜名,可视可感的语言意象直奔眼底。它充满了生活情趣,令人忍俊不禁,使人耳目一新,印象深刻。这说明,正是非指称性语言对语言自身的言说,才使得人们由对语言意图的理性认知转向对语言自身感性的感受、体验,才使得此时的语言充满吸引力。因为,它淡化了语言的所指意义,人的经验世界由此而心灵化,人们在感受语言客体的同时,也领悟到了藏匿在语符中的言外之意,并由此产生出不尽的美感享受。语言的艺术性由此而生,陌生化语言的文学性因此而来。
2、语言组合的超常性
超常性是指陌生化语言因自身的整体性结构,通过语词的内存和张力,打破一般语言线型排列的组合方式,使语意变得灵活生动、丰富多彩。又因其有违常理,使语言产生出一种阻拒性,于是形成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其实,我国老子早在几千年前就认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他看到了语言的超常组合与语言的审美之间存在一种必然联系。著名美学家伊格尔顿认为,“文学语言不同于其他表述形式的地方就在于,它以各种方式使普通语言‘变形’。在文学技巧的压力下,普通语言被强化、浓缩、扭曲、套叠、拖长、颠倒。语言‘变得疏远’,由于这种疏远作用,使日常生活突然变得陌生了。”这里的使普通语言“变形”、“变得疏远”,就是强调语言组合的超常性。因为只有“变形”和“疏远”后的语言,才使“熟悉”变得“陌生”,进而引发了审美者好奇与体验的欲望。中国古代诗人深得陌生化语言超常组合的精髓,诗词中常有新颖奇特的“佳句”。如“雨过柳头云气湿,风来花底鸟声香”、“月凉梦破鸡声白,枫霁烟醒鸟话红”等诗句,“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这些诗句都是不顾概念内涵的疯话。但从诗歌的角度看,它们却不失为有景色,有情致的好诗。”也就是说,语言的变异组合,虽超越了经验事实的限制,却因此传递出新的审美信息,叫人从中品味到含蓄蕴藉的诗意,获得充分的审美满足。从信息论的角度看,语符的排列组合越超常其信息量越大,则解释的不确定性程度越高,其吸引力也就越强。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读者的期待视野是由定向期待与创新期待共同构成,二者相反相成对立统一,为了求新求异,在阅读中读者自然渴望打破定向期待,产生一种“陌生”的审美心理。因此,在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中,特别是现代新潮作品,作者十分注意利用语言超常组合的效果,制造审美心理距离,形成陌生化语言。读者由此获得一种崭新的语言感觉,同时也留下无限延宕的审美韵致。
3、语言表现的体验性
有这样两句话:“我在树下等。”,“我的等待是一棵树”。从它们所表达的等待的意思来说,每个人都能读懂。但是,就人的审美体验而言,很明显第二句更容易抓住读者的心,更能引起一种诗意的联想和美感。它把我们对等待的表达陌生化了。所谓体验性,是指语言中所蕴含的审美主体的知觉、情感、想象等心理因素。古人曰“言为心声”,语言决不是文学的简单物质外壳,而是文学的直接存在,它与人的内心体验、思想感情紧密相关。由于陌生化看重语言的独立价值,这就很容易给人一种误解,认为语言远离现实与人的感受。其实不然,陌生化语言无意否认语词形式与现实之间千丝万缕的必然联系,所不同的是,陌生化语言在彰显“自己的力量和自身价值”的同时,也以独特的方式表现出语言与现实的关系。那就是,要求用新的形式言说新的感觉体验,使日常熟悉的、俯拾即是的事物变成一种特殊的意料之外的事物,并创造出一种对客体从未有过的审美感受,而不是理性认知。王安忆颇有体会地说,“要实现陌生化,不仅要有感受的‘新’,体验的‘新’,还要有语言的‘新’,陌生化是以感受与体验为基础,以语言与修辞为手段。”这说明,语言的体验性审美价值在于,它能把作家内心深处独特审美体验,用恰当形式妥帖地表现出来,并通过新颖的语言句式,在想象中让人体会到一种难以言说的美感。例如“她们的声音都很光滑,让瞎子想到自己捧起碗时的感觉。”(余华《往事如烟》)“远处一页风帆,正慢慢吻过来,间常听到鸽哨,轻轻明丽的天空与抒情地滑过去。”(何立伟《一夕三逝》)“狗崽光着脚耸起肩膀在枫杨树的黄泥大道上匆匆奔走,四处萤火流曳,枯草与树叶在风里低空飞行,黑黝黝无限伸展的稻田旋着神秘潜流,浮起狗崽轻盈的身子象浮起一条逃亡的小鱼。月光如水一齐漂浮。”(苏童《1934年逃亡》)这些句子独特、新奇,感染力极大,有着很强的表现力。声音的圆润,用失明人捧起光滑的碗的感觉来表现;风帆在水上的慢行,犹如情人温柔的吻;鸽哨抒情地滑过,让听觉与触觉换位;在空旷的月夜中疾行,人好似漂浮在水上的小鱼,巧妙地化用了,“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意境,给人一种绵绵不绝的情趣。这样的语言不仅增加了读者感知的难度,延长了感知时间,同时使人在反复体味中的获得一种审美效果。难怪现在流行说,旧式小说读故事,新式小说读句式。这是因为,新颖的句式能更多使人的关注语言,品味语言,并从中领悟那种只可意会的美学韵味。同时也充分显示了陌生化语言自主性的迷人魅力。
间离效果是德国戏剧理论家、剧作家布莱希特所提出的戏剧表演理论,是指将观众疏远于戏剧或**,这被布莱希特称为叙事剧(史诗剧)。布莱希特认为戏剧应为政治服务;观众对舞台上的戏剧投射情感会妨碍观众的冷静判断。在剧本的创作上,他多以异国的、模糊的时空背景,并运用说书人讲述故事,以达到观众与剧情间的疏离效果。间离理论是布莱希特为推行“非亚里士多德传统”的新型戏剧而在“戏剧结构、舞台结构和表演方法等”方面所做的一系列改革实验中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叙述体戏剧所特有的特征。国内长期以来总倾向于将间离理论视为一种表演方法。例如王晓华在《对布莱希特戏剧理论的重新评价》中所归纳的:间离“作为一种方法主要具有两个层次的含义:1 演员将角色表现为陌生的;2 观众以一种保持距离(疏离)和惊异(陌生)的态度看待演员的表演或者剧中人。”[2](P 24)就间离理论而言,表演层面仅仅是其产生作用的外延之一,与其并列的至少还包括导演处理、舞美手法、音乐处理、以及戏剧结构和文本修辞等方面。布莱希特之所以更偏爱就表演问题论间离理论,是因为对于完整的戏剧实践过程而言,剧本创作和舞台表演相对来说是在所有实践环节中更为关键的,在剧作层面,作为剧作家的布莱希特无须多言,只要提供符合间离理论的作品即可——事实上他正是这样做的,而作为导演,他就必须让演员甚至观众明白如何在表演及对演出的欣赏中体现、实践、理解和接受间离理论。如此看来,他的这种理论偏爱体现着一种高明的理论宣讲策略。但作为研究者而言,绝不可以就此将间离理论仅仅视为一种表演理论,并仅在这一层面推究间离理论的内涵。如果我们将概念的外延当作其内涵,并据此展开反思,如此行事,不产生某种认识上的偏差倒是不可思议的。我们要对布莱希特的间离理论作出全面的认识以及反思就必须从它真正的理论内涵出发。
“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核心概念,也是形式主义者最关心的问题,是由俄国形式主义评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所谓“陌生化”,是针对习惯化、机械化、自动化和潜意识化而言的,指把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却又熟视无睹的事物用一种异于常规的手法表现出来,有时违背点常情、常理、常事,却使读者感觉到独特、新奇和惊异。司空见惯的事物容易发现但不容易表达新意,而熟视无睹的事物不容易发现也难以表述。那么学生在写作中引入“陌生化”的手法,往往能使文章达到平中见奇、平中出彩的效果。在语文教学中,“陌生化”应用较为广泛,特别对提高学生写作水平有极大的帮助,如语言思维、写作技巧、文章结构、素材选用、主题表达等方面。语文教材中的一些“陌生化”范例,也很好地为学生提高写作水平提供了暗示和借鉴。
一、语言陌生化
有人曾形象地把语言比喻为写作的“魔水”。 法国文艺批评家布瓦洛说:“一句漂亮话之所以漂亮,就在于所说的东西是每个人都想到过的,而所说的方式却是生动的、精妙的、新颖的。”看一个学生的语文功底如何,也就看他写作中的语言表达如何。很多学生的语言枯燥、乏味,缺少表现力,很可能就是语言表达不够生动、新颖,或是拾人牙慧,这样不妨借鉴教材中的语言“陌生化”的表现手法。如美国作家梭罗看到瓦尔登湖写道:
这不是我的梦/用于装饰一行诗/我不能更接近上帝和天堂/基于我之生活在瓦尔登/我是它的圆石岸/飘拂而过的风/在我掌中的一握/是它的水,它的沙/而它的最深邃僻隐处/高高躺在我的思想中。
――梭罗《神的一滴》
作者对瓦尔登湖的纯美没有一丝一毫的虚伪,把它天然的澄澈美与作者的心灵融为一体,表达了作者内心对瓦尔登湖无限的敬仰之情。又如余光中写“雨”:
“下雨了。”温柔的灰美人来了,她冰冰的纤手在屋顶拂弄着无数的黑键啊灰键,把晌午一下子奏成了黄昏。
――余光中《听听那冷雨》
作者运用拟人、比喻的手法,把“下雨了”写成“灰美人”,形象生动,富有美感;而又把“雨声打在瓦片”的声响比喻成美妙的琴键声,极有情趣。语言的陌生化还可采用词语的反常搭配,形成新鲜、奇妙之感。如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我是你河边破旧的老水车/千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又如2004年高考重庆卷优秀作文标题――《我是一只想死的“老鼠”》。
二、技巧陌生化
古诗文中常用一些修辞手法如夸张、比喻、通感(移觉)、移用(移就)、化用以及超感觉描写等,来达到“陌生化”的效果。宋代词人宋祁《玉楼春》有“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名句,被近代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论说:“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句子富有表现力,大多是运用了某些技巧。学生写作中,语言要出彩,也可通过技巧陌生化的途径来实现。如: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毛泽东《沁园春・长沙》
其“翔”字运用的是移用修辞。“翔”本来是写空中鸟兽飞翔的动作,现用来形容鱼的姿态,生动地描绘了游鱼在水中自由自在、轻快自如的神态。如用“游”字,毫无生气,过于呆板,更不足以表达作者心中的向往之情。
(巫峡)突然是深灰色石岩从高空直垂而下浸入江心,令人想到一个巨大的惊叹号;突然是绿茸茸的草坂,像一支充满幽情的乐曲。
――刘白羽《长江三峡》
两个“突然”写出了诗意变化无穷的特点,却又情趣横生。前一句是比喻,巫峡的陡峭如“惊叹号”一样,垂直而下。后一句是通感,作者行程巫峡中所看的绝美景色转化为听觉,是一支“幽情乐曲”。
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
――王实甫《长亭送别》
作者化虚为实,把看不见摸不着的情感,用夸张的手法具体化,让大小车满载愁绪,于是“愁”既有重量,又“有形”;淋漓地表现了主人公痛苦的深重。这一句又巧妙化用了李清照的《武陵春》中的诗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三、结构陌生化
所谓结构,是文章的表达形式,也就是文章的谋篇布局。传统意义上,文章总是按照某种结构来组织内容,或是事情的发展过程,或是事物构造的内在规律,或是事理的内在逻辑联系,这种结构层层推进,思路较为清晰。但结构上来点“反常”,就会产生陌生化的效果。
《外国小说欣赏》第六单元就是以“结构”为话题的教学。结构是一个“容器”,它并不是无序的,而是在一根主线贯穿下,串起文章的主脉。如瑞典作家斯特林堡的《半张纸》所写之事,纷繁复杂,可以写成一部长篇小说。但作者选择一张记录电话的小纸片作为“容器”,让生活中的事情,全部以电话号码的姿态凝固下来。看上去虽只是一个个号码,简单而不复杂,但人生变迁的喜乐悲愁,却被它们串结在一起。每个号码背后都有一段故事、一番心情,但又被这个“容器”限定着,决不漫溢。
而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牲畜林》为了保持线性结构,故意“延迟”小说的进展:每当朱阿举起猎枪要向德国兵射击的时侯,就会被阻止,而阻止的理由也在情在理。有的文章连“容器”也没有,却使材料粘合在一起。如英国作家伍尔芙的意识流小说《墙上的斑点》没有传统意义上称之为“故事”和“情节”的事件,全凭墙上的一个“斑点”展示人物内心的意识活动。
四、题材陌生化
题材是文章的“血肉”。题材从素材中提炼、加工或改造进入作品。人们面对同样的素材,会因情感态度不同,就会使进入作品的题材被赋予不同的意义,也就呈现出艺术陌生化的妙处。如贺知章写“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而曾巩写“柳”,“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两人同写的是“早春之柳”,前者用比喻手法,如现一美人,婀娜多姿,咏柳歌春,情趣盎然;后者用拟人手法,对柳树明显贬抑和嘲讽,咏柳讽世,理趣横生。题材陌生化,或顺其意而写,或逆其意而著,或赋其意而抒,或虚其意而作。
又如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沙之书》就是虚构了一本奇妙的“沙之书”――像沙一样,无始无终;没有首页,也没有末页。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书文章开头的文字“线是由一系列的点组成的;无数的线组成了面……如今人们讲虚构的故事时总是声明它千真万确;不过我的故事一点儿不假”,让你读着就煞有其事,只要继续读下去,我们就会知道作家在虚构故事,先是一个陌生人在推销《圣经》,接着暗示这本书来自孟买和它的特征,“我”又设法得到这本书,后来这本书让“我”烦恼不堪,“我”又把这本书藏进了图书馆。艺术的真实固然与生活的真实有关,但艺术的真实绝不等于生活的真实。我们写作也不妨来点“编造”,让熟视无睹的事实变得陌生,感觉新鲜、奇妙。有时作文命题的写作要求也允许“编造”,这也在暗示考生对身边的生活或事情可采用陌生化写作,拓宽写作的另一路径。
五、主题陌生化
主题即中心思想或主旨,是文章的灵魂。主题是从题材、语言、情景、人物、情节、细节等方面来加工、提炼而成的,它贯穿作品全文,体现了作者的写作目的和情感态度。主题有显性和隐性之分,是一个多义性的概念。一些作品常常通过客观描绘、夸张、隐喻、象征等暗示出来,主题显得模糊,让读者总觉得“陌生”。
英国作家伍尔芙的意识流小说《墙上的斑点》的主题就难以捉摸,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了“我”看见墙上的斑点而思绪联翩,没有传统小说所说的人物、情节和环境,甚至连“我”的性别也是模糊的,因而它的主题显得多义而又陌生。小说通过对墙上斑点的猜想与思考,主题可理解为:把精神的触角伸向自然与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对生活的偶然性与命运的必然性的问题、对生命在个体死亡之后永恒延续的问题、对自然与机械性现实的对立问题、对文学创新精神与陈旧规范相冲突的问题、对女性反抗男性观念的问题等,进行了意义重大的体验与感悟。
然而“陌生化”并非只追求新奇和惊奇,让人看不懂,它只是打破常规,采用适当的手法,产生新鲜之感。因而不管是在语言、技巧、结构方面,还是在题材、主题方面,使用“陌生化”手法,都要求适度运用,写作才更显得真实。
[作者通联:浙江台州市椒江区洪家中学]
有陌生化的意思。
在教读九年级上册第一单元诗歌的时候,学生普遍感到其中的有些句子读起来比较难懂,就是我们老师在阅读的时候,如果不借助相关资料,有些句子也是感觉陌生,不易理解。这是因为这些诗歌运用了陌生化手法。
什么叫做诗歌陌生化呢?诗歌陌生化是由什克洛夫斯基提出并逐渐发展完善的,但在西方文艺美学史上,第一个对“陌生化”理论进行论述的是亚里士多德。不过,他并没有正式提出“陌生化”,而更多的是使用“惊奇”“不平常”“奇异”等词语代替。
诗歌陌生化的体现有以下两点。一是在诗歌中,陌生化主要表现在语言上,与自动化相反。诗学意义上或语言意义上的“自动化”,是一种不思考或者不经过思考的语言没有阻隔性的惯性语言。而陌生化就是一种创新。比如,风与草相遇人们自动化地用“吹”字。穆旦的《我看》一诗中,是这样写的“我看一阵向晚的春风,悄悄揉过丰润的青草”。这里诗人并没有用“吹”而用“揉过”,这就既写出了春风的温柔,也有一种新奇之感。
二是陌生化,根植于意象创造。比如毛主席的《沁园春雪》一词中的“山舞银蛇,原驰蜡象”一句,就运用了化静为动,化大为小的手法,使这两个喻体有一种陌生的感觉,让读者耳目一新,给人一种奋发的态势和竞争的活力,如果用自动化的语言就是白茫茫的一片,那就不是诗了。又比如林徽因的《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四月天其实就是春天,如果用自动化的语言表达就是《你是人间的春天》,但作者不用春天而四月天,就有一种陌生化的手法所创造的新鲜感。
诗歌语言陌生化的四个主要类型:1倒序2反衬3借代4反复。在这里主要介绍两个类型。一是倒序,例如:比如《我看》一诗中“我看飞鸟平展着翅翼,静静吸入深远的晴空里”。本来顺序应该是飞鸟飞入晴空里,作者却用晴空吸入飞鸟。一下子就给人一种新奇之感。二是反复。比如《周总理,你在哪里》一诗。“他刚离去,他刚离去”,反复出现,一语双关的写出了对总理的悼念怀念之情,语意含蓄而新奇。
同样是选择一个词语,陌生化手法选择的词语就更加的有创意。比如《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一诗中,“笑响点亮了四面风”,这一句就特别的有新意。作者用笑响,不用笑声,一新,点亮是视觉,笑响是听觉,四面风是听觉,二新。三觉用一个点亮来统一,一写出了春天的明媚,也写出了春风的温暖,也写出了春天带给人快乐笑声,三新。三层意思写为一句,表意极为丰富而新异,这就是诗歌陌生化手法的表现力。
当今社会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越来越多的人脱离了诗,疏远了诗。诗被冰冷地搁置在艺术殿堂难以企及的塔顶上,以致于人们怀着某种逆反心理甚至于不屑于诗。但问题就在于人们同时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精神追求,相反随着物质活动的加强,在情感和精神领域的空白带越来越大。除了其他原因外,恐怕这里还存在着一个对诗歌的理解问题。因此,当我看到《现代英美诗歌鉴赏指南》(按照原名直译,应该是《理解和欣赏诗歌的现代导引》,编译者可能是为了照顾国内读者的习惯而命之为“鉴赏指南”)。就不禁想到,这里淡漠了一个重要因素:理解。尽管我们承认,在人类的全部精神现象中,哲学一向是最为精华的一部分,但比起它的严酷抽象性来讲,诗无疑是更具有召唤力和生命感,人类也更易在诗中鉴照出自己的灵魂自己的历史。因为就诗人创作来说,虽然其原始冲动仍旧是一个难于解说的谜,但这种行为本身却实实在在是不同时代的某些人类共通的本能。然而对于诗人和人类来说,创作毕竟是一种发现而非丧失,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生活的创造。同时这种似乎神秘莫测的一瞬间,的创造,不论是起因于什么——一种性格,一个场景,一次顿悟,一掣意念——它决不会是一种完全孤立的存在。一方面,它无疑包含有某种民族的甚至是人类的文化渊源,是民族传统和原型、集体有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的自然积淀;另一方面,它所代表的某种人类精神的创造,总是在适宜地扩展着丰富着,与人类的经验达到了某种沟通。这样,诗也就真正地超越了空间和时间,诗人把自己创作中所发现的自我与世界转达给了读者,使读者在阅读中发现自我和世界。这样理解的含义也就包括了诗人与读者之间通过人生经验所形成的宽广无涯的交流范围。
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人再怀疑诗是人类感觉的某种激情的显示,虽然诗歌在历史的蜕变中早已丧失了它在往古时候的辉煌和魅力。感觉世界,这是全部人类的天性。但把对世界感觉这种最广泛的人类经验转化为一种灵巧的艺术形式,这却只有诗人才能完成。这部“辞典”提供了人们对诗与诗人的可能的理解,不过形成诗歌过程中的参数和变量太多了,可以说任何一部辞典也不可能令人满意,但至少我们要理解诗歌,必须明白诗是一种感情性东西,它既来自宇宙人生甚或一刹那的感觉冲动,却又带有某种超验性质。诗所表现的是人生,却又不是人生琐屑平庸的凡事;它依循着感情的发泄,却不同于生物性的自然排遣,而是一种艺术性的精神创造。因而真正理解的前提,便包含着对诗的艺术的自觉认识。《当代英美诗歌鉴赏指南》的引导价值就表现在这里。到了这一步,我们似乎再也没有必要喋喋不休地争论“诗是什么”这个问题了,那只是理论家们的兴趣所在。对于我们来说,更为亲切的倒是这种娓娓清新的叙述,它没有一般理论的晦涩,但并不缺乏思考的深沉,人生的体验,艺术的感悟。也许是时下文学批评中纯理论性的译作太多了,那种充满逻辑限定和命题推演的长句子常给人以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之感,因此本书才情盎然、诗意流畅的论述,通过译者清丽优美的译笔展示在我们面前,就弥显珍贵和可亲。
诗歌语言的陌生化怎么处理?
四川作家、诗人、评论家尹才干总结出①“词语的反常搭配”②“词语的异类并举”③“语义(或语境)上下对抗”等诗歌语言陌生化的方法(简称“三陌法”),作为诗歌创新方法写进《诗歌创作入门》讲义;作为歌词创新方法写进《歌词创作概论》教材,读者纷纷转发,掀起了“诗歌(歌词)语言陌生化探索的浪潮”。
——摘自尹才干《关于诗歌语言陌生化的探索》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