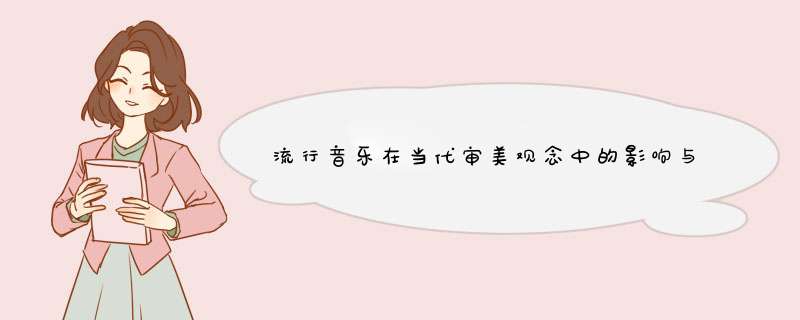
1.提高对音乐审美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在漫长的教育史中,音乐艺术曾作为一种教育手段,长期存在于学校教育中。古今中外,伟大的教育家们都曾不同程度地重视音乐的教育价值,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捷克音乐教育家西赫拉指出,音乐教育要研究的首要问题是:在教育过程中,音乐起什么作用怎样对待音乐教育它的基本思想是什么[2]日本山叶音乐教学法对国民音乐教育有过这样明确的阐述:“这种教育的目的,不只在培养特殊学生,虽然有些学生在音乐上的能力会较其他学生逊色,但是这并无损于他们的人类价值。”[3]1999年,我国发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地将素质教育的内涵界定为“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美育再次被写入国家的教育方针中。音乐教育作为实施美育的重要途径,也就有了根本保障,音乐教育又一次被确认为提高国民素质的主要途径之一。音乐教育的审美本质,表现出其不仅具有其他学科所共同的认识功能,更为重要的是显示出其特殊的教育功能,即以其“直指人心”的审美功能对人自身美的潜质进行挖掘和培养,达到陶冶人的心灵和塑造人格的目的。2.要树立音乐审美教育是学校音乐教育的核心的理念人们已认识到音乐审美教育的功能是如此广阔,有的已超出了美育本身的范围。每个人从小到大都要接受学校教育,音乐审美教育实践活动应不失时机地始终坚持审美教育原则。美育将渗透到学校教育的全过程中,系统地、循序渐进地、目的明确地传播审美知识和培养审美能力,描准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即美,培养各层次受教育者的感知、理解、体验、评价、鉴别和再创造的审美艺术能力。这将是人类自我教育的方式,也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它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是培养祖国接班人不可缺少的重要教育内容。因此,音乐审美教育将奠定人一生的全面素质能力,音乐审美教育由此成为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核心”。三、当代音乐审美教育的新内涵一场波及世界范围的始自20世纪70年代的重视素质教育的改革运动蓬勃发展,至今已有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成果,美育观念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肯定和推广。但是,当代音乐审美教育理念与传统的美育观念相比又具有了许多崭新的内涵。传统美育的本质是情感教育。现如今,包括人文学科在内的科学发展总的特点呈现为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趋势,我们目前所论及的音乐审美教育也涉及众多学科,至少包括音乐教育学、音乐心理学、音乐美学、音乐社会学以及思维科学等等。因此,对音乐审美教育的新内涵的阐释离不开相关学科的发展。从教育学和心理学发展来看,美国当代教育家加德纳提出的“多元智能”的理论,已把音乐智能提高到与语言、逻辑智能同等重要的地位,从而使音乐教育在教育中具有了从未有过的重要作用;1995年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戈尔曼在“情商”概念的阐述中认为,情商是一种调整与控制情感的能力。他认为,人的成功因素中,情商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特别强调通过音乐潜移默化地进行情感教育是培养“情商”的重要途径[4]。还有一些自然学科的研究成果,也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音乐审美教育的新内涵。这一切都在提醒音乐工作者,必须在实践活动中从广泛的教育内涵方面学习、理解和运用审美教育手段,对受教育对象最大限度地实施全面的审美教育,在这一教育中努力做到理论和实践完美的结合。四、当代音乐审美教育的社会意义提高人的素质是社会发展的要求,同时社会发展也为提高人的素质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当前,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新时代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那就是呼唤“以人为本”的教育。由于只有人才能创造知识、掌握并运用知识,因此重视人的本体作用的素质教育就成了时代的必然要求。1.音乐审美教育具有第一生产力的作用知识经济时代要求人才必须具有创新能力,而音乐审美教育对人的创造力中的想象力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这也说明,音乐的审美教育也具有了第一生产力的作用。这将凸显音乐审美教育的地位及社会功能。2.音乐具有教育、审美、娱乐三大基本功能无论主体的音乐条件如何,他欣赏音乐的能力总是高于他从事音乐制作和演奏的能力,所以,音乐审美首先是属于大众的,也正因如此,音乐审美教育就具有了充分的社会性。从美育的角度看,音乐是美育诸多形式的纽带,音乐以其特有的音响美、节奏美、旋律美直接强化审美主体的审美感知,陶冶其情操。重视音乐的审美教育对于提高全民族的审美趣味和审美能力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3.音乐审美教育可以促进人的身心和社会的和谐发展由于当代社会的激烈竞争和高速的生活节奏,人们的身心经受着从未有过的压力,精神疾患成为难以控制的时代病。人类应该拯救自身,特别是拯救自身的心理缺损,这已成为全世界共同的课题。而音乐审美教育对克服人的情感“异化”,使之身心和谐发展乃至全社会和谐发展都具有广泛的效用,而且是其他教育不可替代的。德国作曲家瓦格纳曾说:“心灵的器官是音乐,心灵的艺术意识语言是音乐。”当人们接触一部音乐作品时,其实是正在感受着作曲家的灵魂。或许我们不知道引发作曲家产生这种情感的事由,但我们却能通过其作品直接触摸到他的情感。音乐并不是表现某一个人在某种状态下的激情,而是表现激情本身。每一部优秀的音乐作品,都有一个高尚的灵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过:“节奏与乐调有最强烈的力量深入心灵的深处,如果教育的方式适合,他们就会用美来浸润心灵,使他因此美化……”。音乐能美化人们的灵魂,能激发大众对美好愿望不懈追求的热情;音乐可以陶冶人们的情感,保持和发展人的想象力,激发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美好未来的不懈追求的强烈欲望。这些审美功能的实现,将提高大众群体的文化内涵和修养层次,具有广泛的实践效用和社会意义。因此,加强和发展音乐审美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答案:所谓“审美现象”就是人们感受世界、发现情感的形式,从而内心受到感动的情况。要点a、情感,审美用情感,而不是理智;b、形式,它只取事物的形 式;c、精神享受,审美享受是精神上的,而不是物质的;d、世界,审美价值的体现者是周围世界和事物;e、自我发现,审美的发现是一种自我发现;f、新, 有审美价值的事物是前所未有(新)的。
简述美学在研究方法上的主要特点如下:
美学既然是一门综合性的人文学科,那么它的研究方法自然也应当是多样的、综合的,而不是单一的。
首先,美学既然是研究具体的审美现象和现实的审美活动,就意味着美学研究比一般人文学科更为注重感性的经验、情感的契合、心灵的碰撞,更多地要求经验科学的配合和协助;
其次,美学必须广泛吸收其他人文学科以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成果
譬如,美学可以借助哲学的成果来深化对人和世界、人生价值意义的理解;可以吸收心理学的思想材料和科学成果来研究审美经验、审美意识、审美心理结构和审美心理过程;
可以借助文艺理论的思想成果来加强对艺术审美活动的分析;此外,还可以吸收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等等学科的思想资源。
所以,美学研究的方法应当是多元的、多样的。它既可以单独使用不同方法,也可以同时用多种方法进行综合研究,还可以用不同方法进行不同的组合研究。
这样,不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组合尝试,可以从不同的方向、角度、层次、接口来拓展和推动美学研究。但是,美学研究的多种方法还是有主次之分,核心与附属之分。
我们认为,从学科性质来看,美学的核心方法应当是哲学方法。首先,美学从诞生起就从属于哲学,后来美学成为独立学科,却从来没有脱离哲学,直到当代各种有影响的美学流派和思潮无不有相应的哲学思想为背景。
其次,由于审美活动是人类更高级、更复杂的一种精神活动,而且是具有当下的一次性特征的精神活动,需要主体的全身心投入,尤其需要主体在观念世界中尽情游历,以洞悉审美活动的真谛
这是科学和实验方法及其他任何方法都力不能及的。再次,美学涉及到人生在世、人的生存实践、无限意义等整体深层的本源问题,只有靠理性指引下体验、感悟、冥思、领会的哲学方法才能掌握。
复次,美学作为一门理论学科不仅包括在理性潜在指导下现象的辨析、鉴赏的体验、本质的审察、灵感的沟通等,还必须在此基础上进行逻辑推演、抽象思辨和理论提升,这也离不开哲学思考。
总而言之,美学研究的核心方法应当、而且只能是哲学的方法。
艺术形态的本源就是真,只要我们凡事层层剥皮,追根溯源,最后必然会找到真。宇宙中只有一个真,除了上帝之外,其余的都是幻化的,都是上帝的艺术表现形式。
维护艺术形态有序和谐的机制就是善。具体点讲,凡敬畏上帝、敬畏生命、敬畏大自然的心态就是善,凡维护上帝、维护秩序、热爱生命、保护大自然的行为就是善。
艺术形态的和谐比例搭配和对称就是美。万物之美是上帝添加上去的,维护美是神佛的天职,是圣贤智者的理想和追求,也是普通大众的愿望。
当代审美文化可以分为大众审美文化和精英审美文化。而精英审美文化,它的审美主要是精英艺术的创造性作品,或者说是精神价值探索的是文化的优化。而作为大众的审美文化,指的是,某种意义上确定具有人为精神的文化。
[摘 要] 《叶问》和《叶问II》的成功在于它让大众的审美经验得到了重构。首先影片重构了功夫片的认知图式,让英雄人物以大众形象出场;其次,以情感为核心,成功实现与观众的情感交流;再次,《叶问》系列较好地处理了审美经验中的虚实边界,在虚实相生中让观众得到审美体验和情感认同。《叶问》系列在重构大众审美经验的同时,也为功夫类影片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发展思路。
[关键词] 重构;情感;审美
叶伟信执导的**《叶问》和《叶问Ⅱ》(以下简称《叶问》系列)以写实的手法,还原了一代宗师叶问的奋斗历程。在中华武术推广过程中,叶问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他身上有很多可以大书特书的话题和闪光点。不过,叶伟信并没有落入英雄片的俗套,而是将目光集中到叶问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挖掘那些与武术无关,却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素材,功夫片段反而成为嵌入生活主体的插曲,这使得《叶问》系列极大地拉近了角色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影片中的叶问少了些功夫**中那种笑傲江湖、顶天立地的英雄气,世俗了许多,却也凭借其温情和真实深深打动了观众的心。
《叶问》系列在取得票房成功的同时,也得到了观众的普遍认同。从美学的角度来看,《叶问》系列的成功之处主要在于它们重构了大众审美经验。长期以来,功夫片将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功夫暴力和科幻场景。那些刻意营造出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视觉奇观,一方面让观众的猎奇心理得到充分满足,另一方面却也不断导致观众审美疲劳的产生。另外,过度地追求视觉刺激,很容易使影片脱离大众日常审美经验,让视觉奇观取代了故事的深层寓意,造成观众在眼球疲劳的同时头脑中却是一片空白。审美经验是大众对外界感知、情感、想象及理解等多重活动的结果,它左右了大众对影片的审美感受,如果脱离审美经验的引导,会导致大众对影片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产生误解,片面追求暴力凶杀等感官刺激,忽略在精神上留下深层次的回味。《叶问》系列的成功,正是在于它让大众当前被扭曲的审美经验得到了重新构建,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认知图式、情感共鸣和虚实边界等三个方面来看。
首先,《叶问》系列重构了功夫片的认知图式。《叶问》系列没有走时下工夫片大量堆砌视觉奇观的老路,转为主打情感牌,重构功夫片认知图式。在信息社会里,大众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给予他们获取多重信息的机会,进而在脑中形成多元、多层次和多维度的图式模板。社会属性让人们体验到各种社会环境,得到诸如社会阶层、组织管理和政治实践等各种信息,而自然属性让他们能够有机会直接感知外界,获取视觉、触觉、味觉、嗅觉和听觉等信息。两种信息原本是不同维度的异构信息,经过智能处理,在人们的大脑中形成一种“有用”的图式,它们在影片中具体表现为各种符号标准,比如,谍报片中的钩心斗角,情感片中的爱恨别离,喜剧片中的幽默搞怪,战争片中的血肉横飞,悲剧片中的可歌可泣,惊悚片中的风声鹤唳,科幻片中的时空轮回,历史片中的风云变幻以及功夫片中的“拳拳到肉”等。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些图式已然内化到观众心中,将**内容与图式进行模式匹配既是他们观赏**的必备功课,也是观众认同影片的手段之一。然而,图式本身并非不能更改的,特别是当图式不是出自观众审美本能,而是由影视媒介等宣传机构精心打造、强行植入观众意识的时候,这些被动“植入”式图式与源自审美经验的图式相比,存在简单化、规则化和类型化等特点。以功夫片为例,英雄通常表现为不苟言笑、离群索居、不解风情和高深莫测等一系列符号组合,至于柴米油盐、生儿育女和辛苦赚钱等社会日常行为是大侠不屑做,也不“敢”做的。至于为何如此,其根源在于如果大侠和众多凡夫俗子一样有世俗的喜怒哀乐,那么他就太真实了,不是神秘的云中大侠而是亲切的隔壁大叔。不过,总在云中飘忽会给人一种太过虚幻的感觉,让观众产生距离感。在大众文化时代里,观众需要的是与自己距离相近的世俗化英雄,“这不是对因与不朽者接近而与其他人相区别的、作为神�之子的英雄的崇拜。这只是对那些非常善于做各种不同的事情的、特别出众的男女的羡慕。这样的人不是那些知道一个奥秘的人、已经达到了真理的人,而不过是善于成为人的人。”①《叶问》系列的火爆证明了观众对世俗化英雄的认同,在观众眼中,叶问不只是一代功夫大师,更是一个标准丈夫、好爸爸和循循善诱的好老师,因为他不是一个简单图式的符号代言,他太让人感到熟悉了,在抵御外侮时他曾经退却过,在考虑家庭生计时他曾经怯懦过,而在坚持民族大义、弘扬中华武术以及帮扶弱小等环节上,他最终挺身而出。英雄与非英雄的双重特征在同一对象身上出现,旧图式不再能解释的同时,观众却找到了真实的人性化英雄,毕竟叶问曾经真实地存在过,也会遇到诸如家居生活和人际关系等现实问题。观众在影片中一方面品味叶问的生活细节,另一方面也悄然在心中构建新的图式,一个具有生活化、真实化甚至世俗化的英雄图式,逐渐取代传媒意识形态强行赋予的旧图式。
其次,《叶问》系列以情感担纲,成功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真实的叶问生活在时代风云变幻不定的时期,和那个时代的所有人一样,他也面临许多现实中的困境,《叶问》系列让观众能够感受到叶问心灵的痛苦和生活的窘迫,**通过真切的叙事手法还原英雄的本来面目,并且成功地通过情节的推动来让观众实现移情。通常,影片无需过多的描述,观众根据以往的经验或图式,推断或联想出各种自己需要认知的细节,比如大侠出现的年代、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各个门派的武术风格和优缺点等。不过,这种知识的构建形式是一种被动的感知,观众只是被心理定势牵引着前进,情感方面处于被动接收的地位,有许多影片为了吸引观众,选择在玄幻和暴力层面上加大刺激力度,营造出一种虚幻的视觉奇观,给观众感官上的满足。如此一来,造成功夫片往往陷入争相打造各种“奇观”的相互竞争中,一飞冲天、隔山打牛和劈波斩浪等超自然动作加入武功片中已是常事,至于改变历史、时空穿梭和乾坤轮回等也早已司空见惯。时间一长,观众在联想能力消耗殆尽、感到疲惫不堪的同时,反而加大了对角色真实情感的诉求。移情可以产生积极的情感投射,在影片情节的推进中,观众不经意地将自己的体验和感悟迁移到角色上,融为一体,角色的行动就是自己的行动,角色的情感动荡也深深激荡起自己的爱恨情仇。观众不再置身角色之外,反而积极投入其中,以角色作为第一视角去观察、辨识和认知外部世界,从而引起自己与角色的情感共鸣,产生共同的心理体验和心灵震动。引起观众产生移情行为的关键是提供需要的情感载体,在《叶问》系列中,主角是源自真实的历史人物,叶问原来家境殷实,在经历国祸、外侮及殖民统治等各个历史阶段中,他一方面要坚持民族大义和弘扬中华武术,另一方面也要解决如何保全家人和维持生计等现实问题。许多功夫片较完美地解决了前者,却往往把英雄人物过于虚化,让其陷入了不食人间烟火的虚幻境地,观众对大侠的仰慕近乎对神人的崇拜。相比下来,影片中的叶问要生活化、真实化许多,咏春拳讲究防守,叶问也是走投无路才与日军头目决斗;初到香港,如何养活妻儿是当务之急,收徒、找场地、教授拳法、平息同行捣乱等,与民族大义无关,却与现实生存有关;叶问在获知救命恩人周清泉被日军枪击致疯后,也对自己无法帮助他而感到愧疚和无助;夫妻之间、父子之间的深切感情需要悉心培养,叶问对夫人的关心体贴一反丈夫为纲的传统英雄路线,在击败西洋拳王后,叶问立即赶回家中呵护妻儿的细枝末节,也深深描绘出英雄作为普通人所具有的浓浓家庭亲情。除了片中主角叶问,**中的其他角色也存在类似的生活真实感,金山找不再欺凌弱小,而是想法为老婆、孩子寻求生存空间,同样,作为香港武术领头人的洪震南,为了妻子儿女、为了徒弟们能有饭吃,也不得不甘愿受英国人利用并不断打压同行。这些细节没有采取如传统功夫片的脸谱化操作,将众多角色置于对立面,更多的是展现其中的现实问题,观众将自己移情到各个角色中体验其中人性的同时,也获得了一次次的感动,而这是单纯的奇观性功夫片很难给予的。
再次,《叶问》系列划分了审美经验中的虚实边界,在虚实相生中让观众得到审美体验和情感认同。新图式的构建和观众移情成功与审美经验的理解密切相关,而这需要正确区分影片内外的“虚”与“实”。生活中的“实”与影片中的“虚”既对立又统一,在现实的想象中感悟影片中的真实,才能在徜徉流连于精彩故事情节的同时,获取最大限度的审美快感。详言之,“虚”针对的是一个普遍的环境,具有一般性,作为故事营造的背景,《叶问》系列营造了两个“虚”空间:抗日期间的佛山和50年代英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实”则对应各个现实细节或生活细节,突出表现为叶问为家计奔波的困境和夫妻之间的一往情深。“虚”与“实”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与“实”相比,“虚”表现为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题材、环境和情节,如叶问拳打日本军官、脚踢西洋拳王,可以简化为外部压力对于角色的逼迫,在先抑后扬的脉络下,坚持民族大义和弘扬中华武术的主题,至于军官、拳王、危难中的挚友、有苦衷的同行、阴险的副官、捣乱的小卒也具有相应的表征意义,是一些程序化的符号,它们共同打造出一个“虚”的空间。在“虚”的空间中,观众可以轻松出入,毕竟辨读简单的符号比牢记影片细节简便许多。如此一来,观众既可以方便使用符号重构图式,在“虚”空间中轻松解释和推理符号后的内嵌逻辑,也可以从容移情于角色细节,在“实”情节下品味其中的苦辣酸甜。把握“虚”和“实”的关键在于辨析符号的承载,因为符号无法与对象直接对应,需要一个概念中介,从而形成“符号―概念―对象”的间接映射,比如西洋拳王“龙卷风”是影片中的具体对象,概念表述为西方侵略势力对中国的打压,而符号则可表述为国人熟知的事件或对象,如八国联军等,因此叶问与“龙卷风”的对打可以看做是他与八国联军的决斗。对象可以更换,而符号和概念则无需替换,比如西洋拳王可以换成欧洲搏击冠军等。读懂对象背后的概念就可轻松找到相应的符号表征。“实”也存在映射关系,但是没有中介模块,即“对象―观众”的直接映射,如家庭、亲情和生计问题。社会学家贝尔在谈到现代主义艺术时指出了现代审美反应的特质是:“产生出一种我称之为‘距离的销蚀’的现象,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即刻反应、冲撞效果、同步感和煽动性。”②这种距离感的拉平更容易让观众投入其中,因此,叶问的家庭亲情直接对应观众的家庭亲情,同样,叶问的生计打拼也对应着观众的生计打拼,观众正是在这种对应映射中深度移情到角色中,从而达到许多功夫片无法实现的距离拉近效果。
由此可见,功夫片新图式的构建、观众移情的成功和对影片中虚与实之间关系的正确把握是《叶问》系列获得认同的关键,这为功夫片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不过,以上几点并不能僵硬地理解为公式,在实际运用中需要坚持它们相互渗透、互为支撑的动态观点,如何调动起观众的情感,如何让观众产生认同,如何既赏心悦目,又叫好叫座,《少林寺》成功了,《叶问》系列也成功了。
注释:
① [美]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译,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②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1页。
[参考文献]
[1] 滕守尧审美心理描述[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作者简介] 丁筑兰(1970― ),女,贵州贵阳人,博士,贵州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文化研究。
审美教育一般包括美感教育、美学知识的普及和以美的规律贯穿其中的普遍教育等。美感教育指运用美的规律和艺术的实践(各种艺术的创造和欣赏),训练和强化人的感知、想象、情感、理解等心理能力,健全人的审美心理结构,使人具有敏锐的审美知觉能力和创造力;美学知识的普及主要指在艺术家、广大青年和学生中展开美学原理、艺术史和艺术批评等方面的教育,以提高人的审美趣味和美学素养;以美的规律进行的普遍教育则旨在把美的规律贯穿到智育和德育中,使科学教育中枯燥的公式和定律化为美好的形象,把死板的记忆化为生动的想象,把师生之间单方面的灌输关系变为平等的相互交流关系等。
第一种观点认为,美学研究的对象是美,美学就是关于美的科学。[1]以洪毅然为代表。这一观点是他在50年代提出[2]并一直坚持着。他的理由主要有四点:①从美学史角度看,认为美学本身的历史发展表明:美学最初就是作为研究人类的感性认识为其特殊的专门任务而出现的一门科学,一直保持着“关于美的科学”。[3]②从区别美学与艺术学的角度看,认为为了杜绝以艺术学代替美学,或者相反地以美学代替艺术学的事情发生,彻底辩明美学与艺术学之间的区别,强调美学应当是美学,美学应当不同于艺术学,乃是完全必要的。[4]③从现实功用角度看,认为为着扩大美学的应用领域,使之无愧于一门全面完整的关于美的科学,并且加强这门科学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广泛地、更加密切地联系,从而更多更好地由各方面在人民生活中,起到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服务的作用。[5]④从方法论角度看,认为一切艺术的源泉是生活,了解艺术本来就有必要先了解生活。那么,研究艺术美又怎样能不先了解现实美呢?[6]
这一观点注意到了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区别于艺术学;同时也充分重视美学的群众性现实性,艺术美只能是现实美的反映。不过,将美学研究的对象界定为“美”显然具有狭隘性,片面性。在我看来,这个“美”主要是指现实美而不包括其他的美。
第二种观点认为,美学研究的对象是艺术,美学就是艺术哲学。以马奇、朱光潜为代表。马奇认为美学就是艺术观,是关于艺术的一般理论。它不只是研究艺术中的部分问题,而是全面地研究艺术各方面的理论;它不只是研究部门艺术的理论,而是概括各个部门艺术的一般理论。它的基本问题是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它的目的就是解决艺术与现实这一特殊矛盾。因此,他把自己的美学文集就直接定名为《艺术哲学论稿》。[7]朱光潜认为美学必须以艺术为中心,只有首先把艺术认识清楚,然后才能认识一般现实生活中审美的性质。他们的主要理由是①从美学史角度看,认为历史上绝大多数美学家都特别注重艺术美,并往往将其著作定名为“艺术哲学”。②从实际和方法论角度看,认为艺术是美的高度集中的表现,从艺术入手研究美,更易于抓住美的本质。③从社会作用角度看,认为艺术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艺术有它的巨大而深刻的教育作用。[8]当然,他们之间也有侧重点的不同。
这一观点较充分地注意到了艺术是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并且也注意到了美学与艺术的差异。具有一定的辩证性,为后来的“意象”论美学的兴起有引导作用。
第三种观点认为,美学是研究审美关系的科学。以周来祥和蒋孔阳为代表。在审美关系的理解上,他们之间有差异。蒋孔阳认为,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是美学研究的根本问题。美学是以艺术为中心,并主要通过艺术来研究人对现实审美关系,以及在这一关系中所产生和形成的审美意识的一门科学[9]。这里实则有美学是研究艺术的科学,与朱光潜的观点相类。周来祥认为把审美主体与客体所构成的审美关系作为美学研究的对象,是美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认为审美关系既是认识关系,又不是认识关系;既是伦理实践关系,又不是伦理实践关系,而是介于实践关系和认识关系之间的第三种关系。[10]
这一观点注意到审美活动中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的因素和关系。也就是说开始把审美活动作为一个复杂的有机体来对待。
第四种观点认为,美学研究的对象是审美经验。以高尔泰为代表。他认为离开主体的美感经验,就不能理解美,也不能理解艺术。理由是超越主体美感和美(包括艺术美)是根本不存在的。[11]
这种看法更多地关注到了审美活动的主体方面,尤其是注意到了主体情感活动在审美活动中的建构作用。但在这里“美”和“美感”实质上是一个东西,这就混淆了美感的主观性和美的客观性之间的本质区别。
第五种观点认为,美学是以美感为中心的研究美和艺术的科学。以李泽厚为代表。本来,在50年代,他主张美学基本上应该研究客观现实的美、人类的审美感和艺术美的一般规律。其中,艺术美更应该是研究的主要对象和目的,因为人类主要是通过艺术来反映和把握美而使之服务于改造世界的伟大事业的。[12] 进入80年代,他对美学的研究对象的认识,有了新发展。认为今天的美学实际上是美的哲学、审美心理学和艺术社会学三者的结合。美的哲学是从哲学角度对美和艺术的探讨;审美心理学则是整个美学的中心和主体;艺术社会学是通过审美经验这个中心来展开自己的研究。对艺术美的研究,正是对物态化了的心理结构的研究。因此,美学是以美感为中心的研究美和艺术的科学。[13]
这种观点从人的形上追求、历史考察和心理流程等方面对美学研究的对象进行定位,注意到了美学在人类生活中的不同层次性,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第六种观点认为,美学是研究审美活动及其规律的科学。以叶朗、蒋培坤为代表。他们都认为人类审美活动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叶朗认为以审美活动来作为美学研究的对象,就是要突破以往种种观点的狭隘性,把美学研究的天地拓展得更宽一些。同时又认为审美活动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活动,有着无穷多的侧面,但最重要的构成其现代美学体系的有八个大的方面,而最为核心的是审美心理学、审美艺术学和审美哲学。[14]蒋培坤认为,当代形态的美学理论应该是探索、研究人类审美活动各个方面及其普遍规律的科学。美不是预成的而是生成的。因此,不能从诸如“美是什么”这类关于美的先验定义出发,而要从最简单、最基本、最确定的事实出发,从对审美活动的分析来展开美学的学科体系。当代美学是由思辩走向实证,由分析走向综合,由一般认识论走向实践本体论,在实践基础上把历史上各主要美学学科形态集合、统一起来。这就要首先实证地考察人类审美活动的发生和历史展开,进而对审美活动中的主客体审美关系产生出美和美感,以及艺术中的审美,人自身的审美化等问题进行研究和探索。[15]
第七种观点认为,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生命或生存或存在。以杨春时、潘知常等为代表。他们承认审美活动是美学的研究对象,但与以往对审美活动的理解有着根本的不同。审美活动是一种以实践活动为基础同时又超越于实践活动的超越性的生命活动。[16]美学即生命的最高阐释。美学即关于人类生命的存在与超越如何可能的冥思。也意味着:美学必须把目光集中在审美活动与人类生命活动的关系上,集中在对作为生存方式的审美活动的本体意义上,存在意义、生命意义的诠释上。它不去追问美和美感如何可能,不去追问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如何可能,也不去追问审美关系和艺术如何可能,而去追问作为人类最高生存方式的审美活动如何可能,并且围绕这一追问,建构超美学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生命即审美,审美即生命。[17]
把审美作为人的最高本体、人的生命存在方式,注意到了审美活动具有着理性和非理性等特点,这是该观点有别于上述观点重要之处。这对美学研究的深化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是美学更好地干预生活、回应时代需要的表现。
第八种观点,认为美学研究的对象是审美文化。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观念不断深入人心,人们开始以消费规模的大小来衡量产品(包括物质产品和精神文化产品)的价值。显然那种只重形上追求的、“孤芳自赏”的精英美学受到了冷遇。为了促进美学的转型、消解形而上追问、适应时代的需要,有大批学者将美学的研究对象普泛化为文化活动即审美文化。[18]
从本质上讲,美学是生活之学。干预生活、美化人生、引导人类的实践创造活动、追求美好的未来、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是美学的天职。“文化”本身就是人类按照美的规律创造出来的“产品”,是人类的特性之一,是人类生命创造的确证。也就是说,“文化”就是人类不断进行审美的结晶。由此审美和文化具有极大的一致性。尤其是当代生活的高度文化化、审美化,更使人们领略到美学走入了生活。当然,把美学泛化为审美文化有着对美学失去定性的倾向。
以上观点各有其道理,但其中的优劣也是不言而喻的。把美学界定为艺术或美感,似太狭窄。把美学的对象限定为美,这个“美”又是不准确的,范围十分模糊。把美学对象规定为生命活动或文化,似又太宽泛了。在我看来,将审美活动、审美关系或以美感为中心研究美和艺术规定为美学的对象,似乎更符合实际些。不过,还应作更深入的研究。美学的对象应该是审美活动,而且是人的一种实践活动,它是社会性和自然性,理性和感性,现实性与超越性相统一的过程。而这一活动或过程集中地体现在艺术中。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