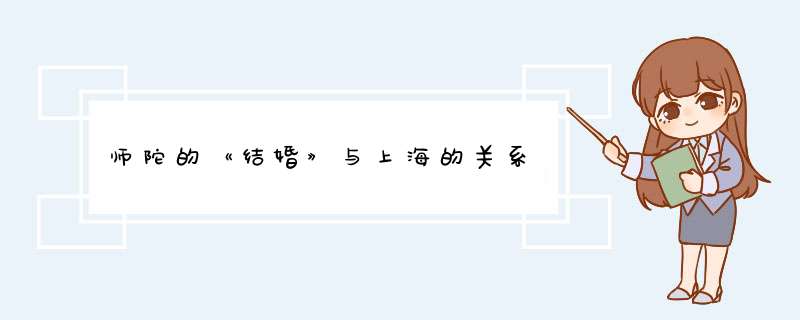
师陀的《结婚》是在上海产生的灵感。在师陀的人生经历中,上海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空间。1937年,师陀逆行于逃离上海的人群中,对面,难民车毫不停留的一列一列迎着人群开过来,此后流落洋场,终其一生定居于上海。
师陀是一个作家,与佛教没有关系师陀,原名王长简,笔名芦焚。作家。河南杞县人。曾参加反帝大同盟。后任上海苏联广播电台编辑、上海文华**制片公司特约编剧。建国后,历任上海出版公司总编辑、上海**剧本创作所编剧。后在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专门人事创作。著有短篇小说集《谷》,长篇小说《结婚》、《马兰》。
作家简介:
师陀(1910.3.10—1988.10.7)原名王长简。1946年以前用笔名芦焚。河南祝县人。1921年高中毕业后赴北平谋生。九一八事变发生,即参加反帝大同盟,进行救亡宣传工作。最初的小说《请愿正篇》,发表于《北斗》。1932年与汪金丁等创办文学杂志《尖锐》。他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谷》,1937年因艺术风格独特而获《大公报》文艺奖金。
1936年秋,从北平到上海。不久抗日战争爆发,遂长期蛰居于日军占领的上海。1941年至1947年,任苏联上海广播电台文学编辑。《果园城记》的大部分写于这个期间。他还写有长篇小说《结婚》等。1946年后相继任过上海戏剧学校教员、上海文华**制片公司特约编辑,写过**剧本。
建国以后,他历任上海出版公司总编辑、上海**剧本创作所编剧,到河南、山东、东北各地访问,写下的作品主要收入《石匠》集中。1957年 后一直是作协上海分会专业作家。60年代初期,曾专注于历史小说和历史剧的创作,发表了剧本《西门豹》、《伐竹记》和小说《西门豹的遭遇》等,颇得好评。
著作书目:
《谷》(短篇小说集)1936,文生
《里门拾记》(短篇小说集)1937,文生
《黄花苔》(散文集)1937,良友
《落日光》(短篇小说集)1927,开明
《野鸟集》(短篇小说集)1938,文生
《江湖集》(散文集)1938,开明
《无名氏》(短篇小说集)1939,文生
《看人集》(散文集)1939,开明
《上海手杞》(散文集)1941,文生
《无望村的馆主》(中篇小说)1941,开明
《果园城记》(短篇小说集)1946,上海出版公司
《结婚》(长篇小说)1947,晨光
《马兰》(长篇小说)1948,文生
《大马戏团》(剧本)根据安特烈夫《一个挨耳光的人》改编,1948,文生
《夜店》(剧本)与柯灵合著,根据苏联高尔基《底层》改编,1948,上海出版公司
《历史无情》(长篇小说)1951,上海出版公司
《春梦》(短篇小说集)1956,香港艺美图书公司
《石匠》(短篇小说集)1959,作家
《保加利亚行记》(散文)1960,上海文艺
《山川历史人物》(散文、小说等合集)1979,上海文艺
《恶梦集》(短篇小说集)1983,香港文学研究社
《芦焚散文选集》1981,江苏人民
《芦焚短篇小说选集》1982,江西人民
《上海三札》(散文集)1984,宁夏人民
1徐志摩诗歌艺术风格方面的若干问题提出新的见解,主要分为三部分。一、认为不应过于强调诗人与19世纪英国浪漫诗派的渊源关系,从风格角度看,徐志摩显然不是中国的雪莱、拜伦。二、徐志摩诗歌浪漫风格的独特价值在于:其中没有一般年轻人那种狂躁不安、雄心勃勃的成分,而是渗透着大孩子似的个性气质。三、如同每一位真诚的作家一样,徐志摩也有意探索诗歌风格的多样化,但从艺术实践角度分析,他的探索基本上是失败的,他缺少把握分寸感的相应艺术功力。但历史对作家作品的自然选择方式是:只认高峰,不看低谷。
3目前,学术界对曹禺的早期戏剧的研究大都集中在作家、作品的比较单纯的层面上,对其深层的文化内涵并未作系统的探究,有的大多也侧重于与西方文化的联系,很少依据曹禺本人真实的文化处境去发掘其深邃的文化内涵,这不仅包括西方文化思想的内容,也当然包括民族传统的(而不是以某种文化偏见去观照)可以说,曹禺要求每部作品都有所推新的潜在心理动力使他的作品流程构成一部形象的旧中国走向新生的文化历史他的创作是动态、富有活力的他本着作家的良心用笔描画出自己的个人经历和激烈突变的时代投影在他的心灵深处的苦闷、迷惘和憧憬他以其内在真善美品格不仅感动着读者,也深深打动着观众他的剧作无论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还是话剧表演艺术的角度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成功蕴涵着的孜孜以求的人格精神和宝贵的艺术经验对我们当代的文艺创作,尤其是话剧、影视剧创作仍然是有着深刻的启发、批判和引导作用该文立足曹禺早期戏剧流露出的真实的文化处境,从文化价值(文化悖论,文化抉择,文化拯救)和审美形态表现出的文化因素(激情的节奏,浑圆的梦境)对其文化内涵作一尝试性的阐析特点:第一, 把心理刻画与写形传神的艺术表现相结合,精细地展现人物的灵魂世界。第二, 浓郁的抒情与深沉的人生哲理的有机统一。第三,地方民俗风情的艺术表现与诗的意境创造相互交织
15沦陷区文学的构成比同一时期的国统区、延安根据地显得复杂而多样化,而各种文学都有其特殊的存在方式。
就爱国的进步文学而言,同敌伪统治直接对抗的逆鳞之作并不多见,而大多采取曲折的抗争方式。比如,“抵抗意识”是沦陷区进步文学描写的主要对象,但“武装的抵抗”的描写只能在“抗联文学”一类的特殊文学形式中得到表现,较多的作品致力于“心理的抵抗”的开掘或描写种种蕴含着民族复苏生机的传统民风,其中潜行着种种民族正气;或由日本侵略野心的得逞而引起对民族性格的反思,结合着异族欺凌的现实透视某些民族劣根性。“隐忍”、“深藏”也成为相当多作品的特色,表面似乎对现实统治采取冷眼旁观态度,实际上深藏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满、反抗,对现实的愤愤不平。尤其是一些进步作家利用一些政治背景复杂的刊物所发表的作品,如上海的中共党员束纫秋、王元化,丁景唐等当时都巧妙利用过《天地》、《苦竹》、《风雨谈》一类刊物发表作品,更具有曲折抗争的特点。
考察媚敌文学,明目张胆助纣为虐的也不多,或是当局发起的征文,或由以政者为之,也有作者“表态”性的偶而为之。这类“作品”无法从沦陷区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开掘到能和谐地表达其政治、艺术观点的生活具象,更无法构筑一个源于沦陷区历史和现实并与之保持谐调的艺术世界,有的只是苍白无力的政治图式和膨胀的审美恶趣,作者也大多为文学青年,如1942年北京所出配合治安强化运动的《短篇小说展览会杰作集》,武汉所出配合“和平运动宣传”的剧作集《三个方向》,广东省宣传处1942年所出《和平剧集第1集》等。文学味较浓的是如周作人那样的散文。在谈天说地、论古道今中隐现出难以言明的民族变节者的心态。
在汉奸文学背离民意,不得人心,日伪当局虽大力扶持也无法使其支配沦陷区创作局面,而爱国的进步文学也由于环境的严酷而得不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得以在夹缝中大量生存的是“中间状态”的文学,这类创作本身的成份就是复杂的,存在着无益有害、无益无害、有益无害等种种情况,但都因不直接涉及时事,离抗日现实较远,所以往往不为当局封禁。这些创作中,有的重视知识性、娱乐性,或品茶饮酒,或谈狐说鬼,或纵谈古事,或言情武侠,以此取悦读者;有的则在描绘家庭琐事、抒写个人感慨中,淡淡透出着某种现实生活的气息。比如上海沦陷时期同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苏青,在1943年至1945年,频频出版小说集,显示出一种别有风味的“闺秀派”格调,其成名作《结婚十年》,作者自己也承认是一本“抗战意识也参加不进去”的小说,甚至自溺于既“不大高兴”“高喊什么打倒帝国主义”,也“始终未曾歌颂过什么大东亚的“超脱”(《关于我——〈续结婚十年〉代序》)。小说当时整体上吸引读者的是描写中的盎然的日常生活的情趣。尽管缺乏强烈的时代意识,但某些章节,比如前半部中对积淀着传统意识的种种家庭生活习俗的描摹,后关部中对“八·一三”战争中逃难生活的叙述,都还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现实生活的某些真实,因而在当时冷落的文坛倒也获得了一部分读者的共鸣。自然,也有些消闲文学虽未直接为虎作伥,但也污染读者心灵。1942年华北文坛发生过一场论争,一些作家对公孙yàn@①以“暴露真正的人生”为幌子连续发表的一系列“色情”小说进行了批评。便反映了创作界对这类消闲文学的警惕和拒绝。总之,这类作品既没有对现实生活进行粉饰和美化,但也没有深入反映日伪统治下的黑暗和苦难。
这些“中间状态”的创作,自有其历史价值。例如,有这样一种情况,在该地区沦陷之前的左翼文学同国民党右翼文学的对峙中,有些文学刊物“超然”于这种对峙之上,或以经营为目的,因而被视为“中间派”。沧陷之后,这类“中间派”刊物得以继续存在,但它们并未与日伪同流合污,而是或借历史题材张扬民族正气,或描摹种种世态人生来抨击黑暗。其中不少作品让人能体悟到弱小民族的阴柔抵抗哲学。一些当年留居沦陷区的日本文化人曾谈及他们对一些中国作家创作的感觉,觉得其中有“看不透”的谜,在文学上找不到反抗的形式,却让人感觉得到有反对的情绪,有抵抗的力量。日人感觉况且如此,中国读者也许更能从中体悟到自己民族的感情。在种种貌似“中间”的形式中有夹带、有包藏、有潜流,正是沦陷区文学构成上的一个特点。而在公开宣传抗战的刊物无法生存的特殊情况下,这类“中间派”刊物及其创作实际上已成为沦陷区中华民族文学血脉得以保存、发展的一个阵地,其历史功绩不可湮没。
在异族统治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格局中生存的沦陷区文学,其创作形态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情况。例如,在其创作主题上往往出现同一主题交织着多重含义的情况。如当时华东沦陷区的东吴派小说,华北沦陷区的旧京小说,东北沦陷区的艺文志派小说,不约而地开掘着“批判旧家族制度”的主题,这几乎成了他们既不直接触及时弊,又不甘沉沦于粉饰文学泥潭的最好选择。但这主题的表现存在着分化,或把旧家族制度作为“暗”的世界的主要目标来攻击,或在“历史的批判中”思考现实,同时,也不是没有由此走向“东方古典的复归”。再如,创作中的乡土倾向,作为民族意识的隐性表现是显而易见的,但作家们对其开掘的侧重点仍有所不同,有的乡土小说以其对“生命”这一主题原型的重新开掘参与对民族存亡问题的发言。“爱国也需要生命,生命力充溢者方能爱国”(沈从文语),大概是一些乡土小说追求粗犷的人心、强悍的民风等生命形态的潜台词。《大草原》(谷正kuí@②)、《雪岭之祭》(疑迟)、《风雪》(袁犀)等都极力显示在风雪肆虐中跃动着野性、土味的生命情感和生命意识、即使是《高原上》(郭明)那样宁可“牺牲”人物,也要写出其对“血性”生命力的迷恋那样的描写“失误”,也让人看到了作家对强悍生命力的迷恋。而有的乡土小说则着意捕捉独异的乡情,在乡情同民族情的交融中去引起共鸣。自然,民有的乡土小说在“复归故乡”、“复归历史传统”中隐伏着某种误入“国策”文学的危机……。这种同一主题的选择的背后,有着作家们共同的积淀着民族意识的心态;而同一主题的变异多重奏,则反映了作家们从不同侧面遭受到的沉重压力及其有着差异的群体、个性心态。
林榕1944年在一封信中曾这样论及当时沦陷区作家的人生态度:“我总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以为今日的从事文艺工作者,不是在做官样的文章,就是以文学为求生的工具……今日活跃于文坛上的人物,恐怕只是很少的一部。另外的一些却是在沉默中工作的,也不为我们所知,他们既不以文学为生,更不是以文学做职业。这才是一个文学者的应有态度,真正的龙虎或许产生于这里也未可知。”[①a]屈从于环境。文而官而奸;为生活所迫,卖文为生;甘于寂寞,在默默耕耘中重操守……这三种情况,基本上概括了沦陷区作家在纷纭复杂的现实环境中作出的人生抉择。而作为这几种人生抉择的作家创作心态则呈现出更复杂多变的走向。
有人当时用“无救”一词来描绘身处沦陷环境中作者心灵的窒息[②a],而以文学自救成为沦陷区作家最基本的创作心态。一些进步作家秉烛待旦,蛰居为文,他们在沦陷前创作中所蕴积的民族忧患意识,在沉默中趋向新的发展轨道。师陀自述其沦陷区生涯“如梦如魇,如釜底游魂”,而使他“在极大的苦痛中还抱无限耐性”写下去的,便是要借他当时所要写的“果园小城”写出“中国一切小城”的生命、性格、思想、情感(《果园城记)序》),就是说,借咀嚼中国城乡普通人生的命运意味,借反省中国民族的社会文化性格,来寄托自己在异族统治下的激愤怨恨。“当一个国家的大部分公民连他们自己有没有人的资格都不知道,我们怎么能希望他们过了一夜就积极起来,怎么能使他们自觉的去和敌人战斗呢?”[③a]这种焦灼不安的对本民族的透视反思中,无疑潜行着强烈的民族意识。杨绎当年所作《称心如意》、《弄真成假》等“政治色彩不浓的作品”,着重剖析在封建传统文明和现代西方文明夹缝中生存的中国知识分子、市民阶层的心态,却是意在用“这喜剧里的几声笑”,表示虽“沦陷在日寇铁蹄下”,仍“不妥协、不屈服”、“不愁苦、不丧气”的民族“乐观精神”[④a],其中蕴含的也是民族自新图强的意识。
民族存亡意识在深层的心理上影响着作家创作心态的,最明显的莫过于“鸳蝴派”的创作变化。沦陷区的特殊环境,使“有益无害”,或“无益无害”的中间状态作品大量存在,也使“鸳蝴派”的趣味主义、“超政治观”有了适宜土壤,其创作实际上面临着一种严峻的选择。而恰恰是这种选择,反映出了民族意识高涨的社会心理对作家创作心态的影响。如一向被称为“鸳蝴派五虎将”之一的周瘦鹃1943年在复刊的《紫罗兰》上多次表明其创作旨趣:“虽重趣味,但也不能忘却意义”,写“言情”,也须顾及“这些年来,兵连祸结,天天老是在生活线下挣扎着,哪里有这闲情逸致侈谈恋爱呢”的现实。如果说,昔前鸳蝴派创作注重趣味主义,主要出于投合小市民读者的口味,那么,此时他们仍不放弃“重趣味”的主张,则含有借此来躲避文网以求自存的因素了。而同时,中华民族史上最黑暗的岁月又使每个具有民族意识的作家都无法缄默。“趣味与意义兼顾”成了此类作家此时的共同心态。从实际创作情况看,他们的创作一方面继续迎合着中国广大市民阶层的阅读心理,如中国历史长期对官场的掩饰,对性意识的禁锢所加剧的人们对这些文化层面的好奇心和神秘感等,另一方面,趋俗的审美趣味有所减少,通俗创作中现实的生命意识有所加强。
当时沦陷区文坛上活跃着大多是青年作家。他们中不乏热血青年。象关沫南那样“作家若要深入地创造,就不得不在阶级意识上使自己肯定”[①b]的信念,徐开垒那种“阳光将永恒的存在/西山会崩裂/地下的蚯蚓会哼它欣幸的劳歌”(诗《笼里》)的创作追求,也构成着许多青年作家的创作心态。然而,沦陷区毕竟是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九月的晴空”已不复存在,“大地的歌唱”也已不可能,青年时期难免的迷惘、惶惑会在这一环境中强化,而不甘沉沦又是必须作出的历史选择,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环境中,青年作家们形成了几种较为独异的心态。
一是急于在文学上“造坛”的心理。沦陷区文坛的冷寂,使一些青年作家急于改变现状。东北沦陷时期最有影响的“艺文志派”便是一个由青年作家聚合成的创作群体,其重要成员古丁多次讲过:“东北作家必须一面作文,一面造坛,这苦难是非同小可的,但是倘不决心冲入这非同小可的苦难之中,满洲文学是不会本格地发展起来的。”(《谭·梦境》)为此,他们提出了所谓“写印主义”,即第一紧要的是“努力写出作品”,至于“写什么,怎样写。那都是有了作品以后的事”(同上)。他们结社时,也强调“文艺团体并不是为了文艺以外的任何东西而设置的”,“文艺团体的意欲的具体的表现”乃“写作”、“印书”、“出刊‘同人杂志’”(古丁《谭·斗牛》)。这种“只有写出来,才有意义”[②b]的心态中既有着在当时纯文学凋零,庸俗作品充斥文坛的情况下想把冷落萧条的文艺事业振兴起来的积极作用,也有着“避世”因素,“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等。值得注意的是,急于“造坛”,而“低气压”的社会环境本来就窒息着文学的发展,于是,为“造坛”而同在华的日本文化人发生种种联系,而日本文化人此时复杂的背景正潜伏着种种失落文学的危机。
另一种引人注目的情况是,在沦陷区这一特殊环境中,既力图远离敏感的现实政治,又想避免陷入精神困境,于是写作成了最好的“自存”方式,由此产生出两种较有代表性的创作心态。一种是追求日常生活的情趣,甚至以其创作在恢复日常性的大胆上取得突破而引起文坛小小的轰动,这显然迥异于“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小说几乎总以贴近现实政治的大胆、深刻引起社会的“轰动”效应。对这一类作者而言,现实社会的变迁不会有什么震撼力,他们醉心的是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趣味。苏青所言:“我对于一个女作家写的什么‘男女平等呀,一齐上疆场呀’就没有好感,要是她们肯老实谈谈月经期内行军的苦处、听来倒是入情入理的”[③b],张爱玲所言“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朴素,也更放恣的”[④b],都可以表现出一种“超然”于现实政治的创作心态。在华北,东北沦陷区,也都有作家把自己的创作称之为“超然派”,同样表现出避开“爆炸性”的政治题材,恢复日常性描写来还原现实、挖掘人物善恶的创作倾向。但这种非“为民清命”式的创作,本身仍是作家心灵并不自由的一种生存形态。
在以写作为基本生活方式的青年作家中,还有另一种创作心态:以对“恒常”、“哲理”的思索来超越于现实的苦难。被称作为“鬼才”的东北作家爵青就自称“是一个哲学思维的患者”,“作者一贯的创作态度是:他反对描写身边的庸俗的现实,他主张在作品中要倾注作者的哲学思想”[⑤b]。这样一种创作心态不仅使爵青小说题材有超现实倾向,而且往往追求空玄的哲理。他的《废墟之书》(原载《艺文志》第2期)便是一部反映其作为“哲学思维的患者”特色的小说,作品通篇有与友人的通信组成,种种自白中充满着灵魂与精神、生与死、新旧废墟、孔子的东方文化与巴黎的现实沙龙等的思考、探索,作者关注的并非是现实灾难造成的废墟,这在作者看起来也许微不足道,他所要体验的是超越于现实的“人类废墟”之痛苦,所以他的小说都是“意在并无素人的味气”[①c]。这种创作心态有时也并非对现实的冷漠,而多少来自对“文学”的执着。袁犀的创作是关注着现实的,但当他后来越来越执着于“文学者存在于‘文学’里”[②c]时,他的创作视野也开始较多地转向带有整个人类共通性的一些层面,即对人的生存状态、人的心理结构,尤其是人的潜在意识的思考。他的未完长篇《释迦》便是力图通过一个喜好独自沉思的冥想者悉达“参悟人生妙理”的心理历史,来表现其对于人类精神实质的思考。
事实上,在沦陷区这样一个心灵窒息、苦闷丛生的环境,写作越来越成为文学青年探寻生路的主要方式。对文学的虔诚构成着青年作家们的基本心态:“文学是一种生命的燃烧”(古丁语),“文学者的精神,就是我们在人类的历史里见到的,不同于市侩、买办、倡妾、奴才等等之类的对人对已的态度”(关永吉语)。……这些自叙中都有着把文学作为一种全身心投入的精神状态来对待的追求。而其中,对文学的“诚实”又成为其追求成为“真正的文学者”的重要侧面:“文学者至少要诚实,文学者失去了任何的节操以后也必要诚实的。”《袁犀语》[③c]正是在这样一种群体的创作心态中,产生了一种在特殊环境中经过锤炼的现实主义,从而形成了沦陷区文学中最有其文学史意义的创作特色。
这种现实主义,首先是一种向“五四”时期文学“回归”的现实主义。环境的严酷使大部分作家已无法用文学直接介入民族解放的政治,民族灾难的现实又无法使作家们置生灵涂炭的人生于不顾。于是,以“五四”时期表现人生的多元追求作为创作基本格局的情况便形成了。而借助于“五四”时期“表现人生”的文学观念,在不同层次上开掘异族统治下中国人的心理人生,成为相当多作家的创作追求,从而产生了两组整体上相当厚实的沦陷区文学形象。
作为最能折射出异族统治下中国人的复杂心态的文学形象是知识分子,而一批在4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中呈现出相当或一定光彩的沦陷区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如胡去恶(师陀《结婚》)、方鸿渐(钱钟书《围城》)、周大璋(杨绛《弄假成真》)、柳原(张爱玲《倾城之恋》)、景二爷(高深《兼差》)、林小彪(梁山丁《绿色的谷》)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构成着讽刺对象。不管这些形象的生活背景是否被置于沦陷国土上,形象的被嘲讽是都包含着作家对沦陷区知识分子心境的剖析的。应该承认,沦陷区的知识分子很少是出于政治上的理由而留下来的。所以作家对他们剖析也较少从政治角度切入,而侧重于文化认识角度的考察。异族统治的现实迫使知识分子重新认识、估价自身所受到的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于是,方鸿渐式的凭借西方文化的盲目冲撞,景二爷式的喘息于传统文化中的懦弱无能,林小彪式的徘徊于“乡土文化”和“洋场文化”间的犹豫,以及种种屈从于殖民文化的奴化心理等,都作为对外来和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而得到发展。“中国人有一种民族的病态,我们想改正它还来不及,再到这个地方和日本人学习,这是一种病态上再加上病态。”这是萧红离开沦陷后的东北不久又东渡日本后在给萧军一封信中说的话,自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沦陷区作家的某种典型心态:对民族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各自“病态”的双向审视。在日本殖民者极力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沦陷区环境中,中国作家塑造的这一类形象、批判、破坏的因素多,而见不到多少建设的新因素,正包含着作家对现实人生认识上的一层深层心理,也使“五四”时期对中西文化的审视得到了某种延续。
沦陷区文学中另一类显得较为厚实的文学人物是市民形象。张爱玲笔下众多小市民的价值已为人们认识。其他如《亭子间阿嫂》(周天籁)、《结婚十年》(苏青)、《予且短篇小说集》、《太平愿》(马骊)、《萍絮集》(萧艾)、《秋初》(关永吉)等作品集中,都有着对市民阶层敷衍、苟且、怯懦和庸人哲学的入骨描写。作家们集中刻划这类形象,是因为市民阶层的心理波动远甚于其他阶层。沦陷初期惊魂未定中的惶惑,随后各种工于心计的苟且,喘息之后对于各种生活趣味的寻求,当然也有着苦难中的呼号、沉默……这些显然能比较广阔地展现沦陷区动荡不安的心理人生。
在沦陷区文学中,也产生过一些自有神韵的工农劳动者的形象,这类形象的塑造,也有着向“五四”时期的“回归”。如当时的东北华北,都有一批作家明确打出“乡土文学”的旗号,着力于农民心理的开掘来进行苦难农民形象的塑造。总之,借助于“五四”文学表现人生的观念,在不同层次上开掘异族统治下中国人的心理人生,成为沦陷区文学首先引人注目的现实主义特色。
这种现实主义也是在多个方向上探索的艺术,其目的显然在于增强文学在险恶环境中的应变能力。以散文为例,一部分作家着笔于侵略奴役下城乡生活场景的广泛描写,有的大胆直接描述血泪生涯,有的在喜笑怒骂中对现实进行社会批评,如洛川、王韦、鲁风、桑榆的报告文学,田贲、裴馨园、季疯、金光军等的杂感。但时势多难,环境杌陧,较多的作者是在含蓄曲折中借助于象征性意象或梦幻等抨击时弊,寄托激愤、如林榕、也丽、黄肃秋等的散文。缠绵深沉的思乡恋家情绪的抒发,成为作家寄托国家民族兴亡之感的载体。《松堂集》(南星)、《离乡集》(戈壁)、《两都赋》(纪果庵)、《风土小记》(文载道)、《驿站》(陈烟帆)、《归乡》(爵青)等和达秋(唐景阳)等创作便提供了这方面的佳作。不少作家转向抒写“自我”,以个人抒情的真实性和独特性折射出“炼狱”历史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在《画梦录》那种深重的孤寂、抑闷、痛苦之外,更多一些时代重压的色彩,如但娣、杨絮、尤其、姜灵菲等的散文。也有不少作家转向人情世态的体察和日常情趣的玩味,其中有对社会现实的某种洞察,有在抚今追昔中体察世相,有在闲话家长琐事中某种不平,也有在古今“杂学”中思考现实的,如纪果庵、谭正璧、丁丁、予且、韦长明、辛嘉等的创作。絮语体随笔体的散文中,有袒露真性、玩味人生的,如苏青、张爱玲、朱tí@③之作;有在幽默中评论人生的,如古丁、刘汉之作。而在众多的品酒论茶之作中,也不乏现实的感慨。多种特殊的生存形态,使沦陷区散文获得了某些发展。
这种现实主义是艺术上经过了更多锤炼的现实主义。1992年11月上海“孤岛”文学研讨会上,王元化在发言中特意强调了沦陷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特点:越来越重视艺术上的锤炼。以小说创作而言,便是以艺术上的锤炼来求得自己的生存发展。如当时被允许存在的自然有言情一类的通俗小说,但作家如果不摆脱自身趋俗的市民意识,仍一味迎合读者的表层需要,在民族遭受灾难之时,恐怕很难再象以往那样拥有读者。所以,他们一方面开始注意到市民读者审美趣味蕴含的特定时代的文化内涵和心理特征并加以引导,充实通俗小说中现实的生命意识;另一方面,打破以往注重情节的编造为基础的传统构思,革故鼎新小说技法。当时《小说月报》、《紫罗兰》、《大众》、《中国文艺》等刊登的一些言情小说,其美感已不再完全由故事情节来激发,而侧重由充溢着生活实感的叙述本身来引导。又如当时颇为引人注目的乡土小说,在以描写存在于乡野百姓中的生命情感,生命智慧、生命意志等生命形态而揭示出民族更新力所在时,颇具艺术功力。被称为“东北沦陷时期乡土文学代表作”的长篇小说《绿色的谷》1943年出版日译本时,作者在《序》中说:“绿色象征青春、健壮、活泼,并含有追求成熟的喜悦,这就是小说的主题”。小说正是在多种生命形态(其中如林淑贞萎枯于金刚经中的生命情感,霍凤被奴性扭曲了的生命智慧等,都刻划得令人难忘)的强烈对比中,生动凸现了祖居于狼沟的下坎乡民们纯真的生命情感、顽强的生命意志和成熟的生命智慧。华北的毕基初则借“绿林传奇”来张扬起民族正气。他的《盔甲山》、《第25支队》等将清纯,雄旷的自然环境同古老的青龙剑、酒旗等人文之物交织在一起,重笔渲染舍生取义的浩然之气,深入开掘“替祖宗洗羞”的人物心理,在一个个“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者身上写出不甘屈辱的民族精神,在当时实在是意味深长的。至于师陀、唐tāo@④、闻国新等此时的小说创作,比起他们的旧作来,艺术上的锤炼更显其深沉了。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