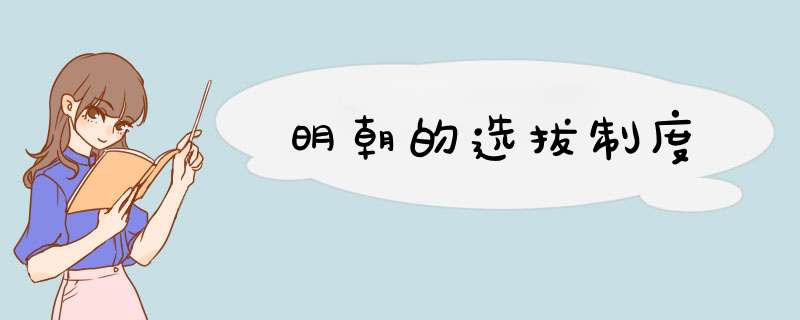
主要是科举制度。明代沿袭了自隋唐以来的科举取士制度,公元1367年朱元璋开设了科举,设文、武二科。按照当时的规定,规定凡应文举的人,通过考察言行,以品评他们的道德;通过考试经术,以了解他们的学问;通过考核书算,以了解他们的实际能力;通过考核经史时务策,以了解他们的从政能力。凡应武举的,先试之以谋略,次试之以武艺,但求实效,不尚虚文。主要的考试内容是八股文,因此又叫八股取士。成为进士就有做官的资格。通常第一甲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都是正六品官。二甲则授以正七品之职,三甲授正八品之职。二甲、三甲进士考选为庶吉士的授翰林院官,其他或授六科给事中、监察御史、各部主事、中书舍人、行人司行人等京官及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地方官。
除了科举之外,还有一种制度叫作庶吉士制度。庶吉士制度是明朝为了选拔和培养高级官员而所设置的制度,并在不断的发展当中得到了完善。庶吉士,其实就是某种进士的代称,指的是观政于某些朝廷部门的进士,这些进士主要是在翰林院等部门进行进修。而这些进修的进士,则是明朝朝廷的重要培养对象。明代内阁当中的大部分人,都来源于庶吉士制度。
1规模加大了,隋唐宋元科举,录取的人数极少。明朝科举的规模比之要大上很多。 2考试内容越发当一,只读四书五经,八股文形式束缚人的思想。明朝以前,唐宋的科举不仅考经史典籍,也考数学、农学等等,推动了人才的全面发展。 不过能从八股文死板的考试中脱颖而出的那些人,也必是拥有超乎常人的实力的。明朝很多科举出身的官员,都在历史上留下了赫赫功名。这就跟现代的应试教育一样,那些高考状元们,智商能力必有过人之处,状元不是每个人都能当的。真正的天才,无论在怎样形式的泥潭中,都能够取得成绩脱颖而出。何必贬低那些应试教育的“书呆子”呢?能考100分,说明他的智商就是有过人之处。能考中八股文的状元,也只有真正的天才才能办到。
院试、乡试、会试、殿试。
科举取士制度建立于隋朝,确定于唐代,历宋而至明清,各朝都有所沿革,而明朝科举制度最为完备,清朝基本上是沿袭明朝制度,没有太大的变化,因此把明清两朝科举取士制度综述如下:
明清的科举制度,可归纳为三级考试:第一级是院试,第二级是乡试,第三级包括三种考试,即会试、复试和殿试。此外,还有一次朝考。
扩展资料
1、院试:在府、州的”学院“举行,又分为“岁试”、“科试”两级。岁试是每年举行的童生“入学”考试,录取后即为“生员”,通称“秀才”。科试则是对已在学校的秀才进行考试,成绩优者方可参加下一级考选举人的乡试,成绩劣者要受处罚甚至取消生员资格。
2、乡试:又称为大比、秋闱,每三年一次。乡试三场,分别在八月初九、十二日、十五日。明清乡试录取举人名额由中央规定下达,各省按人口多少分别为数十名到一百数十名不等,全国录取总额为一千人至一千二三百人。
由于考取举人即具备做官资格,乡试可说是明清科举最重要也最艰巨的一关。乡试之榜明清时称乙榜,乡试则称乙科,与进士会试的甲榜、甲科相对。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
3、会试:乡试后的次年的二月初九至十五日举行于京师礼部,又称春闱、礼闱。会试三场的内容于乡试一样,明清每科会试录取进士约二三百人。明清会试正榜以外一般还有副榜。录入副榜的举人虽不算进士,但可以授予学校教官或其他较低级官职,或吸收入国子监为监生,获得国家一定的俸禄。
4、殿试:明清科举的最后一级考试,在会试后一个月即三月十五日举行。殿试内容试时务策一道,试题由内阁大臣预拟数种,临时呈皇帝圈定。明清殿试一律不黜落,只排定名次。
状元、榜眼、探花等前三名列为一甲,算是进士及第;第二甲若干人,算是进士出身;第三甲又若干名,算是同进士出身。三月二十五日,新进士和殿试官员在礼部享受御赐“恩荣宴”。
宴后陆续进入封官任用阶段。一甲的三名进士一般授予翰林院编修等清要之职,其余进士往往还要进行一次馆选或朝考,然后结合殿试名次,分别授予官职,优者亦进入翰林院。
-科举制度
-明清选官制度
明代内阁制度
然无论如何,在明代,一切事,总之是皇帝最后总其成。但皇帝一人当然管不尽这许多事,因此我们就得讲一讲皇帝的秘书处。明代皇帝的秘书处,当时称为内阁。秘书便是内阁大学士。因为皇帝在宫里办公,他需要几个秘书帮他忙,这些人的办公地点在中极、建极、文华、武英四殿,还有文渊阁、东阁两阁。这些处都在内廷,所以这些人就称为内阁学士或内阁大学士。内阁学士原本的官阶只五品,而六部尚书是二品,可见内阁学士在朝廷上地位并不高。上朝排班,大学士的朝位班次也在尚书的下面。今且说这些大学士做些什么事情呢?在太祖时,内阁学士不过像是皇帝的顾问,遇皇帝有不清楚的事,可以随时问他们,听他们意见,做皇帝之参考。奏章批答,从前是宰相的事,现在是皇帝的事。皇帝不能一一亲自动笔,便口授大学士写出,这所谓“传旨当笔”。由皇帝吩咐下来,这事怎样办,那事怎样批,他们只照皇帝意见写下。所以照理,大学士不过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政治大权还是在皇帝,不在大学士。
据当时统计,自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先后八日间,内外诸司送到皇宫里的奏章,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件。每件奏章里,有讲一件事的,也有讲两三件事的,共计有三千二百九十一件事。此因中国地方大,一切事集中到中央,中央政府所当预闻的事当然多。远从秦始皇帝时,早已把天平秤着公文,兀自天天看到深夜不得息,何况到明代?那时,西方还没有现代像样的英、法诸国。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小国家,不论疆土那么小,政治规模也简单得可怜。这当然不能与中国比。试问当时偌大一个国家,件件事要经皇帝批核,这当然很困难。我们试看北平故宫,前面三大殿,是朝会之所,后面如乾清宫等,由皇帝住宿。他天天要到前面来办公,距离既相当远,北平之气候九月就结冰,次年二三月才解冻,早上天气尤其冷。而中国政府传统习惯,会议上朝,总要在日出前,早上天不亮就朝会,皇帝也须黎明即起,等到太阳出来便散会了。一般做官人,多半住宫城外,远的如前门外骡马市大街等处。早上跑进皇宫有很远的一段路,骑着一匹马,带着一个仆人,掌一盏灯笼,四更五更就要去。到了紫禁城,还得下马,仍准骑马的只有少数几个人。一律须先到朝房,静候皇帝上朝。皇帝出来,天还没大亮,遇到天气寒冷,那时也没有近代的防寒设备。火炉很简陋,生些炭火,不过摆摆样子而已。明制一天有三次朝,称早朝、午朝、晚朝,如实则皇帝要三次出面见群臣及民众。明制常朝有两种:一叫御殿,一叫御门。御殿又称内朝,是在大殿内朝会议事。御门是到奉天门,就在阳台上,让老百姓也可以见面说话。现在西方国家有什么大集会,还有在阳台上讲话的风气,我们称这是一种民主政治的精神,其实清朝故宫的午门,就是与被皇帝和民众见面的阳台,不过这种制度清朝没有行,但明朝却有。皇帝一天要上朝三次,多少的麻烦。明太祖是开国皇帝,天下是他打来的,以前他是皇觉寺和尚,扫地挑水也干过,他有这样精力,可以做独裁的皇帝。明成祖也还是亲手打天下,他是封出去的王,从北京打到南京来篡了皇位,他也有精力可以亲裁庶务。再下去的儿孙,生长在深宫,精力逐代萎缩,便不能这样做。甚至不能天天出来上朝见群臣。今天不上朝,明天事情就接不上。事情接不上,不能叫文武百官在那里老等着,也不能群臣们说了话,皇帝无辞可答。后来皇帝便只有偷懒,把政权交付与内阁,阁权慢慢地重起来。
不过阁权虽重,而他们的官阶还是低,仍只五品,因此通常内阁大学士都由尚书兼,这样一来,内阁学士地位虽不高,尚书地位是高的。同时也和宋代般,他们都有经筵讲官。经筵讲官,是教皇帝或太子读书的,那是皇室的老师。由曾任这些官职的人来兼内阁大学士,自然和皇帝关系是既尊且亲了。所以明代的大学士(皇帝私人秘书)以六部尚书(政府行政长官)和曾任经筵讲官(皇帝的老师)的来兼任,他们的地位就尊严了。然而明朝大学士的官衔,却始终是某部尚书兼某殿(阁)大学士,譬如兵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之类,他的本官还是尚书,大学士还是一兼职。直到明代亡国,大学士还是一个五品官。不过上朝时,他以尚书身份而兼大学士,已经是站在其他尚书的前面了。然照制度正轨论,他之所以尊,尊在其本官,不尊在其兼职。所以明代内阁大学士,就官制论,绝对不能和汉唐宋时代的宰相地位相比论。
然而明代大学士,他在官职上的地位虽然低,他在政府里的权任却很高。因为一切奏章,政事,看详批答,都要经他们手。太祖、成祖时代,皇帝自己处决事情,口头吩咐大学士代笔,大学士自然只如一秘书。后来皇帝年轻不懂事,事事要谘询大学士意见。而且皇帝因于自己不懂事,也怕和大学士们时常见面,内外一应章奏,现由大学士看过,拿一张小签条,写出他们意见,附贴在公事上,送进宫里,在由皇帝细阅决定,这在当时叫做“条旨”,就是向皇帝分条贡献意见的意思。又称“票拟”,是说用一个小条子(即票)拟具意见,送皇帝斟酌。待皇帝自己看过,拿这条自撕了,亲用红笔批下,名为“批红”,亦称“朱批”。批好拿出去,这便是正式的谕旨。在唐代,一切政令由宰相拟定,送皇帝画敕。在宋代,是宰相向皇帝上箚子,先得皇帝同意或批改,再正式拟旨。现在明代,则一切诏令,皆出皇帝亲旨,大学士只替皇帝私人帮忙,全部责任在皇帝。而皇帝失职,却并无办法,算只有给事中有时可以封驳。给事中究竟是太小的官位,哪能拗得过皇帝。所以明代制度,可以说是由皇帝独裁了。不过碰到大事情,皇帝还是要到文华殿、武英殿来同那批大学士当面商量,只小事情不重要的,由内阁写了条子送进皇宫给皇帝慢慢地批。
但我们应知明代的天下,将近三百年之久,最初是皇帝亲自在内阁,后来有些皇帝不常到内阁,由内阁条旨票拟送进去批。甚至有几个皇帝则长久不管事,因不管事而更不能管事,就变成怕见大臣了。于是经年累月,不再到内阁,一切公事都要送进宫里去。最有名的就是万历皇帝明神宗,他做了几十年皇帝,有二十几年没有上过朝,政府里大臣都没有见过他一面。当时人传说他抽大烟,真假不知,不过这也很可能。自宪宗成化以后,到熹宗天启,前后一百六十七年,皇帝也都没有召见过大臣。但我们也不能尽怪这些皇帝的不好,因他们精力、智力有限,天天困在深宫,而要处决一应国家大事,这何等的不容易。无怪他们要怕事偷懒,避不上朝。我们只该怪明太祖订下那制度的不好。即是废宰相而由皇帝来独裁政事,那一制度确实在要不得。
现在再说皇帝和内阁日常不见面,于是皇帝和内阁中间的接触,就多出一重太监上下其手的机会。皇帝有事交付与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内阁有事,也同样送太监,再由太监上呈与皇帝。这样,太监就慢慢地弄了权。甚至皇帝嫌麻烦,自己不批公事,私下叫太监批。批红的实权,落到太监手里,太监变成了真皇帝,掌握政府一切最高最后的决定权。遇到太监懒批的,便把来当作包鱼包肉的废纸用。这种黑暗腐败,在历史上,只有明代有。太监领袖称司礼监,明代政制最坏时,私礼监便是真宰相,而且是真皇帝。当初太祖定制,一面废去宰相,一面却也预防到太监预闻政事的可能。故在洪武十七年,铸了一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挂在宫门里。可见太祖心里尽明白,废了宰相,由皇帝来独裁,太监接近皇帝,易于得弄权。正如汉武帝把相权揽在宫里,也预知嗣皇帝幼小,容易招致皇太后预政,所以要先把母后赐死。这些可有之流害,他们也是想到的,然而明太祖规定不准立宰相,这是他后人遵守了,始终没有敢违背。至于不准太监干预政事,他后人却没有遵守。明代太监预政,就比任何朝代干预得厉害。这哪里是太祖始料所及呢?
在这种情形下,外面弄得没办法,内阁学士若真要做点事,也必须先勾结太监。因为内阁见不着皇帝面,非结合太监,一切政事便透不上最高层。明代有名内阁大学士张居正,这是近人所推中国历史上大政治家之一个,但他也只能结合太监,才能揽实权。在神宗万历还没有做皇帝时,张居正就是神宗的师傅。神宗做了皇帝,张居正是当朝皇帝老师,而且又是内阁大学士。然而先生见不到学生面,大学士照政制论,是无法主持政令的。于是张居正只有同司礼监勾结,他才能舒展抱负,来策动当时的政事。但当时朝臣大家都反对张居正,说他不像前朝宰相,不是政府正式的行政首长,不该弄权专政。这批评实在也不错。当时尚书六部才是政府最高行政长官,他们只须听命于皇帝,并不须听命于内阁。若内阁和六部发生意见,六部可以说:你不是宰相,不是大臣,不该管我们的事。不该管的事而管,不该揽的权而揽,此是权臣,非大臣。权臣弄权与大臣当权,在中国传统政治观点上是大有分别的。大臣是在当时的制度上有他正当的地位的。在中国传统制度下,宰相无事不该问,无权不该把。他不问事,不当权,是失职,是无能。并非宰相,而问事揽权,是奸臣,是权臣。权臣弄权,这是违反国法的,也是违反政治上的传统道德的。然而明代的制度,则根本没有一个正式的宰相。六部尚书乃及七卿九卿,始是名正言顺的大臣。当时反对张居正的人,他们心里想:部(六部)院(都察院)长官,分理国事,只受皇帝节制,你做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私人顾问,你在皇帝面前,“从容论思”是你的责任,你不该借着这一点关系正式出面来干涉部院,那是你越权。因为张居正要管事,所以他要各衙门奏章公事每样备两份,一份送内阁,一份送六科给事中。这又是他不对。给事中虽官阶低,但在当时政制法理上,一切文件,该他过目,这是不错的。内阁则并无必须预闻之职权,只皇帝私下要他预闻才预闻。所以当时人反对张居正,张居正市没有理由答辩的。他于是只有向皇帝去辞职,他说他“所处者危地,所理者皇上之事,所代者皇上之言”,这几句话,丝毫也不错。然试问当时何尝有一道正式命令叫张居正代理皇帝呢?依照中国政治传统,皇帝不该干预宰相的事,此在讲汉、唐、宋三代政制时,已详细述及了。现在是内阁不得干预皇帝的权,就明论明,是不错的,张居正也无法自辩。现在我们不了解当时这情形,总认为张居正是一大政治家,他能主张讲法治,其实他本身就已违法了,而且违反了当时国家的大本大法呀。该皇帝管的事,他来管,那岂非不法之至吗?若张居正在汉唐宋三代,那是一好宰相。依明代制度论,张居正是一内阁学士,不是政府中最高领袖,不得以内阁学士而擅自做宰相,这是明代政制上最大的法理,也是明代之所以异于汉唐宋传统的。张居正要以相体自居,他一死,他家就被抄了。虽然他在明代有很大的建树,但当时清议,并不讲他好话,这就因为认他是一个权臣,非大臣。这不是专就他功业言,而是由他在政府之地位上的正义言。此刻我们要提倡法治,却又来推尊张居正,这正为不了解明代政治制度。当知明代的政治制度,早和汉、唐、宋传统有了很大的变化。张居正并未能先把当时制度改正,却在当时制度下曲折谋求事功,至少他是为目的不择手段,在政治影响上有利弊不相抵的所在呀!我们以上的说法,只就制度与法理论,不从事业和居心论。至少在当时那些反对派的意见是如此。我们详细讲述这一层,正为阐明制度如何牵制着人事,而明代此项制度之要不得,也就即此更可论定了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突出进士一科。考试大致分为以下四个步骤。
第一步称为“童试”,也可说是预备性考试。考生无论年龄大小皆称“儒童”或“童生”,先参加州、县级考试(即童试),由州、县长官主考,通过以后称为“生员”,又名“庠生”,俗称“秀才”。“秀才”又分三等,成绩最好的称“廪〔lin 凛〕生”,由国家按月发给伙食补助费;其次称“增生”,不供给伙食补助费。“廪生”和“增生”是有一定名额的。三是“附生”,初进学的附学生员。明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为了加强中央王朝对地方各级学校(府、州、县学)的统一集中管辖,便任命了一个负责专管一省教育的学官,叫“提调学校官”,这个学官也称为“学院”,由“学院”主持考试,所以“童试”又称为“院试”。院试合格后的“秀才”,同时也可入地方州县学为生员。获得“秀才”资格之后才能参加高一级的考试。秀才地位比老百姓高出一等,见了知县可以不下跪,官府也不能随便对其动用刑法了。所以《儒林外史》第三回写到范进中了“秀才”之后,他的老丈人胡屠户说:“你如今既中了相公(秀才),凡事要立起个体统来……家门口这些做田的、扒粪的,不过是平头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这就是坏了学校的规矩,连我脸上都无光了。”“童试”仅是科举考试的漫长征途中迈出的第一步,却有成千上万的人难以迈出这艰难的一步。据《清朝野史大观》卷十一载:“久试不第者尤甚。某叟年五十余,应县试考三十次,尚未冠。自题七绝云:
县试归来日已西,老妻扶杖下楼梯。
牵衣附耳高声问:“未冠今朝出甚题?”
童试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四书》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还有《孝经》、《性理》及《太极图说》、《西铭》、《正蒙》等儒家经典和理学著作,以及清朝廷颁布的“圣谕广训”、“训饬士子文”等。试《四书》文的体裁为八股文,亦称制义。“试帖诗”是试场考律诗的专称,题目与音韵有限定,并默写“圣谕广训”等。
考试之日黎明前点名入场,入场时要经过严格搜检,解开头发,脱下外衣,不许携带片纸只字及金银等物。入场后发给试卷,考生按卷面钤印的坐号入座,随将大门、仪门封锁。堂上击云板,试场即刻肃静,差役执题目牌在甬道上来往行走,使考生看清题目,视力不好的考生可站起来请求考官将题目高声朗读两三遍,但考生不得离开座位。考场周围有兵丁监视,如发现考生有移席、换卷、丢纸、说话、顾盼、吟哦等情况,立即扣考,重则枷示。在考生得题一段时间后(约上午九、十点钟左右),监考官持学政发下来的小戳盖于誊正考卷上(约在百字试文之间),以防倩人代考或抽易试卷之弊。下午一点到三点(未时)大门外击鼓三声,堂上巡绰官击云板三声,高呼“快誊真!”下午三点到五点(申时)大门外再次击鼓,不论是否誊完都必须交卷。受卷官每收一卷,发给一牌,积至30人,开门一次,放一批出考场者,先放头牌,继而再放二牌、三牌,到终场为止。出门时收一牌,放一人。试卷的背后右角上弥封糊号,其上加印。院试第一名称院案首。院试揭晓,称作“出黉〔hong红〕案”,也谓“红案”,即由学官将此届各县入学之人的姓名,按县分籍,以红色印出,汇成一册,分送各生。
严格地说起来,童试只是一种入学考试,童试合格者只表示已取得了地方官学生员的资格。而真正意义上的科举考试取士制度,是从乡试考举人开始的。
第二步称为“乡试”,是省一级的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叫“大比”,一般在子、卯、午、酉年举行,因为考期定在农历八月,故又称“秋闱”。每场乡试设主考二人,同考四人,统称为“内帘官”。考官一般由皇帝临时任命,多由进士出身的京官和教官担任,主考多是翰林出身。(中学生读书网)提调官多在布政司或京府抽出一名司官担任,负责行政和总务工作。为保证考试“至公”,按察司或都察院派两名司官或御史担任监试官。提调官和监试官统称为“外帘官”。外帘官不得侵夺考官的权力,不得干预考官判卷录取工作。
乡试在各省省城举行。八月初九日为第一场,十二日为第二场,十五日为第三场。每场均是先一日点名放入,后一日放出。考试文体亦用八股文(或称制艺、时艺、时文、《四书》文)。明代第一场试《四书》义三道,每道限200字以上,经义四道,每道限300字以上。第二场试论一道,限300字以上,诏、诰、表内科一道,判语五条;第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均须达300字以上,但能力稍差者可酌情减二道。清初基本上随明制,乾隆年间,对乡试三场的内容作了调整,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皇帝因士子专治一经,于他经不旁通,非敦崇实学之道,命自次年起废专经,乡、会试在每连续的五年内,每年轮试一经。于是定首场《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第二场经文五篇,题用《易》、《书》、《诗》、《春秋》、《礼记》。第三场策问五道,题问经史、时务、政治。自是遂为永制。每场试卷字数亦有限制,清初顺治二年定,初场文字,每篇不得超过550字,二、三场时表不得超过1000字,论策不得超过2000字。由于文字规定得太短,词意难尽。康熙年间,第一场文字宽限到650字。乾隆四十年(公元1778年)又定每篇以700字为率,违者不予录取。
乡试三场共计九日,农历八月天气尚热,日间烈日炎炎,加上炉火灼炙,闷热得使人难受。另外,每排号房尾部有厕所,臭气弥漫。有一位参加数次乡试的考生在《科场回忆录》中记载其亲临浙江乡试的情景:“一号之中,分数十间,一间坐一考生,极底则为厕所。坐近厕所者,谓之‘臭号’,第一场犹可,第二场则秽气远播,实不可耐,以考生贪近便,大小解不必皆至厕中也。余丁酉科(清光绪二十二年,即公元1897年)二场,坐臭号,天气郁蒸,竟至发病,曳白(考试交白卷)而出。又有与炊爨〔cuan窜〕之地相对者,曰‘火号’,烟熏火炙,亦不可耐。”这位考生因坐“臭号”而得病,交白卷出场,后又多次赴乡试,直到癸卯科(公元1903年)才中举。
乡试通过者称为“举人”。乡试中举称“乙榜”,也叫“乙科”。第一名叫“解〔jie介〕元”,“解”,发送也,意思是说由地方考取了将发送到京城去参加“会试”,“元”是第一。第二名叫“亚元”。第三、四、五名叫“经魁”。第六名叫“亚魁”。其余称“文魁”。中举以后,照例要报喜。报喜的人叫报子,头上顶着红缨帽子,骑着马,敲着锣,带着报条,到中举的人家门口去张贴。报条上写着:
喜 报
贵府老爷×××应本科×处乡试高中
第×名举人
报喜人×××
清代诗人张子秋(学秋氏)的《续都门竹枝词》,有一首《报喜》诗:
高升高中任高才,添喜红条便报来。
讨赏门前无别话,今朝小的喝三杯。
这首诗形象地描写了登第中举送喜报的风俗,抒发了报喜人和作者对高升高中的喜悦之情。
报条贴过之后,便由考中的人家出来招待报子。考中了“举人”,不仅可以进京参加全国性的“会试”,即使“会试”未能考中“进士”,也具备了做官的资格。所以《儒林外史》第三回,说范进中了举人以后,很多人来拜“新中的范老爷”,“自此以后,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环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难怪范进听到自己中举的消息,竟然高兴得发了疯,而他的老丈人胡屠户也变了一副嘴脸,说:“虽然是我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举人的铨选,其职高者为知县,其低者为地方官学学官,能跻身于宦海者,占举人总额的比例不多。有的等上几年、甚至几十年,仍为布衣。《都门竹枝词·候选》诗云:
老叟皤皤〔po 婆〕发似银,龙钟带病少精神。
贵班请问居何职?四十年前老举人!
第三步称为“会试”,是中央级的考试。在乡试后的第二年,即丑、辰、未、戌年之春季农历二月在京城举行。故又称为“春闱”或“礼闱”。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及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因有闰月,天气寒冷,会试时间临时改在三月。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有上谕曰:“明年二月会试,天气尚未和暖,搜检时不无寒冷,且各省俱需复试,士子到京,未免稍迟,著改期于三月举行。”(《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三○)故从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起会试的时间均在三月举行。三月初九为会试首场,十二日为第二场,十五日为第三场。各场均是先一日领卷入场,后一日交卷出场,每场计三日。会试时各场的内容、文字的限制等,与乡试大体相同。
会试由礼部主持。皇帝从翰林和教官中任命主考二人,同考八人负责。明中叶后,正主考由翰林出身的大学士担任,副主考由翰林院或詹事府的长官担任。同考官增加到20人,其中翰林12人,科、部官各四人。提调官二人由礼部遣员担任。监试官二人由监察御史担任。参加会试的是全国各地的举人。录取的名额没有定制,有时只有30余人,有时多达400余人。会试录取后被称为“贡士”,第一名叫“会元”。明仁宗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会试录取名额开始有南北之分,规定南方人占3/5,北方人占2/5。以后又曾分南、北、中三卷,在100个名额中,南卷取55名(淮河以南的各省考生),北卷取35名(淮河以北的各省考生),中卷取10名(云、贵、川、桂、皖等省的考生)。采取了“分地而取”的原则,照顾了各地区的利益。清朝也曾按南、北、中三卷分配会试的录取名额,一般大约按20名考生录取一名的比例分配。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特准台湾来京会试举子够10名便可取一名,以示关照、鼓励。录取总名额由皇帝临时决定。如果会试未被录取,可改入国子监做监生,待以后有条件时可授予京师小官或府佐、州县正官等。当时会试还有副榜,凡上副榜的举人,不算正式录取,但大多数可授予学校教官。入监的举人也给与俸禄。
会试本无复试,清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壬辰科时,有人作弊,遂进行复试。雍正及乾隆年间亦有过复试,嘉庆时始著为令。凡贡士发榜后数日,即进行复试,地点在乾清宫,后来改为保和殿。复试时试《四书》文一篇,五言八韵诗一首,当日交卷。复试列一、二、三等者,准予参加殿试。
第四步称为“廷试”或“殿试”。会试之后(一般在农历四月)举行,由皇帝亲自主持,由大学士、尚书、都御史、通政史、大理寺卿、翰林学士、詹事等担任读卷官,以礼部尚书、侍郎任提调,由御史监试。殿试只试策问一场,要求考生当场交卷,弥封后送读卷官审阅。殿试并不淘汰,参加殿试的贡士均能获取进士资格。殿试考中称“甲榜”,也叫“甲科”。出榜分为三甲:一甲赐进士及第,只有三名,为状元(又称殿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鼎甲。状元一般授翰林院修撰,榜眼和探花一般授翰林院编修。二甲赐进士出身若干名,
其第一名为传胪〔lu庐〕。三甲赐同进士出身若干名。二、三甲的进士可以参加翰林院庶吉士的考试,叫“馆选”。考取后称“庶吉士”,学习三年然后补授重要官职。馆选未考取的进士可能被授予给事中、御史、六部主事以及诸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官。殿试之后,在揭晓录取结果时,要在殿前举行一次隆重的唱名典礼。殿试后,皇帝要亲赐诸进士宴。当时中了进士,功名就算到了尽头。所以《儒林外史》第十七回浦墨卿说:“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凡是通过乙榜中举人,又通过甲榜中进士而做官的人,叫做“两榜出身”。一身兼有“解元”、“会元”、“状元”的,叫做“连中三元”。据清王之春所著《椒生随笔》载,唐朝以来“连中三元”的共有13人。他们是:唐朝的张又新、崔元翰;宋朝的孙何、王曾、宋庠、杨置、王岩叟、冯京;金朝的孟宗献;元朝的王崇哲;明朝的商辂〔lu路〕;清朝的钱棨〔qi起〕、杨继昌。在科名中,荣誉最高的要算是状元,故中状元者号为“大魁天下”。
“状元及第”匾
抡材天子重文章,金殿胪传姓字香。
分道红旗来谒庙,满街争看状元郎。
这是清代诗人杨静亭《都门杂咏》中的一首七言诗《传胪》,描述了明清金殿传胪典礼的科举考试习俗,宣扬了中状元、登进士的荣耀。
据《明宰辅考略》载,明永乐初至崇祯末,历任内阁大学士计163名,按明代的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地域划分,这163名的籍贯如下:南直(包括今江苏、安徽、上海)27名,浙江26名,北直(今河北) 17名,山东13名,福建11名,四川9名,山西5名,广西2名,江西22名,湖广(今湖北、湖南) 12名,河南11名,广东5名,陕西2名。从上述人员分布可看出江南的南直、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共98名,占全部内阁大学士的60%,这无疑体现了通过科举考试制度进入官僚机构上层的南方士人要多于北方人。如果没有南北卷的分设,或许南方士子进入统治集团上层者还要多一些。
据查,在清朝114名状元中,江苏49名,浙江20名,安徽9名,山东6名,直隶、广西各4名,江西、湖北、福建、广东各3名,湖南、贵州、满洲各2名,河南、陕西、四川、蒙古各1名。其中,满洲、蒙古三状元属八旗系统。山西、云南、甘肃等地区无状元。又查,在清112科殿试中,共产生三鼎甲(即状元、榜眼、探花)342名。其中江苏117名,浙江75名,安徽21名,江西18名,山东14名,湖北13名,湖南13名,广东11名,福建10名,满洲8名,直隶8名,顺天8名,河南5名,广西5名,贵州3名,陕西3名,四川3名,汉军(即汉军八旗,清自崇德七年汉族士兵编为军队称汉军八旗) 3名。
有趣的是,各省殿试夺魁的人数,大致和各省地区中进士人数比例相同,反映了当时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水平之高下。清朝对于七八十岁乃至百岁老人参加会试落第者,也常赏给国子监司业或翰林院编修、检讨等虚衔。据传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顺天乡试,考生黄章已达百岁;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98岁的广东考生谢启祚中举人,还自我解嘲作诗云:
行年九十八, 出嫁弗胜羞。
照镜花生面,光梳雪满头。
自知真处子,人号老风流。
寄语青春语,休夸早好逑〔qiu球〕。
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春季,在北京举行会试。在众多的举子当中,有一位两鬓苍苍、年已103岁的老人,他是来自广州府三水县的陆云从。主考官发现这位举子竟是年逾百岁的老人,十分吃惊,便立刻上奏皇上。道光皇帝很高兴,认为这是“人瑞”,是吉祥的预兆,当即赐给陆云从老人国子监司业的官衔。
南闱放榜图
明清时期,各省多在城的东南建立贡院,作为乡试的考场。北京贡院,开始狭小,直到明万历年间,开始重建,建于崇文门内观星台西北,南向。大门正中悬“贡院”二字大匾。二门正中悬“龙门”金字匾。龙门的北面,是一座二层的明远楼。考试期间,监临、监试、巡察等官登楼眺望,居高临下,整个考场尽收眼底,便于防察。明远楼北面是“至公堂”。自龙门到至公堂甬道东西两侧是东西文场,东西文场各有南向成排、形如长巷的号房57排,共9064间。每排号房为一字号,用《千字文》编列次序,在巷口门楣墙上书“某字号”。每一字号内,号房的间数多少不一,隔以砌墙。每间号房,约高六尺,深四尺,宽三尺。东西两面砖墙离地一尺多至二尺多之间,砌成上下两层砖缝,上有木板数块,可以移动。白天,将木板分开,一上一下,上层是桌,下层是凳;晚上,将上层木板移至下层,并在一起,又成了卧榻。在考试期间,考生经搜身后,携带笔墨、卧具、蜡烛、餐食半夜进入号房,吃饭、睡觉、写文章都离不开这几块木板。“三场辛苦磨成鬼,两字功名误煞人”,当年考生在号房的生活,是十分艰难的。明英宗天顺七年(公元1463年)的会试,天气还很冷,巡逻士兵生火取暖,引起火灾。号房是简易的砖木结构,一排排号房,顿时变成一片火海。号房的门都锁着,考生们蜷曲在里面,无法逃出来,竟有90余人葬身火海,受伤者不计其数。号房卫生条件极差,吃的是冷食,大小便也只能在号房里,考生们很容易生病,瘟疫时有发生。考生答题,须避皇帝之讳及庙号,也不许吐露自家身世和门第。答卷须用墨笔(即“墨卷”),誊录者用朱笔(即“朱卷”)。仍沿用宋制,采用糊名、弥封、誊录之法。
至于殿试,清初在天安门外,后改在太和殿的东西石阶下,遇风雨则就移到殿东西两廊下。乾隆后改在保和殿。由于殿深光线暗淡,矮几仅一尺之高,考生盘膝书写一天,腰腿酸痛,眼花头晕,十分受罪。且黎明时分,考生们就要来保和殿恭候,直到皇上升殿,众官员及考生们参拜行礼后,礼部官员才散发考卷,考生们还须下跪接受,再归到自己座位上开始答题,已是耗费几个钟头了,还要书写工整,写出2000字的策问文章,日落前交卷,其紧张辛苦之状是可想而知的。
殿试试卷,用白宣纸裱糊而成。起初裱四层,清乾、嘉以后增加到七层。每份试卷,可以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卷面,占一页。上面盖有满汉合璧的礼部官印,写应殿试举人的姓名。第二部分:履历,占两开,四页。实际上只用第一页,空三页。写本人年龄、籍贯、乡试中式及会试中式年份,开具三代姓名,注明已仕未仕。交卷后,弥封官要把这两部分对折成筒状,以纸糊封,加盖“弥封官关防”之印。直至确定名次后才拆封,将姓名书于金榜。第三部分:试策正文,也是全卷主体部分,起初为九开,清嘉庆以后减为八开,两页为一开,每页六行。有红线直格,无横格。每行最多限写24个字,一般只写22个字,上面要留两个空格为抬头之用。第四部分:卷背,占一页,印有印卷官姓名。卷背的背面,印有读卷大臣的姓氏,大臣读卷后要在本姓氏下画出标志,最后根据各官意见,确定该卷等次。殿试卷的大小尺寸,据《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介绍,清初每页长一尺五寸三分,宽四寸三分强;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改小为长一尺四寸,宽三寸七分弱。殿试时,另外给草稿本一册,尺寸略小,纵行与正卷相同,但有横格,每行24个字。有时,殿试策试题,便印于草本前面。
1、明朝选官制度包括科举、举荐、学校和铨选。科举就是科举考试,是最主要的选官制度。举荐就是通过向别人或自己向皇帝推销以获取官职,这在明初较多,后世较少,且多次废除。
2、学校就是国子监,国子监的学生又分为科举落榜的、因祖上功绩入学的、交钱入学的等多种,但无论哪种都可以直接做官。铨选只在官员中进行,就是考核官员政绩,择优提拔。
明朝科举制度的优势
1、明朝的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家对于人才的需求,通过层层考科,可以为国家选拔出一些可以满足统治需求的官员。
2、明朝的科举制度也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统治,选拔人才的权力在中央,有利于国家管理。
3、有了科举制度,一些寒门子弟也有了做官的途径,有利于皇帝打破世家大族垄断官场的局面,在社会上营造了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给予了这些底层百姓一个向往美好生活的希望。
4、明朝的科举制度倡导的也是公平与合理,意味着大家相对同属于一个起跑线。
5、明朝的科举制度也是文化教育的一种普及方式,这在某种程度上极大的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明朝科举制度的局限性
1、明朝的科举制度采用的是八股取士,后来不断严格,演变的越发刁钻,而且考试对文字的技巧性要求已经超过了对实质内容的要求。
2、八股文的盛行也导致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这种严格禁锢思维的模式下,考试只注重形式,写的内容却生硬空洞。
3、明朝的科举制度并不是一种普及的教育体制,在这种有差异的选择制度下,只有一少部分人能够有资格参加考试。
4、而且要参加科举需要的花费巨大,不是一般家庭可以负担的。
明朝是通过庶吉士制度选拔高级官员,并在不断的发展当中得到了完善。相对于“八股取士”对于文学只有伤害作用不同,庶吉士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教育的发展。在庶吉士制度之下所形成的馆课赋和馆课文学,正是对学术教育的肯定以及对其效果作用的展示。
一、 庶吉士制度是明朝重要的取才来源,是官僚机构的重要支撑
庶吉士,其实就是古代某些进士的代称,指的是观政于某些朝廷部门的进士,这些进士主要是在翰林院等部门进行进修。而这些在翰林院进修过的进士,则是明朝朝廷的重要培养对象。
(一) 以文学取士为途径的庶吉士制度,有一定的选拔标准
庶吉士制度的产生,主要目的是为了选拔人才,但与其他途径不同,庶吉士制度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文学来取士。具体的流程可以分为馆选、教习和散馆三个主要阶段。
作为第一阶段,馆选的具体操作比较宽松,也没有统一的标准。
这在《明史》当中就有记载,“自永乐二年以来,或间科一选,或连科屡选,或数科不选,或合三科同选,初无定限。或内阁自选,或礼部选送,或会礼部同选。或限年岁,或拘地方,或采誉望,或就廷试卷中查取,或别出题考试,亦无定制。”从中可以看出,馆选的路径很多,没有特定的选项内容。
教习阶段,主要学习的内容就是诗词文学,这也体现了其文学性。此时的教学内容,主要以研读经史和诗学,并且定期参与一定的考试,用以考核和选拔人才。到了散馆阶段,其实就是针对庶吉士的具体学习内容来进行考察,留用成绩优异者。
从这三个具体阶段可以看出,庶吉士的学习和进修内容都以文学为主,甚至连最后的决定去留的散馆阶段,也是以文学作为考试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此种“文学取士”的重要途径。
(二) 作为官僚机构的制度支撑,庶吉士制度割裂了官员身份和能力
虽说,庶吉士制度远远好过于之后的“八股取士”制度,但实际上的庶吉士制度在选材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原因就在于,庶吉士制度是内阁机构的重要支撑。
明代内阁当中的大部分人,都来源于庶吉士制度。而内阁是明代主要的行政机构,势必对于人才的这方面能力要求很高,但是庶吉士制度以文学取士的此种途径,并不满足内阁对于人才的需求。这也是庶吉士制度最大的弊端,并没有对人才的行政能力提出一定的要求,就造成了人才和行政之间的一种矛盾,这也是对明朝官僚机构最严重的一种打击。
当时也有不少的官员对其进行了批评,比如说在《明经世文编》当中就记载了这种批评,“其选也以诗文,其教也以诗文,而无他事焉。夫用之为侍从,而以诗文犹之可也,今既用之平章而犹以诗文,则岂非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乎!……群天下英才为此无谓之事,而乃以为养相材,远矣!”
庶吉士制度的初衷和目的是为了选拔人才进入官僚机构,培养高级官员,但是其用文学取士的模式,不仅没有达到这个目标,还割裂了人才和行政机构之间的关系,存在着较大的漏洞。
二、 受到庶吉士制度的影响,明朝馆课赋文学也开始崭露头角
虽说庶吉士制度并没有达到选拔人才的目的,但是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馆课赋文学的发展兴盛,对于文学教育的积极作用远远超过其本身所具有的选拔人才的作用。
(一)以文为主的庶吉士选材途径,促进了馆课文集发展和兴旺
直到万历年间,庶吉士制度才不断发展成熟。正是由于倾向于文学取士的选材标准,庶吉士制度成为了馆课文发展的重要支撑。当时的馆课文集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甚至已经出现了多科馆课集、单科馆课和单人馆课集的分类。
多科馆课集的数量规模是比较庞大的,这是因为大多数的馆学教育都以多科为主。诸如《皇明馆集》、《八科馆课录》、《皇明名臣言行录》等等多课馆课集,都留存到了现在,成为了当时馆课赋的经典著作。
与多科相比,单科馆课集和个人馆课集的规模并没有如此之大,但同样也存在于明代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如此多的馆课集的存在,已经证明了当时的馆课赋文学发展程度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二) 受到庶吉士的影响,馆课赋体裁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明朝的馆课赋,已经成为了当时文学教育的重要代表,体现了当时的文学发展高度。不论是从数量还是体裁方面来说,当时的赋课赋的确代表了当时的重要文学形式。
数量上不用多说,从上面的馆课文集的诸多分类当中就可以看出。而体裁呢?馆课赋在一开始基本上是延续的元朝的骚体赋和汉赋体,但之后就开始扩大了体裁内涵,关注到了唐律赋和宋文赋等等体裁,并将不同的体裁内容和形式融会贯通,渗透到了馆课赋的创作当中。这也能证明当时的馆课赋的发展程度和文学教育的兴盛,体现庶吉士制度在文学方面的作用。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