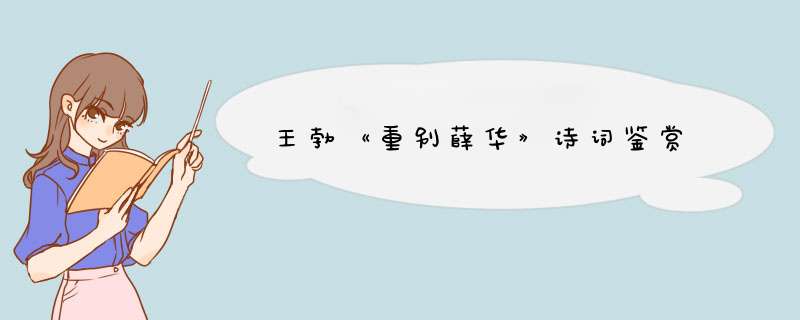
重别薛华
唐代:王勃
明月沉珠浦,秋风濯锦川。
楼台临绝岸,洲渚亘长天。
旅泊成千里,栖遑共百年。
穷途唯有泪,还望独潸然。
译文
明月照在冒珍珠似的水泡的江水上,秋风洗刷着能把锦缎洗得更好看的锦江。
这分别的地方,有楼台,紧靠着又高又陡的江岸;有洲诸,很长很长,长得要跟远天连起来。
旅途飘泊,现在要以千里计数了;而凄凄惶惶的情景,看来要陪伴我一辈子了。
眼前的穷途末路,只能叫我眼泪洗面;回头看看我走过的里程,也只能叫我潸然出涕。
注释
沉珠浦:河岸的美称。浦,江岸。
濯(zhuó)锦川:即锦江。岷江分支之一,在今四川成都平原,传说蜀人织锦濯其中则锦色鲜艳,濯于他水,则锦色暗淡,故称。
绝岸:陡峭的江岸。洲渚(zhǔ):水中小块的陆地。
亘(gèn):绵延。
长天:辽阔的天空。
旅泊:飘泊。旅,一作“飘”。
栖遑(xīhuáng):同“栖皇”,奔波不定,神情不安。遑,一作“迟”。
潸(shān)然:流泪。
创作背景
此诗是咸亨元年(670)诗人在蜀中与薛华再次分别时所作。
鉴赏
这首诗的创作特点是随心而发,直抒胸臆。面对好友,诗人郁积在心头的愤懑凄苦,倾泻无遗。
诗的首联不仅写出时间、地点,还暗含了自己的不满,用夜明珠自喻,说明自己的遭遇如同夜明珠,虽然璀璨夺目,但埋没在泥沙中不能熠熠发光。
第二联直接写眼前景物,视线由近及远,极为开阔。秋天的江水如同郦道元《水经注》中描绘的景象:“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凄凉悲苦之情由景而生。
第三联很自然地过渡到抒情,面对滔滔江水,诗人产生旅泊千里、栖遑百年的感觉,李煜的词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是的概括。
最后一联,诗人难以自已,直接写出与好友即将离别,漫漫旅途,只有泪水相伴的悲凉和哀愁。诗中反映出沛王府放逐事件对王勃是致命一击,乐观向上、热情豪放的王勃渐渐远去,凄凉悲苫、忧郁彷徨的王勃开始出现。
此诗写景浩荡开阔,抒情真实自然,借景传情,景中见情。
王勃是神童。他的神,不仅是聪明,而且还早熟。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哪像不到20岁的人写的?短短两句诗、10个字,境界宏大,格调豪迈,乐观豁达,情感跨越了时空,温暖和激励了无数离子。
其实,遍览王勃的送别诗,如此豁达之作极少,大多低沉悲切,这和他的人生际遇分不开。
1,从“奇才”到“歪才”
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16岁的王勃应幽素科试及第(幽素科,唐朝科举制科目之一),得到了“朝散郎”一职,成为朝廷最年轻的命官。这之后,他才思泉涌,写了一篇《乾元殿颂》,大拍高宗马屁。文章绮丽惊艳,高宗得知文章乃是未及弱冠的神童所为,惊叹不已,连呼“奇才”。
朝散郎毕竟是个闲官,主考官见王勃如此有才,就把他介绍给沛王李贤,当了沛王府修撰。王勃很讨沛王欢心,渐渐就不知高低了,毕竟年少气盛。有次,沛王与英王李显斗鸡,王勃为沛王助兴,写了一篇500字的檄文《檄英王鸡》,声讨英王的鸡。这篇文章洋洋洒洒,可称骈体文中的精品。但文章写得再好,如果矛头指错了,当然就有了麻烦。不会说话的鸡无故挨了一通损,可皇上不干了。高宗看了此文很生气,认为王勃是歪才。高宗觉得,二王斗鸡,你王勃身为博士,不进行劝诫也就罢了,反倒作檄文(古代属于政府公告或声讨、揭发罪行之类的文书),夸大事态,挑拨离间,应该逐出王府。王勃无奈,伤心地去了蜀地。
2,“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
《别薛华》是王勃在绵州(今四川绵阳一带)写的:
送送多穷路,
遑遑独问津。
悲凉千里道,
凄断百年身。
心事同漂泊,
生涯共苦辛。
无论去与住,
俱是梦中人。
薛华是王勃的老乡兼好友。那日,薛华远行,王勃相送。他要去的地方可能又偏又远吧,所以王勃一开头就说“送送多穷路”,“送送”就是来来回回、送来送去的意思,可见恋恋不舍。为什么?因为未来“多穷路”。这两句借送友远行,也喻世路艰难,语义双关。后面四句,写友人也写自己:未来的路(也包含人生之路)很远,可能命途多舛。结尾两句,写各自要承受离别后的相思之苦——不论咱们各自远行到何方,彼此的梦里都会有你我。
当时王勃在蜀地,心情不佳,这首诗发泄了他不满现实、感叹人生悲苦的情绪,也表达了在人生旅途中的切身感受。王勃是山西人,薛华是王勃的同乡,当然也是山西人。两个在异乡的同乡人,还要你送我、我送你的,这就是“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个中凄苦,非旁人可理解。
这首诗写得惨惨淡淡,读者以为他俩今生难再见。哪想,他们相隔时间不久就又见面了。但咱们没见到二人的见面之喜,只看到了王勃的一首诗《重别薛华》,可见是重逢不久又分开了:
明月沉珠浦,
秋风濯锦川。
楼台临绝岸,
洲渚亘长天。
旅泊成千里,
栖遑共百年。
穷途唯有泪,
还望独潸然。
这首诗写于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上一首写于绵州,这首写于成都。
好友再相见又再别离,才华横溢却不得不在异乡飘零,王勃的心情可想而知。他表面写景,同时把自已(也包括薛华)喻为明珠沉于泥塘(“明月沉珠浦”),愤懑溢于言表。放眼望去,楼台绝岸,秋水长天。想当下,旅途漂泊千里;看将来,眼下的凄惶情景,恐怕要陪伴一辈子了。结尾两句,他已经难以自控,“穷途唯有泪,还望独潸然”——未来的旅途(也含人生旅途)只有泪水相伴了。
《别人》(四首)也是王勃在蜀中的伤心之作。这几首诗不是在一个地方写的,送别之人也不同。现选二首做鉴赏:
其一
久客逢馀闰,
他乡别故人。
自然堪下泪,
谁忍望征尘。
其二
江上风烟积,
山幽云雾多。
送君南浦外,
还望将如何。
在异乡,王勃自己本就是客人,还要送人别离,心里肯定更别扭,所以在蜀中3年里写的送别诗,大都低沉悲伤。
送别亲人或朋友,肯定会悲伤,但王勃年纪轻轻,很多送别诗里却透着超越年龄的身世之感,不是一般送别诗所能比。
3,“寂寞离亭掩,江山此夜寒”
《江亭夜月送别》(二首),也是王勃流落蜀中之作,时间是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到咸亨二年(671年)之间。
其一
江送巴南水,
山横塞北云。
津亭秋月夜,
谁见泣离群?
其二
乱烟笼碧砌,
飞月向南端。
寂寞离亭掩,
江山此夜寒。
两诗合着看,能了解个大概:送客的地方是巴南江边的津亭,时间是一个秋天的夜晚。友人要去哪里?遥远的塞北,所以才有两人的惜惜相别。
两首诗,第二首更好,没有伤离别的字句,但每个字构成的环境,却凄清无比。在江边送走朋友后,王勃环顾离亭、仰望明月、远眺江山,心情寂寂。“乱烟笼碧砌”,写烟用“乱”字,形容夜雾弥漫,也写诗人心情的迷茫。“飞月向南端”,一个“飞”字,既写时间推移之快,也有聚散匆匆的感觉。“江山此夜寒”,“寒”字是全诗点睛之笔。正因为朋友远走,诗人才顿觉天地之“寒”。一片离情,都由“寒”字托出。
秋夜,江边,这样的送别本来很怅惘,但却被王勃很自然地融入月景里,离别的伤感从每个字里透出来,又不着痕迹。这种空灵之美,直到多年后的王维诗里才常见。
4,“去去如何道,长安在日边”
王勃的送别诗也不都是低沉哀伤。相比他在蜀中写的送别诗,这首《送卢主簿》则积极多了:
穷途非所恨,
虚室自相依。
城阙居年满,
琴尊俗事稀。
开襟方未已,
分袂忽多违。
东岩富松竹,
岁暮幸同归。
诗的前四句写与卢主簿的交往,卢主簿“穷途”也罢、“虚室”也罢,似乎都不大在乎,王勃的敬意油然而生。后四句写送别,开阔豁达。王勃期待着“岁暮”与卢主簿相会于东岩松竹之下,并肩前行。这里的“松竹”,既是长安东岩的实景,也含有诗人的自勉,像松竹那样。
这首诗能乐观向上,是因为诗写得早,是王勃在长安时写的。
《白下驿饯唐少府》也是王勃早年写的,虽是送别,但一点也不悲切:
下驿穷交日,
昌亭旅食年。
相知何用早,
怀抱即依然。
浦楼低晚照,
乡路隔风烟。
去去如何道,
长安在日边。
当时王勃在白下的驿站(白下,现属南京)送远赴长安的唐少府。诗的头四句写与唐少府的交往,他认为,相交不一定要多早,三观一致即可。后四句写别离,朋友走后,风烟相隔,但“去去如何道,长安在日边”(去吧去吧,不用再说什么了,你去的地方,是太阳那边),意为前途光明,以此勉励友人。
王勃年少成名,在遭遇斗鸡檄文风波之前,他眼里的未来,一定是一条宽广的大道,是为他这样的意气风发的年轻人铺设的。所以,他诗里的离别,没有愁苦,只有勉励,所以他才能写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那样温暖又励志的诗句。
王勃流传下来的诗有80来首,写别离的有16首,所占比例不多。其中去蜀中之前在长安的诗,如《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等,都昂扬向上,天宽地阔,大气磅礴。
5,“谁谓波澜才一水,已觉山川是两乡”
被逐出沛王府这件事,对王勃来说是致命的。从此,乐观、豪放渐渐变成了凄苦、忧郁。
被贬到相对荒蛮地方的古人多了去了,杜审言被贬峰州(今属越南)、王昌龄被贬龙标(今在湖南怀化一带)、柳宗元被贬柳州(今广西柳州)并客死他乡、刘禹锡被贬湖南广东重庆20多年、苏轼被贬海南,但也没见他们愁苦得如何如何。
但王勃不一样。他家境优越、家传深厚,爷爷王通是隋末唐初大儒,学生遍及各地;他是神童,年少即入朝为官,一帆风顺。所以,他受不了挫折。
《秋江送别》(二首)是王勃在蜀中写的,其中一首如下:
归舟归骑俨成行,
江南江北互相望。
谁谓波澜才一水,
已觉山川是两乡。
客中送客,异常伤感。此诗同时以江水、归舟等意象来表达别情和乡情,感情深沉绵长。王勃说,由于离别,仅仅是一江之水,却隔成了两个世界(“谁谓波澜才一水,已觉山川是两乡”),所表达的情感,感动了千百年来无数人,由此,这两句诗也成千古名句。
看王勃的这两句诗,忽然想起王昌龄的两句诗。
唐玄宗天宝七年(748年),50岁的王昌龄被贬为龙标尉。龙标远在湘西,当时是很荒的地方,王昌龄在这里一住就是8年,迎来送往,写了不少送别诗。
和很多诗人不同,王昌龄的送别诗,悲伤的句子少,胸襟更豁达,能给人力量。比如他在任龙标尉期间写的《送柴侍御》:
沅水通波接武冈,
送君不觉有离伤。
青山一道同云雨,
明月何曾是两乡
诗里说,流过龙标的沅江,也流到武冈,两地有沅江相连,我们其实并未分别。青山绿水一路相连,我们共沐风雨;一轮明月同时辉映你我,我们又何曾身处两地?风雨相同,明月与共,人在两地,情同一心。“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十四个字能展现如此博大的胸襟、如此温暖的宽慰,冠绝古今。
王勃的“谁谓波澜才一水,已觉山川是两乡”,其意思和王昌龄的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正好相反。王勃说,别看仅仅是一条江水,就把我们隔成了两个世界。王昌龄说,不论多远,我们同饮一江水、同在明月下,这等于没有分开啊。
两组名句各有千秋,但我更喜欢王昌龄的。
6,“落花春正满,春人归不归”
唐高宗咸亨二年(671年)秋冬,王勃从蜀地返回长安。他的一个朋友在虢州(今河南西部灵宝一带)公干,给他谋了虢州参军之职。这期间,有个官奴犯了罪,王勃把他藏匿起来,后来又怕走漏风声就杀了他。王勃因此犯了死罪,幸遇大赦,保住一命。不过也有说王勃藏匿官奴一事,是与王勃有过节的人下的套。
王勃的死罪免了,但他父亲却受他牵连,被贬到偏远的交趾(今属越南)。
王勃出狱一年多后,朝廷恢复他的旧职,但他已视宦海为畏途,没有去赴任。老爹受连累被贬遥远的交趾,王勃万分自责和羞愧,说什么也得去看看老爹啊。
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年)秋天,王勃从洛阳沿运河南下,一路奔波,到第二年春夏才到交趾县见到了老爹。在去探望老爹的途中过南昌,他写下千古名篇滕王阁诗及序。
王勃返程时正是夏天,南海风急浪高,王勃过海时不幸溺水,惊悸而死,时年27。
王勃有一首古体诗《落花落》:
落花落,落花纷漠漠。
绿叶青跗映丹萼,
与君裴回上金阁。
影拂妆阶玳瑁筵,
香飘舞馆茱萸幕。
落花飞,燎乱入中帷。
落花春正满,
春人归不归。
落花度,氛氲绕高树。
落花春已繁,
春人春不顾。
绮阁青台静且闲,
罗袂红巾复往还。
盛年不再得,
高枝难重攀。
试复旦游落花里,
暮宿落花间。
与君落花院,
台上起双鬟。
这首诗写花落的场景,实际上是写自己,用落花象征自己,人生的感慨(伤感)在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有人说这是王勃的临终绝笔,说得挺吓人,好像要自杀似的。这首诗是他出狱后写的,应该写于674-676年间的某个春天。经这次打击,王勃似乎更灰了,从内容看,诗里透出的春天虽美好但人却年华老去(其实才二十几岁,哪跟哪啊)的春伤之感,确带有厌世的情绪。即便王勃后来没有溺水英年早逝,恐怕也不一定能走出这种青春已逝、无心向前的情感困局。
失州入幕,年岁已垂垂老矣;虽然寄身有地,但心情不能不是感伤多于慰藉。这首诗即写这种帐触之情。
首联写诗人奉诏内移沿海的感受。起句字面上称美皇恩浩荡,实际止用春秋笔法,以微言而寄讽意。诗人曾被贬南巴,此次奉诏内移,也是一种贬滴,只不过是由极远的南巴内移到较近的近海之睦州罢了。所以“承优诏”云云,实是反说,愤激不平才是其真意。对句则由止句之婉讽陡然转为无可奈何的一声浩叹,是真情的淋漓尽致的倾吐,也将上句隐含的讽意明朗化了。醉歌,它常常是作为古之文人浇愁遣愤的一种方式。刘长卿两次被贬在其心灵上留下创伤,借“醉歌”以排遣,已属无奈,前面冠以“空知”二字,则更进一层透出诗人徒知如此的深沉感慨,这就将苦清暗暗向深推进了一步。首联二句已点出诗人情绪,次联则以江州景色而染之,诗脉顺势而下。
颔联所写即眼前之景——江水、明月、北雁、落木、楚山,渲染清秋气氛,借以抒写宦海浮沉的深沉感慨。浩荡江水,凄清明月,一群北来南去的大雁掠空而过;江州一带万木凋零,落叶飒飒,原先被树木遮蔽的古楚地的山岭突然裸露出来,似乎比往日增加了许多。二句写景,一天上,一地下,一写水,一写山,一近一远,一动一静,上下俯抑,参差交互,成就了二幅水天空寂、江山寥落的江州秋色图。而作者的真正用意则在于通过这貌似孤立的景物画面,来抒写孤寂凄凉的心境和贬滴天涯的感恨。北雁南飞,暗寓诗人迁播;落术飒飒,隐含诗人晚景萧条,且与尾联“老”字遥相呼应;楚山之多亦正好反衬出作者的一己之微。所以,此联妙在以景传情,情从景出,情景相为珀芥,二者互藏其宅。
颈联的感喟即由此种氛围中生发。“寄身且喜沧洲近”,努力想从萧瑟感中振起,但下句“顾影无如白发多”又跌落到感伤中。这一联的脉理很细腻,寄身沧洲,自然是从上联将往淮南引起的悬想,而“沧洲近”,就离自己北国的家乡更远了,其意又隐隐上应领联上句的“胡雁过”。“沧洲近”又有悬想此后得遂闲适初志之意,但忽见明镜里,白发已多多,“白发”又隐隐与颔联下句萧瑟的“楚山多”在意象上相呼应。生涯如同一年将尽的深秋,遥远的故乡更回归无日,因此这“喜”只能是“且”喜,而白发缘愁长,却是“无如”其“何”的严酷的现实。
“今日龙钟人共老,愧君狄遣慎风波。”以感愧友人情谊作结,并隐隐透出前路上尚有风波之险。在关合诗题“重别薛六柳八二员外”的同时,以“慎风波”暗暗反挑首联的“生涯”、“世事”之叹。分别之际,诗人感愧万端地说:如今我和你们都已老态龙钟,多亏二位旧识还叮嘱我警惕旅途风波。在此之前,刘长卿因“刚而犯上”被贬到遥远的南巴,此次奉诏内移,薛柳二人担心他再次得罪皇帝,故有“慎风波”之劝。对此,诗人深深地为之感愧。“风波”一词,语意双关,既指江上风波,又暗指宦海风波。这样一结,既写出了薛柳二人对诗人的殷殷叮嘱之情,又传出了诗人感愧友人的神态。
综观全诗,或委婉托讽,或直抒胸臆,或借景言情,运用多种笔墨,向友人倾诉了因犯土而遭贬滴的痛苦情怀。语言看似质实,却不乏风流文采。前人评对长卿七言律诗云:“工绝秀绝。”当不为溢美之词。
别薛华 别薛华 作者:王勃
送送多穷路,
遑遑独问津。
悲凉千里道,
凄断百年身。
心事同漂泊,
生涯共苦辛。
无论去与住,
俱是梦中人。
唐乾封元年(666 ),王勃17岁,进入沛王府任修撰,奉命撰写《平台秘略》。写完后,沛王赏给他帛50匹,十分赏识他。王勃少年得志,可惜好景不长。据《旧唐书·王勃传》记载,总章二年(669),“诸王斗鸡,互有胜负,勃戏为檄英王鸡文。高宗览之,怒曰:‘据此,是交构之渐。’即日斥勃,不令入府。”被逐出沛王府时王勃年仅20岁。他在《夏日诸公见寻访诗序》中说:“天地不仁,造化无力,授仆以幽忧孤愤之性,禀仆以耿介不平之气。顿忘山岳,坎坷于唐尧之朝,傲想烟霞,憔悴于圣明之代。”对自己的被驱逐,他心中怀着一腔悲愤。当年五月他离开长安南下入蜀,后来客居剑南两年多,遍游汉州、剑州、绵州、益州、彭州、梓州等地。在此过程中,他对现实生活有了新的深切的感受,写下了一些影响深远的诗文。《别薛华》就是其中一首。
这首送别诗的色彩、风格,和《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大相径庭,其中原因,就像公刘所说的:“诗是一种感性经验和主观情感占很大成份的东西。诗人此时的生活环境变了,思想感情也发生很大变化了,写出的诗也就迥然不同。《王子安集》中有一篇《秋夜于绵州群官席别薛升华序》,有可能是这首《别薛华》诗的序。从序言推断,诗人与薛华在绵州相逢,很快又分手。在一个清秋的夜晚,他送走薛华,作下了这首痛彻肺腑的诗篇。
诗的首联“送送多穷路,遑遑独问津”,是以事写情,又以情生景。两句诗,描绘出人生的一幅凄惶场面,一对患难知音跋涉在漫长、曲折、险阻的山道上。他们相送了一程又一程,难舍难分,但最后还是分别了,各自匆忙惶恐地去“问津”。“穷路”,借用的是阮籍穷途而哭的典故,含有“守死善道者,滞涸穷路”的意思。这就促人联想,发人深思。阮籍之所以穷途而哭,是想假作醉酒躲避迫害,时常独自驾车信道而行,走到绝路就痛哭而返,以示对现实的强烈不满。汉李固之所以“滞涸穷路”,正因为他“守死善道”,屡次上疏直陈外戚、宦官擅权的害处,后来被梁骥诬告,招致杀身之祸。在此,诗人以阮籍、李固自况,含蓄地指出:凡正直耿介之士,往往很难被当权者所容。这也说明了诗人与其挚友“多穷路”
的原因。下句中的“遑遑”,不只是形容凄惶貌,或自嘲“遑遑尔竞一时之虚荣”,还兼取宋玉《九辩》中“众鸟皆有所登栖兮,凤独遑遑而无所集”的意义,借以表示自己象凤凰一样清高,而不愿象凡鸟一样随处栖登。颔联“悲凉千里道,凄断百年身”,是分别承接首联中“穷路”、“问津”,进一步具体描写道路的险远,设想未来,抒发情怀的。所采有的手法是虚实相生,语义双关。诗人既为朋友颠沛流离于·132·《唐诗鉴赏大典》
千里道上而感伤,又自伤其远在千里之外的异乡。眼前道路崎岖漫长,展望未来满目悲凉,前程暗淡。这是诗人走上仕途三年来,对社会现实的真切的感受,从心底发出的深沉慨叹,说明了诗人当时内心失望情绪低落。
生活是艰难的,但仍要坚持下去而且要努力使之变好,年轻的诗人虽然沮丧但没有完全绝望。因此诗的颈联写道:“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意思是他们心中所期望的事业、建立功勋的志向与抱负,只能与船只一同在风浪中漂泊不定。正因为风华正茂的诗人,有追求,有希望,因此才对挫折、失败倍感痛苦。王勃《春思赋·序》中写道:“咸亨二年,余春秋二十有二,旅居巴蜀,浮游岁序,殷忧明时,坎土禀圣代。此仆所以抚穷贱而惜光阴,怀功名而悲岁月也。”可见他的“悲”是因为“怀功名”而难以实现。这联诗所表现的正是理想与现实矛盾,希望、失望交织的复杂心境。有志之士,不被赏识与重用,又不甘心自暴自弃,执意追求。就是他们“生涯共苦辛”的主客观原因。李东阳在《麓堂诗话》中曾说过:“薛华与李白并称,而无一字可传,岂非有幸不幸也。”薛华也是才志高远之人,也陷入同样的境遇,可见,怀才不遇并非偶然,也更说明志向的难以实现。
尾联“不论去与住,俱是梦中人。”上句承诗题中的“别”字,下句直抒惜别之情。从字面看,这联诗可以理解为王勃对朋友的安慰,表示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会永远相忆。另一方面,“俱是梦中人”包含有“命运之舟”难测的意思,彼此都像在梦里由不得自己。诗人对朋友和自己的前程怀着无限忧虑,而对明天仍抱着美好的希望。这个结尾,是隽永深长的。
《别薛华》与一般五言律诗借景抒情的方法不同,是以叙事直抒胸臆。语言简练,表达了真挚的情感。
赏析
抒写离情别绪之作,历代诗歌中不计其数。但是,“诗要避俗,更要避熟”(刘熙载《艺概。诗概》)。《别薛华》则堪称是一首含意隽永,别具一格,意境新颖的送别诗。
首联即切题。“送送多穷路,遑遑独问津”,是说送了一程又一程,面前有多少荒寂艰难的路。当友人踽踽独去,沿途问路时,心情又该是多么的惶惶不安。此联中一个“穷”字、一个“独”字,真乃传神之笔:穷路凄孤送挚友,把悲苦的心情,渲染得十分真切。但是,它又不仅仅是作者,也是远行人——薛华心情的真实写照,语意双关。
颔联和颈联俱是工稳而妥贴的对子。近体诗到初唐“四杰”手中,已日臻成熟,从此诗亦可略窥一斑。
颔联“悲凉千里道,凄断百年身”,紧承上联“穷路”、“问津”而深入一层述说:在这迢迢千里的行程中,惟有一颗悲凉失意的心作伴,这简直会拖垮人生不过百年的孱弱身体。诗中“千”字极言其长,并非实指。这二句是作者发自肺腑之语。王勃早年因“戏为檄英王鸡文”,竟触怒了唐高宗,从此不得重用。此诗是王勃入蜀之后的作品,时年仅二十出头,仕途的坎坷,对于王勃这样一个少年即负盛名,素有抱负,却怀才不遇、不得重用的人来说,其感慨之深,内心之苦,是可以想见的。所以,诗意就不能仅仅理解为只是在向远行人指出可能会遭受的恶运,其实也是作者在短短的人生道路上所亲身感受到的切肤之痛。
写到这儿,作者仍觉得意犹未尽,还不足以倾诉心声,更不忍与知音就此分手,于是又说:“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意思是:你我的心情,都象浩渺江水上漂泊不定的一叶小舟;而生活呢,也是一样的辛酸凄苦。这一方面是同情与劝慰对方,一方面也是用以自慰,大有“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的情意。
但是,离别却又是不可避免的。这样,就顺理成章地逼出了尾联“无论去与住,俱是梦中人”两句:离开的人,还是留下的人,彼此都会在对方的梦中出现。杜甫《梦李白》的“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便是这个意思。而这篇在诀别之时,断言彼此都将互相入梦,既明说自己怀友之诚,也告诉对方,我亦深知你对我相思之切。“俱是梦中人”的“俱”字,似乎双方对等,而由作者这方面写出,便占得了双倍的份量。
袁枚说:“凡作诗,写景易,言情难。何也?景从外来,目之所触,留心便得;情从心出,非有一种芬芳悱恻之怀,便不能哀感顽艳。”(《随园诗话》)此话说得不确的地方是,情和景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但是,就“言情难”而言,把这段话用在王勃这首诗中倒是十分妥贴的。由于此诗讲究匠心经营,反复咏叹遭遇之不幸,仕途之坎坷,丝丝入扣,字字切题,又一气流转,缀成浑然一体,确是感人至深。据作者《秋夜于锦州群官席别薛升华序》所说,作者不仅和薛是同乡、通家,也是良友;又据《重别薛华》一诗来看,两人之间确有非同一般的深情厚意。而此时王勃正当落魄失意之际,不平则鸣,因此,面对挚友,他以肺腑相倾。写法上,诗不着意写惜别之情,而用感人的笔触,抒发了悲切的身世之感,使人感到这种别离是何等痛苦,更显出这对挚友的分手之难。诗中所蕴含的深邃而绵邈的情韵,堪称自出机杼。这首诗与作者的另一首《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相比,虽题材同为送别,而风格情调迥异,前后判若两人。这是由于作者在政治上屡遭挫折,未能摆脱个人的哀伤情绪所致。
别薛华
王勃
送送多穷路, 遑遑独问津。
悲凉千里道, 凄断百年身。
心事同漂泊, 生涯共苦辛。
无论去与住, 俱是梦中人。
赏析
抒写离情别绪之作,历代诗歌中不计其数。但是,“诗要避俗,更要避熟”(刘熙载《艺概·诗概》)。《别薛华》则堪称是一首含意隽永,别具一格,意境新颖的送别诗。
首联即切题。“送送多穷路,遑遑独问津”,是说送了一程又一程,面前有多少荒寂艰难的路。当友人踽踽独去,沿途问路时,心情又该是多么的惶惶不安。此联中一个“穷”字、一个“独”字,真乃传神之笔:穷路凄孤送挚友,把悲苦的心情,渲染得十分真切。但是,它又不仅仅是作者,也是远行人——薛华心情的真实写照,语意双关。
颔联和颈联俱是工稳而妥贴的对子。近体诗到初唐“四杰”手中,已日臻成熟,从此诗亦可略窥一斑。
颔联“悲凉千里道,凄断百年身”,紧承上联“穷路”、“问津”而深入一层述说:在这迢迢千里的行程中,惟有一颗悲凉失意的心作伴,这简直会拖垮人生不过百年的孱弱身体。诗中“千”字极言其长,并非实指。这二句是作者发自肺腑之语。王勃早年因“戏为檄英王鸡文”,竟触怒了唐高宗,从此不得重用。此诗是王勃入蜀之后的作品,时年仅二十出头,仕途的坎坷,对于王勃这样一个少年即负盛名,素有抱负,却怀才不遇、不得重用的人来说,其感慨之深,内心之苦,是可以想见的。所以,诗意就不能仅仅理解为只是在向远行人指出可能会遭受的恶运,其实也是作者在短短的人生道路上所亲身感受到的切肤之痛。
写到这儿,作者仍觉得意犹未尽,还不足以倾诉心声,更不忍与知音就此分手,于是又说:“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意思是:你我的心情,都象浩渺江水上漂泊不定的一叶小舟;而生活呢,也是一样的辛酸凄苦。这一方面是同情与劝慰对方,一方面也是用以自慰,大有“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的情意。
但是,离别却又是不可避免的。这样,就顺理成章地逼出了尾联“无论去与住,俱是梦中人”两句:离开的人,还是留下的人,彼此都会在对方的梦中出现。杜甫《梦李白》的“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便是这个意思。而这篇在诀别之时,断言彼此都将互相入梦,既明说自己怀友之诚,也告诉对方,我亦深知你对我相思之切。“俱是梦中人”的“俱”字,似乎双方对等,而由作者这方面写出,便占得了双倍的份量。
袁枚说:“凡作诗,写景易,言情难。何也?景从外来,目之所触,留心便得;情从心出,非有一种芬芳悱恻之怀,便不能哀感顽艳。”(《随园诗话》)此话说得不确的地方是,情和景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但是,就“言情难”而言,把这段话用在王勃这首诗中倒是十分妥贴的。由于此诗讲究匠心经营,反复咏叹遭遇之不幸,仕途之坎坷,丝丝入扣,字字切题,又一气流转,缀成浑然一体,确是感人至深。据作者《秋夜于锦州群官席别薛升华序》所说,作者不仅和薛是同乡、通家,也是良友;又据《重别薛华》一诗来看,两人之间确有非同一般的深情厚意。而此时王勃正当落魄失意之际,不平则鸣,因此,面对挚友,他以肺腑相倾。写法上,诗不着意写惜别之情,而用感人的笔触,抒发了悲切的身世之感,使人感到这种别离是何等痛苦,更显出这对挚友的分手之难。诗中所蕴含的深邃而绵邈的情韵,堪称自出机杼。这首诗与作者的另一首《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相比,虽题材同为送别,而风格情调迥异,前后判若两人。这是由于作者在政治上屡遭挫折,未能摆脱个人的哀伤情绪所致。
抒写离情别绪之作,历代诗歌中不计其数。但是,“诗要避俗,更要避熟”(刘熙载《艺概。诗概》)。《别薛华》则堪称是一首含意隽永,别具一格,意境新颖的送别诗。
首联即切题。“送送多穷路,遑遑独问津”,是说送了一程又一程,面前有多少荒寂艰难的路。当友人踽踽独去,沿途问路时,心情又该是多么的惶惶不安。此联中一个“穷”字、一个“独”字,真乃传神之笔:穷路凄孤送挚友,把悲苦的心情,渲染得十分真切。但是,它又不仅仅是作者,也是远行人──薛华心情的真实写照,语意双关。
颔联和颈联俱是工稳而妥贴的对子。近体诗到初唐“四杰”手中,已日臻成熟,从此诗亦可略窥一斑。
颔联“悲凉千里道,凄断百年身”,紧承上联“穷路”、“问津”而深入一层述说:在这迢迢千里的行程中,惟有一颗悲凉失意的心作伴,这简直会拖垮人生不过百年的孱弱身体。诗中“千”字极言其长,并非实指。这二句是作者发自肺腑之语。王勃早年因“戏为檄英王(又鸟)文”,竟触怒了唐高宗,从此不得重用。此诗是王勃入蜀之后的作品,时年仅二十出头,仕途的坎坷,对于王勃这样一个少年即负盛名,素有抱负,却怀才不遇、不得重用的人来说,其感慨之深,内心之苦,是可以想见的。所以,诗意就不能仅仅理解为只是在向远行人指出可能会遭受的恶运,其实也是作者在短短的人生道路上所亲身感受到的切肤之痛。
写到这儿,作者仍觉得意犹未尽,还不足以倾诉心声,更不忍与知音就此分手,于是又说:“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意思是:你我的心情,都象浩渺江水上漂泊不定的一叶小舟;而生活呢,也是一样的辛酸凄苦。这一方面是同情与劝慰对方,一方面也是用以自慰,大有“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的情意。
但是,离别却又是不可避免的。这样,就顺理成章地逼出了尾联“无论去与住,俱是梦中人”两句:离开的人,还是留下的人,彼此都会在对方的梦中出现。杜甫《梦李白》的“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便是这个意思。而这篇在诀别之时,断言彼此都将互相入梦,既明说自己怀友之诚,也告诉对方,我亦深知你对我相思之切。“俱是梦中人”的“俱”字,似乎双方对等,而由作者这方面写出,便占得了双倍的份量。
袁枚说:“凡作诗,写景易,言情难。何也?景从外来,目之所触,留心便得;情从心出,非有一种芬芳悱恻之怀,便不能哀感顽艳。”(《随园诗话》)此话说得不确的地方是,情和景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但是,就“言情难”而言,把这段话用在王勃这首诗中倒是十分妥贴的。由于此诗讲究匠心经营,反复咏叹遭遇之不幸,仕途之坎坷,丝丝入扣,字字切题,又一气流转,缀成浑然一体,确是感人至深。据作者《秋夜于锦州群官席别薛升华序》所说,作者不仅和薛是同乡、通家,也是良友;又据《重别薛华》一诗来看,两人之间确有非同一般的深情厚意。而此时王勃正当落魄失意之际,不平则鸣,因此,面对挚友,他以肺腑相倾。写法上,诗不着意写惜别之情,而用感人的笔触,抒发了悲切的身世之感,使人感到这种别离是何等痛苦,更显出这对挚友的分手之难。诗中所蕴含的深邃而绵邈的情韵,堪称自出机杼。这首诗与作者的另一首《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相比,虽题材同为送别,而风格情调迥异,前后判若两人。这是由于作者在政治上屡遭挫折,未能摆脱个人的哀伤情绪所致。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