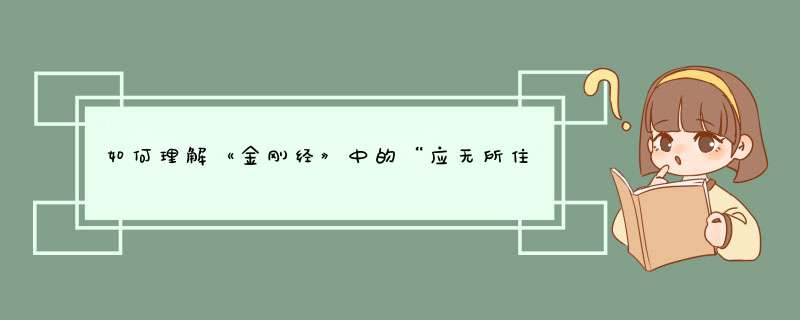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思维反复,自现其意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其心不凭借外在的相而生起,诸心皆为非心,是名为心
住者即为非住, 是名为住
思维的遍数到了足够多的时候,你可能会恍然大悟,佛法把不可能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意义,灌注于寥寥数字之中,反过来,如果要表达一样的意思,还真找不到更好的语言来代替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若心有住,即为非住
这句话的意义不止在于它文字的含义,更在于它的实用性
在你为一件事情愤怒的时候,请想起这句话: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不应住愤怒生心,不应住贪嗔痴恨而生其心,应生无愤怒心,若心住于愤怒,则为非住,是名为住于愤怒,是故一切愤怒皆非愤怒,是名为愤怒;当你如是想,如是作意,如是思维,知道愤怒即空无,而消除了愤怒的时候,再回过来看,真的仅仅是名为愤怒而已,没有实相的,愤怒不是真的,是因缘和合而成的虚妄,是不值得住的,所以说不应住愤怒生心,得知此意,应感谢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本身,也应感谢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智慧,应看到不住生心的无量功德力;
当你为任何一件事痴迷的时候,放不下的时候,乃至任何一个人为任何一件事痛苦的时候,这句话都可以派上用场;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从不执著于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开始,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来自印度的初期大乘佛教。因其包含根本般若的重要思想,在般若系大乘经中可视为一个略本;本经说“无相”而不说“空”,保持了原始般若的古风。
《金刚经》传入中国后,自东晋到唐朝共有六个译本,以鸠摩罗什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最为流行。唐玄奘译本,《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为鸠摩罗什译本的一个重要补充。其他译本则流传不广。
《金刚经》通篇讨论的是空的智慧。一般认为前半部说众生空,后半部说法空。
唐咸通九年刊刻《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金刚经),是我国现存有确切纪年的最早的雕版印刷品,由卷首画、经文及施刻人组成。
其卷首扉页画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版画作品之一。清光绪二十五年英国人斯坦因在敦煌石窟中发现,骗掠回英国。此卷现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即可读通此经,开悟人生。
《金刚经》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人生的大问题: “云何降伏其心?”也就是滚滚红尘中的芸芸众生,如何才能降服心中乱七八糟的想法?如何才能使得自己身心清静?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就是金刚经的主旨。
在生活中,当我们遇到烦恼时,往往只是责怪环境,而很少有人懂得去反省自己的内心,其实心才是一切烦恼的根源。佛法说“一切唯心造”,我们拥有什么样的心态,就会出现什么样的世界。心态的健康与否,直接关系到人生的苦乐。拥有健康的心境,是快乐幸福的根本。
一、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
所谓相,是指事物的现象和表现。所谓虚妄,不是你所理解的虚幻和徒劳的概念,而是指因为变化、因为无常,而认识到的无可执着。因为一切都是有种种因种种缘在参与,所以表现出来的现象都是如幻、如梦,而经中更有关于水沫、泡沫、影等等这些比喻。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并不是说你所认识和发现、感受到的外界事物都不存在、也不是说你参与的任何事任何社会行为都没有意义,而是说作为我们凡夫,因为自己经常被自己的意识思维所局限和束缚,经常执着在自我的意识里面,所以我们所认识的理解的事物,未必是真实的。
由于各种事物、各种事物的表现都是无永恒无常态的变动的,所以说有生死、有变异而出现种种“苦”。由于苦而理解世界上一切人、我、事理,都是在发展和变动之中,根本不存在“我”“我所有”这样的概念,所以说无我是空。再深入理解,则需要从真假、有无这样的理性概念入手,理解这些事物其实也是空的表现,即一切存在的并不是我们习惯中所见所认知的,而我们所见所认知的一切事物其表现也并不一定是真实的面貌或者并不是完全可掌控的。
佛法说空,说无相,不是说没有,说虚无,而是说源于无常使我们感受的变异,并由这个变而知如何随缘应对,不执着任何“我”的概念便无苦恼,这才是佛法的本质。所谓如来,就是本来如是的意思,也就是说事物的这个现象所表现,并不是其真正的内涵,而是我们自己做自己在解释,明白这个基本思路,自然就有如何应对无常而不是逃避的思路,平静、清净去观察和思维,才能理解事物为什么这样表现,所以说是如理如法作意而不是无明行事,这才是即心即佛的简单说明。
一切诸相都是虚妄不实的,不要执着于任何形象和境界,一切都会随顺而变。
如果能够照见各种现象的空性,便是真正的悟到了佛性。
六祖惠能的“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也是契合了这个道理。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并不是说一切相都不存在,而是说一切相都有,但是当我们看清相的本质的时候,心不会受其影响而波动。
之所以发生影响和波动,是因为考虑到自身的利益,觉得那些人、事、物、环境状况种种对自己太重要了,和自己的利害、得失有关,所以认为是真实相。
《坛经》里。其中有一个故事最能解释这句话。
一个旗在风中飘动,有的人说是风在动,有人说是旗在动,而六祖说,风和旗都没有动,而是心在动。
风也是相,旗也是相,当旗与风都是相,都是虚妄时,唯一能使旗动的就是心念了。
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一切依靠因缘而生的法,都如梦幻,如泡沫中的影子,如雾霭一样的不可琢磨,无常变幻。同时又如同闪电一样的快速变化。我们要无时不刻地这样看待这个世间的一切,不要执着它而被它束缚我们本来解脱自在的体性。
对于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诸佛菩萨的看法是这样的,它像闪电,它像露水,它不是真的,存在的时间很短。
在梦中,一切皆只是念头形成的‘相’,可说是‘名字相’,不是实物,称之为“无”;但是不能说没有这个梦,也不能说没有一切相,称之为“有”,也就是‘相有体无’。心的念头和心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就叫做“不一不二”,也是:“色(相)即是空(心),空即是色“。
‘一切唯心造应作如是观’——我们的生活的空间就是和”梦“一样的,是心的显现。量子学已发现粒子不是物质而是波动的现象——但是科学不知道是心念的波动形成的现象而已。
有个比喻是非常不错的,一滴水放在桌子上很容易干枯,如果把它投入到大海里去,那么这个生命就长了。人总有一死,在没死的时候,我们何必把一滴水孤立起来?我们把自己投入到众生那里去,念念不忘众生,还会活得健康一点,活得长寿一点。
我们一个人生活在世间不过几十年而已,寿命长的,七、八十岁就算是寿命长的,四、五十岁过世的很多,真的是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这样看就正确,就对了。
三、法尚应舍,何况非法。
诸法的实相, 不可以用文字语言来描述。
佛陀为了引导众生能够最终离苦得乐、到达彼岸。不得不随顺世间言辞习惯, 不说而说, 所以《金刚经》里面讲:“说法者, 无法可说!”, 所有一切讲出的法并不是法本身,都是为了让我们更方便理解法的本质。
“法”,它有两重解释。狭义的“法”就是指佛教,也就是释伽牟尼说的佛法;我们说皈依“三宝”(佛、法、僧),三宝的“法”指的就是佛陀说的法,说的能令众生涅槃的道理。广义的“法”指的是我们众生的思想能够想到的一切外在存在的事物。“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尘之法,对应的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法”对应的是“意”,“意”就是思想。佛陀说“人我空”、“法我空”,这里的“法”也是指我们想到的一切的外在的世界。当我们读佛经遇到“法”这个字的时候,一定要想是取“法”的狭义的理解,还是广义的理解呢。
用刷碗的例子来比喻,如果把一个油污的碗比作我们众生的心,那么佛所说的法就是洗洁精和水。
只有用洗洁精和水才能把碗洗彻底洗干净,但是一个沾满了洗洁精的碗绝对不能算一个干净的碗。
所以还要把洗洁精也冲干净,把水也晾干,然后才能算一个真正干净的碗。
同样我们当通达了某个法的真正意趣之后,不可以对这个法太执着,该舍的时候就要舍弃掉。
然而, 如果我们还没有真正通达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随便舍弃这个法的。
《金刚经》里面同样还有一句“知我说法如伐喻者”, 就是说, 佛所说的这个法呢, 就像一个小船, 如果你过了河呢, 就要果断地把船舍弃掉, 不然带着船怎么继续前进的行程。
可是如果你还没过去这个河, 就把这个船给舍弃掉了, 这河可怎么过呀?
四、 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
所谓佛法者,其实没有佛法之相,贵在体悟。能悟,一切法都是佛法。不能悟,你就是拿了佛法也会把他变成世俗法、轮回法。因为你不能真正体悟,执著于这个相。比方说你诵《金刚经》,你要求的是世间怎样身体健康,这就把佛法变成世俗法了,所以“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
白居易有过一首诗名为《僧院花》:“欲悟色空为佛事,故栽芳树在僧家。细看便是华严偈,方便风开智慧花。”这也可以说明,在一切之中能悟的话都能见佛法。
在名言现相之中,释迦牟尼佛宣说了八万四千法门,但这些都是为了引导我们破执著,明心见性的方便法,都如阳焰、如水月一般的存在。实相之中,无任何所谓的佛法存在。名言显现的佛法也要众生通过积累资粮,有福德因缘才能得以遇见。所以也不要轻视这个名言显现的佛法,如果没有福慧资粮,没有善根因缘,还是难以得遇,所谓的“佛种从缘起”,也是非常重要的。
从胜义谛来说,佛法即非佛法。因为佛法只是引导众生的方便法而已。佛说种种法,为了种种心。若无种种心,何须种种法?真正的法是离一切戏论边执的实相无为法。
所谓的佛法,其本性并非实有,如果你有一个佛法的观念存在,你已经执着在法的虚相的概念上了,佛法不一定在佛经上,世间皆是佛法……
真正的佛不认为自己是佛,真正的圣人,不认为自己是圣人。
“佛法”即是佛所说的一切教法。这句经文的关键在于第二句话“即非佛法”。
佛陀教导我们,要看破世间万物,不要去执着。所谓佛法也是教导我们如何去看破、放下世间万物的方法。
《金刚经》的根本思想,就是让我们去掉一切牵挂,放下一切烦恼,达到心灵的绝对清净安宁,得大解脱。
所以最后,我们也不能执着于佛法带来的种种不可思议。
五、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关键是“住”和“心”二字,住,指的是人对世俗、对物质的留恋程度;心,指的是人对佛理禅义的领悟。人应该对世俗物质无所执着,才有可能深刻领悟佛。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两句,乃体用并显。云何体用?“应无所住”是体,“而生其心” 是用,用不离体,体不离用。“应无所住”既不著有,“而生其心”亦不落无,方是金刚本旨。
应无所住,就是一切不住。若能一切不住,即是实相境界。既悟实相无相,一无所得,还有什么我执、烦恼、生死、无明可住?若执著无住,又落于偏空。何以故?当知真空不空。云何不空?空寂灵知,起用自见。用云何起?依般若智而生其心,即是起用。云何生心?即生吾人本具之妙明真心,就是生悲愿无尽之菩萨心、菩提心、慈悲心、平等心、利他无我心。如是等心,皆是无所住而生之心。便是真心、清净心,亦即是佛心。而众生所生之心,乃贪心、我执心、贡高心、差别心,乃至八万四千烦恼心。如是等心,皆是有所住而生之心,便是妄心、业识心,亦即是众生心。所以者何?因众生处处著相,相多故心亦多,心多即不能清净,心不清净,即不能悟得实相真心。故学佛人欲悟实相真心,即要放下一切,则一切不住,真心自见,即是道心。道从心生,心由道见。讲到究竟,这一个道字,也不可说。所谓言语道断,心行路绝。此理微妙,初学人不易领悟。佛要人领悟实相无相,离念即是真心,故说“应无所住”。佛又要人领悟起用之妙,故又方便说“而生其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二句,看来似觉矛盾,其实就是如是。
应该无任何执着的升起清净心,真正的清净心,不是有个光,有个境界,而是不把心念停留在色、声、香味、触法上。
真正的修行,应该随时随地无所住, 坦坦然,物来则应,去则不留。
六、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
何为“四相”?
“我相”:指(能感知)的那个,亦即执着我的观点。例如小明食过榴梿雪糕感觉好食~“我相”。
“人相”:指(被感知)的那个,亦即由执着我的观点而建立的二元对立观点。如小明食过榴梿雪糕感觉好食,故此只要有人否定榴梿雪糕好食,小明就不认同~“人相”。
“众生相”:指是无数个由我被感知的那个,而产生的执着种种二元对立观点。如:小明食过榴梿雪糕感觉好食, 将这个观点一直伸延,去建立种种榴梿雪糕感觉好食的观点,同时排斥否定榴梿雪糕的点子~“众生相”。
“寿者相”:寿指寿命,亦即是时间。内涵是指是于“过去、现在、未来”时空上,所建立的一切观点。如小明食过榴梿雪糕感觉好食这个观点,一直纠缠于小明的脑海,谁知道经过时间的洗礼,市场上已经出现一种“番薯雪糕”,而且榴梿雪糕已经被社会淘汰,不再生产,但是小明仍然不知道,只不断坚持这个时空上曾经体验榴梿雪糕感觉好食的观点~“寿者相”。
破四相是为了解决执着的苦。
人只能随着那一刻实际状况运用某观点面对,观点更加是“中性、空性、虚幻、无常”。
所谓“中性、空性、虚幻、无常”是指人、事、物所呈现的只是“心的感觉”,这份感觉更是人人不同,只是误以为相同。
原因是随着那一刻实际状况运用某观点面对然后,必须将某观点马上放下,不能滞留,否则就叫“执着”。
因为当时某观点只是个人及时空匹配而呈现,事情一过,观点可能已经完全失去意义。
如果菩萨在心中还有对自我的执着、对他人的执着、对众生的执着、对生死的执着,那他就不是菩萨了。
七、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一切众生的心都在变化中,像时间一样,永远不会停留,永远把握不住,永远是过去的……
我们刚说一声未来,它已经变成现在了,正说现在的时候,已经变成过去了。
“无住”精神,可以缓解现代人的压力感,使人保持澄明心性。当今时代是一个物欲涌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的时代,有些人不再谈论人生、理想、国家、社会,而是更多地谈论**、股票、服饰、美食、足球、明星等等。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五光十色目不暇接的世界。
享受现代物质文明是现代人应有的权利,但人切不可成为物质的奴隶,陷溺于拜金主义的狂潮,从而导致精神家园的失落。人除了物质生活,还要有充实的精神生活,精神上去充实才是真正的富贵,精神上的满足才是真正的幸福。
现代心理学理论告诉我们,人都具有“庸人自扰”的本性:对于悠关自身之事作过多的无谓思考,是困扰自身的主要原因。更要命的是,人的这种“能力”不需要有事实依据,但凭想象就可以了。假使心起了烦恼,那么即使在社会上很有地位、财富,生活也是空虚的。
如果心中颠倒梦想,高楼大厦无异于监狱,美味佳肴就是毒药。古人说:心安茅屋稳,性定菜根香。只要心安定了,就算吃的是粗茶淡饭,住的是茅草小屋,心中也很安定、 自在。
八、是法平等,无有高下。
世出世间一切事物、现象、概念都是“自体相空”,即万事万物都是因缘和合,没有独立不变的本质,也就是说,在空性的层面,万事万物都是平等的。
法无高下,因为无法相,亦无非法相。法只是相而已,在这个层面上,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万法唯心,是说对这个世界的一切观点、见解、情绪、情感…等等,都是由心而生,佛法也是由心而生,大乘由心而生,小乘由心而生,藏密由心而生,乃至儒家、道家,无一不是由心而生,全部都是圣人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观点和见解,所有这一切者是由心而生。
八万四千法门,念佛也好,修密宗也好,参禅也好,修止观也好,甚至于说修外道也好,以华严境界看来,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真正的佛法是平等,无有高下的。
契机的法就是最好的法,法法都可以达到目的,达到目的了就无有高下了。法是途径,道是目的,从达到目的这个角度讲,哪条路都是可行的,只要适合自己,所以,路路皆通,法法平等。从契机的角度看,法无优劣,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万法唯心,法不离心,心不离法,法外无心,心外无法,心法一体,哪有高下?
九、所作福德,不应贪著。
最好解释是菩提达摩祖师与梁武帝的那段对话。梁武帝一生造了许多寺庙,剃度了许多僧人,主持编订了许多佛典,大力弘扬佛法,做了许多有福报的事情,但是因为他是以一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心来做这些事情的,所以这最多也只是得了一个天人的果报,而不是菩萨的果报。正因为如此,禅宗初祖菩提达摩祖师认为梁武帝并无甚功德。真正的行菩萨道、行布施波罗蜜是不求回报、不贪著的,以清净自然、没有功利的心态去做善事。
真正行大乘菩萨道的人们,做善事不求福德的果报。菩萨并不以求福德之心去行善,是做应该做的事,本份的事,做了就过了,不住不著。虽然有福德,但菩萨自己并不贪著,虽然有好处,但是菩萨并不领受,而是回向给世间一切的众生。布施波罗蜜中包含的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三种,都是同样的道理。这也就是佛家所讲的“三轮体空”了,真正的布施,无布施者,无布施物,亦无接受布施者。
《金刚经》是十分有意思的般若经典,每每说福德,每每又将福德推翻。三千大千世界的一切,本来都无一物,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是修福德,是提得起;智慧成就了会晓知福德也空,无可贪著,这就真的懂得放下了。
对于所做的福报功德,不应因贪求而升起执取之心。
有好处,自己并不领受,而回馈给世界一切众生,愿这个世界一切众生受这个好处,自己并不需要。
十、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
到底什么是“如来”?“如”是比喻,意思是“好像”,“来”则是代表了“来去”等之相状。成佛就是好像不来不去,如如不动。这个状态或许很难体会,但当我们自问“过去的时间、记忆”在哪里时,多少就能有些体会了。好像是来了又去了,又好像是不来也不去。不生不灭,不增不减。
因此《心经》中有言“是诸法空相”,即便我们想去执著,其实也是无有所得。就像我们每时每刻的念头,贸贸然来了,贸贸然去了,当我们拼命想把念头、妄想空掉时,就已经离如来十万八千里了。妄想本空,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所以《坛经》告诉我们“烦恼即菩提”。妄想烦恼留也留不住,我们又在烦恼什么呢?我们若是如此懂得了“如来”,那就自然时时刻刻都在清净之中了。
众生本具的如来本性,不停驻于任何时间和空间而存在,离一切分别妄念,即是如来清净本性。
《金刚经》中字字句句、在在处处皆是平凡无奇的不二法门,信受奉行就在当下。
我始终相信:心如莲花,你就不会辜负于天下之人;念如菩提,天下之人亦当不会辜负于你。
当我们悟透了岁月,悟透了世事,悟透了自已,才知道何为人生之终极,何为生命之真谛。
《金刚经》始终强调不执着于任何一面,既不会执着于有,自然也不会执着于空。下面是其中第三十一品知见不生分的解说,希望你能喜欢。
须菩提。若人言。佛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须菩提。于意云何。是人解我所说义不。不也。世尊。是人不解如来所说义。何以故。世尊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即非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是名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须菩提。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一切法。应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须菩提。所言法相者。如来说。即非法相。是名法相。
见不是见
须菩提。若人言。佛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须菩提。于意云何。是人解我所说义不。
佛讲到这里,先问须菩提,假使有一个人说,佛说的,人见、我见、众生见、寿者见,对不对佛经上都讲四相,这里又转一个方向,提出来的不是「相」,而是「见」。「相」就是现象。「见」是自己的思想见解,是属于精神领域。所谓见解,就是现在新观念所谓的观点,都属于见。所以禅宗的悟道叫做见地,要见到道,不是眼睛看见啊!楞严经上讲见道之见,有四句话:
「见见之时,见非是见。见犹离见,见不能及。」
你看这个佛经,讨厌吧!都是什么见呀见的。第一个见,我们眼睛看见的见,心与眼看见。第二个是见道的见,换句话说,第一个见是所见之见,第二个是能见之见。我们眼睛看东西,这是所见,这是现象。所见回过来,自己能够见道,明心见性那个见,不是所见之见,不是眼睛能够看见一个现象,或者看见一个境界,那不是道啊!
所以「见见之时」,自己回转来看到见道之见,明心见性那个见的时候,「见非是见」。这个能见,见道的见,不是眼睛看东西所见的见,故说「见非是见」。那么能见道的见,难道还有一个境界吗「见犹离见」。当眼睛也不看,耳朵也不听,一切皆空以后,说我见道了,有一个见存在,还是所见,这个见还是要拿掉,见犹离见,还要拿掉,空还要空下来。「见不能及」,真正明心见性的见,不是眼睛看见的见,不是心眼上有个所及,能见的见。说了一大堆的见,多么难懂啊!
告诉我们明心见性之见,可不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青蛙扑咚一声跳进水……要一切见无所见,一切山河大地,宇宙万有,都虚空粉碎,大地平沉,那可以谈禅宗了,明心见性有点影子了。记著!还只是一点影子啊!
楞严经上也有几句很重要的话:「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斯即涅槃。」知与见,后来是佛学一个专有名称,知就是知道,把佛经道理都懂了的这个知。见,也看到过这个现象、境界,就是知见。道理懂了,你去修行打坐,坐起来一切皆空,可是有知性,也知道自己坐在那里很清净。但是有一个清净在就不对了,「知见立知,即无明本」,就是无明的根本。有一个清净就会有一个不清净的力量含藏在里面,就有烦恼的力量在了,所以知见立知,即无明本。要「知见无见」,最后见到空,「斯即涅槃」,可以达到见的边缘了。
知即无明本
从前有好几位大法师就是看经典走禅宗的路线,后来就悟道了。所以学禅不一定是打坐参禅,不一定要打坐参公案、参话头。宋朝温州瑞鹿寺有一位遇安禅师,天天看佛经念佛。他看到前面这一段,忽然心血来潮,把原来的句子「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斯即涅槃。」改了标点,变成「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斯即涅槃。」自己因而大彻大悟。后来他自称「破楞严」,改了圈点破开来读以后,自己忽然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知见立」,有知有见,有个清净有个觉性,「知即无明本」,这一知,本身就是无明本,就是烦恼。「知见无」,一切皆空,理也空,念也空,空也空,「见斯即涅槃」,见到这个就是悟道了。这是他悟了道,自己楞严破句,就懂进去了。
现在我们说明了这个道理,说了半天,不要把话转开了,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金刚经前面都提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中间也提过,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见,不能见如来。到这里,忽然一转,提出「见」,不提出相。相是相,茶杯是现象,毛巾是现象,书本也是现象,我也是现象,他也是现象,你也是现象,山河大地一切房子都是现象,连虚空也是现象,清净也是现象,睡觉也是相,作梦也是相,醒了也是象,一切现象都是生灭变化。
所以有些人天天打坐,问他好吗好啊!好清净。著相!著清净之相。相不是道,道不在相中。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斯即涅槃。你要立一个清净是道,再加上背上督脉通了,前面任脉通了,拿水龙头一开灌进去,都通了,那不是成道,那都是著相。一著相,知见立,知即无明本;要知见无,见斯即涅槃。
所以现在告诉你知见之见是什么他告诉须菩提,假使有人说,我提出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你说说看,那人了解我所说的意思没有他这个人还算真正学佛,懂了佛法吗
不也。世尊。是人不解如来所说义。
须菩提说,那不对的,这个人虽然学佛,根本不通啊,不懂佛法的道理。
何以故。世尊。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即非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是名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
那么佛也跟著说,你现在提出来一个假定的问题问我,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见道之见,这只是一个讲话上的方便;假设有这么一个见处,一个明心见性,见道之见,那也只是一个表达的方法而已,一个揭穿真义的名辞而已。实际上啊,明,无可明处;见,无可见处,所以叫做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
如是知见
须菩提。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一切法。应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不生法相。
佛告诉须菩提最后的结论,你要注意啊!真正学大乘佛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想求得大彻大悟的人,于一切法,包括世间法,出世间法,应「如是知」,要了解知道金刚经这些一层一层的道理。「如是见」,要有这样一个见解,所以有知有见。
知见两个字,再加一个说明,一切大小乘的佛法,尤其是小乘的佛法,是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五个次序。按次序来修行,先守戒,再修定,再由定发慧悟道。真的悟道了,解脱一切苦厄,但是解脱的最高程度,仍是物质世间一切的束缚。当这些欲界、色界一切的烦恼、情感都解脱光了以后,还有个东西就是心性的所知所见,这个知与见仍要解脱,最后要彻底的空。刚才举出来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斯即涅槃;这里也讲,发大乘心,想由凡夫修道而成佛,应该对一切法,「如是知,如是见」。
如是怎么知怎么见呢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是名佛法;那么所谓外道者,即非外道,是名外道;所谓魔鬼者,即非魔鬼,是名魔鬼;所谓我者即非我,是名我。就是这一套8一切」,整个归纳起来,空有都不住,无注无著,所以一切法应如是知,如是见。
你理解了,也见到了这个道理,「如是信解」,理性上清楚了,才是不迷信。如果佛法的教理都没有弄清楚,情绪化跑来学佛参禅,全体是迷信!所以把知见搞清楚了,如是信,才是正信。如是解,正信以后,由这样去理解它,这才是理性的。学佛修道是理性的,不是情感的,不是盲目的迷信,是理性的如是信解。
我们自己的法相
为什么说「不生法相」为什么不说不「用」法相,或者不「坠法相,不「著」法相,不「落」法相呢这些字都不用,而用不「生」法相,这是有区别的。
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叫法相一切的现象、观念都是现象,是意识思想构成的一个形态。每个人意识里都有自己一个构想,幻想;幻想久了,变成牢不可破的一个典型,自己就把它抓得牢牢的。这个就是意识思想境界里的形态,在佛学名辞里叫做法。法包括了一切事,一切理,一切物,一切思想观念。
譬如大家认为大彻大悟,一片光明,都在清净光明中,在一般人心目中,下意识已经构成一个形态,认为悟了道打起坐来,大概内外一片光,连电力公司的发电机都可以不要了。把光明看成电灯光、太阳光、月亮光那样,下意识的构成法相,构成一个形态在那里。
又譬如说,悟道以后,大概什么都不要,什么也都不相干,一切一切都不管,跑到古庙深山,孤零零的坐在那里,就以为成佛了。如果成了这样的佛的话,世上多成一千个佛对我们也没有关系;山里早有的是佛,许多石头、泥巴摆在那里,从开天辟地到现在,都可以叫做佛。反正它们对一切事物,一切出世入世的一概不理。换句话说,那是绝对的自我,看起来很解脱,一切事物不著,实际上是自我,为了自我而已!认为我要这样,因为他下意识的意识形态有了这个法相。
一般人打坐入定什么都不知道了,那不是佛法,那是你的意识形态,是你造作了这个法相。乃至于说一切空了就是佛,空也是个法相,是个现象。有些人任督二脉打通了,奇经八脉打通了,河车大转,也都是法相。我经常问:你转河车,转到什么时候啊不要把自己转昏了头。你转转……总有不转的时候吧转到什么时候才不转呢任督二脉打通了,通到那里去呢通到阴沟里去吗还是通到电力公司还是通到上帝菩萨那里你都要搞清楚啊!可是我们许多人,不知不觉的都落在自我的法相里了。自我意识形成一个道的观念,一个道的样子,一个道的模型。
由此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世界上的宗教,因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所画的天堂也都不同。我们的天堂是穿大袍子古代帝王相的人,一切房子都是中国古时候的。西方人的天堂是洋房,他的神和上帝也是高鼻子蓝眼睛;阿拉伯人画的另有不同。所以说,天堂是根据自己的心理形态构成的,谁能去证明呢这些都是自己心理下意识构成的法相。
佛法唯识宗也称为法相宗,法相宗是先从现象界开始分析研究,现象界也就是世间一切事,所谓的一切法;最后研究到心理状态,研究到心性的本来,以至于证到整个宇宙。也就是说,法相宗从现有的人生,现有的世界的相,加以分析,归之于心,然后反回到形而上的本体。如果套一句佛学的名辞来讲,这是从自己的身心入手,进而打破了身心,证到形而上的本体。
华严宗不同于法相宗,是先从形而上的宇宙观开始,从大而无比的宇宙,慢慢收缩,最后会之于心,是使你由本体而了解自己。普通的佛学,是由你自己而了解了本体,这是两个不同的教育方法,我们必须要弄清楚。这些不同的路线不同的方法,佛学的名辞就叫做法相,一切法相。
现在金刚经快要结束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非常严重的道理,佛告诉须菩提,你想证得无上菩提大彻大悟而成佛,你应该这个样子知道,应该这样去看清楚,理解清楚,应该这样子相信,这样去理解。怎么理解呢一句话,「不生法相」,你心里不要造作一个东西,你的下意识中,不要生出来一个佛的样子。每个人心里所理解的佛,所理解的道,所理解清净涅槃的境界,都各不相同,为什么不同呢是你唯心所造,你自己生出来的,是此心所生。
所以你不要自生法相,不要再去找,不要构成一个自我意识的观念。譬如我们上同样一个课,一百个同学中,各人理解的深浅程度都不相同,因为每人心里自生法相,自己构成一个现象,都非究竟。这就是佛经上说,众盲摸象,各执一端的道理。尽管瞎子摸象,各执一端,可是摸的那一端,也都是象的部分,并没有错。只能够说,每人抓到一点,合起来才是整个的象。要想完全了解整个大象的话,佛告诉我们的是「不生法相」,一切不著。下面,佛又推翻了。
我要过去你过来
须菩提。所言法相者。如来说。即非法相。是名法相。
佛经所说的法相,根本就不是法相,所以叫做法相。这个话在金刚经上常说。道理在那里那些都是教育上的方法。等于过河的船,目的是使你过河,已经过了河就不要把船背著走,要赶紧把船丢下,走自己的路。
佛经三藏十二部,各种各样的说法,有时候说空,有时候说有,有时候说非空非有,有时候又说即空即有,究竟那一样对呢那一样都对都不对,要你自己不生法相。
讲一个法相,包括了各种现象,譬如唯识宗,除了把心的部分分成八个识来讲外,再把心理活动的现象,纲领原则性加以归纳,成为一百个法。如果详细分析起来,当然不止一百个;可是后世一般人研究唯识,就钻进去爬不出来了。这些人钻到什么境界里头了呢钻到「有」,钻到一切法「胜义有」的法相里去了。就像龙树菩萨讲般若拿空来比方,与法相唯识宗的教育方法不同,可是一般人研究般若,又落到「空」的法相里去了。所以说,任何法相都不能住,都不是。
佛最后告诉我们,所谓法相,「即非法相」,那只是讲话的方便,机会的方便,教育上的方便,目的是使你懂得。如果这样不懂,他换另一个方法,总是想办法使我们懂得。可是后世的人,把他的教育方法记录下来以后,死死抓住他说过的那个空,或拚命抓个有,永远搞不清楚。事实上佛交代得很清楚,一切不落法相。不落法相以后,大家反而都说金刚经是说空的,前面我们已经说过,金刚经没有任何重点是教我们观空,金刚经都是遮法,挡住你不正确的说法,至于正确的是个什么东西,要你自己去找。
记得金刚经开始的时候,我曾经提到过禅宗的两个公案,一个是儿子跟父亲学小偷,对不对还有一个是坐牢的那个公案,现在再说一个禅宗故事。有一个年轻人出家学佛求道,想要开悟,跟著师父几十年。这位师父总是对他非常严厉,生活、行为都管得非常严。但是一问到佛法,师父总不肯说。这个人就像我们现在青年人学佛一样,好像找到一位老师,马上就有妙诀告诉他,传你一个咒子罗,或者传你一个方法,今天一打坐,明天就会飞了,就成佛了;自己意识中构成了这样一个法相。这个人的心理也是如此。可是这个师父呢,问到他真正佛法时,就说:你自己参去!自己研究去!
他自己暗想,十二三岁出家,天天求佛道,搞了几十年,这个老师嘛!是天下有名的大老师,是有道之士,跟著他却辛苦的要命,佛法也没有传给他一点,心中真烦恼。有一天他想了一个办法,带了一把小刀上山,师父快要走这一条小路回来了,小路只能走一个人,他就站在路口等师父回来。那天下雨,山上路滑难走,他看见师父低著头,慢慢走到了。其实他师父大概早知道这家伙在那里,他以为师父不知道,看到师父过来了,就一把抓住师父说:「师父啊,我告诉你,我几十年求法,你不肯告诉我,今天我不要命了。」说著就把刀拿出来,「你再不告诉我佛法的话,师父啊,我要杀了你。」这个师父很从容,手里还拿把雨伞,看他这个样子,就用手一把抓住他拿刀的手说:「喂,路很窄,我要过去,你过来。」师父把他拉过来,自己就过去了。他听到「我要过去,你过来」就忽然大彻大悟了。
我们大家参参看,「我要过去,你过来」,这一句话他就悟道了,这个理由在什么地方这个就是所谓禅宗公案。现在大家很难找出答案,我说的也不是真的答案,只能打个比方给你听:我们大家学佛最困难,心中的烦恼,身体上的感觉,坐起来腿发麻,不坐时心里烦恼不断;很想求到清净,清净永远求不到。烦恼不断,自己问自己怎么办你自己里面的师父一定告诉你:「我要过去,你过来9烦恼跑过了就是清净,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不生法相,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那么简单。所以说,我要过去,你过来,这一条路根本是通的,烦恼即是菩提,那里有个烦恼永远停留在心中呢!你要是去想办法把烦恼空掉,求个清净,你不就是那个师父跟徒弟永远堵在路上,走不过来了吗
你看人家的教育法很简单,我要过去,你过来,也不理刀,也不理徒弟,这个徒弟就清楚了,就悟道了。可见他平常都在自生法相,都是著了一个佛的观念,著了一个道的观念。人生最怕是著魔,实际上,你学了佛法,学了道,把道跟佛法捆起来,你正是著魔了;著了佛魔,著了道魔,著了功夫魔,著了清净魔。
清净也是魔啊!所以禅宗祖师有几句话:「起心动念是天魔」,什么是天魔是你的起心动念而已,你自己生的法相。「不起心动念是阴魔」,大家注意啊!很多人都落在这个魔境,光想打起坐来什么都不知道,以为什么都不知道是入定,那个是不起心动念,不起心动念落在五阴境界,是阴魔。「倒起不起是烦恼魔」,有时候好像很清净,你觉得很清净吗有时候又觉得心里头好像有一点游丝杂念,可是也不要紧,可是也迷迷糊糊,这个就是倒起不起烦恼魔,无明之魔。说什么走火入魔!魔从那里来魔完全是自心所造,没有其它的东西。「起心动念是天魔。不起心动念是阴魔。倒起不起是烦恼魔。」如此而已。
佛学把魔境分析得很清楚,禅宗的大师们是用归纳的方法,非常简单扼要告诉你。实际上,这些心理的状况,这些境界,都是自生法相。由此更进一步说,我们佛学越学多了,唯识研究到最后,佛经三藏十二部都学了,你越学的多,越被法相的绳子捆得紧,都是著了法相。所以在快要作结论的时候,佛告诉我们,不生法相才是最究竟。我们给它的结论偈子:
第三十一品偈颂
九霄鹤唳响无痕泣血杜鹃落尽魂
谱到狮弦声断续为谁辛苦唱荒村
这是一个感想,在座的人,要是到过西北和中国的高山,或到过青城山峨嵋山,可能会听到白鹤的叫声。中国文字很妙,鸡叫是啼,鸟叫是鸣,虎叫是啸,表示不同的声音形态;白鹤叫称为鹤唳。白鹤是在高空叫的,声音像打锣一样,传得很远,所以这个鸟与其他的鸟特别不同。
「九霄鹤唳响无痕」,就是说,佛的说法像九重天上的白鹤,叫声响彻云霄,要叫醒世界上所有人的迷梦。但是,我们有没有被他叫醒呢世界上许多人是叫不醒的,想一想真够伤心。结果千里迢迢去学佛,不论在家出家,都变成杜鹃鸟一样。
「泣血杜鹃落尽魂」,据说杜鹃是上古一个因亡国而伤心到极点的帝子,因为天天哭,后来他的精魂变成杜鹃鸟,还在哭,哭到最后眼睛流血,滴在泥土上变成现在的杜鹃花。杜鹃另有很多的名字,也叫杜宇,也叫帝子,就是蜀国皇帝的儿子。我们后世学佛学道的都是杜鹃,抛家弃子专心学佛,到最后,道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只怪自己没有遇到明师,没有碰到佛,没有得到法。其实佛法是最平凡,最简单,佛在金刚经上都说完了。
「谱到狮弦声断续」,金刚经等于狮子之弦,用狮子身上的筋作弦的琴,它发出的琴声,百兽听到都会头痛,再重一点,百兽听到脑子都裂了,因为狮子是百兽之王。佛说的法是哲学里的哲学,经典里的经典,世界上真正形而上的道法,直截了当,全部都告诉我们了,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琴谱弹到狮子之弦,这个声音弹的金刚经也好,法华经也好,华严经也好,断断续续,都弹给我们听了,高明的歌曲统统唱给我们听了,我们还是不懂。等于一个叫化子沿门唱莲花落一样,唱了半天没有人理,人不觉得好听,「为谁辛苦唱荒村」啊!这是对释迦牟尼佛幽默一下。实际上,我真为释迦牟尼佛一洒同情之泪,他讲到三十一品了,快讲完了,有谁懂得他呢他又何必在那里讲呢为谁辛苦唱荒村啊再唱一遍也没有用,因为知音难遇啊,永远不懂。实际上,他说的最亲切,最平凡。
我们现在再一次回过头来看,金刚经最开始,第一个重点是三个字──善护念。凡夫也好,成佛也好,只有一个法门,就是善护念。护什么念无所住怎么无所住很简单,不生法相。成了佛的人怎么样呢也是一样,也是吃饭穿衣,饭吃饱了,洗脚打坐,就是那么平凡。没有什么头上放光啦!心窝子放光啦!六种神通啦!都不来。吃饭穿衣敷座而坐。然后你问话,他答覆,就是那么简单。金刚经就是平凡里头的真实,平凡里头的超脱。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是《金刚经》中的一句话,意思是所有有形的事物都是瞬息万变、无常无据的,就像梦幻泡影、露水、电光一样,没有任何固定的、真实的实体。因此,我们应该以这种“无常”的视角来看待世界。
这句话所说的“有为法”,指的是所有有形的事物,即所有因缘汇聚而成的现象和存在。这些事物都是不断变化的,没有一个是永恒不变的,所以都是无常的、虚幻的。
通过这种“如是观”的方式来看待世界,我们可以摆脱对于物质世界的执着,认识到一切事物的本质皆是无常,从而达到超越苦难、超越生死的境界,达到了佛教所说的涅槃之境。
《金纲经》全文没有出现一个“空”字,但通篇讨论的是空的智慧。一般认为前半部说众生空,后半部说法空。经文开始,由号称佛陀十大弟子中“解空第一”的须菩萨发问:“当众生立定志向要达到无上圆满的佛陀觉智时,应该将发心的目标定在哪里?如果在实践过程中心不能安住,应该如何降伏?”即如何使心灵平和地安住在终极关怀,如何在走向终极目标的过程中,对各种错误认识和患得患失心理进行克服?《金刚经》就是围绕佛陀对此问题的解答而展开的。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就是解答这些问题的精髓。其意思是世间的一切物质和现象都是空幻不实的,如梦幻泡影,实相者则是非相。因此修行者应该“远离一切诸相”而“无所住”,即放弃对现实世间的执著或眷恋,以般若慧契证空性。
此经主要通过非此非彼有无双遣的重重否定,指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虚幻不实的,要成就无上知觉,就得破除一切执著,扫除一切法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世上的一切事都如梦、如幻,如水面的气泡,如镜中的虚影,如清晨的露珠,日出即散,如雨夜的闪电,瞬息即逝。世上的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成,并无自性,所谓“缘起性空”。因此,我们平时看到的一切事物的形相,实际都不是它们真正的形相,事物真正的形相(实相)是“无相”。这样,世界上一切都不什值得执著,这就叫“无住”。在修竹实践中,能真正认识到无相之实相,能做到于世界万物都无念无系的“无住”,就可以得到真正的解脱。
为了使人们真正做到“扫相破执”,“无相无住”,《金刚经》进一步说明,大乘菩萨在自觉觉他的修行过程中,其终极目标定位在和一切众生其同成就佛果的广大境界。但是根据缘起论,凡因条件关系而形成的事物,都不存在绝对不变的实体(自性)。因此,要以空观的智慧,破除在“我”、“众生”、“佛”之间的人为分别。故要尽己所能广度众生,但不要执著于“我”在帮助众生中具有多大的功德。唯心量大者,才有大格局,方能成就大事业。
《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实相,是世界的真实,事物的本来面目。唯有以般若观照实相,即对此名相采取不住、不执、不取的如实态度,才能认识真相。故经中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释迦牟尼的色身有三十二种端庄的特征,但是不能依据这三十二相来认识如来,因为三十二相只不过是外在的虚妄之相,如果执著于这三十二相,就不能认识如来的真实面目(法身),因为真正的法身是无相的。
要如何不执著呢?《金刚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如上所述,唯有不住相、不偏执,才能把握实相。《金刚经》中以布施为例,讨论了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做到“不住相”。世人在布施时,每施一东西,即作功德想,于是施恩图报,算计此布施行为将积累多少的功德。但实际上,应以“三轮体空”的精神在布施,也就是要对能布施的我、受布施的人和所布施的财物不产生任何的执著,方能证得离相无住、性空无所得的道理。
虽应不执著于外相,但也不能否定“相”的存在。即是肯定“性空”,也不否定“幻有”。“空”是破除一切名相执著所呈现的真实,并非人们所误解的虚无。“性空”,是说一切法都没有实在的自性,,故无相、无住,才能把握真谛。“幻有“,是凭借条件关系而暂时存在的现象,故在空的甚础上随缘生起一切法,这就是俗谛。所谓“肯定一切存在的存在,否定一切存在的自性”即是此意。如何把握真俗二谛的关系,《金刚经》是这样说的:“佛说般若,即非般若,是名般若。”即佛说的般若等佛法,是出于广度众生的目的而在文字层面的权且施设,并非实相般若本身,众生藉此文字般若入门,到彻底觉悟佛法时,则一切名相皆可舍弃。
在迈向解脱的过程,《金刚经》强调般若智慧是佛门修行解脱的最高智慧,“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承诺如果有人能够虔诚信受此部经,即使奉持其中四句偈等,又能够为他人宣说,必能“成就第一希有功德”、“果报不可思议”。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