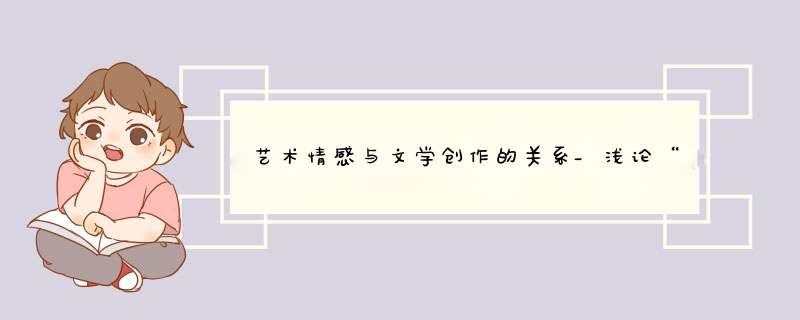
摘 要 “漫游”作为古代文人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为文学提供了重要的创作源泉,同时在主体创作情感和创作冲动的激发下,作家们自然而然烦地就会把漫游中的所见所闻诉诸笔端,形成了情感充沛,贴近自然,贴近生活的优秀作品。文学作品中的“江山之助”正体现了“漫游”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关键词 “漫游” 文学创作 关系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识码:A
1 何谓“漫游”
“漫”字含义很丰富,在这里指“随意”的意思。
《汉语大词典》:“漫”字第15条义项:随意;胡乱。唐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逰”和“游”本是两个词,两者的本意是不同的。
“逰”字:《诗·唐风·有杕之杜》:“彼君子兮,噬肯来游。”毛传:“游,观也。”①
《论语·里仁》:“子曰:父母在,不远逰,逰必有方。”②
可知“逰”字最初的含义为游览、云游。
“游”字:《诗·邶风·谷风》:“就其浅兮,泳之游之。”③
《诗·秦风·蒹葭》:“遡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毛传:“顺流而涉曰‘遡游’。”④
可知“游”字最初的含义是指在水中游行。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渭水一》:“(万石湾)渊深不测,实为灵异。先后漫游者,多罹其毙。”⑤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词的最早含义当是指在水里游泳,和今天的“漫游”有所区别。后来在汉字的演化过程中,渐渐的“逰”和“游”两个字通用了,意思也逐渐演化成我们今天所说的漫游。
“漫游”:《辞源》作随意遨游。《汉语大词典》作随意游玩。
本文所使用的“漫游”一词,不能是指泛化的随意游玩,还要着重与“旅游”概念区别开来。现代学者给“旅游”下了这样的定义:旅游是非定居者出于审美、游览、商务等非就业的目的而在异地旅行和逗留所引起的一切社会经济文化现象的总合。⑥这个概念当中所包含的“非定居者”、“非就业目的”、“异地旅行”这几个特征都是我们所说的“漫游”也同时具有的,但是现代旅游还包括商业旅游、公务旅游等等,本文的“漫游”把这种形式的旅游排除在外。
这里的“漫游”是指古代文人进行的随意的游历山川、探寻古迹、观览名胜的的旅游活动。可以把“漫游”看作为旅游的一类,但两者不是完全等同的。
漫游的重要特征在于随意性,如上所论,漫游指随意游玩。随意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为时间上的,一为空间上的。一般来讲,漫游的时间也比较长,比如王勃在蜀地所漫游的时间长达两年以上,李白杜甫等漫游的时间也都是以年计算的。这也是漫游和旅游的重要区别。再者,在空间上,漫游活动的地域十分广泛,古人漫游活动的地域遍及海内,无论是西北的边关广漠,还是江南的灵山秀水,都有所涉及。
古代文人在漫游过程中的副产品——文章和诗歌,必然与漫游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这也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2 “漫游”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览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⑦《王子安集注》卷十五:“野旷川明,风景挟江山之助。”欧阳修《和圣俞聚蚊》诗云:“江南美山水,水木正秋明。自古佳丽地,能助诗人情。”
刘勰的“江山之助”论,应该算作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命题。说的是造化自然对作家创作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作家创作情感和创作冲动的激发。他所举的例证,便是战国时期的爱国诗人屈原。这一说法,也得到后代文学家和文论家的赞同。历数古典文学中的重要作家,二谢、李杜、王孟,韩柳等等,无不是走遍天下,遍游四海,见闻广博的大学者。
文学作品中“江山之助”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自然美的新奇性:
山川的新奇性也就是异域事物的特殊性,清代赵翼《论诗》诗:“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这里强调的是天工造化的新奇性,审美对象的新鲜度。长期生活在一种环境之下,一旦置身于陌生环境之中,便会对主体造成巨大的冲击力,作者的审美感觉就会被很好地调动起来。
例如沈佺期《过蜀龙门》:“伏湍喣潜石,瀑水生轮风。流水无昼夜,喷薄龙门中。”作者看到龙门水石激荡,汹涌喷薄,作为长期在朝中为官的学士,他恐怕从来都没有见过此等雄壮的情景。这种视觉冲击力所带来的新鲜感立刻就起了作用,诗人把他的赞叹与惊奇诉诸笔端,写成诗歌,传与后世。杨炯《广溪峡》一诗写到:“乔林百丈偃,飞水千寻瀑。惊浪回高天,盘涡转深谷”。堰高百尺、瀑布千寻、惊涛拍岸、漩涡急转,使人读了以后感觉三峡奇险,历历在目,如临其境。作者的审美感受也来源于自然造化的新奇独特。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开篇写道:“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几句便形容内地人到了边塞,便感到景致也与中原差异的巨大,这种感受作家的加工,再经过审美的传达,就形成了“千树万树梨花开”这样的千古名句。
(2)自然美的丰富性:
在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各个地区都有自己丰富的山水美景和人文传统。从大的方面来讲,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是我们中华民族文明的两大发源地。两个地域从地理地貌、民风民俗、语言等等各个方面都很不相同,甚至说生活在这两个区域的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有区别。当然,这种区别对文学创作会起到一定的作用,试看《楚辞》所使用的语言和叙述方式、思维方式就可以知道,楚地文学创作和中原地区风格差异很大。从小的区域看,越中、江南、岭南、皖南、巴蜀、西北边塞、大漠等等,各地都拥有卓有特色的自然风景,所产生的文明成果更是丰富多彩。
例如江南和巴蜀同以山水著称于世,但不同的是巴蜀多山,江南多水;巴蜀以山水的奇险名世,而江南则以山水的灵秀著称。李白《陪族树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其五“淡扫明湖开玉镜,丹青画出是君山。”《江上望皖山》写到:“奇峰出奇云,秀木含秀气”。而在他的《蜀道难》中描绘的蜀地山水风情:“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暴流争喧豗”。从这些诗句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江南皖南的清灵俊秀和蜀地山水奇险雄浑之区别。
(3)主体情感的深挚性:
文学创作中反映了出游者的见闻和思想情绪。《诗经》反映先秦人民真实的生活和真情实感,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了不适意的事情,可以通过出游来使自己的忧愁郁闷发泄出来。这是人类的一种共同的行为方式,今天社会的人们在现实中失意时也会选择出游。很显然这出游并没有功利性的目的,仅仅就是去接近自然,感受造化所赋予人类的无穷无尽的山水美景。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可以获得一种超越现实的解放感。有了这些见闻和感受,作家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把它诉诸笔端,形成了情感充沛,贴近自然,贴近生活的优秀作品。
例如孟浩然的《宿建徳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旅途思归之情和江上朦胧凄寒之景融为一体,构成了清幽的意境。使得景色更加迷茫,思乡之情更加浓郁深挚。
中国古代文人把漫游看成是超凡脱俗、完善人格或是求知寻美,对社会生活所造成生理、心理失衡的一种暂时补偿手段而加以推崇和追求。他们遍游名山大川,并以此为题材写作出大量的为世瞩目的传世之作。漫游因此也成为古代文人的一种重要的生存方式,极大烦人推动了文学创作。
一、短歌行写作手法——引用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青青”二句原来是《诗经·郑风·子衿》中的话,原诗是写一个姑娘在思念她的爱人,其中第一章的四句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引用固然是直接比喻了对“贤才”的思念;但更重要的是他所省掉的两句话:“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曹操由于事实上不可能一个一个地去找那些“贤才”,所以他便用这种含蓄的方法来提醒他们:“就算我没有去找你们,你们为什么不主动来投奔我呢”由这一层含而不露的意思可以看出,他那“求才”的用心实在是太周到了,的确具有感人的力量。而这感人力量正体现了文艺创作的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结合。
二、短歌行写作手法——用典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出自《诗经·小雅·鹿鸣》篇。《鹿鸣》篇本是宴宾客的诗,意思是说只要你们到我这里来,我是一定会待以“嘉宾”之礼的,我们是能够欢快融洽地相处并合作的。
这里作者借用典故来再次表达自己欢迎贤才的心情。曹操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非常懂得人才的重要,认为“将贤则国安”,“天地间,人为贤”。为了完成统一大业,他曾亲自颁发《求贤令》、《举贤勿拘品行令》,实行“唯才是举”的政策。诗中一再表露的这种求贤若渴的心情与他的远大政治抱负是完全一致的。
三、短歌行写作手法——比兴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
贤才喻为明月,恰如其分地表达贤才难得而忧虑不绝的心情。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乌鹊南飞中以乌鹊比喻贤才尚在徘徊选择之意,流露诗人惟恐贤才不来归附的焦急心情。
《短歌行》赏析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若是英雄怎么能不懂寂寞” 这是流行歌曲里写给曹操的两句歌词,由罗贯中《三国演义》里的“奸雄”到京剧舞台上白脸“奸臣”再到这里的“英雄”,曹操可谓中国历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然而,在文学史上,曹操才华横溢,给后人留下很多上乘之作。上高中时,我就学习过他的《短歌行》,现在重读经典,心中似升腾起万丈豪情,一股英雄气让我有了鉴赏的冲动。
《短歌行》共128个字,“忧”字出现三次,成为贯穿全诗的诗眼,也是曹操英雄气概的最好体现,“忧思”中,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饱经忧患、真诚恳切的老者形象,尽显明主风度,全然没有了战场上硝烟的味道,也没有了军事里奸诈的阴霾,是最“真心”的表白,最“实意”的胸怀。
第一段两个“忧”,“忧思难忘。何以解忧”一前一后,再加上“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慨,再加上“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形象比喻,给全诗奠定了一种悲凉的气氛。然而这一悲凉,不是“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及时行乐的思想,不是“不知老之将至”的消极嗟叹,他对汉末“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现实担忧, 他又看到晨风吹干的露水,想到人生短暂,想到时间紧迫,他的“人生几何”的慨叹,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积极态度,这一“人生几何”之“忧”不能不说是渴望建功立业的老者发自心底的最良心的呐喊,怎能不对这种英雄之气油然而生敬意。
当时,各据一方的军阀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都在用尽一切办法网罗人才。曹操是一个草莽英雄,他没有显赫的身世,不象袁氏出生名门望族,也不像孙氏一家出身世家,更没有刘备的整日挂在嘴边的那么一点点的皇室血统,曹操虽然拥有诸多的谋士猛将,但为了完成统一天下的宏伟功业,他希望天下所有的人才都聚集在他这里。接下去以“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仿佛是随口吟咏《诗经》中的名句一般,如女子对待情人般痴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只因为你的缘故,让我渴念到如今,又进一步明誓自己心思。“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先起兴,“野鹿呦呦呦呦地叫,欢快地吃着野地里的艾蒿”再表心情,“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我的尊贵的客人啊,你要到来,我一定在席间弹起琴瑟,吹起笙乐欢迎你。这一“求贤若渴”之“忧”不能不说是渴望大展宏图的老者对待贤才的最深沉的期待,又怎能不被这种真诚渴求之心所打动。
第二段一个“忧”,“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而接下来的四句,同样用到了比喻的修辞。“明明如月,何时可掇”“明月”,比喻人才。“掇”,拾取,摘取。意思是:贤才有如天上的明月,我什么时候才能摘取呢“忧从中来,不可断绝。”由于求才不得,内心不禁产生忧愁,这种忧愁无法排解。想想此时曹操已53岁高龄,他率大军南下,列阵长江,欲一举荡平孙刘势力。看着皎月当空,以“欲上青天揽明月”之心求贤,然而贤才什么时候可以得到啊这一“贤才难得”之“忧”不能不说是一位明主对良臣的呼唤看看接下来的语句,你能想象出来诗人心情。“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此时,诗人将感情推向了高潮,一切进行了小说般虚构境界。穿过纵横交错的小路,枉驾来访。主客久别重逢,欢快畅谈,念念不忘往日的情谊。他想象着与贤才欢饮畅谈的情景,爱贤之情也油然而生。前四句,表明求贤不得的苦闷和忧思;后四句,描写贤才既得,喜不自胜,欢乐无穷的情景。诗人在求贤过程中既喜又忧的曲折心情,通过一唱三叹,吞吐往复的手法,以鲜明的形象表现出来了。不是英雄,就没有这种打江山的抱负,不是英雄,就没有这种求贤才的热情。
这种抱负,最后终于从“天下归心”中得以体会。“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最后四句诗,“匝”,周,圈。意思是:明月朗朗星星稀,乌鸦向南高高飞。绕树飞了多少圈,不知哪根树枝可栖息。这四句是说那些贤才在三国鼎立的局面下无所适从,不知道投靠到谁的门下。诗人希望他们不再犹豫,赶紧到自己这边来,以乌鹊择木而栖比喻贤才的徘徊歧路。这一“贤才前途”之“忧” 不能不说是一位明主对良臣的前途的担忧。
接着作者把这种担忧具体话,用心来证明,“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借用《管子•形解》中的话:“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士不厌学,故能成其圣。”直抒胸臆,表明自己广纳天下贤才的心愿和胸襟,当然也是希望人才多多益善。“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借用典故,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周公说他“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看那周公热切殷勤地接待贤才,使天下的人才都能心悦诚服地来归顺,自己愿意像周公那样,虚心接受天下贤人志士,希望贤才全部归己,帮助自己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宏图大愿。这几句画龙点睛,点明了全文的主旨,将文章推入高潮。这一“统一天下”之“忧”不能不说是一位明主渴望贤才的坦荡胸襟。到此,读者已被他的真诚与豪爽所折服。而这最后一“忧”才是笼罩全篇的忧思“人生苦短”之忧、“求贤不得”之忧皆由它而来。
由此,我们读懂了曹操。实现统一大志,是曹操毕生的奋斗目标。而眼前,赤壁之战前景未卜,作为一个深谋远虑、渴望建功立业的将领,他能不产生这样的忧思吗愿学大海纳百川,愿学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还不是为了实现心中的宏愿诗中,他向世人证明着自己的广博胸襟,有容乃大,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各位贤才,还犹豫什么呢他的忧患意识愈强,更看出他的只争朝夕,他的惜时如金,他的心情是多么地迫切,全诗的出这种大气磅礴之势,这种慷慨激昂的英雄之气,正是靠“忧”字传达。所以,曹操之“忧思”,洋溢着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激荡着一股慷慨激昂的感情,给人以鼓舞和力量。
论“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张捷德裔美国学者苏珊·朗格承继了西方人类文化哲学创始人德国学者恩斯特·卡西尔符号学的理论体系,在《情感与形式》一书中给艺术下了这样一个定义:"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在二十世纪中叶,朗格的符号论美学曾经风靡一时,并且占据了当时西方美学理论的统治地位,尽管到了六十、七十年代有所衰落,但迄今为止,在研究现代美学理论方面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甚至对于我们的艺术创造实践,也同样值得研究和借鉴。但在朗格的艺术符号论中,也掺杂着许多荒谬和错误的观点,有些甚至是唯心主义的,这些都需要我们加以认真地分析和思考。本文仅仅结合个人专业上的艺术体验,对朗格的艺术符号论作些粗略的例证,虽属自抒鄙见,也权作存商求正而已,至于朗格许多错误的观点不再作详细的讨论。为了更准确地把握苏珊·朗格的思想实质,我们必须了解其思想来源,那就是对卡西尔的符号论哲学的研究。卡西尔的著作被誉为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学术总结",他把康德"经验的规律性和逻辑结构"中的"静态"思想发展为"动态"思想,由此认为:一切人类的文化现象的精神活动,如寓言、神话、艺术和科学、都是在运用符号的方式来表达人类的种种经验,概念作用不过是符号的一种特殊的运用。符号同时连接了意识的流动,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文化指向,是社会文明的有机统一体。朗格接受了卡西尔的符号理论,她的主要贡献是对不同的符号加以确定,从而给符号创造活动和理解活动打下了更为清晰的印记。朗格的艺术理论是其整个符号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她以符号行为这样一个人类特有的基本活动为支点,详细地解析了艺术活动的各介方面;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对艺术现象这种无比绚丽多彩、无比神奇美妙的人类活动的展示,进一步揭开人类心灵的奥秘。但朗格又片面地认为:"艺术家的使命就是:提供并维持这种基本的幻象,使其明显地脱离周围的现实世界,并且明晰地表达出它的形式,直至使它准确无误地与情感和生命的形式相一致。"(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0页)又如"符号不是反应客观世界,而是构成客观世界"。这些都体现了朗格所存在的唯心思想,她颠倒了人类的精神活动与物质活动的真实关系,错误地认为人类实践活动的起点在于符号的制造、精神的内省和意识的抽象,并将符号的含义远远超离了一般语义学相对概念的狭窄范围,而进入了整个人类文化更为广泛的使用之中。当然,科学思维不同于艺术思维,形象思维也不同于抽象思维,在某一个前提下看问题,才能够使我们作出相对正确的判断。在艺术领域里,一件有意味的作品的诞生,往往是一个艺术家对自然表象真切心理体验的结果,其表现出来的语言图式都是艺术家情感外化的结果。在中国山水画的创作中,人们用自己对自然界变化无常的景致入微观照之后的理想化境界转化为笔下具体的艺术形象时,必需经历一个从感知到再现(理知)的文化转换过程。个体的情感活动转换为具体的艺术图式时,不仅仅融入了个人的语言、符号、形式,同时也投射出了画家独立的人格精神魅力。而写意性较强的水墨山水画创作,更需要画家具备一种"意象"性笔墨思维,即从自然界的表象中抽取最为本质的东西,在内容要素无法掩盖其心里情感理念时,被最纯粹地表现在画面上,从而使其作品成为超离物象的一般存在价值,所以,艺术是高于生活的。朗格认为"意象"是 "即从实际的、因果的秩序中抽取出来,仅为感知而存在的某种东西,是艺术家的创造"(《情感与形式》第57页第二部分:符号的创造,第八章:表象)。实际上"意象"是一种理智和情感的复合物,它既入理又含情。写意山水画的意象表现形式,在追求形神兼备的同时,也注重寓意抒情,求象外之意,给人以画外的精神联想,而并非单纯的客观描摹。它旨在通过精炼●永的笔墨语言和符号样式来表达艺术家对客观事物的主观意念和思想,抒发个性,寄托襟怀。而"意象妙得"又是建立在画家对自然景物的真实而又概括地观察和把握之后,才得以因景生意,因意立法,而赋予灵活多变的笔墨形式和符号语言。这种 "独得于象外"而超于自然的以意命笔、借笔达意的手法,是艺术创作中最为重要的人文取向。在这里,自然界的繁杂景象己被去掉枝叶,只剩下那些己让心象迹化了的精神本质。"语言能使我们认识到周围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周围事物同我们自身的关系,而艺术则使我们认识到主观现实、情感和情绪。"使我们能够真实地把握到生命运动和情感的产生、起伏和消失的全过程。"(苏珊·朗格《艺术问题》第66页)语言绝非人类唯一的表达工具,既然语言不能完成情感的表达,人类的符号能力,就必然创造出服务于情感表现的另一种符号,因此,艺术应运而生。宋人郭若虚曾说"画乃心印",它"发之于情思,契之于绢堵"。自然山川的千变万化,给画家带来不同的情感体验,这种 "有感而发"所建立起来的艺术形象就成了一种情感符号,笔墨仅仅是寄托和传达情感的样式。唐人符载在《观张员外画松石序》中认为张躁的创作是"物在灵府,不在耳目,故得于心,应于手。孤姿绝状,触毫而出,气交冲漠,与神为徒"。所谓"在灵府"的"物",意味着"得于心"的"物",是画家融于内心世界的自然美,通过毫端而宣泄出来,只有这样的"物",才是 "应于"画家的"手"的。与此同时,张躁并不排斥客观的"物" 或自然美,相反地他以频繁地接触自然来丰富自己的"心源",以生成主观的对象来进行造化。"单有形式而无情感,或单有情感而无形式,这对于艺术创作来说都是不可想象的,所谓"默与神会",是指由心物契合来达到物为心用,情景交融的目的。王维《辋川图》中的那些山、谷。云、水的种种情景,乃是借以传达其"出尘"之意的,也就是说,王维不仅仅歌颂辋川之美,更重要的还在于用笔墨语言写出辋川之美来托出他所自命“一尘不染”的心境。这种以意寄物,落墨写心的意象表现手法,是个人情感理想化后的形式语言的再现。在此,笔墨也就成了其中一者充当另一者的符号意义。"符号性的形式,符号的功能和符号的意味,全部溶为一种经验,即溶成一种对美的知觉和对意味的直觉。"(苏珊·朗格《艺术问题》第32页)在艺术创作中显而易见包含着较为突出的情感因素,情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艺术的生命,而这种情感上的"心境"是靠与此相吻合的"语境"来传递的,这也就印证了符号活动的实质含义。所以,艺术符号与其表现的情感内容是不能分开的,只有把人类语言思维活动与艺术表现活动统一起来,再通过直观符号形式和推论符号形式,才能解释艺术符号的抽象意义。但艺术绝对不能等同于一个符号体系,符号只是反应客观世界的一种社会意识活动,而绝不是构成客观世界的本能行为。也可以说艺术符号是构成情感再现的必要因素和途径。南朝宋炳在他的《画山水序》中这样说道:"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昧象。至于山水,质有而趋灵。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余)画象布色,构兹云岭。身所盘桓,目所绸缪,以形写形,以色貌色也。披图幽对,坐究四荒,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己;神之所畅,孰有先焉?"这段话反映了山水画家具有一定的主观思想感情,由此出发去接触自然,探索与这主观愿望相契合的自然美而加以描绘;通过这种借物写心的过程,追求画中天人合一的境界,从而达到"畅神"的目的。其"万物与我为一"的道家思想中包含了人类精神自我完满的祟高理想,而营造这样的"大境界",其前提也是需要经过人类情感的"内营"之后,才能实现笔下由符号语言构筑起的"丘堑",而艺术符号本身是单一和苍白的,只有注入画家的情感之后,才能获取符号的生命意义。所谓"胸中有丘堑,笔底见云山"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没有自然表象的存在,就不会有画家情感冲动后的意象表现。所以,情感是人以客观现实的一种心理反映形式,是人类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自己需要所作出的一种心理反应。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朗格通过艺术即人类情感符号创造的理论依据,给艺术领域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无不给人以很大的启发。但艺术的定义并非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艺术的真理只有在艺术家各自的艺术创造实践中才能得以证实。
理智,是通过对周围环境或事物全面而深刻的观察,运用缜密的思维,对可能发生的事件和发展的结果以及应该采取的措施进行逻辑思维扩展。
理智通常具有王者风范,来自于知识的积累,标志着一种成熟。象温暖的阳光一样,催生着个体不断从浅表的感性认知,升华到理性经验,从而形成一定的行为准则。处事态度,活动规范。
理智的经验和智慧,更多地来自于曾经地感情冲动受到挫折和惩罚。
然而,过于理智的生活既枯燥又乏味,活得累,无任何乐趣可言,因为理智多攻入心计,将自己装入过去生活的狭窄的经验中。享受不到感情带给人知觉体验的激励和鲜活。
感情是主观的,理智是客观的;感情的自然属性如潮水,如女人因女人多感性;理智的自然属性如高山,象男子因男子多理性。如果说感情年轻的,那么理智便象一个成熟的长者;如果说感情如鲜花,理智则如树长青;如果感情的结果是一个个催人泪下的故事,那么理智的过程便是一部部法理经典。
感情越深厚,理智越成熟。这便是有朋友提到的,理智是感情的升华。爱得越深,越会为对方考虑,行为和言谈越理智。试问,一个薄情的人,怎么可能有成熟的理智呢?而真正成熟的人,又怎么可能不通情达理呢?感情流于表象,所以激昂;理智沉淀深沉,所以睿智。二者穿插交互,才能完美协调我们的精神世界。
我反对将感情与理智绝对对立的说法,那会将我们的认识引向极端。女人偏重感情,并非与理智无缘。女人,往往把感情看得高于一切,过分的理智带给女人的伤害要比爱护多得多。许多时候,女人宁舍理智不舍感情。这一选择使得她们要求生活更富梦想、浪漫和激情。所以说,真正丰富的精神生活需要理智,更需要感情!
所谓:“情之所倾,心之所向”如果完全的理智,我们就无法看到生活中美的亮点。梁祝,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故事,也不会为后人所传唱,所讴歌。
然而,假如没有理智这个堤防,情感的洪水就会泛滥。历史上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显然是理智与感情的较量和搏斗。在法律面前理智是占上风的。当然,事实上,许多法律的设定,又多是符合正当情感需求的。
理智是理性的,感情是感性的,理性认识是感性认识的基础,没有感性认识何来理性思维?可见,感情与理智互相作用,又相互促进。既矛盾又统一。感情是理智的基础,理智是为了不让感情轻易泛滥成灾。但是如果没有感情,那还谈什么理智与否呢?
所以合情合理,才会情理交融,才有最完美的境界。感性强的人唯美,易受伤害;理性强的人有点冷漠似乎没有人情味,世故。就象男人和女人,阳和阴,虽然矛盾,但永远不可分割,只有在认知的基础上不断平衡和协和感情和理智,让二者相互达到统一,才会有相对完美的人生。
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后人对其的评价无非主要就是情感评价还有思想评价。但就情感评价来论述是毫无意义的,就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单独论述是绝对片面的。所以本人将从两方面来论述一些问题。并且首先对“评价”这个问题做一些展开。
文学作为一种样式,一种载体,自然承载着作者本身的思想还有情感,否则文学便失去了其本身的意义。然而,作者本身的思想还有情感却难以摆脱当时所处时代社会之中,故而我们在分析文学作品里作者的情感还有思想的时候就不得不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进行综合思考。需要注意的是,不论是创造文学作品的作者还是后人在评价作品的思想情感时,都不可能脱离其所处历史的环境。“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是指创造者创造出了如此之多层面的文学意象,更多的是指后人在评价鉴赏时会结合当时不同历史环境,以及个人在历史社会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来审视文学作品。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文学人物,文学作品都能在不同人的思想下反映出来不同,每个人的情感评价都有其正确性可存在性,但是往往我们看到接受的评价却是一些名家大家之学说,并产生了一种崇拜盲信感,这已经是把文学给精英化了,非可取之道也。
一般来说,自己对于自己作品的评价乃是作品本身最为原始的评价,但是大部分时间我们看到的都是后人对作品的评价,这样就需要讨论一些问题了。不论是思想还是情感,都不可避免的带上了时代以及自己所处地位身份的烙印。后人对文学的情感评价,往往有不同于作者创作本意的情况出现,显然的,在一些精英知识分子在对文学作品某些评价中往往甚至怀着某种政治目的,这点是不能够忽视的。
我们都很熟悉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如果按照作者本意来说,完全是一个臣子忠于皇帝,收复河山的宣言书。从岳飞一生来看,他所做的与他的词里所表述的可谓完全一致,终生以收复山河迎回二帝作为宗旨。在今天的宋词选本里,后人对这首词的评价是以高度的肯定作为主要基调的,即高度肯定其爱国主义精神,其人也被公认为民族英雄。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最近十年间,对于他的民族英雄的称号以及对这首词的评价就越来越多异议,具体表现为更加突出这首词的忠君性以及对民族英雄称号的否定。
许多人不明就里的就加入到对抗阵营之中,却很少有人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大家可以想想持反对态度的到底是什么人,具体地说他们有着怎样的政治倾向。文学从来就不是独立的,文学观点的不同根本原因乃是社会地位思维方式不同,也就是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这些把岳飞的词里面的忠君思想拿出来大肆攻击的人,他们的政治倾向大多是右派的意识形态的。右派政治理念便是支持资本主义,宣言民主自由普世价值的一群人,那么他们在讨论中国历史时无时无刻不在猛烈的抨击,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普世价值民主根本不知为何物,是与他们的政见所抵触的,所以右派们反对这首词也就十分之有他们自己的理由了。
在近代,文学作品与政治经济方面已经大大挂钩,在文学情感评价上不时的体现评价者的政治观点,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更有左翼文学团体与京派产生的文学上的论争。这都说明了,在阶级矛盾尖锐,意识形态逐步产生分歧的社会,对于文学作品或者文学作品情感评价更多的夹杂了评价者的意识形态与某些政治目的。这是不得不忽略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古人云“文以载道”。这里的“道”,固然指的是道理,思想。那么古人亦有云:“诗言志”,“志”这便是注重于情感方面。但是两者并不是分割没有联系的。有些文学作品中承载的“道”也正是作者所欲表达出来的“志”。比如杜甫的一些诗句表达出来的思想,一些道理,也就正是他忧国忧民志向的体现,反之亦然。所以在情感评价的时候也不可能不对其文学作品里所承载的“道”进行阐述。比如说在读辛弃疾的《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会从情感评价转移到“道”的讲述中来。所以两者并不是冲突的,而是交融的。
文学的情感评价作为文学评价里的重要一环,其本身自然不需要过多的阐述。这个命题本身就有其引导性,使得学生在论述只会论述情感评价本身而忽视了其中更为重要的问题。每个人在每段时期的情感有所不同,情感评价作为后人对作者文学作品的评价就不可能完全一致,那么其中为什么会不同,如何不同,以及某些不同后面隐藏的某种动机,这才是我们需要深思的。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