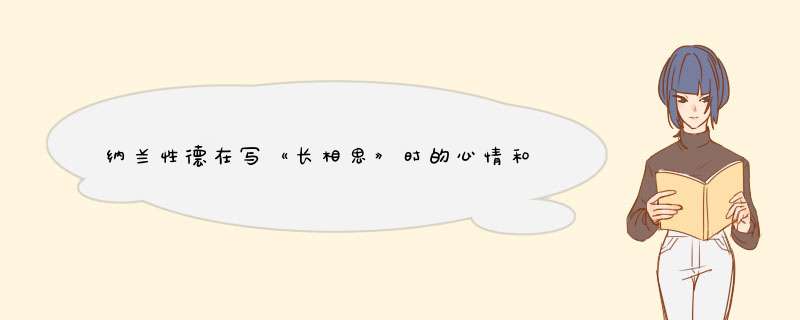
这是一首描写边塞军旅途中思乡寄情的佳作。
天涯羁旅最易引起共鸣的是那“山一程,水一程”的身漂异乡、梦回家园的意境,信手拈来不显雕琢,难怪王国维评价“容若词自然真切”。
这首词更可贵的是缠绵而不颓废,柔情之中露出男儿镇守边塞的慷慨报国之志。一句“夜深千帐灯”不愧“千古壮观”。纳兰性德是朱邸红楼中的贵公子,才华艳发,多愁善感,气质上受汉文士影响很深。虽曾有积极用世的抱负,却更向往温馨自在、吟咏风雅的生活。侍卫职司单调拘束、劳顿奔波,远不合他的情志,使他雄心销尽,失去了“立功”、“立德”的兴趣。上层政治党争倾轧的污浊内幕,也使他厌畏思退。诗人禀性和生活处境相矛盾,是他憔悴忧伤、哀苦无端的悲剧性格形成的根本原因。长期随驾出巡还破坏了他的家庭生活。职业苦闷和离愁别恨交织,再加上爱妻亡故的打击,使他深陷苦海。他怨天不成,尤人不成,便把无尽凄苦倾诉于笔端,凝聚为哀感顽艳的词章。投殳久戍之苦,伤离感逝之痛,以及难以指名的怅闷是纳兰词的基本内容。纳兰性德以特出的艺术功力弥补了题材狭窄的不足。他的词全以一个“真”字胜,情真景真,“纯任性灵,纤尘不染”(况周颐《蕙风词话》)。写情真挚浓烈,写景逼真传神,并以高超的白描手段出之,看去不加粉饰,却如天生丽质,无不鲜明真切,摇曳动人。王国维曾说:“纳兰性德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遗愿,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人间词话》)所谓“未染汉人风气”,就是指他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意境天成,没有因袭模拟、堆垛典故的毛病。清初词家如陈维崧、朱彝尊等,不脱古人羁绊,以化用前人旧境为能事,总有名家词句梗搁在眼前,所以他们的词,即使是最好的作品,也难免隐现着前贤名作的影子,终不能超越古人;他们并非不想创出新的意象,思想习惯和才力束缚限制了他们,使他们寻觅终身而不得一字。纳兰性德却凭敏锐的观察、新鲜的感会和高度的语言概括力,独造新境,表现出非凡的艺术创造才能。他善于用自己的心眼,直视眼前之景,直抒心中之情,把人人得见又人人所难言的情景真切准确地传达出来,创出未经人道的崭新意境。他的“夜深千帐灯”、“冰合大河流”等名句足以和“明月照积雪”、“长河落日圆”并称为千古壮观。他写愁情常似不经意的随口掷发,却不使人嫌其直率浅露。他把原属个人的哀怨融扩为带有普遍性的人性抒发,从而引发读者的共鸣,具有了独特的美学个性和强烈的感染力。三百年来,尤其近百年来,他是拥有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清代词家。他也是中国最杰出的古代词人之一。
用“粗服乱头”来形容李煜的词最恰当不过。 每每细读李煜的词作,不无觉得是在翻阅着一个帝王的成长与血泪史。从最初的《浣溪沙》(红日已高三丈透)到《浪淘沙》(帘外雨潺潺),从一个江南大国的皇子,南唐属国的皇帝,沦为破国亡家的降臣,四十二年间,李煜仿佛是做了一个繁华但又凄凉的梦。在这一场梦中,虽没有身为帝王应有的魄力,但为后人留下了为数不多却堪称是词坛不朽的词作,国后的词作尤其是其亡国后的词作。李煜的词作在词坛上的影响力,不亚于唐朝杜甫。王国维《人间词话》评价到:“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晚清王鹏运亦在《半塘老人遗稿》中所说:“盖间气所钟,以谓词中之帝,当之无愧色矣。”
李煜的亡国后的词作,从字里行间不无透露着真率的情绪与血泪的倾述。因为真率,所以他的倾述毫无做作,因而即使是了了数语,亦能让人忘却他是一个亡国帝王,只记得他是一个词中的苦情者。在词作中,李煜是如何将性情中的真率融入不幸的命运遭际中,使得词的情感深度加深,词境与众不同?本文将对李煜亡国后词作进行探究分析。
一、巧用白描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中说:“王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飞卿,严妆也;端己,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用“粗服乱头”来形容李煜的词最恰当不过。细读李煜的词,不难发现,他极少用典,而多用平直的白描手法。白描手法丝毫没有减少李煜词作的风彩,反而更显出他的“神秀”(王国维),因而使得他的真率和血泪自然流露。
《临江仙》(樱桃落尽春归去)就是体现其白描手法的很好例子。
樱桃落尽春归去,蝶翻金粉双飞。子规啼月小楼西。画帘珠箔,惆怅卷金泥。
门巷寂寥人去后,望残烟草低迷。炉香闲袅凤凰儿,空持罗带,回首恨依依
整首词共写了16种意象,通过对这16种意象的描写串联,将一副帝王与繁华盛景作最后告别的迷烟袅袅、欲语无言的别离图形象地描写出来。全词不着一字华丽修辞,更无重文叠字,一切都是娓娓道来,全无人工砌凿痕迹。这就是李煜的过人之处。词中“樱桃”、“金粉”、“凤凰儿”等意象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李煜再熟悉不过的,因而运用起来如鱼得水。
意象的串联,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帝王对过往酒醉金迷生活的不舍,对从此成为阶下囚的恐慌。回首恨依依,不是恨人,只是恨从此太平不在。在自己命运如直坠地狱的时刻,李煜似乎没太多的顾忌,只是一如既往地坦率地表达自己的心绪,沿袭了自己一贯的写词作风,真率之至。真率之余,却又不可忽视其中的化不开的愁去惨淡。
如果说《临江仙》是意象的白描,那《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就是其感情的白描。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他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几曾识干戈”,试问世上有几个帝王敢如此呼出这样一句辩解?只有李煜,只有他才敢如此。面对国破家亡,自己的无力回天,归为一句“几曾识干戈”。我们即痛恨他的无能,未能深识亡国的本质,但又只能报以一个叹息。 “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这两句李煜的性情写真,后人多为不予赞同,认为这不是一个帝王该有的风貌。他生来本是词人,而不应是帝王。而又因他的真率,让我们在叹息之余多了一份感同身受的怜惜。
二、比喻——化虚为实
运用比喻手法,往往能够使诗中可意会不可言传之情、之物能够形象生动,跃然纸上。愁,本是人的一种情感,无形无影,但是在李煜的词中,我们却能真切地感知。这得益于李煜在词中所运用的比喻手法。
《相见欢》中,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离愁是什么,恐怕纵是千言万语也无法说清。于是李煜就干脆把这离愁在心里的纠结比喻成某样可感的事物,剪不断,理还乱,成了他感情的真实表达。而这愁到底是比喻成了什么,李煜并没有明说。因为已是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对于一个曾经的帝王,有什么能比成为阶下囚,被独自幽禁在清秋深院中更耻辱。平常、朴素而又富于表现力的语言,表现了深刻而真挚的思想感情,创造了一个和谐完美的艺术整体,让我们看到了的一个帝王的无奈的凄苦。字里行间,没有丝毫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之感,也没有这个必要。
再看被大多数人认作是李煜的绝笔之作《虞美人》中对愁的刻画。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去国之痛,失国之悲,亡国之恨,这一切都融入一江春水中。李清照《武陵春》中把愁寄予在“只恐双溪舴艋,载不动许多愁”。相比之下,李煜的愁来得更加猛然,因为是一江的春水波涛滚滚向东流去,情感的表达更加强烈。而且,一江春水向东流,又有让人有过往一去不复返,此恨绵绵无绝期之感。神来几笔,却有语浅情深的艺术效果,是因为他敢于真率地披露自己的真实感受。身为阶下囚,在宋皇帝的监视下,他仍敢呤出这样旷古所无的对故国之思的愁绪,这完全是赤子之心使然。
王国维《人间词话》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柔妆来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大家之作,李煜是也。
因为真,所以情深;因为真,所以后人每读,仍是痛心不已。
三、虚实并存
诗词中运用虚实并存手法,可以使得诗词更有层次感,内容更有厚实感。对于一个亡国帝王,李煜的生活前后有着前后的截然不同。由于这样的特殊的命运遭际,所以在李煜生命的后期,他经常处于一种追忆过往与悲痛现实的时虚时实的精神状态。因此,从他的词作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常运用虚实并存手法去表达自己的真切情感。
《子夜歌》被历代选家多选作是最能代表李煜词白描风格的词作。但我同时认为,它也能够很好地体现了李煜虚实并存手法。
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
高楼谁与上,长记秋晴望。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
上下阙各有一“梦”字,但内涵各异。上阙的“梦”是思念故国而所作的重游故国之梦,下阙的“梦”是面对现实的落差,内心似乎一时还未反应过来,还未能接受。唐圭璋《唐宋词简释》所言:上下两“梦”字亦幻,上言梦似真,下言真似梦也。在这里,不是虚景与实景的交换,而是词人内心情感的虚实交换,现实与梦境的交换。叶嘉莹评价这首词说,亡国哀思,词明白如话,不加修饰,本色天然,读来却使人感到意味深长,令人黯然销魂。确实,三千繁华瞬间消逝,让这个曾经的帝王一时间恍如梦中。受制于人,仍能坦陈自己梦中的所思,梦醒后的不确定。因为这种坦陈,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只有李煜,也只有李煜,才使得我们在现实与梦的交叠并存中,能深切感受到李煜的苦楚,不能不为这真实情感、天成语言发出衷心的爱悦。
《浪淘沙》同样也是能够体现虚实并存手法的佳作。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饷贪欢。
独自莫凭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梦里昨日欢乐重现,梦醒独对无限江山,却是主人已易,自然是含思凄婉。梦境与现实的对比,不免突显今日身陷囚牢的浩淼憾恨。有了这种对比,“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这种感慨来得非常自然。现实的不可逆,内心的彻底绝望,清陈廷焯说,一声恸歌,如闻哀猿,呜咽缠绵,满纸血泪。“天上人间”,这明显是家国仇恨情感的倾泻,气象之宏大,古时少之又少。
李煜之所以成为千古词帝,不是因为他的身世所影响,而是他的真率情感全部投注在词作中所致。作为一个亡国帝王,像李煜,不能痛痛快快地了结一身,反而还要过着备受凌辱阶下囚生活的帝王,是何其的痛不欲生。可是他不算是一个真正的帝王,因此面对耻辱,他所选择的抗争不是帝王式的,而是文人式的(叶嘉莹),这与他的生活性情有关。屈辱地苟活一生,用血与泪去喂养成那只字只句的词作,最终在性情的彻底解放中——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完成自我的救赎。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