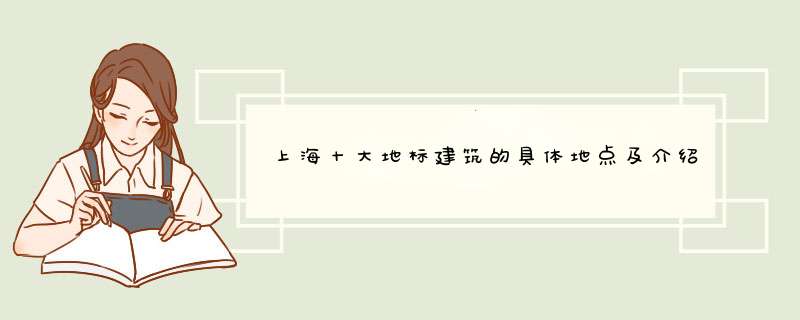
1、金茂大厦
地点:位于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与著名的外滩风景区隔江相望。
简介:上海金茂大厦占地面积24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9万平方米,其中主楼88层,高度4205米,约有20万平方米,建筑外观属塔型建筑。裙房共6层32万平方米,地下3层57万平方米,外体由铝合金管制成的格子包层。
金茂大厦1-2层为门厅大堂;3-50层是层高4米,净高27米的大空间无柱办公区;51-52层为机电设备层;53-87层为酒店;88层为观光大厅,建筑面积1520平方米。
2、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
地点: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坐落于黄浦江畔浦东陆家嘴嘴尖上,与外滩的万国建筑博览群隔江相望。
简介:该建筑于1991年7月兴建,1995年5月投入使用,承担上海6套无线电视发射业务,地区覆盖半径80公里。
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是国家首批AAAAA级旅游景区。塔内有太空舱、旋转餐厅、上海城市历史发展陈列馆等景观和设施,1995年被列入上海十大新景观之一。
3、上海展览中心
地点:位于上海市中心静安区。
简介:上海展览中心承办了许多国内外重要的展览会,也担当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和政府工作会议举办场所的重要角色。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
2016年9月,上海展览中心入选“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
4、上海图书馆
地点:位于上海市徐汇区淮海中。
简介:是上海市综合性研究型公共图书馆和行业情报中心,也是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上海市分中心、文化部公共文化研究基地,是首批国家重点古籍保护单位。
上海图书馆创立于1952年,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成立于1958年,1995年上海图书馆与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合并,1996年12月上海图书馆新馆正式对外开放。
截至2015年底,上海图书馆建筑面积127万平方米,拥有各类阅览室36个,设有24个机构部门,在编职工751人。图书馆藏有中外文献5500余万册,其中中文古籍线装书约170万余册,善本25万种17万册,属国家一、二级藏品2256种13526册。
5、上海国际会议中心
地点: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位于浦东滨江大道,与外滩建筑群隔江相望。
简介:她与东方明珠、金茂大厦一起组成陆家嘴地区的一道著名的景观。
上海国际会议中心总建筑面积达11万平方米,拥有现代化的会议场馆:有4300平方米的多功能厅和3600平方米的新闻中心各1个,可容纳50-800人的会议厅三十余个;豪华宾馆客房,有总统套房、商务套房、标准间近270套;还有高级餐饮设施、舒适的休闲场所和600余个车位。
1999年9月,20世纪最后一次“财富”世界论坛就是在这里举行的。
6、上海博物馆:
地点:上海博物馆创建于1952年,原址在南京西路325号旧跑马总会,1959年10月迁入河南南路16号中汇大楼,现位于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的南侧黄浦区人民大道201号。
简介:1993年8月,上海博物馆新馆开工建设,1996年10月12日全面建成开放。上海博物馆建筑总面积39200平方米,占地面积11万平方米,地下二层,地上五层,高295米,总投资57亿元。新馆是方体基座与圆形出挑相结合的建筑造型,具有中国“天圆地方”的寓意。馆名“上海博物馆”系建国后上海第一任市长陈毅所书。
上海博物馆设有十一个专馆,三个展览厅,陈列面积2,800平方米。馆藏文物近百万件,其中精品文物12万件,其中尤其是以青铜器、陶瓷器、书法、绘画为特色。收藏了来自宝鸡及河南、湖南等地的青铜器,有文物界“半壁江山”之誉,是一座大型的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
7、上海大剧院
地点:位于上海市黄浦区人民广场,南靠上海博物馆,西临黄陂北路,北望人民公园和上海历史博物馆,东毗位于人民广场中轴线北端的上海市人民政府。
简介:上海大剧院占地面积约为21000平方米,建筑总面积70000平方米,建筑总高度40米,共有10层,是上海的文化标志性建筑物,上演过歌剧、音乐剧、芭蕾、交响乐、室内乐、话剧、戏曲等各类大型演出和综艺晚会。
2000-2017年,上海大剧院连续九届获得“上海市文明单位”称号;2004年,上海大剧院被命名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2006年,上海大剧院获得“中国最佳剧院经营金奖”;2008年,上海大剧院通过ISO9001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8、上海新锦江大酒店
地点:新锦江大酒店坐落于上海著名的淮海路商业中心,毗邻新天地、人民广场,高架地铁直达。
简介:582间(套)客房,客房配置酒店数字视讯系统,集平板电视、高清、电脑、高速上网。
酒店拥有7个风味餐厅和酒吧,提供各色中西日式料理。另有9个多功能和会议厅,其中大宴会厅用上海市花“白玉兰”命名,可同时容纳400人。
酒店还设有购物中心、商务中心、票务中心及室内健身设施。
9、上海体育场
地点:位于上海西南部要脉,是上海地铁唯一的环线4号线和内环高架路交汇处。
简介:上海体育场是目前我国规模较大、设施较为先进的大型室外体育场(我国规模最大、设施最为先进的大型室外体育场是北京奥运会的主体育场——国家体育场)和上海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建筑面积达17万平方米。
1998年,上海体育场被评为"上海市最佳体育建筑";1999年,又评为"新中国50周年上海十大经典建筑金奖之一"。地址在上海市徐汇区天钥桥路666号。
10、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地点:浦东国际机场位于上海浦东长江入海口南岸的滨海地带。
简介: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于1999年建成,1999年9月16日一期工程建成通航,2005年3月17日第二跑道正式启用,2008年3月26日第二航站楼及第三跑道正式通航启用,2015年3月28日第四跑道正式启用。
根据2017年11月官网信息显示,浦东机场有两座航站楼和三个货运区,总面积824万平方米,有218个机位,其中135个客机位。拥有跑道四条,分别为3800米2条、3400米1条、4000米1条。 截至2016年底,浦东机场已吸引了37家航空公司在此运营全货机业务,全货机通航31个国家、112个通航点,每周全货机起降近1000架次。
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木心?
木心是谁
2015-11-17 源自网络
本名孙璞,1927年生于桐乡乌镇。毕业于上海美专。曾任杭州绘画研究社社长,上海工艺美术中心总设计师。1982年定居纽约。2011年12月21日逝世于故乡乌镇,享年84岁。他的画作被大英博物馆收藏,其散文被收入《美国文学史教程》。一批当代著名的画家、文学家深受其艺术影响。
木心去世后,他的一首小诗《从前慢》被广泛流传:“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 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 人家就懂”
昨天,乌镇木心美术馆落成。它由建筑大师贝聿铭弟子——纽约OLI事务所冈本博、林兵设计督造,陈丹青出任馆长。
从照片上看,第一眼,它十分和敬清寂,仿佛有点儿安藤忠雄;大体量采用木质地,是为了呼应木心的“木”字吗?
据说,木心先生临终前,看着美术馆设计图,喃喃说道:“风啊、水啊,一顶桥。”
木心纪念馆的馆长 亲自将三幅陈丹青的题字带到杭州
木心遗作里有几百幅绘画作品,从未在国内展出,在美术馆里将作为常设展览。美术馆还将推出木心老师林风眠以及对木心产生影响的德国哲学家尼采等三个展览。
乌镇木心美术馆,像广袤长夜中的一颗新星,给木心迷的情感和视线,提供了一个可期许可投注的方向。
而在杭州,已经有一颗星,呼应它,以明亮以沉默——木心咖啡馆,创办者是李加文,在杭州文艺界,没有人不知道他的凡人咖啡馆,一个文艺中青年的文化地标。
作为资深木心迷,李加文参加了乌镇木心美术馆的落成典礼。他感慨:“做到了极致又很节制,有着恰到好处的美感。木心先生会喜爱的。”
2009年,李加文第一次读到木心的书,《哥伦比亚的倒影》,“那一篇《上海赋》,把上海写活了。”他读得哑口无言,极受震动,唯有一个心悦诚服的“好”字。从此他开始收集各种关于木心的书籍,2013年,还开过两周的木心书店,只卖木心的书。他说,不知道读什么书的时候,拿起的总是木心。
做一间“木心咖啡馆”,是李加文心心念念已久的事。2014年5月,乌镇木心纪念馆开幕,他以朝圣的心情前往,还穿了新衬衣和新鞋。见到了陈丹青,他斗胆上前求字,还真求成了——两周后,木心纪念馆的馆长王瑾专程将三幅字送到杭州,请他挑一幅,剩下的两幅,带回交还陈丹青,亲自销毁。
在乌镇与杭州 读他的书和他读过的书
和乌镇木心美术馆相比,杭州的木心咖啡馆,具有“处江湖之远”的有趣和惬意,每一把椅子都不一样。老式吊扇,尼采和福楼拜的早期印刷品,都由ebay订购,纽约发货,山水迢迢,构成了一间超越商业意义的“木心的书房”。
在这里,从中午11点到凌晨2点,读一本书,与两三好友小聚,这应该就是木心和陈丹青在纽约的交往方式。
木心曾写道:“从中国出发,向世界流亡,千山万水,天涯海角,一直流亡到祖国、故乡。”在这间咖啡馆,你能看见木心的纽约和乌镇。
为了完成这个多年念想,李加文花费了一番心血。先是选址,木心年轻时在杭州逗留过的地方,孤山、平湖秋月、老吴山、老浙大、南山路、武林门……都去考察过。最后落址环城北路市政府大楼对面的这一处老式房屋。
乌镇与杭州,这两颗关于木心的星星,交相辉映,像不像失联多年的音符,联袂成出尘的乐章?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木心?
木心一生如镜,人人得以观照自身,并看到超越自身局限的各种丰富与可能。
热爱者们穷尽人力,打捞碎片,以各种真实的物质的怀念方式,让我们尽可能地看到一个完整丰富的文学家与画家。我们进入乌镇木心美术馆,进入杭州木心咖啡馆,读他的书以及他读过的书,看他的画和他赞赏的画,并不是要摹仿他,而是获得一种力量,一种超越现实的、精神世界的力量。
“情感地理”(Emotional Geographies)[1]是都市空间研究的重要概念之一,它是情感表现与地理空间关系的具体化。上世纪20-30年代,上海都市亚文化的情感—空间—身体结构呈现出“杂糅感”和“抵抗欲”等包容性特质。同时,传统文化中的“游民心态”也参与到了地理身份的构建,并且借助“群落生态”的亲缘聚合效应在亚文化中重构了社会关系。这种激进的人文地理学孕育出了集体主义均分式的空间观,进而形成对“五四”传统中指向个体解放的存在主义空间观的压制。这对当下都市亚文化的研究和规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上世纪20-30年代上海文化的大繁荣很大程度得益于亚文化的大勃兴。随着一大批“薄海民”(小资产阶级流浪文人)在上海聚集,一个激进的都市青年亚文化社群初具雏形。
这些“浪子”基本生活在租界亭子间中,并且抱有左倾的观念。经过毛泽东两次讲话的界定与重申,“亭子间来的人”一度成为上海文人代名词[2]。这一时期,上海亚文化弥漫着颓废、抵抗、悲哀、亢进、屈从、团结的复杂情调,这既来源于历史的观念、作家的灵感,同样来源于亭子间和租界的空间创造。在批判人文地理学视野下,这个“他者”被视为外在于“城市共同体”,但作为城市的一种要素却不可或缺。如曼海姆所说,社会学研究中知识分子的共性在于往往“不是把精力集中于环境的积极的潜在性上,而是成了潜在于环境中的诱惑性的俘虏”[3]。在错综复杂的理想、主义、人事、 口号 之争的背后,基于“情感—空间—身体—社会”差异结构的分析,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超越琐碎,理解都市亚文化潜在的人文地理脉络。
一、杂糅感:情感与空间
在都市人文地理学中,租界和亭子间在某种意义上都代表一种“定位政治学”无法看清的领域,具有包容性和混杂特质。都市亚文化是“大都市精神”的体现。现代大都市居民具有在情感上亲近亚文化的冲动,他们往往以隶属于某一亚文化空间为荣,以期获得一种新的文化、性格和身份。
在不同的环境、居所有着不同的历史想象,使得后来的研究者可以看见各种情感地理的社会结构。虽然被家人几番催促北上投考北平女师大,谢冰莹却割舍不了上海这个“文人的摇篮”,宁可躲在亭子间喝自来水,“但不受别人限制的生活是自由的、痛快的,那里的一切是活跃的,进步的,她爱这所‘社会大学’”[4]。作为城市边缘和灶披间的上层建筑,上世纪20-40年代的上海亭子间是一个多方杂处的市民社会的底层。穷学生、失业者、妓女、小贩、佣工借此生息,这里也是滋生青年作家、流浪艺人的域外飞地。在同一空间中,不仅通俗文学和左翼的边缘知识分子日渐成长,即使作为现代主义文学先锋的新感觉派在大革命失败之后也翻译出版过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而且还“转向”写过一些普罗小说。
作为早期的带有全球化色彩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文化飞地,上海都市文化带有鲜明的“杂糅”色彩。贾植芳先生说:“要定义海派文化或海派文学确实是个难题。”[5]我们不必讳言这里是西方人的一种文化构想物,西方世界用一种“异托邦”的幻象来陪衬和确证自身的优越,并且维护自己的利益为侵略扩张服务。但在部分知识人的心中,这恰恰是“必要的邪恶”,边缘文人于其间可以实践知识的挑战者的角色。1850年代以后,上海租界便成为商人、政客、激进知识分子和普通市民聚居的城中城。无论“云里雾里的第三种作家”“跳舞场里的前进作家”,还是“亭子间里的无名作家”都有自己的存在理由。这个控制松散的空间,却充满了活力和能量。徐志摩在《新月》的发刊词中,将当时的上海“思想市场”分为感伤派、颓废派、唯美派、攻击派、偏激派、*秽派、热狂派、标语派、主义派等等十三个派别。至于鲁迅的杂文更是拉拉杂杂,报刊新闻电报信手拈来、随意拼贴,更加从形式上衬托了租界文化的混杂色彩。因此,当1927年南京政府设立上海特别市为收回租界做准备的时候,大部分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并不响应,他们并没有因对租界外国势力不满而迁入特别市。
先有现代都市“矛盾特色”,方有早期的都市公共空间形态,这激发了“小群”与“大群”之间的能量转换。1930年2月16日,夏衍、鲁迅以及一批亭子间文人在公共租界的公啡咖啡馆秘密集会。在公共租界越界筑路区域窦乐安路233号(今多伦路201弄2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随后便宣告成立。租界为亭子间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宽松自由的语境。当然租界也不完全是一个安全地带,但是正因为它始终处于危险的边缘,这个反抗的社会更需一个乌托邦理想照耀他们前行。如小派正之所见,社团已经是“日常生活的社会依托” [6]。沈从文也痛感,如果底层文人不参与社团,门路便会越来越窄,感情自然越来越坏,终有一天会在“都市病”中一蹶不振。租界和亭子间作为亚文化飞地的重要特点就是,这种居住区的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他们愿意临近亲密关系群体而聚居的偏好。底层阶级在这里聚合,以左联为代表的租界社团和亭子间文人群体因此具有了天然的“邻里关系”。这是带有革命文化亲缘性的亚文化团体的标记。
要言之,都市公共空间的包容性为多样化的亚文化群体提供寄居的家园。虽然在“新月”的号召下,精英文化人依然保持着骄傲的姿态。但是在左联的周围,新兴的亚文化社群因为空间的“亲缘性”正逐渐聚合,这里才是孕育着希望的“另一度空间”。
二、抵抗欲:情感与身体
寓于亚文化空间中的底层文人生活呈现杂糅性特质—一种“色—魔—幻”的杂糅。这体现出现代都市亚文化中身体解放与革命激情互为表里的关系。亭子间是一种开放的空间的边缘,一个意义深远的边锋。这一亚文化空间需要诉诸于一种挑战性的身体姿态完成自我的建构。
早期的“享乐主义青年”的形象,例如蒋光慈《冲出云围的月亮》的王曼英、《追求》中的章秋柳,醉心于到跳舞场、到影戏院、到旅馆、到酒楼,甚至于想到地狱里,到血泊中感觉一点生存的意义,追寻时时刻刻热烈的痛快。并且章秋柳的“要求新奇刺激的瘾是一天一天地大起来了”,这一点和海派的性爱作家以及刘呐鸥、穆时英的新感觉异曲同工。性的刺激和身体的迷向是新生的都市诱惑的最好表达。沈从文在《论海派》中讥讽海派文人既关心“现代人的悲哀”,也关心“十月革命”,也经常谈到小说的内容与技巧的问题,谈到没落的苦闷,以至于还大谈嘉宝的“沙嗓子”“眼珠子”和“子宫病”,追究“沙嗓子的生理原因”,以及她的“性欲的过分亢进”。可见,亭子间青年作家选择文学道路更多的出于革命“热情”,而不是对文学的“热爱”。这一激进的人文地理风行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青年亲近政治多采取“恋爱”的态度,所以很容易成为“社会主义追求者或信仰者”。成仿吾们对斗争哲学的“机械的地运用”,也不仅仅因为他们脱离国情,还与他们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浪子”的劣根性有关。鲁迅先生批之为中了“才子加流氓的毒”。至于京派文人更是以“流氓和妓女的文化”形容海派激进的抵抗欲。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