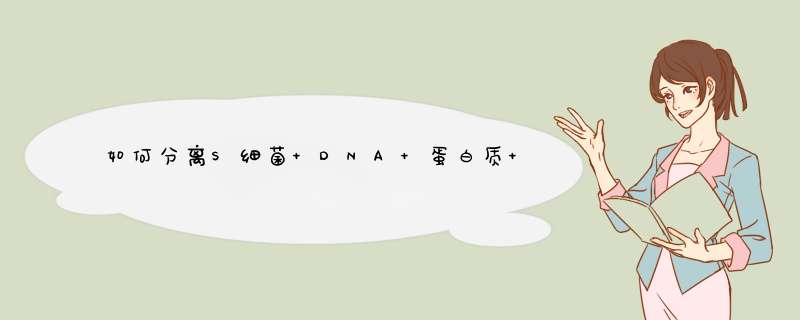
1926年肺炎球菌被命名时,学名是Diplococcus pneumonia(肺炎双球菌),但1974年,它的学名被改为Streptococcus pneumoniae(肺炎链球菌)。(双球菌的细胞沿一个平面分裂,新个体成对排列。链球菌的细胞沿一个平面分裂,新个体不但可保持成对的样子,并可连成链状。一定种的全部细胞,不一定都按照一种方式排列,占优势的排列方式才是重要的。)在抗菌素发明之前,它一直是人类的主要杀手,使人患肺炎而死亡。它对小鼠的危害更严重,往小鼠体内注入一个肺炎球菌,就能导致小鼠因败血症而死亡。
肺炎链球菌有具多糖荚膜的致病菌S型菌(Smooth,因菌落外观光滑)和非致病菌R型菌(Rough,因菌落外观粗糙)。荚膜有不同的构造,根据免疫反应可以分成I型、II型、III型等,细菌是否具有产生荚膜的能力,以及产生荚膜的类型,为“遗传特性”。S型菌经过突变可以产生R突变体,反之亦然,但是突变总是涉及丢失或获得产生一个特定类型荚膜的能力(如II-SII-R;而不是III-SII-R)。
1928年,在英国卫生部任职的医生格里菲斯(Frederick Griffith, 1879-1941)对肺炎球菌的致病情况做了研究。当他把热处理的S细菌(III-S型)与活的R细菌(II-R型)的混合物注射到小鼠中时,尽管这两种细菌本身都不是致死的,但是小鼠还是死亡了!更重要的是,从注射了这类混合物而死亡的小鼠身上分离的到S型菌,而且是与加热杀死的S细菌相同的S型(III-S),因此这些S细菌不可能是通过这些特定的R细菌突变而来的。
格里菲斯将这种引起转化(transform)的未知物质称为转化因子(transforming principle),他不知道转化因子的本质,但错误地猜想它可能是一种涉及到荚膜合成的蛋白质,或是一些作为细菌荚膜前体的物质。
对此实验,不同的科学家分别做出三种解释:
1 R型菌以某种方式使加热杀死的S型菌“复活”;
2 (新拉马克主义理论)III-S品系死菌刺激小鼠体内产生免疫物质,后者刺激II-R品系突变成了III-S品系(直至1958年,仍有教科书把肺炎球菌转化实验当作新拉马克主义的定向诱导的例子);
3 III-S型菌的遗传物质进入II-R型菌,合成了III-S型菌的荚膜。
20世纪30年代的遗传学家主要在研究果蝇(Drosophila melanogaster),而对细菌的遗传不感兴趣。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是免疫化学家。
1931年,道森(Martin Henry Dawson)和西亚(Richard HP Sia)成功地在体外进行了转化实验:只在培养皿中使II-R型菌转化成III-S型菌,不需要以小鼠为媒介。——这否认了新拉马克主义的因小鼠体内免疫物质诱导的解释。
1933年,阿洛维(Lionel J Alloway)将II-R型菌和III-S型菌的无细胞提取液(所有完整细胞、细胞碎片、荚膜分子都通过离心和过滤从提取物中去掉)混合,培养皿上仍长出了III-S型菌。——这否认了R型菌以某种方式使加热杀死的S型菌“复活”。
因此,结论是S型菌细胞提取物中含有转化因子,而它的化学本质还是未知的。
(格里菲斯是低调而又务实的人。唯一一次参加学术会议是1936年的微生物大会,还是被他的朋友硬拉去的。他在会上敷衍地做了一个报告。他的报告和他1928年著名的肺炎球菌转化实验毫不相关,因为当时他自己都没意识到他转化的实验的重要性。1941年,在一次纳粹德国对伦敦的空袭中,格里菲斯和同事不幸牺牲在实验室中。)
(1913年,艾弗里的母亲不行死于肺炎,36岁的性格内向的艾弗里从此立志称为一名细菌学家,研究肺炎。)
1935年至1944年,经历了10年的不断研究,美国洛克菲勒学院的三位免疫化学家艾弗里(Oswald Theodore Avery, 18771021-195522)、麦克劳德(Colin Munro MacLeod, 1909128— 1972211)、麦卡提(Maclyn McCarty 191179–200512)证明了DNA是肺炎球菌的遗传物质(The evidence presented supports the belief that a nucleic acid of thedesoxy-ribose type is the fundamental unit of the transforming principle of Pneumococcus Type III)。
艾弗里的实验其实并不是如高中教材所说的那样,“将提纯的DNA、蛋白质和荚膜多糖等物质分别加入到培养了R型细菌的培养基中,结果发现:只有加入DNA,R型细菌才能够转化为S型细菌”。
艾弗里等人的工作实际是:不断地去除S型细菌中各种成分,然后得到纯化的“转化因子”;接着对纯化的“转化因子”进行鉴定,确认它就是DNA。并不是像人教版教材中说的那样:对S型细菌中的各种成分进行提纯,再用提纯的各种成分去做转化实验测试。
转化因子中DNA纯度越高,转化效率越高;当用DNA酶处理转化因子后,则没有转化功能。但即使用蛋白质酶处理转换因子,转化效率也不降低。
1944年,当艾弗里等人提取的“最纯”的DNA中,仍有1%的蛋白质杂质。到1949年,Rollin Hotchkiss提纯的DNA中仅含002%的氨基酸杂质(后来的研究表明,这些氨基酸是核酸降解后的核苷酸经生化反应生成的,不是之前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仍具有转化能力。 Rollin Hotchkiss还证实了和荚膜无关的细菌性状也能转化。
事实上,艾弗里的实验已经严谨地证明了DNA是遗传物质,只是受当时科学界的环境所限,他的结果受到指责,不被接受。
当时的反对者主要有一下三种观点:
1 受“四核苷酸”假说的局限,认为四种碱基的含量是相同的,DNA是四核苷酸的简单的多聚体,就如淀粉是葡萄糖的多聚体那样,因此DNA不太可能是含有复杂遗传信息的遗传物质;
2 认为转化实验中DNA并未能提得很纯,还有蛋白质杂志,可能正是这些少量的特殊蛋白在起转化作用。当时人们难以忘记二十年前著名的生化学家维尔施泰特(Richard Martin Willsttter, 1872813-194283)由于不能将酶提纯而错误宣称酶不是蛋白的沉痛教训;
3 认为即使转化因子确实是DNA,但也可能DNA只是对荚膜形成起着直接的化学效应,而不是充当遗传信息的载体。
1952年,赫尔希(Alfred Day Hershey, 1908124–1997522)和蔡斯(Martha Cowles Chase, 192788–2003827)做了T2噬菌体侵染埃希氏大肠菌(简称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实验。
在进行实验之前,他们已知噬菌体的侵染开始于噬菌体对细菌的附着,结束于被侵染细菌的裂解和子代噬菌体的释放,中间发生的事情尚不明确。但噬菌体的遗传物质,无论它是什么,都必须进入细菌中。
T2噬菌体由核酸和蛋白质衣壳组成。核酸是唯一含磷元素的,蛋白质衣壳是唯一含硫元素的。他们先分别用含P32的磷酸盐培养基和含S35的硫酸盐培养基培养大肠杆菌,接着用T2噬菌体侵染大肠杆菌,这样就分别得到了带P32标记核酸和S35标记蛋白质衣壳的噬菌体。
用带标记的噬菌体分别侵染普通的大肠杆菌,一段时间后离心,再分别检测离心后的上清和沉淀中的放射性。
该实验又被称为搅拌机实验(Blender Experiment),因为搅拌离心是实验中很关键的一步。通过离心能使噬菌体的进入细菌细胞的部分和未进入细胞的部分强行分开。若不搅拌或很长时间时候才搅拌,T2噬菌体就完成复制,裂解大肠杆菌而释放了。这样就没有“沉淀”和“上清”的区别了,检测放射性也失去了意义。
当时发现75%的S35标记在上清中,25%在沉淀中。(若干年后表明,25%仍然与细菌相关联的S35,主要由与噬菌体相关的尾部碎片构成,这些碎片与细菌表面黏附过于紧密,而不能通过搅拌去掉。)
当时发现85%的P32仍然与搅拌后沉淀中的细菌细菌相关联,只有15%的P32位于上清中。上清中放射性的大约1/3,被认为是搅拌时细菌的破裂造成的。(若干年后表明,剩下的2/3是附着在细菌上有缺陷的噬菌体颗粒造成的,这些噬菌体颗粒不能注射它们的DNA。)
更重要的是,P32标记噬菌体产生的子代噬菌体中,检测到了P32;而S35标记噬菌体产生的子代噬菌体中,(按实验论文的原文)放射性不到1%。
由于并不是组成蛋白质的所有氨基酸都含硫(硫元素只能标记甲硫氨酸和半胱氨酸),因此该实验无法证实是否有不含硫而未被标记的蛋白质进入细胞并起到遗传功能。所以从严谨和精确程度上,它不如艾弗里的实验。
(该实验启发了病毒学家的思路,提出了病毒的繁殖过程,其遗传物质(DNA)和非遗传物质(蛋白质)可以先分开,后组合。)
但由于当时的科学界已经普遍接受了蛋白质不是遗传物质,并对DNA研究火热,加上噬菌体小组在分子生物学领域的巨大影响力,使得赫尔希-蔡斯实验被广泛接受,甚至作为DNA是遗传物质的最后证明。而艾弗里的实验则常常被人们故意忽略,以致某些教科书甚至把赫尔希-蔡斯的实验作为证明DNA是遗传物质的唯一实验。后来在艾弗里的同事的强烈主张下,才后加入的对艾弗里实验的介绍。
后来的Phi X 174噬菌体实验,将病毒分离成DNA和蛋白质衣壳两部分,仅有病毒的DNA就具有感染能力,而病毒的蛋白质衣壳不具备感染能力。这才最终证实了DNA是遗传物质。
1969年,赫尔希和德尔布吕克(Max Ludwig Henning Delbrück,190694–198139)、卢瑞亚(Salvador Edward Luria, 1912813–199126)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后两者也是噬菌体小组的成员,他们于1943年做了经典的“彷徨试验”,又称变量试验(fluctuation test)或波动试验,该实验证明大肠杆菌对噬菌体的抗性是在接触相应的噬菌体前,在细胞分裂过程中随机地自发地产生的,不是由噬菌体诱导出来的,噬菌体仅起着淘汰原始的未突变的敏感菌和甄别抗性突变型的作用。因此某一性状的突变与环境因素是不相对应的,这进一步肯定了达尔文学说,否定了新拉马克主义主义。
1926年肺炎球菌被命名时,学名是Diplococcus pneumonia(肺炎双球菌),但1974年,它的学名被改为Streptococcus pneumoniae(肺炎链球菌)。(双球菌的细胞沿一个平面分裂,新个体成对排列。链球菌的细胞沿一个平面分裂,新个体不但可保持成对的样子,并可连成链状。一定种的全部细胞,不一定都按照一种方式排列,占优势的排列方式才是重要的。)在抗菌素发明之前,它一直是人类的主要杀手,使人患肺炎而死亡。它对小鼠的危害更严重,往小鼠体内注入一个肺炎球菌,就能导致小鼠因败血症而死亡。
肺炎链球菌有具多糖荚膜的致病菌S型菌(Smooth,因菌落外观光滑)和非致病菌R型菌(Rough,因菌落外观粗糙)。荚膜有不同的构造,根据免疫反应可以分成I型、II型、III型等,细菌是否具有产生荚膜的能力,以及产生荚膜的类型,为“遗传特性”。S型菌经过突变可以产生R突变体,反之亦然,但是突变总是涉及丢失或获得产生一个特定类型荚膜的能力(如II-S�6�2II-R;而不是III-S�6�2II-R)。
1928年,在英国卫生部任职的医生格里菲斯(Frederick Griffith, 1879-1941)对肺炎球菌的致病情况做了研究。当他把热处理的S细菌(III-S型)与活的R细菌(II-R型)的混合物注射到小鼠中时,尽管这两种细菌本身都不是致死的,但是小鼠还是死亡了!更重要的是,从注射了这类混合物而死亡的小鼠身上分离的到S型菌,而且是与加热杀死的S细菌相同的S型(III-S),因此这些S细菌不可能是通过这些特定的R细菌突变而来的。格里菲斯将这种引起转化(transform)的未知物质称为转化因子(transforming principle),他不知道转化因子的本质,但错误地猜想它可能是一种涉及到荚膜合成的蛋白质,或是一些作为细菌荚膜前体的物质。
对此实验,不同的科学家分别做出三种解释:
1 R型菌以某种方式使加热杀死的S型菌“复活”;
2 (新拉马克主义理论)III-S品系死菌刺激小鼠体内产生免疫物质,后者刺激II-R品系突变成了III-S品系(直至1958年,仍有教科书把肺炎球菌转化实验当作新拉马克主义的定向诱导的例子);
3 III-S型菌的遗传物质进入II-R型菌,合成了III-S型菌的荚膜。
20世纪30年代的遗传学家主要在研究果蝇(Drosophila melanogaster),而对细菌的遗传不感兴趣。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是免疫化学家。
1931年,道森(Martin Henry Dawson)和西亚(Richard HP Sia)成功地在体外进行了转化实验:只在培养皿中使II-R型菌转化成III-S型菌,不需要以小鼠为媒介。——这否认了新拉马克主义的因小鼠体内免疫物质诱导的解释。
1933年,阿洛维(Lionel J Alloway)将II-R型菌和III-S型菌的无细胞提取液(所有完整细胞、细胞碎片、荚膜分子都通过离心和过滤从提取物中去掉)混合,培养皿上仍长出了III-S型菌。——这否认了R型菌以某种方式使加热杀死的S型菌“复活”。
因此,结论是S型菌细胞提取物中含有转化因子,而它的化学本质还是未知的。
(格里菲斯是低调而又务实的人。唯一一次参加学术会议是1936年的微生物大会,还是被他的朋友硬拉去的。他在会上敷衍地做了一个报告。他的报告和他1928年著名的肺炎球菌转化实验毫不相关,因为当时他自己都没意识到他转化的实验的重要性。1941年,在一次纳粹德国对伦敦的空袭中,格里菲斯和同事不幸牺牲在实验室中。) (1913年,艾弗里的母亲不行死于肺炎,36岁的性格内向的艾弗里从此立志称为一名细菌学家,研究肺炎。)
1935年至1944年,经历了10年的不断研究,美国洛克菲勒学院的三位免疫化学家艾弗里(Oswald Theodore Avery, 18771021-195522)、麦克劳德(Colin Munro MacLeod, 1909128— 1972211)、麦卡提(Maclyn McCarty 191179–200512)证明了DNA是肺炎球菌的遗传物质(The evidence presented supports the belief that a nucleic acid of thedesoxy-ribose type is the fundamental unit of the transforming principle of Pneumococcus Type III)。
艾弗里的实验其实并不是如高中教材所说的那样,“将提纯的DNA、蛋白质和荚膜多糖等物质分别加入到培养了R型细菌的培养基中,结果发现:只有加入DNA,R型细菌才能够转化为S型细菌”。
艾弗里等人的工作实际是:不断地去除S型细菌中各种成分,然后得到纯化的“转化因子”;接着对纯化的“转化因子”进行鉴定,确认它就是DNA。并不是像人教版教材中说的那样:对S型细菌中的各种成分进行提纯,再用提纯的各种成分去做转化实验测试。
转化因子中DNA纯度越高,转化效率越高;当用DNA酶处理转化因子后,则没有转化功能。但即使用蛋白质酶处理转换因子,转化效率也不降低。
1944年,当艾弗里等人提取的“最纯”的DNA中,仍有1%的蛋白质杂质。到1949年,Rollin Hotchkiss提纯的DNA中仅含002%的氨基酸杂质(后来的研究表明,这些氨基酸是核酸降解后的核苷酸经生化反应生成的,不是之前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仍具有转化能力。 Rollin Hotchkiss还证实了和荚膜无关的细菌性状也能转化。
事实上,艾弗里的实验已经严谨地证明了DNA是遗传物质,只是受当时科学界的环境所限,他的结果受到指责,不被接受。
当时的反对者主要有一下三种观点:
1 受“四核苷酸”假说的局限,认为四种碱基的含量是相同的,DNA是四核苷酸的简单的多聚体,就如淀粉是葡萄糖的多聚体那样,因此DNA不太可能是含有复杂遗传信息的遗传物质;
2 认为转化实验中DNA并未能提得很纯,还有蛋白质杂志,可能正是这些少量的特殊蛋白在起转化作用。当时人们难以忘记二十年前著名的生化学家维尔施泰特(Richard Martin Willst�0�1tter, 1872813-194283)由于不能将酶提纯而错误宣称酶不是蛋白的沉痛教训;
3 认为即使转化因子确实是DNA,但也可能DNA只是对荚膜形成起着直接的化学效应,而不是充当遗传信息的载体。
1952年,赫尔希(Alfred Day Hershey, 1908124–1997522)和蔡斯(Martha Cowles Chase, 192788–2003827)做了T2噬菌体侵染埃希氏大肠菌(简称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实验。
在进行实验之前,他们已知噬菌体的侵染开始于噬菌体对细菌的附着,结束于被侵染细菌的裂解和子代噬菌体的释放,中间发生的事情尚不明确。但噬菌体的遗传物质,无论它是什么,都必须进入细菌中。
T2噬菌体由核酸和蛋白质衣壳组成。核酸是唯一含磷元素的,蛋白质衣壳是唯一含硫元素的。他们先分别用含P32的磷酸盐培养基和含S35的硫酸盐培养基培养大肠杆菌,接着用T2噬菌体侵染大肠杆菌,这样就分别得到了带P32标记核酸和S35标记蛋白质衣壳的噬菌体。
用带标记的噬菌体分别侵染普通的大肠杆菌,一段时间后离心,再分别检测离心后的上清和沉淀中的放射性。
该实验又被称为搅拌机实验(Blender Experiment),因为搅拌离心是实验中很关键的一步。通过离心能使噬菌体的进入细菌细胞的部分和未进入细胞的部分强行分开。若不搅拌或很长时间时候才搅拌,T2噬菌体就完成复制,裂解大肠杆菌而释放了。这样就没有“沉淀”和“上清”的区别了,检测放射性也失去了意义。
当时发现75%的S35标记在上清中,25%在沉淀中。(若干年后表明,25%仍然与细菌相关联的S35,主要由与噬菌体相关的尾部碎片构成,这些碎片与细菌表面黏附过于紧密,而不能通过搅拌去掉。)
当时发现85%的P32仍然与搅拌后沉淀中的细菌细菌相关联,只有15%的P32位于上清中。上清中放射性的大约1/3,被认为是搅拌时细菌的破裂造成的。(若干年后表明,剩下的2/3是附着在细菌上有缺陷的噬菌体颗粒造成的,这些噬菌体颗粒不能注射它们的DNA。)
更重要的是,P32标记噬菌体产生的子代噬菌体中,检测到了P32;而S35标记噬菌体产生的子代噬菌体中,(按实验论文的原文)放射性不到1%。
由于并不是组成蛋白质的所有氨基酸都含硫(硫元素只能标记甲硫氨酸和半胱氨酸),因此该实验无法证实是否有不含硫而未被标记的蛋白质进入细胞并起到遗传功能。所以从严谨和精确程度上,它不如艾弗里的实验。
(该实验启发了病毒学家的思路,提出了病毒的繁殖过程,其遗传物质(DNA)和非遗传物质(蛋白质)可以先分开,后组合。)
但由于当时的科学界已经普遍接受了蛋白质不是遗传物质,并对DNA研究火热,加上噬菌体小组在分子生物学领域的巨大影响力,使得赫尔希-蔡斯实验被广泛接受,甚至作为DNA是遗传物质的最后证明。而艾弗里的实验则常常被人们故意忽略,以致某些教科书甚至把赫尔希-蔡斯的实验作为证明DNA是遗传物质的唯一实验。后来在艾弗里的同事的强烈主张下,才后加入的对艾弗里实验的介绍。
后来的Phi X 174噬菌体实验,将病毒分离成DNA和蛋白质衣壳两部分,仅有病毒的DNA就具有感染能力,而病毒的蛋白质衣壳不具备感染能力。这才最终证实了DNA是遗传物质。
1969年,赫尔希和德尔布吕克(Max Ludwig Henning Delbrück,190694–198139)、卢瑞亚(Salvador Edward Luria, 1912813–199126)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后两者也是噬菌体小组的成员,他们于1943年做了经典的“彷徨试验”,又称变量试验(fluctuation test)或波动试验,该实验证明大肠杆菌对噬菌体的抗性是在接触相应的噬菌体前,在细胞分裂过程中随机地自发地产生的,不是由噬菌体诱导出来的,噬菌体仅起着淘汰原始的未突变的敏感菌和甄别抗性突变型的作用。因此某一性状的突变与环境因素是不相对应的,这进一步肯定了达尔文学说,否定了新拉马克主义主义。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