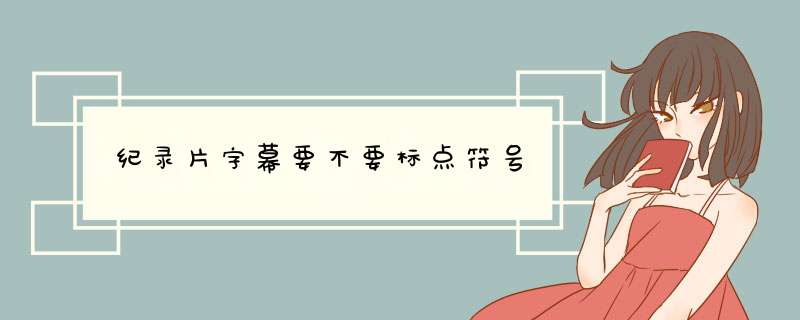
不要标点符号。
纪录片字幕如果加标点符号的话,是会影响观众的阅读速度,这是因为标点符号是需要通过大脑反应的,大脑以确定其语气,进而重新分析全句语气。
但是在纪录片的拍摄和配音的时候,已经完成了这部分工作,如果再加标点符号的话,不仅显得多余,而且纪录片的镜头切换较快时会影响观众对纪录片内容的欣赏。
此外加标点符号还会误导观众,标点符号不仅代表字幕组对纪录片剧情的认知,而且还会限制观众自己的理解,更有甚者把糊加一气,反而会误导观众。因此在纪录片的播放过程中,字幕是不需要加标点符号的。
问题一:电视节目名、栏目名用什么标点符号? 引号
问题二:电视节目名称用什么标点符号 书名号。
问题三:节目名用什么标点符号 用《》 符号
问题四:电视节目符号是什么 呵呵。。。。
sd 标清
hd 高清
fll 全画幅
1080 1080i 你说的是这个吧
问题五:什么是电视的传播符号 传播符号是传播活动里必不可少的因素。电视传播符号是电视文化传播得以实现的基础。一般包括语言符号系统和非语言符号系统。依靠这些传播符号,电视文化才得以广泛传播,其作用才得以发挥,价值才得以实现、放大与增值。
电视语言符号系统主要包括声音符号和文字符号。声音符号包括解说词、主持人或记者镜前的讲述(谈话)等播音语言和节目中的现场同期声语言。声音符号已成为当今电视传播信息的重要符号甚至是主要符号。文字符号有屏幕符号(标题、同期声字幕、插入字幕、整屏文字字幕)、画内文俯等。
电视非语言符号系统包括图像符号和音响符号。图像符号不仅包括实地拍摄的画面,还包括影片、照片、录像、文献资料、绘画、美工制作的图表、示意图、模型、动画以及各种特技镜头等等。扩而大之,演播室设计、栏目题花、主持人和播音员的形象等等,也都属于图像符号。音响符号是指现场音响和音乐符号。音响是利用现场音响和音乐传达出的一组非语言符号。音响指的是现实生活中人们能听到的各种各样的现场声音。音乐符号的使用往往体现了一种电视节目创作者的主观表达意识,并以此折射一种情感,传递某种心灵语言和观念形态。
问题六:电视节目动物世界写作文应该用什么符号 电视节目―动物世界 我最喜欢的电视栏目是CCTV3每晚7:00播出的《动物世界》。这个栏目,让我认识了许多小动物,知道动物的生活习性,还增长知识、开阔眼界。
记得有一集,雏燕无力地扑打着羽毛未全的柔嫩的翅膀。只见一只白底黑条的花猫猛得蹿出,像闪电一般冲向小燕子。只听“刷”的一声,一只羽翼丰满、肌肉健全的母燕横挡在小燕子面前。大花猫急速向前的身躯,像急刹车一样猛地止住了。这只母燕真是勇气可嘉,在这样的庞然大物面前竟然毫无惧色。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杀气,明摆着一场猫燕大战就要开始,可是双方都纹丝不动,似乎在等待时机。突然,猫弓起后背,猫毛都被憋得竖了起来,它猛地跃起。母燕反应也极快,它腾空而起。顿时燕羽猫毛参杂在一起,纷纷扬扬飘了一地。花猫突然改变对象,朝雏燕扑去。在这危急的时刻,那只母燕不顾一切地冲向花猫,它要用生命保护自己的孩子,锐利的鸟嘴啄着花猫的后背,花猫残叫一声,落荒而逃。这个画面看得我胆战心惊。
《动物世界》这个栏目演绎着动物之间的精彩故事,我不仅学到了许多动物知识,欣赏到了大自然天然的美,更让我明白了动物世界和人类世界一样,充满机遇,充满竞争,也充满了爱。
问题七:电视节目的节目类型 大致的可分为新闻类节目(正规的),财经类节目(相关咨讯及评述),体育类节目(赛事转播及体育消息报道),文化娱乐类节目(包括影视,综艺,娱乐咨讯等),生活类节目(包括生活见闻,百姓平日关心的一些内容),谈话类节目,军事类节目,教育类节目,科技类节目,少儿节目,老年节目,广告节目等等。由于电视节目的发展,许多节目的类型复杂多样,包含了多种类型。电视新闻资讯节目定义:以现代电子技术为传播手段,以声音、画面为传播符号,对公众关注的最新事实信息进行报道的电视节目类型。电视谈话节目定义:以电视为传播媒介,通过话语形式,营造屏幕内外面对面人际传播的“场”氛围,以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双渠道来传递信息,整合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电视节目类型。电视文艺节目定义:以文学、艺术和文艺演出作为创作原始素材和基本构成元素,在保留原有艺术形式的基础上,运用电视视听语言进行二度创作,具有较高欣赏艺术性和审美价值的电视节目类型。电视娱乐节目定义:以电视为传播媒介,利用综合性的表达手段,将多种娱乐性的元素组合在某一种形式中,在某一时段强化电视的娱乐功能,单纯地使观众身心放松、精神愉悦的电视节目类型。电视纪录片定义:非虚构的、审美的(非功利的),以建构人和人类生存状态的影像历史为目的的电视节目类型电视剧。定义:灵活运用文字、戏剧、**等多种表现手法,广泛深入历史、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交织使用电子传播、家庭传播、人际传播的各种手段,在当下社会影响最大、收视份额最足的电视节目类型。电视**定义:按照**的艺术规范和电视的叙事规律来制作,通过电视媒介播放的电视节目类型。电视特别节目定义:各级电视机构打破常规播出之栏目、时间、长度等诸多限制,充分投入人、财、物资源,以各类特别事件作为内容载体,以特别策划、精心编排为形式特征,能够收获巨大社会影响和优质经济效应的特殊的电视节目类型。如果按中央电视台的频道分类来划分电视节目,则有新闻综合类 如朝闻天下、第一时间、法治在线、环球视线、每周质量报告、新闻1+1、新闻30分等科技教育;如百家讲坛、探索・发现、人与自然、科技博览等影视娱乐;如非常6+1、第10放映室、开心辞典、九州大戏台等经济生活;如购物街、经济与法、每日农经等。体育赛事外语参考:中央电视台节目分类
问题八:为上么电视节目上的字幕都没有标点符号? 亲身体验,兴冲冲的给视频加了标点,结果发现缺点多多,又逐句给删掉了,当然有许多愿意,但分析一下我的感受1影响伐读速度,标点需要大脑反映,以确定语气,进而重新分析全句语气语境,**画面和配音已经完成了这部分工作,再加不但多余,而且在子木屋,镜头切换较快时反而影响关照欣赏。2误导观众,字母租的标点只代表字幕组对剧情的认知,主管加上标点,反而限制观众自己的理解,更有甚者,糊加一气,反而误导观众。且有些语气语境,即是反问,又是感叹,加哪个?都加怪异混乱让人不知所云,所以干脆都不加,反而内容丰富了。3杂乱累赘,有的剧情紧凑,情节 的剧情,如果要加,几乎通篇下来每句后面都是叹号,看着都累心,而且句句叹号,让人腻歪。所以,影视作品,一般不要加标点,顶多加些书名号,引号这种也就够了。不是可有可无,没有必要这么简单,而是除非必要,一半千万别加!
山水画的创作过程无时无刻不体现着画家们的个人心理与情感,将个人情感与客观物象联结,达到情与景合一的境界,这个创作过程是观察、感受、表达的过程,这个阶段的情感融入,是创作不可缺少的部分。通过山水画创作中的情感表达分析,对于创作实践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情感的融入,对于改变绘画僵化模式,让作品充满强烈的个人情感符号有重要作用。
1山水画创作中色彩与情感分析
山水画中颜色的使用一方面和“儒道释”“五行说”有一定关联,使山水画发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对于墨色与水的效果运用以及画面“留白”的处理也从另一方面也给了山水画另一种面貌。王维的“破墨”山水画一直有很多人推崇,他的作品体现着水墨的魅力,蕴含着禅意与诗意,表现着超然的人生情感。“随类赋彩”也要求着在创作赋色时要注意情感因素,不是完完全全真是地描摹客观物像的颜色,而是要融合画家的内心情感和创作经历以及创作设想融汇后形成的理想的画面效果。
2山水画创作中构图与情感分析
构图要根据所要表达的主题,把画面中安排的东西很好地组织起来,尤其是安排好位置和前后穿插关系和整体与前后的关系,从而更好地表达作者的主观想法。在这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达到画面的和谐与均衡。中国山水画的构图中讲究画面中各种客观物象的连续性与气势贯通,通过物象的联系把整幅画的气息贯通起来的和谐的表现。山水画中不关用笔墨达到和谐,用印和提款也有着相同的效果,例如八大山人的提款和篆刻都有着强烈的个人色彩,这都是为了他的主观情感表现服务。
3山水画创作中皴法与情感分析
皴法是不同时期的山水画家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具有很多个人特色,贺天健先生曾说:“中国画艺传统的山水画,是以山石的皴法美为主要艺能,除掉这个表现,便不是山水画,而是一种风景画”[3]。皴法能在细节上表达作者不同的风格,不同的皴法可以形成不同的效果,也代表着不同画家的审美和个人情感的不同表述,也有不同的情感表现,很多作品都会注重使用不同的笔法,例如李思训和李昭道父子的大青绿山水的“空勾无皴”、荆浩的勾和皴结合使用等,都能在山水画创作上表现情感的方式,也能让欣赏者感
4创作中情感表达的深层理解
创作中情感的缺乏,其实与对客观物象的观察和表现方式有着必然联系,大自然是鲜活的,任何的植物、树木、水流、云朵、空气等等这些元素都是运动着的并且拥有鲜活的生命力。创作的时候是否只是单纯地描摹物象,而不是仔细观察物象在空间中远近高低的不同姿态,再经过思考,融汇自身的情感和经历、经验,最终再落实在笔上。
从纪录片的角度上来说,许多其它评论都已经指出了舌2的不足之处——过度强调了人文关怀而忽视了“食物”本身的制作工艺和流程,食物已变成了叙事的附属,甚至,部分叙事内容采用了故事片而非纪录片的拍摄手法——如留守儿童的远望,麦客的秦腔等,在许多专业人士看来可能是摆拍而成……等等。
但是,如果从更广义的角度去认识《舌尖》系列片子,看清其希望传达的是什么理念,以及纪录的是什么内容,也许我们便不会从狭隘的“讲吃的少了啊”这个点去理解了。
《舌尖》系列,固然讲的是中餐精湛的制作工艺,以及各地独具特色的美食,但这仅是第一层意义。
我认为这并不是一部纯粹的美食片,至少不是一部具有严谨科学探索性的食物介绍纪录片。
这部片子本身,也犹如中餐一样——不严谨,但讲求“意境”和“味道”。
与其说它介绍了中华文化中的美食,倒不如说通过美食传达出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以及中国社会在剧变之下的世间百态——这一切,都由“吃”给符号化,物质化,从而以一种抽象的方式传递给了大家。
中餐,无疑是中华文化最具对外传播力的一个文化内容,其对西方世界的影响力,甚至远超中国的艺术和商品。
这其中原因,除了中餐菜色丰富,口味鲜美外,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哲学理念,生活习惯等等,都倾注在了“吃”中。
中国人衡量生活品质的最高标准是吃,所有庆典活动的主体都是吃。
中国东西南北人们口味,菜式差别之大,譬如山东大饼和广东精致小盘之间的区别,绝不只是气候,食材的不同,更是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区别——看懂了吃,便看懂了中国文化,想看懂中国文化,恐怕相当部分需要从“吃”下手。
从这个角度来看,《舌尖2》的意图也许已经并非单纯客观地描述食物本身的工艺,口感等内容,而是将食物做成了一个线索,去纪录中国当代社会下,人性的美好,人们为了生活的奔波,以及传统与现代的冲突。
《舌尖2》第一集《脚步》,描写了西藏采蜂少年,夫妻养蜂队,陕西麦客,浙江夫妻船,各种面食,贵州打工夫妇,福建归国老华侨等人的故事。每个故事中,都有一种或几种食物作为线索,但侧重描写的,却是人的情感——这种情感的表达,是非常内敛,隐晦,也非常符合中国人特点的。
而情感的强烈部分,却“尽在不言中”地被食物的画面所传达了——譬如片中不厌其烦地描写了贵州鱼酱和稻花鱼的复杂工艺,事实上已将难得的打工父母与孩子团聚的时光一并描写了。
而在短暂的团聚之后,父母几句看起来很平淡的“走了啊”便离开了孩子,但那种感情,却仿佛浓缩在了几罐随身带走的鱼酱中,成为一种精神的寄托——除了食物,还有什么更适合成为中国人的情感寄托呢?除了中国人,还有谁会在吃中倾注了如此的情感呢?
纪录片用书名号即可。
知识扩展:纪录片是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并对其进行艺术的加工与展现的,以展现真实为本质,并用真实引发人们思考的**或电视艺术形式。纪录片的核心为真实。**的诞生始于纪录片的创作。1895年法国路易·卢米埃尔拍摄的《工厂的大门》、《火车进站》等实验性的**,都属于纪录片的性质。中国纪录**的拍摄始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第一部是1905年的《定军山》。最早的一些镜头,包括清朝末年的社会风貌,历史人物李鸿章等,是由外国摄影师拍摄的。纪录片又可以分为**纪录片和电视纪录片。
编者按 本期“点评・学术”栏目的两篇文章都涉及到了“符号”问题。在段炼的 《视觉再现与符号研究》中,他从再现这个问题说起,主要“关注再现的符号特征,以及符号再现在艺术研究中的应用实践。”从视觉图像层面来讲,符号代表着艺术家在作品中的组织方式,同时带有社会与文化性的特质。因此符号学作为艺术史的一种方法,它超越了仅从审美经验来看待艺术的方式,一方面使得形式得以更加纯粹和自在,另一方面将观看艺术的视野根植于社会与文化之中,拓展了艺术的维度。
后一篇是Syvere Lotringer对于波德里亚《艺术的共谋》的导读。波德里亚也强调现代艺术的“再现”性,但是波德里亚论证的是,艺术作品如何以符号的形式成为具备价值、进入市场流通并参与构建消费社会(即所谓的共谋)的“物”,并且在这个游戏中拙劣地模仿、展现,伪造着这个世界。再没有所谓纯粹与独立的艺术,他们只是一场共谋中不可或缺的符码。
无效(归于零)的艺术要死亡?波德里亚说,它(艺术)无处不在,在具体社会环境中构建、运作、流变,却唯独不在“艺术具备特殊意义”之类的神话中。因此,波德里亚解构的只是一个关于艺术的“神话”,他用一句貌似狠毒的“咒语”表达了对艺术真正的关心。关于机械复制时代以后的艺术,我们确实要放下身段,重新打量。
作为中国艺术经验的一个方面,我国在20世纪后半期的基本艺术理论是“反映论”,其渊源是经前苏联绕道而来的西方“再现论”。但是在20世纪后半期,再现论在西方走了一条与其在中国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直到20世纪末才有机会再次进入中国,而这时在中国艺术界,“再现论”已几乎被放弃。面对这一情况,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再现论,了解其在西方当代艺术理论中的发展趋向。为此,本文从语言与文学领域进入视觉艺术领域,探讨文本再现和图像再现。虽然福科在他著名的小册子《这不是一只烟斗》中专门讨论了这两种再现及其关系,但本文关注再现的符号特征,以及符号再现在艺术研究中的应用实践。
一、从文本进入图像再现
西方文艺理论界在20世纪后半期对再现概念的质疑,旨在从现代主义时期的形式研究,转向后现代以来的信息研究和文化研究。米歇尔是后现代和文化研究时期的形式主义者,其研究游走于形式与非形式之间,他从皮尔斯符号学的角度来讨论再现问题,认为再现的三大类型是图标(icon)再现、象征(symbol)再现和索引(index)再现,由此引出了再现与符号的关系及互动问题。
照米歇尔的观点,一件艺术作品可以被视作一个符号,与此相应,艺术再现便是符号的意指,再现的行为和机制也可看成是符号意指的过程和机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米歇尔借用了皮尔斯的三种符号,来指称再现的上述三种类型。
传统的具象艺术是再现的,但在再现型具象艺术中却不乏象征符号,而西方艺术史的象征传统则几乎与再现传统一样长久,二者甚至是平行发展且又相互渗透的。例如,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绘画中,大天使手里的百合花就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符号,象征着圣母怀胎的纯洁。19世纪后半期英国拉斐尔前派的绘画,继承了这一象征传统,而到了现代主义初期,法国和德国的象征派艺术,则在具象绘画中不仅继承而且发展了图像符号的意指性。
在20世纪的现代主义时期,艺术中的表现、抽象和观念形态相继出现,学者们为其一一找到了相应的符号形态。如果说再现对应于写实艺术,那么当英国学者艾利克斯・帕茨(Alex Potts)将形式主义的抽象艺术也视作符号时,我们对再现的老旧定义便不得不改变了。这就是说,再现并不仅仅是关涉视觉表象的意指行为,而且也是象征和指示的,现当代艺术中的抽象形式和观念符号,就此一变而为超越事物表象的非具象再现。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被福柯所质疑的再现、被福柯颠覆了的视觉秩序,便获得了重建的机会。但这里的困难是,一旦将再现视作符号,再现便有可能无往不胜,成为包罗万象的概念,却远离了再现的本义,从而自我解构,使再现的概念失去理论的价值。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觉。
由此看来,还是米歇尔对再现的研究别有一番心机,因为他看重再现的符号特征,看重再现的意指性和代表的功能,这样,他就不必固着于视觉表象的相似,而得以在不同层次上分析再现的意指作用。这分析展示在他对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人勃朗宁的名诗《我的前公爵夫人》的解读中。当然,这几个层次的划分,及其整体结构的形式构建,并不是米歇尔特意指出的,而是笔者在阅读米歇尔的研究文章时辨识出来的。
这是一首关于一幅绘画的诗,或者说这首诗再现了一幅绘画,再现了关于这幅画的故事,也再现了画中人及其故事,而在画外讲故事的人则与这一系列再现密切相关。诗歌之再现的第一层,是用戏剧独白体来再现可能的舞台演出,用一个独白的片断,再现了公爵向客人讲故事的场面。第二层是公爵所讲的故事,是用语言来直接再现一个已经发生了的往事,虽是片断,但却间接地指向了他谋杀妻子的整个秘密。第三层是公爵的戏剧独白,描述了前公爵夫人的肖像画,再现了这幅画的视觉特征。第四层是公爵对这幅画的再现,这是一个重要的过渡和转折,这首诗从语言再现转入图像再现,而这幅画则再现了画中的人,再现了前公爵夫人的相貌、习性和可能的事件。到诗歌的第五层,这一切视觉的再现,又指向了肖像背后的隐秘故事,并就此返回到故事本身,与第一层对接,构成了一个完美的起承转合,在形式上建成了再现的整体结构。
这五层再现所构建的整体,是一个形式的结构,其中有两个重要关键。首先,诗歌用语言来再现图像(诗中的肖像画),是再现的再现, 或曰用再现来再现的 “再现”, 暗藏了悖论的可能。其次,诗人本身并未出场,诗歌不表明他对前公爵夫人的态度,也不表明他对公爵及其谋杀的态度。诗人站在一个貌似超然的高处,调度着所有的再现。换言之,诗人用诗歌的语言来再现了上述五个层次的再现。在这个框架里,每一层次的再现,都是一个符号或复合符号,而再现之各层次的递进,则是符号之意指的深入,具体地说,就是最后对谋杀事件的终极暗示。
如前所言,米歇尔是当代批评理论界的形式主义者,他将再现的概念同符号学贯通起来,让我们可以一窥形式主义再现论在今天的发展,及其在当代批评理论中的位置。
二、从再现到符号
符号学是研究符号表意的学科,是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理论的基石之一。符号学的两大派系,一是源自索绪尔语言学的欧洲学派,二是源自皮尔斯逻辑学的美国学派,二者皆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并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独立学科,称现代符号学。在形式主义之后,尤其是在20世纪后期,符号学发展到文化研究和视觉文化研究领域,其实际应用更延伸到当代社会各方面。
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一位开拓者,原在哈佛大学学习化学,练就了严谨的理性思维,后来从事形式逻辑研究,创立了实用主义符号学。如果说欧洲学派的索绪尔符号学看重能指与所指二元体系中的一一对应及其意指关系,那么皮尔斯则以三元体系与之相区别。按照皮尔斯的理论,符号的整个意指系统有三项基本元素,第一项为“再现者”,即符号,类似于能指;第二项为“事物”,即被再现的客体或对象,类似于所指;第三项为“阐释者”,处于前两者之间,是沟通二者的中介,是意指过程的实现者。
相对于索绪尔的二元论,皮尔斯的三元论强调第三项的阐释功能,认为 “再现者”与被再现的“事物”之间的关系,由阐释者的解读来决定,符号的意义也由此诞生。也就是说,正是阐释者的阐释行为,才使“再现者”与“事物”建立了联系,而“再现者”的意义也才得以产生,其再现事物的意指作用方得以实现。要之,没有阐释者,便没有再现者的价值和意义,也没有再现者与被再现者的意指关系,更没有整个符号系统和意指行为。
在皮尔斯的三元体系中,“再现者”也称“符号项”,具有三种主要形态,分别是图标(icon)、索引(index)和象征(symbol),符号之再现正是通过这三种具体形态来实施的。皮尔斯的第一种符号“图标”涵盖宽泛,几乎包括所有可视图形,但仅就艺术作品而言,图标符号与被再现的“事物”有视觉上的关联,体现着“再现”一词的本义,例如一幅具象写实的静物画中的苹果,再现着桌上那个真正的苹果。第二种符号“索引”不一定具有图形上的这种直接关联,而更多的是一种间接关联,例如一个苹果可以让我们联想到整片果园,而文字标牌“苹果园”也是一种索引符号。第三种符号“象征”更为间接,因为这类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并没有视觉或逻辑上的关联,其意指关系是约定俗成的,例如“苹果”一词(或其发音)与画上或桌上的苹果之间,并无内在联系,仅因人们都用这个词来称呼画上和桌上那种水果罢了。再如绘画中的蓝色代表冷静、幽深、孤独、忧郁等抽象概念和主观情绪,也是一种象征关系。
在读图实践中,美术批评家和普通看画人都是阐释者,都扮演着“第三项”的角色,正是他们对以上三种符号的阅读决定了艺术作品的含义。这个观点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西方盛行的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理论。
在此,图标符号的含义易于通过视觉阅读而直接触及,索引符号的含义则可通过联想来间接获得,但理解象征符号却不是这样简单。艾利克斯・帕茨的研究,大体上是从皮尔斯关于象征符号的观点出发的,他通过对抽象艺术的解读,来演示了符号学在读图过程中的功用,涉及符号学之于艺术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帕茨的图像阐释有两个重点,一是倚重 “文化习俗”的作用,也就是说,“阐释者”对作品的解读,处于文化传统的语境中,阐释之所以可行,正是借助了文化传统的规约。帕茨的第二个重点是 “无限制的符号过程”,也就是说,由于文化习俗或传统的作用,在符号系统中,一个符号的破译,构成了下一个符号及其破译,并如此这般无止尽地向前滚动。于是,阐释者对作品的解读便得以步步深入、层层推进,使作品的含义得到越来越深刻的揭示。
帕茨从皮尔斯符号学的角度对读图实践的演示,所涉作品为美国雕塑家戴维・史密斯(David Smith)的雕塑《马车一号》。这是作于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形式主义艺术高潮时期的一件抽象作品,虽被命名为马车,但并非一辆马车的如实再现。由于这件作品的抽象特征,常规的再现式相似性符号链断裂了,通常的符号学阐释短路了。帕茨认为,如果作品是再现者或能指,那么阐释者通常需要到作品之外去探索符号的所指和含义,但这件让人思维短路的抽象作品却不是再现的,它不指涉作品之外的任何东西,这是一件形式主义的自在自为的作品。这时候,短路的思维只好返身回来,回到作品本身来探索其含义。在此,帕茨不仅延伸了皮尔斯的阐释者决定论,也否定了罗兰・巴特所说的那种外延含义,以及潘诺夫斯基所说的外在文化决定论,从而使阐释得以专注于作品自身的内涵含义,例如作品各形式元素之间内在的构成关系。
阅读帕茨,我们可能会期待他演示一番怎样通过符号解读而在作品之外寻获这件抽象雕塑的含义,不料他竟给了我们一个短路的回馈,将我们引回到作品之中,说这件形式主义作品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其形式关系的反应。这既是视觉反应,也是情感反应,当触及含义时,更成为思维反应,而这一连串反应,正好呼应了皮尔斯对“阐释项”的倚重。同时,这一切也正是符号的意指过程在往返中所具有的无限制推进,这使并无外在意义的抽象形式,获得了意指的层层递进和含义的步步深入。
三、符号学的实践
英国学者哈特和德国学者科隆克在二人合著的《艺术史:研究方法导论》一书中,有《符号学》一章,主要讨论索绪尔和皮尔斯的符号理论及其方法,并将其放到艺术史研究的实践中进行具体阐述。
按照通常的说法,符号学是研究符号表意的科学,包括表意的机制、过程、系统,涉及类比、隐喻、蕴意、传播、反馈、交流等环节,其核心元素是符号与象征。符号学同语言学密不可分,二者的研究对象直接相关,大体上有三方面。一是语义学,考察符号何所指的问题。二是句法学,考察符号间的关系。三是语用学,考察符号的使用问题。语言学一路的符号学,起自索绪尔,包括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称符号学的欧洲学派或法国学派,以法国后结构主义文论家罗兰・巴特为现代符号学的重要人物。巴特对符号学发展的贡献,主要在于他超越了索绪尔的语言学局限而走向了文化研究,将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向前推进了一步,使语言学的所指变成文化研究的能指,从而指向一个更具深意的所指。在此,巴特不仅将语言符号学引入象征符号学,也赋予符号学以社会和政治意义。
哈特与科隆克的《符号学》一章,先以第一节讲解索绪尔关于能指与所指的问题,并借美国当代艺术史学家、批评家罗萨琳・柯劳丝(Rosaline Krauss)对毕加索的一幅立方派室内静物画的解读,来阐述其理论和方法。然后,二位作者在第二节转向皮尔斯的理论和方法,探讨20世纪后半期美国学者夏皮罗的实践,指出他没有机械地套用符号学某一特定学派的分析模式,而是将其与多种方法结合起来,开创并拓展了符号学在艺术史研究中的运用。
在西方学术界的艺术史研究领域,梅耶・夏皮罗(Meyer Schapiro,1904―1996)有着特殊地位,他的学术事业成长于美国本土,他是标志美国在二战后学术独立的第一代学者,同时他又承传了欧洲学术,是沟通美国学术与欧洲学术的集大成者。在艺术史研究和艺术理论与方法的运用方面,夏皮罗不仅是潘诺夫斯基、阿多诺、本雅明的继承者,也是他们的朋友、同事或有一面之交。更重要的是,他将沃尔夫林的形式主义艺术理论,引入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方法中,将不同时期的学术思潮贯通了起来。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夏皮罗在哲学方面也融会贯通,将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将列维・斯特劳斯和雅克・拉康的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将杜威的实用主义等欧洲和美国的现代思想,引入到自己的艺术史研究中,形成了美国学术的特色。
对此,西方学术界有一共识:夏皮罗为艺术史研究作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其一,他主张通过高度集中注意力的“观照”,来对艺术作品进行探究式的视觉形式分析;其二,他指出艺术的实践无论是不是一种异化了的活动,都是体力与智力的双重形式的劳动;其三,他认为艺术作品的含义既来自作者意向,也来自读者接受的历史过程,二者的对话决定了作品的意义;其四,他宣称“批评理论”并不在于建立一个体系,而在于有体系地从事批评活动。具体地说,在研究方法上,夏皮罗有六大治学特征。其一,在视觉分析中以形式分析为基础。其二,在图像解读中以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为参照。其三,在作品阐释中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其四,将现代符号学引入艺术史研究和批评实践。其五,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入艺术史研究和作品分析。其六,反对存在主义在艺术研究中的非历史倾向。
在以上这万花筒般的理论思想和方法论语境里,我们阅读《符号学》中关于夏皮罗对符号学的运用,应该注意一点:虽然夏皮罗对罗兰・巴特情有独钟,但他更倾向于皮尔斯的理论,换言之,他在欧洲学派和美国学派之间发现了连接点,这就是符号意指的延伸与扩展,这使符号学的运用不必局限于索绪尔语言学关于能指与所指相对应的说法。
如果说夏皮罗是将符号学引入艺术史研究领域的先驱,那么相对而言,荷兰学者米柯・巴尔(Mieke Bal,1946―)便是一位新起者,是在视觉文化研究领域里运用符号学的典范。在《符号学》中,两位作者也重点考察了巴尔的符号学方法实践,这便是她对伦勃朗等古代大师的研究。巴尔对符号学的运用,不是严格追随索绪尔或皮尔斯,而是取其所长来建立自己的方法论,其特征也是多种方法的综合与灵活运用。
哈特与科隆克在《艺术史:研究方法导论》中对符号学方法的探讨,以评述某一学者的具体研究为基础,重在分析其操作机制,并给予相应评价,这给我们的艺术研究提供了实践的参考,尤其是对我们从符号学的角度去理解图像再现问题,具有参考意义。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