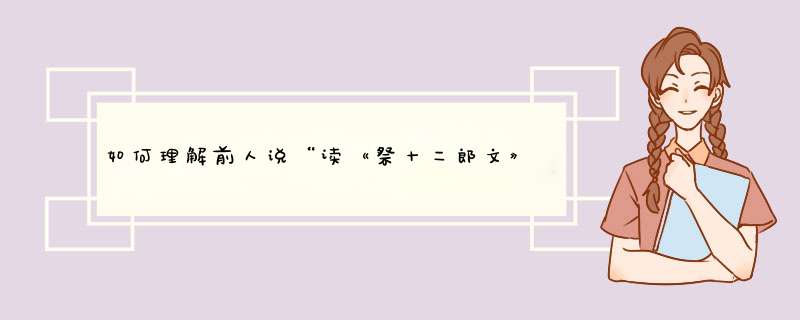
《祭十二郎文》和《出师表》《陈情表》,分别被称为千古至情、千古至孝、千古至忠,
所以说有感情的人读完应该落泪的,如果没有落泪的话,那么这个人是没有感情的,这个人必定(比:通“必”)对朋友不够真心
“言有穷而情不可终”抒发了作者身宦海沉浮之苦和对人生无常之感,并以此深化亲情。作者原以为两人都还年轻,便不以暂别为念,求食求禄,奔走仕途,因而别多聚少,而今铸成终身遗憾。作者求索老成的死因和死期,却堕入乍信乍疑,如梦如幻的迷境,深感生命瓢忽,倍增哀痛。
整句:呜呼,言有穷而情不可终,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呜呼哀哉!尚飨!
译文:唉!话有说完的时候,而哀痛之情却不能终止,你知道呢还是不知道呢悲哀啊!希望享用祭品吧!
出处:出自韩愈的诗《祭十二郎文》
赏析:这篇祭文强烈的感情力量,能如此深刻地感染读者,也得力于作者高超的语言文字技巧。它全用散文句调和平易晓畅的家常生活语言,长长短短,错错落落,奇偶骈散,参差骈散,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得不止;疑问、感叹、陈述等各种句式,反复、重叠、排比、呼告等多种修辞手法,任意调遣,全依感情的需要。再加之作者取与死者促膝谈心的形式,呼“汝”唤“你”,似乎死者也能听到“我”的声音,显得异常自然而真切。这样全文就形成了一种行云流水般的语言气势和令人如闻咳謦的感情氛围。文章就像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拥抱住了它的读者。
作者采用与死者对话的方式,边诉边泣,吞吐呜咽,交织着悔恨、悲痛、自责等种种感情,似在生者和死者之间作无穷无尽的长谈。如写闻讣的情景,从“其信然邪”到“未可以为信也”,再到“其信然矣”,语句重叠,表现其惊疑无定的心理状态。末尾“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一段,多用排句,情绪激宕,一气呵成。这一切又都从肺腑中流出,因而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整体赏析
作者把抒情与叙事结合在一起,联系家庭、身世和生活琐事,反复抒写他对亡侄的无限哀痛之情。同时,也饱含着自己凄楚的宦海沉浮的人生感慨。全文以向死者诉说的口吻写成,哀家族之凋落,哀己身之未老先衰,哀死者之早夭,疑天理疑神明,疑生死之数,乃至疑后嗣之成立,极写内心的辛酸悲痛。文章语意反复而一气贯注,最能体现在特定情景下散文的优长,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韩愈写此文的目的不在于称颂死者,而在于倾诉自己的痛悼之情,寄托自己的哀思。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强调骨肉亲情关系。作者与老成,名为叔侄,情同手足,“两世一身,形单影只”。老成先逝,子女幼小,更显得家族凋零,振兴无望。这在注重门庭家道的古代,引起韩愈的切肤之痛是理所当然的。二是突出老成之死实出意外。老成比作者年少而体强,却“强者夭而病者全”;老成得的不过是一种常见的软脚病,作者本来不以为意,毫无精神准备,因而对老成的遽死追悔莫及,意外的打击使他极为悲痛。三是表达作者自身宦海沉浮之苦和对人生无常之感,并以此深化亲情。
分段赏析
祭文全文共分四段,第一段重在叙述韩门两代,只有“我”与侄儿两人,所谓“两世一身,形单影只”,身世之戚苦,及对嫂嫂的深切感念;第二、三段重在痛惜与侄儿的暂别竟成永别,及侄儿的夭折;第四段是对侄儿病情的推测,沉痛的自责,后事的安排,及无处诉说、没有边际的不可遏制的伤痛。文、情前后紧相呼应,浑然一体。结构精巧,层层推进,环环相扣,而又步步深入,随着叙述的展开,作者沉痛的情感波涛,也一浪高似一浪。使人读完全篇,不能不掩卷叹息,为作者因失相依为命的侄儿所遭受到的深切的精神悲痛,潸然泪下,并得到一种美的享受。
祭文开头几句,叙述了“我”听到侄儿去世后,准备祭墓的经过。接着转入身世的叙述和悲叹:“我”从小失去了父亲,依靠着哥哥、嫂嫂的抚养,而哥哥又在中年殁于南方。年纪幼小的“我”与你,在孤苦零丁中没有一天不在一起。韩愈三岁丧父,十一岁前,韩愈随兄韩会在京师。大历十二年(777年),韩会被贬为韶州刺史,韩愈随兄到韶州(今广东韶关)。韩愈回到故乡后,适逢中原战乱,遂到江南宣城避难,这就是祭文中所说的“又与汝就食江南”。
自“承先人后者”至“亦未知其言之悲也”这一小段,是写得很感人的一段。字里行间,流露出形单影只的凄苦之情,及对他的嫂子的无限感念。前面那一段铺叙家世,为颠沛流离中的嫂嫂的话“韩氏两世,惟此而已”,增加了浓重的感伤之情,及无限的分量,因为在封建社会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可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通过嫂嫂的两句话,把嫂嫂当时的悲伤、期待、焦虑之情,活画了出来,并使人感受到两句话中凝集着多么深厚的感情力量。
从“吾年十九”至段末,叙述了韩愈在十九岁以后至侄儿殁去之前的经过。
祭文第二段开头几句是倒叙,叙述自己为什么愿意离别形影相依的侄儿的原因。自“诚知其如此”起,笔锋一转,直至段末,是韩愈为此而悲痛、失悔,还有得到侄儿死去的消息后,将信将疑的复杂情绪,以及为此而发出的深挚的慨叹。写得跌宕有致,情思深沉,感人至深。这一大段可分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着意在痛悔自己的去取。接着痛悔,又深入一层,回叙自己父兄的早死,和侄儿本来有可能多在一起呆些日子,共享天伦之乐,却失去了这样的机会。
在这一小段中,为了说明自己身体的病弱,一连用了三个“而”字,“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不仅加重了语气,读起来铿锵有力,而且反衬并强调了本段末提出的问题,加强了作者的失痛感。
接着思绪又深入一步,以将信将疑的口气描绘了自己内心感到的无穷的惶惑:这不可能是真的,世间没有这样的道理!准是传的信不确切。可是东野的来信、耿兰(奴仆名)的报告又怎么放在“我”的身边呢?在这一段对于内心惶惑的叙述中,作者对侄儿之死所引起的情感的剧烈震荡,不仅为结尾的天命无常的慨叹加重了分量,而且为下段的痛悔准备了心理条件,使下段的责备、失悔、哀惜、慨叹,语语仿佛从肺腑中沛然流出,使悲伤的情感逐步达到高潮。
自“汝去年书云”起,至文末,包含几个小段:一是用回叙的手法,推测侄儿得病的原因,及去世的日期;二是对于侄儿后事、家务的安排;三是表示自己“无意于人世”的沉痛的心迹;最后则是深切的寄哀。
在这一小段中,作者通过对侄儿的生、病、死、葬料理不到的沉痛自责,表现了失去侄儿后的痛惜之情,哀思深挚,读之使人回肠荡气,不能不为之悲戚不已。这是这篇祭文在情感力量上所达到的又一高潮。
祭文接着述说了在经过这次精神上的打击之后,“我”已无意于留恋人间富贵,只求在伊、颍河(皆在今河南境内)旁买上几顷地,把“我”的和你的儿子养大,希望他们成人,把我的和你的女儿养大,嫁出去,也就罢了。通过对自己心灰意冷的描述,又进一步加深了已有的哀痛。既属叙事,又是抒情。以“言有穷而情不可终,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的问句为结束,更进一步扩展和加深了作者的哀思。明知死后无知,还要如此提问,就使作者更加伤痛不已。“尚飨”,是祭文中常用的结束语,意谓请你来享受这祭品吧。 本文一反传统祭文以铺排郡望、藻饰官阶、历叙生平、歌功颂德为主的固定模式,主要记家常琐事,表现自己与死者的密切关系,抒写难以抑止的悲哀,表达刻骨铭心的骨肉亲情。形式上则破骈为散,采用自由多变的散体。这种自由化的写作形式,使作者如同与死者对话,边诉边泣,吞吐呜咽,交织着悔恨、悲痛、自责之情,因而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这篇祭文强烈的感情力量,能如此深刻地感染读者,也得力于作者高超的语言文字技巧。它全用散文句调和平易晓畅的家常生活语言,长长短短,错错落落,奇偶骈散,参差骈散,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得不止;疑问、感叹、陈述等各种句式,反复、重叠、排比、呼告等多种修辞手法,任意调遣,全依感情的需要。再加之作者取与死者促膝谈心的形式,呼“汝”唤“你”,似乎死者也能听到“我”的声音,显得异常自然而真切。这样全文就形成了一种行云流水般的语言气势和令人如闻咳謦的感情氛围。
作者采用与死者对话的方式,边诉边泣,吞吐呜咽,交织着悔恨、悲痛、自责等种种感情,似在生者和死者之间作无穷无尽的长谈。如写闻讣的情景,从“其信然邪”到“未可以为信也”,再到“其信然矣”,语句重叠,表现其惊疑无定的心理状态。末尾“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一段,多用排句,情绪激宕,一气呵成。这一切又都从肺腑中流出,因而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苏轼:“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
南宋谢枋得《文章轨范》引安子顺语:“读《出师表》不哭者不忠,读《陈情表》不哭者不孝,读《祭十二郎文》不哭者不慈。”
茅坤评《祭十二郎文》为“祭文中千年绝调”。
《古文观止》:“情之至者,自然流为至文。读此等文,须想其一面哭,一面写,字字是血,字字是泪。”
林纾《韩柳文研究法·韩文研究法》:“祭文体,本以用韵为正格……至《祭十二郎文》,至痛彻心,不能为辞,则变调为散体。”
《祭十二郎文》,唐代韩愈作品,写于贞元十九年(按《文苑英华》说是写于五月二十六日,应是笔误,因是年六月下旬十二郎还写过信),文章的十二郎是指韩愈的侄子韩老成,“八仙”中著名的韩湘子即是老成之十七子。十二郎与韩愈两人自幼相守,由长嫂郑氏抚养成人,共历患难,因此感情特别深厚。但是长大之后,韩愈本人在外飘泊,与十二郎很少见面。孟郊告知韩老成六月二日已逝,但韩愈又疑问六月二十二日老成还在写信,种种的疑点让韩愈悲从中来。韩愈在文中提到自己的衰老“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 《祭十二郎文》 - 作品背景 韩愈与十二郎,在家庭连遭不幸的情况下一起度过了苦难的童年。又因为家族的、亲情的和年龄上的关系,韩愈与十二郎虽名为叔侄,却情同手足。这是韩愈写作本文无需为文造情的感情基础。韩愈写这篇文章时三十六岁,十二郎稍小一些,都正当人生的壮盛时期;就韩愈而言,他与十二郎虽暂分离而此后必然有很长时间相聚,可以充分体味叔侄之间的天伦乐事。但是,令韩愈想不到的是十二郎竟先己而死,于是对家族、亲情的悲痛回忆和自己与十二郎聚少离多的遗恨便一下子涌上笔端。 《祭十二郎文》 - 作品评价 南宋学者赵与时在《宾退录》中写道:“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祭十二郎文〉〉是一篇千百年来传诵不衰,影响深远的祭文名作,不管我们对文中的思想感情作如何评价,吟诵之下,都不能不随作者之祭而有眼涩之悲。 一、 感情真挚,催人泪下 韩愈写此文的目的不在于称颂死者,而在于倾诉自己的痛悼之情,寄托自己的哀思。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强调骨肉求情关系。作者与老成,名为叔侄,情同手足,“两世一身,形单影只”。今老成先逝,子女幼小,更显得家族凋零,振兴无望。这在注重门庭家道的古代,引起韩愈的切肤之痛是理所当然的。二是突出老成之死实出意外。老成比作者年少而体强,却“强者夭而病者全”;老成得的不过是一种常见的软脚病,作者本来不以为意,毫无精神准备,因而对老成的遽死追悔莫及,意外的打击使他极为悲痛。三是表达作者自身宦海沉浮之苦和对人生无常之感,并以此深化亲情。作者原以为两人都还年轻,便不以暂别为念,求食求禄,奔走仕途,因而别多聚少,而今铸成终身遗憾。作者求索老成的死因和死期,却堕入乍信乍疑,如梦如幻的迷境,深感生命瓢忽,倍增哀痛。 二、不拘常格,自由抒情 祭文原本偏重于抒发对死者的悼念哀痛之情,一般是结合对死者功业德行的颂扬而展开的。本文一反传统祭文以铺排郡望、藻饰官阶、历叙生平、歌功颂德为主的固定模式,主要记家常琐事,表现自己与死者的密切关系,抒写难以抑止的悲哀,表达刻骨铭心的骨肉亲情。形式上则破骈为散,采用自由多变的散体。正如林纾在〈〈韩柳文研究法韩文研究法〉〉中所说:“祭文体,本以用韵为正格……至〈〈祭十二郎文〉〉,至痛彻心,不能为辞,则变调为散体。”全文有吞声呜咽之态,无夸饰艳丽之辞,为后世欧阳修〈〈陇冈阡表〉〉、归有光〈〈项脊轩志〉〉、袁枚〈〈祭妹文〉〉等开辟新径。这种自由化的写作形式,使作者如同与死者对话,边诉边泣,吞吐呜咽,交织着悔恨、悲痛、自责之情,因而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三、语言朴素,行云流水 这篇祭文强烈的感情力量,能如此深刻地感染读者,也得力于作者高超的语言文字技巧。它全用散文句调和平易晓畅的家常生活语言,长长短短,错错落落,奇偶骈散,参差骈散,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得不止;疑问、感叹、陈述等各种句式,反复、重叠、排比、呼告等多种修辞手法,任意调遣,全依感情的需要。再加之作者取与死者促膝谈心的形式,呼“汝”唤“你”,似乎死者也能听到“我”的声音,显得异常自然而真切。这样全文就形成了一种行云流水般的语言气势和令人如闻咳謦的感情氛围。文章就像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拥抱住了它的读者。
这是韩愈在贞元十九年(803)为悼念他的侄子老成而写的一篇“衔哀致诚”的祭文。要让学生体会作者哀痛、诚挚的情感,首先应了解他们叔侄的特殊关系。韩愈三岁丧父,一直依靠兄嫂抚养。不久,哥哥又宦死于南方,寡嫂携带年幼的韩愈叔侄回到故乡河阳,艰难度日。这时,兄弟辈只剩韩愈一人,子侄辈只有老成一人,“两世一身,形单影只”!韩愈视长嫂如母,和比自己小几岁的侄子情同手足。后来,又一同移居宣州,孤苦零丁,一家人相依为命。韩愈十九岁来到京师谋生,二十五岁中进士后便在朝廷和地方任职,而老成则一直羁留在南方,他们叔侄每隔数年才得相见一面。韩愈本以为彼此都还年轻,指望着将来生活稳定后,便接侄子来同住。没想到老成竟突然病死,他悲痛欲绝,为悼念老成乃写成了这篇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祭十二郎文》。 这篇祭文打破了传统的祭祀文体的固有格式,不去铺排郡望,历数祖辈官阶,赞颂死者的品德、业绩,而是完全根据情感的起伏变化奋笔直书。由于情绪的激动以及生活经历的繁富,所要书写的内容很多,所以文章乍看起来似乎往复重叠、散漫错综,实际上却是气脉不断,一种骨肉至情充塞全文,贯串始终。要理解这一艺术特色,就必须把握住两点:他一面要追忆往事,叙述二人亲密的关系;一面要面对现实,抒发自己得到噩耗后,震惊、疑惑和万分悲痛的思想情绪。正是为了更好地表达这些内容,作者只在开头的“年月日┄┄告汝十二郎之灵”,和结尾的“呜呼哀哉!尚飨!”数句使用了固定格式,中间主要部分运用的都是直接对话的方法,就像是在和侄子促膝把手,谈论家常,倾诉心声。 文章的主体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自“呜呼!吾少孤”至“吾不以一日辍汝而就也”)记叙自己幼小丧父后,依靠兄嫂抚养,和早年与侄子南北迁移,“零丁孤苦,未尝一日相离”的经历。又详细地回忆了自从他来到京师,“其后四年”“又四年”“又二年”的三次相会,以及几番错过了重聚的机会。他为自己因求食逐禄,不能与侄子长相厮守而悔恨不已。第二部分(自“去年,孟东野往”至“其然乎?其不然乎?”)写自己因比他年少体强的、生性‘纯明’的侄子遽然辞世而悲痛欲绝。写当噩耗传来时他从不信到确信的复杂心理活动,写他因少者、强者夭殁,长者、衰者存全而埋怨天道难测,神灵不明,又为不能弄清老成的死亡月日,不能亲自抚尸、凭棺、临穴而愧疚。第三部分(自“今吾使建中祭汝”至篇末)主要交代对老成身后事的安排,说终丧后,他将把老成的遗孤接来,与自己的子女一同抚养,直到男成业,女出嫁。他还要把老成迁葬到北方的祖坟。文章开头说他是“衔哀致诚”地撰文来祭奠侄子,结尾说“言有穷而情不可终”,前后呼应,进一步说明了自己彻骨钻心的悲痛并不因文章的结束而终止,它将绵绵延续,永无尽期!所以说这是一篇以真情凝聚成的,感人至深的祭文。 本文的作者在语言上放弃了传统骈俪文的整饬、华美,而采取韵散结合,以散为主的形式来表达。而且不沿袭传统祭文的固定格式,运用了与亲人对面交谈以叙家常、吐心曲的方法,这就构成了这篇祭文的语言自然、质朴,明白如话,而又宛转、细密的独特风格。 作者很重视语句的前后呼应,善于利用排比句式,并讲究用词的精巧。例如,在文章的第二部分中,有两处前后对应地讲到自己未老先衰、体弱多病的情况,前面说:“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这里特意连用了三个起转接作用的“而”字,意思是说三十多岁的人,本应身体健壮、精力旺盛,可是自己反而视力减退、反而鬓发班白、反而牙齿动摇,这就强调了作者的身体状况竟然是一反常规,过早地衰象毕露。后面再一次说:“吾自今年以来苍苍者或化为白矣,动摇者或脱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气日益微,几何不从汝而死也!”这里又特意连用了两个“或┄┄而”,两个“日益”,说明其身心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并强调了这日甚一日的变化速度。通过对这种迅速变化的描绘,作者内心的悲伤、颓丧之情就都充分地表达出来了。我们从文章表情达意的效果上,可以领会到作者高超的语言艺术技巧。 作者的笔法具有宛转、细密的特色。如第二部分,写噩耗传来时自己复杂、变幻的心理活动,说:“其信然邪?其梦邪?其传之非其真邪?”他乍听到噩耗时感到非常意外,非常震惊,以至怀疑消息的可靠性;接着由于惊疑、悲痛,而神智恍惚,感觉像是在梦里一样;待稍稍冷静一些后,他仍然觉得老成已死的消息是误传。下面他又重新思考、分析说:“梦也,传之非其真也?东野之书,耿兰之报,何为而在吾侧也?呜呼!其信然矣!”自己身边的书信为他切实地证明了老成的死是肯定无疑的,他只能去面对这残酷的现实了!作者具体、细腻地记录了自己接到噩耗后,从怀疑到确信的心理变化过程,这样做就更真实地反映出来他对侄子的骨肉深情。再如第三部分写到:他估计自己很快就会随着老成而死去,他说:“死而有知,其几何离!其无知,悲不几时,而不悲者无穷期矣。”他想到自己死后如有知,不久即可与侄子相聚;如无知,那死后也就不会再因悼念亡侄而悲伤了!作者利用死后有知与无知来表达与老成的真挚、深厚的骨肉之情,委曲、宛转,凄恻动人!
祭文是对死者表示崇敬和怀念的一种文体,一般着重叙述死者的功业。为了应和当时礼仪的需要,作者往往作一番无泪之哭,不哀之嚎,常让人感到浮而不实,夸而失信,缺乏一种感人的力量。但是唐代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和清代袁枚的《祭妹文》叙写的也是亲人之间的笃深情意,但它们一改过去祭文的矫揉造作,让人感到字字出肺腑,句句断肝肠,因而成为为祭文中不可多得的千古绝唱,和古代抒情散文中的不朽名篇,虽然两篇文章出自不同时代的不同作家之手,但把它们进行比较分析学习,还是大有裨益的。 一、从两篇文章的写作思路来看 《祭十二郎文》构思精巧,别巨匠心,它按照时间顺序,先通过家世的衰落颓败、幼时的孤苦伶仃及叔侄二人之间三别三会的叙述,抒写了两人之间的深厚情谊,表达了作者内心的悔恨无穷与抱恨终生。然后叙写十二郎之死,流露出内心无穷的迷惘和无尽的悲伤,最后通过对家属的吊慰、坟茔的迁徙及遗孤的教养的叙述,极写内心无处诉说、不可遏止的辛酸与悲苦,显得哀婉凄楚。行文自始至终以时间为顺序,以怀念为线索,层层推进,环环相扣,而又步步深入,随着叙述的展开,作者沉重的情感波涛,也一浪高过一浪,使人读完全篇不能不掩卷深思,为作者因失去相依为命的侄儿所遭受到的深切的精神悲痛而潸然泪下,并得到一种美的享受,构思严谨而富有变化。《祭妹文》同样也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从素文墓地入笔到病根祸源的交代,从野外同捉蟋蟀到书斋共读诗经,从胞妹送哥泪花流到把盏喜迎兄长归,从离家出嫁到中道回归,从侍奉老母以示其德到关爱长兄以显其情,从素文之死到后事料理,情节层递步进,感情波涌浪推,叙事历历可见,抒情句句见心,文情呼应,浑然一体。 二、从两篇文章的感情基调来看 情感是客观对象与自己关系的主观反映,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态度,“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庄子《渔父》)真而浓的情愫才能有动人心魄的美学力量。两篇祭文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个“情”字。《祭十二郎文》从家世的凄凉、身世的不幸,到父母的早逝、兄嫂的抚养,从自己的衰病到晚辈的幼小,这一切的一切都汇聚成一股感情的急流使作者百思萦集,情不能已。这里有怀念也有内疚,有哀愤也有感激,有期望更有辛酸,字字似血,句句是泪,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无任何修饰和渲染,无一字一句不是作者骨肉至情的的真切流露。拳拳爱心,绵绵深情,质朴洗练,哀婉久绝,成了祭文中难得的绝调,难怪宋代著名的大作家苏轼说:“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古文观止》也评论说:“情之至者,自然流为至文。读此等文,须想其一面哭,一面写,字字是血,字字是泪。”袁枚的《祭妹文》贯穿全文的同样是凄楚哀婉的情调。本文基本上采取了顺叙的写法,先写兄妹幼年情事,以“呜呼”二字,直呼亡妹,为全文奠定了凄切哀婉的悲怆基调,再写自己中年归家之后的景况,最后写妹妹病危和亡逝。末段连呼“呜呼哀哉”,更是直抒胸臆,坦言心怀,言辞哀婉凄切,情意缠绵悱恻,把对亡妹的思念、同情、内疚、哀痛统统浓缩在伤心欲绝的悲叹之中,叙事中寄寓哀痛,行文中饱含真情,同时还穿插些许景物描绘,从而使痛惜、哀伤、悔恨、无奈之诸多成分有机地揉和于一体,具有令人肝痛肠断的艺术感染力。 三、从两篇文章的抒情方式来看 从抒情方式来看,采用对话形式,是这篇《祭十二郎文》的一个重要特点。全文用了四十个“汝”字,用第二人称直呼老成,好像老成并没有死,正坐在他对面听他倾诉衷肠;又好像老成虽死,但其亡魂还可以听到他的家常絮语;他甚至向老成直接提问:“其竟以此殒其生乎?抑别有疾而至斯乎?”“其然乎?其不然乎?”来询问其病因、死期。这种对话形式,不同于一般祭文纯客观地歌功颂德,而具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和抒情意味,因而也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量,这种“汝”“吾”相称的叙述形式,让人感到好象同死者家常对话一般,读来显得亲切感人,也易于感情的抒发和流露。同时,本文在选材上一反过去祭文对功绩或德行的赞颂,而选择了作者和十二郎之间的个人家常琐事,从自己幼年丧父到叔侄相以为命,从漂泊天涯到未老先衰,从病情揣测到沉痛自责,从后事安排到吊慰家属, 虽多记生活琐事,但无一字不关“情”,无一句不含“情”,可谓事事关情,语语动情,句句系情,字字含情。此外,本文还特别注重虚词的应用以增强行文的感染力,使文章独具风采。全文多处反复运用了“而”“邪”“也”“矣”“乎”等语气词,不仅加重了抒情的语气,使表达的感情更加强烈,而且增强了文章顿挫有力的节奏,突出了作品的感人力量。 在这一点上,《祭妹文》同样是选择了生活琐事来抒发对亡妹的悼念之情,纯以散体形式抒写情感,文不加饰,朴素无华,在家常琐事的诉说中贯注着诚挚的骨肉之情,确是不可多得的杰作。从朝夕相处同捉蟋蟀,到比肩并坐相伴读书;从椅裳拽衣不放悲声,到衣锦归家瞠视而笑;从妹归母家服侍阿母,到治办文墨见其才学;从阻人走报宽慰长兄到终宵刺探兄妹情深;从绵啜盼兄挣扎应诺到临终之际一目未瞑;从轻信医言远游他乡到痛悔自责伤心悲绝,这一切都属于琐琐屑事,可正是这些极富情致的生动细节,字字凄楚,句句动人,让人睹之神伤,闻之心动,从而产生出追魂摄魄的魅力。“总见自生至死,无不一体关情,悱恻无极,所以为绝世奇文” (林云铭《韩文起》卷八)同时《祭妹文》的抒情方式还表现在借景抒情,情景交融上。例如一开始写素文墓地所在,“羊山矿渺,南望原隰,西望栖霞,风雨晨昏,羁魂有伴,当不孤寂。”羊山空旷荒凉,所伴者唯三死者而已。写自己祭奠时,只见“纸灰飞扬,朔风野大”,北风肆虐,其声啸,其势猛,其气寒,穿野掠坟,怎么不叫人萌生“身前既不可想,身后又如何知”的茫然之感! 总之,两篇文章作为祭文中不可多得的精品,尽管出自不同时期的不同作者之手,但是还是有颇多相似之处。因此,把这两篇文章对照阅读,比较分析,相信会从中受到不少启发的。 你可以去这里看 http://wwwruiwencom/news/14443htm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