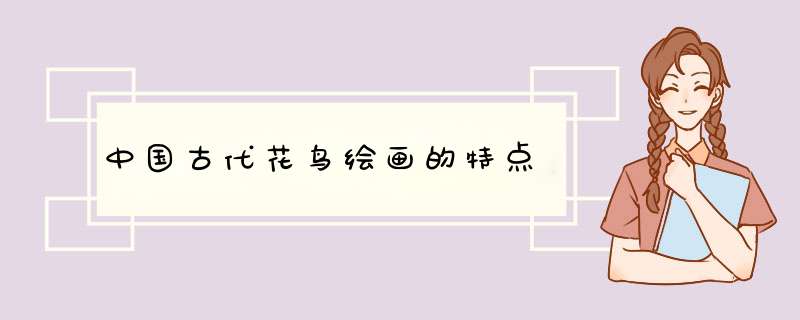
纵观艺术史,可发现花鸟画历来被人民大众,以及官僚机构的人士所喜爱,在政府的大立支持下,以及画家们的不懈努力中,使中国花鸟画得到空前的发展,民间画家们的道路虽然艰难,但他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前进,丝毫不亚于宫廷绘画,仍然大师辈出,著名画家比比皆是。而且风格独特,绘画题材更是胜于宫廷,技法多样。在长期的发展中,为了适应中国人的社会审美需要,形成了以写生为基础,以寓兴,写意为精髓的传统风格。
所谓写生,就是传达花鸟的生命力与各种不相同的特性。所谓寓兴,就是通过对花鸟草木的描写,寄托作者的独特感触,以类似于我国的诗歌当中的赋比兴的手段,缘物寄情,托物言志。所谓写意,就是强调以意为之的主导作用,追求像我国书法艺术一样淋漓尽致地抒发作者的情意,不因对物象的描头画角有束缚思想感情的表达。
中国花鸟画的立意往往关乎人事,它不是为了描花绘鸟而进行绘画,也不是照抄自然,而是紧紧抓动植物与人们生活的遭遇,思想情感的某种联系而以强化的表现。古代的花鸟画即重视写实,又非常注意美与善的观念的表达,强调它的怡情作用,主张通过花鸟画的创作与欣赏影响人们的志趣,情操与精神生活,表达作者的内在思想与追求。
这表现在造型上,中国花鸟画重视形似与不似之间,借以实现对象的神采与作者的思想。在构图上,古代花鸟画突出主体,善于剪裁,将求布局中的虚实对比与顾盼呼应,而且在写意花鸟画中,尤善于把发挥画意的诗歌题句,用与画风相协,调的书法在适当的位置书写出来,辅助以印章,成为一种以画为主的综合艺术形式。
画法上,花鸟画因为绘画对象较山水画具体又比人物画丰富多彩,所以工笔设色很具有写实色彩或者带有一定的装饰意味,而且写意花鸟画则对笔墨更加简练,更加具有程序性。宋代是花鸟画的成熟和鼎盛时期,在应物象形,意境营造,笔墨技巧等方面都臻于完善。北宋前期的花鸟画主要继承五代的传统,画法多继承徐熙,黄荃二体,而黄体“勾勒添彩,旨趣浓艳”的富贵风格更为世人所喜爱。北宋后期由于宋徽宗赵佶对绘画的特殊爱好,在其大力倡导之下,花鸟画以院体为主的流派进一步向工笔写实发展,笔法工整细腻,使工笔花鸟画达到了巅峰的水平。
北宋绵延到南宋宫廷,花鸟画创作长期不衰,并呈现多样化的局面,如工写结合,墨彩兼施,花鸟画树石,山水相配合等,形成了新颖多彩的面貌,不仅仅有册页小幅,还有长幅巨制,以北宋徽宗到南宋宁宗,理宗这一时期的作品为最多,风格多以严谨,精巧,工细见长。画面小中见大,意趣无穷。
材料方便与画面效果的表达,比如传统中国画颜料可以表现的淡彩效果,矿物色表现的重彩效果,加之盐粒等非绘画材料的结合运用更加丰富画面层次等效果,还可以引进国画材料之外的材料,如日本樱花水彩颜色,色相更丰富,色彩更艳丽,不仅使画面色彩有的创新也不失中国画颜料的晕染特征,
构图方面,满构图啊,局部构图啊,复杂化,平面化啊……
色彩方面呢,偏向与重彩发展,通过各种肌理制作,使画面更具冲击力……
意义:丰富绘画表现形式啊,拓展绘画发展空间啊……
第一,关注构图
每一幅作品的构图都非常重要,要注意实际情况,还要考虑主次关系。我们这幅画想要突出的重点是什么。一幅画牵涉的东西很多,花鸟的位置不一样我们的构图和侧重就会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我们在心上花鸟画的时候一定要多观察构图,合理布局,达到最佳效果。
第二,细节刻画
细节决定成败,一幅优秀的花鸟画的细节各方面也是经得起推敲和考究的。名家在画一幅花鸟画中已经在脑海中构思过千万次,下笔前已经胸有成竹,所以一气呵成。对各种细节也已经思考清楚,手随心到,想到哪就能画到哪,而且刻画的生动形象,细致入微。
第三,色彩
我们花鸟画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我们的颜色运用方面。比如说我们的泼墨画,只有一种颜色,但是我们利用这种黑色的浓淡来调配,也达到一种最佳效果。花鸟画也是这样,通过少数集中颜色的深浅运用,构成一幅极佳的作品。
第四,神韵
我们观察名家作画,仅用寥寥几笔就能很形象的勾画出作品的形象,而且很富有灵性,像是活了一样。所以我们在欣赏花鸟画的时候,可以观察一下画家在刻画这些形象时的神韵。
第五,共鸣
好的作品是可以引起共鸣的,我们必须要相信这一点。欣赏优秀作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体会一下作者创作时的情绪情感。
好了,这就是我们欣赏花鸟画时应该注意的几点,需要用心体会。
我在面对陈林画作时突然发现,此前评说过的画家虽然不在少数,却没有一位正儿八经画花鸟的。之所以这样,完全不是有意为之,潜意识里却应当有些原因。陈林接受《书画名家》记者访谈时表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人物画和山水画的承载能力更强,容易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花鸟画程式相对固定,更容易墨守成规。对于我等评说者而言,人物画和山水画多有变化,提供了更多的评说话语,从而有话可说;花鸟画缺少变化,可说的话也就多乎哉,不多也,甚至无话可说,所以留下空白。但是陈林很清醒,花鸟画不是容易陈陈相因吗?那就寻求突破,努力画出新的观念和新的图式。评说者很幸运,碰到了评说花鸟画的合适对象,感到有话可说,甚至不吐不快。
诚如陈林所说,相比人物画和山水画,花鸟画的稳定性显而易见。自唐代成为独立画科以来,两宋直至明代前期的花鸟画图式一直处于稳定不变的状态,大抵就是全景构图,以及从全景中截取部分景观而分化出来的折枝构图。稳定不变的图式结构与再现自然形态的创作方法密切联系,全景也好,折枝也罢,都是真实再现客观存在的花鸟景观,例如,南宋林椿的那幅《果实来禽图》,就是呈现了成熟的果实引来小鸟觅食的画面。晚明以来诞生的大写意花鸟画有所变化,以徐渭为代表的淋漓尽致、以八大为代表的言简意赅,都是以意笔取代工笔,简约了画面元素,丰富了画面寓意,却在图式上、以及与图式密切相关的叙事功能上没有质的突破。此后,花鸟画沿着工笔和写意两条技法线路向前推进,再也不见重大变异。有了一千多年的花鸟画发展史这个深厚背景,再来审视当代出现的新工笔花鸟画,包括堪称这个阵营中坚力量的陈林的画作,我们便感到价值不菲,意义非凡,如同张见先生在《定格迷局》中所说的那样:“陈林的理念是,叙述比再现更为重要。”
是的,《果实来禽图》叙述了“果实引来小鸟觅食”的事件过程,不能说不是叙事。然而,在陈林和新工笔画家们看来,叙事虽然是人所熟知的常用语词,此时却偏离了既定的语词阐释框架,进而引申为超越了视觉经验的一种创作观念。也就是说,陈林试图呈现的叙事性花鸟画面,与花鸟自然景观的客观再现已经大相径庭,他想对笔下的物象及其物象之间的组合做出描述,这种描述中渗透了主观意味,解读为超现实的逻辑关系,目的是要表现出衔接着传统笔法却又面貌一新的花鸟艺术世界。沿着这样的创作思路,陈林开始了他的不懈追求。大约是2002年,陈林先后推出《红豆角红蜻蜓》《红扁豆黄月亮》等画作,所呈现的画面与千年以降的花鸟画自然景观模式拉开了距离,从中可以感到强烈的主观重组意识和借鉴而来的构成倾向,可以感到画家已经发出了求新求变的明确信号。其后几年,陈林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攻读美术学博士学位,在北京与悄然兴起的“新工笔”画家群有了频繁接触,并且一拍即合,加速了求新求变、特别是在创作中强化叙事功能的步伐。到了博士毕业的2006年,陈林笔下的禽鸟身份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物象,而被赋予具有现代意义的叙事姿态。这些禽鸟面对新鲜的、眼花缭乱的人文景观,正在细致观察,深入思考,准确判断,努力沟通,从而形成识别性很强的新工笔花鸟画风貌。
从2006年到2008年,陈林屡屡以《误入》系列参展。虽然现今找不到属于这个系列的太多作品,我还是对此充满兴趣,并确信这批作品在他加入新工笔阵营之初具有标志性意义。仅仅是这个带有悬疑意味的画题,包括那些同样带有不确定因素的子画题如“疑”、“恍”、“探”、“巡”等,就能激发旁观者的追问意愿和打探究竟的冲动。陈林果真是“误入”吗?应当不是,他以坚定的步伐走上“新工笔”的创作道路,无疑是蓄谋已久,掂量再三,准备充分。既然不是,陈林仍以“误入”冠名,乃是运用了灵活机动、以退为进的叙事技巧。毕竟处在冲撞传统工笔画法的尝试阶段,有所疑虑的画题为踏入新路留有很大的余地,展示了低调的身段,表达了谨慎的态度,发挥了缓冲的作用。即使前路受阻,抑或此路果真不通的话,反正有言在先,折回头重新探路就是。在这样的叙事背景下,《误入》系列里的那只雉鸡粉墨登场,表演十分精彩:它来到了一个通向远山的陌生路口,有时东张西望,显得四顾茫然;有时索性把头躲藏起来,遮挡着不能确信是否“误入”的尴尬表情。它心中正在盘算着未来的走向,前面的路还有多远?前面的山是我的归宿吗?其实,它知道自己没有走错路,只是作为开拓者,需要多思索一会,多权衡几次,以便找到准确无误的方位。循着这只先锋雉鸡的足迹,陈林的“误入”一发而不可收,不仅快步跨入先贤大师们的经典画廊,还径直闯入了中国画家很少涉足的西方名画禁区,从古今中外的文化冲突中寻找融合的可能性,延伸着“新工笔”的叙事旅途。比如那幅2006年画成的《梦中宣和·芙蓉锦鸡》,宋徽宗笔下的锦鸡正在诉说远离尘嚣的寂寞,经由几何体的折射呈现为顾影自怜的情状,失去了昔日拥有的五色斑斓的华贵和回眸翘望的典雅。陈林派出的麻鸭面对着时代变迁,沧海桑田,感到始料未及,一只脚爪不由自主地向后翘起。我们隐约听见麻鸭的慨叹,它踌躇于自己是不是走错了地方,而不管“误入”与否,锦鸡头上闪烁的光环终究有些恍如隔世,不可能永葆青春。又比如2008年画成的《凡·爱克的婚礼》,陈林派出两只冠鹤“误入”这幅尼德兰画家的名作,用以置换原画中的阿尔诺芬尼新婚夫妇。冠鹤已经意识到自已扮演着不速之客的角色,但是,既来之,则安之,事已至此,只能勉力掩饰内心的忐忑不安,融入略加改造的崭新环境,营造与婚礼仪式相适应的和谐氛围。应当承认,陈林派出的几批禽鸟都很胜任,它们打着“误入”的旗号,顺利完成了趟路和试水的光荣任务。它们的叙事过程充满了戏剧性,以疑问和悬念开场,以文化冲突转向文化融合的圆满结局落下帷幕。与此同时或者稍后一些,陈林还画出一大批性质类似的作品,诸如《偶遇韩干》《盛宴》《致维米尔的信》《镜中的玛格丽特》《怀斯的阳光》《波提切利之舞》《莫兰迪·误入》《游记·里斯特》《飞过爱德华·霍珀》等等,都可以视为巩固胜利果实之作,共同证明了此路并非“误入”,前途畅通无阻。
经过三、四年时间的创作实践,一种个性鲜明的新工笔花鸟画图式从陈林的笔底应运而生。在这种图式中,前景的禽鸟具备了灵性和知性,具备了审视与思考、分析与判断、回眸与展望的功能,它们与身处的虚拟场景组成了淡化矛盾、促进沟通、达成和解的叙事结构,从而摆脱了再现自然形态的传统程式,洋溢着浓郁的时代审美气息。此时,陈林对于精心谋划的既定方向愈加感到自信,不再是低调的“误入”,转而是执着的“寻觅”、深情的“迷恋”和欣慰的“共鸣”。到了这个阶段,陈林画作的叙事主题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不再探讨“新工笔”的可能性,转而展示“新工笔”的丰富性。2010年,陈林先后推出《寻觅十二钗》系列、《瓷恋》系列和《天工之恋》系列,派出各类禽鸟广泛寻访,涉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领域,深入梳理新工笔花鸟画与历史文脉之间的传承路径。很显然,与“误入”相比,“寻觅”的内在涵义更为积极主动,清晰表明了方向已经明确,目标就在前头,完全没有是否走错路的疑虑。《寻觅十二钗》系列是非常值得琢磨的作品,各色禽鸟摆出各种各样的寻找姿势,它们正在努力寻索的对象,在第一幅中只是空空如也,而在随后各幅中不过就是一串很平常的饰物。这个系列颇多耐人寻味之处:首先,“十二钗”的画题和那些画中饰物的点缀,共同给出寻觅目标上的提示,无论是《红楼梦》里的大家闺秀,还是珍珠手串与其他古典物件,无不富有强烈的历史文化指向,指引着苦苦寻觅的禽鸟们奔向前方,奔向传承文脉的深层空间。其次,那根用于串联饰物的红丝线,则给出寻觅关系上的提示,红丝线很细,但是很结实,很牢靠,牢固捆绑着各色禽鸟与它们的标的物,紧密牵引着新工笔花鸟画的来龙去脉,既是传统的变异,也是传统的衍生。再有,大同小异的画作竟然接连画出12幅,又给出寻觅立场上的提示,就是乐此不疲,就是不厌其烦,数量上的积累传递了不容置疑的叙事语气,宣告了不达目的、势不罢休的坚毅态度。遵循《寻觅十二钗》系列所提供的叙事线索,《瓷恋》系列和《天工之恋》系列朝着扩展领域和强化情感浓度两个方面深入行进,使个性突出的新工笔花鸟画图式趋于丰满,趋于成熟。在扩展领域方面,两个系列分别引入了瓷器和纺织器械,两者都是中国传统手工艺的杰作,而前者简约、纯净、温润如玉,更加贴切本土文化精神;后者带有几何构成倾向,更加衔接西方艺术理念,尤其是从未入画的后者,为工笔花鸟画的题材范围增添了新的审美趣味。在强化情感浓度方面,禽鸟们已经认定了心仪良久的对话物象,进而陷入深深的迷恋之中,这就增添了浓郁的情感色彩,这些禽鸟的叙事状态随之转换,或者愈加亢奋,有如《瓷恋·歌》中放声咏唱的大麻鳽;或者愈加心无旁骛,有如《天工之恋·牵》中咬定丝线不松口的两只火鸡。及至2011年,陈林的《共鸣》系列面世,把禽鸟与各种各样的民族乐器、西洋乐器并置在一起,不仅再次扩容了访问对象的范围,广泛调动了题材元素的参与意识,尽情拓展了画面构成样式的想象空间,而且开启了古今交流、中外碰撞的双重对话机制,体现了坚持不懈的学术追求和所达到的叙事深度。
大概是2012年以来,陈林每年都要画成几幅《畅神》系列的作品,至少持续了四、五年。其间,他还在画着《乐逍遥》系列、《逍遥游》系列和《醉潇湘》系列。我们看到上述画题,似乎看到了陈林派出的禽鸟们正在自由自在地翱翔,看到了一种更为宽松、更为放逸的叙事风度。此时,原先画作中那些起到分割块面作用的转角、扶梯、窗棂、屋檐等建筑构件已然退隐,那些与中外经典图像相关的拼贴痕迹也被悄然抹去,画面空间显得相对简净和恬淡,减少了舶来的构成倾向,进行了较大限度的还原性处理,为禽鸟的往返畅游营造了良好氛围。比如《畅神·潇湘之思》《畅神·半千之韵》《畅神·鹊华之秋》等作,没有局部镶嵌名人名画,而是全景式地展开了董源、赵孟頫、龚贤的山水画卷,处于同一时空的禽鸟们顾盼生姿,两者之间没有构成并置关系,而是相互包容,荣辱与共。《畅神·半千之韵》里的番鸭借助那座引桥,准备进入画卷,《畅神·鹊华之秋》里的角雉悠闲自如,干脆连引桥都不要,即将穿梭在宁静、疏旷的山水怀抱当中。还是《畅神·得鱼》更有意思,那只琴鸡闯入了一处文人书房,看到书桌上摆放着画有芦雁和墨竹的册页,以及压在上面的线装画谱,激动得难以自制,腾空而起,展翅高飞,毫不理会自己本是天外来客。由此看来,从《畅神》系列开始,陈林再次转换了创作重心,他的禽鸟们也再次转换了叙事话语:关于创新图式的形式感的探索,可能会暂时告一段落;关于传统文化内在精神的探究,相比之下则显得更为重要。
从“误入”到“畅神”,陈林经历了与笔下禽鸟朝夕相处的愉快的创作旅程,经由他的主导和有效掌控,所有的禽鸟成功实现了一次华丽的转身,不再是自然景观中步入画面、从而被真实再现的客体物象,它们肩负着画家的嘱托和重要的使命,成为画面的叙事主体。我们一面倾听着这些禽鸟的呢喃细语,一面见证了新工笔花鸟画所取得的显著进展。接下来,这些感动过我们的禽鸟们将要飞向何方,让我们满怀期待。
2018年8月
前言
中国工笔花鸟画源远流长,色彩与线形结构是工笔画的主要构成之一,现代工笔花鸟画的语言形式在近几年随着我国对外联系的日益增长,在各国与我国的文化艺术的交流频繁中已经不可避免的受到西洋绘画的冲击。如何较好的与中国传统绘画结合,吸取优良传统而发展自己的独立个性已经成为了现代画家们为之努力和创新的首要目标。画家们不仅要延续古代优秀传统,也要对这一画种进行创新与开拓,赋予其色彩与形式的独立审美价值和表现性功能。这些问题使得现代工笔花鸟画画家,在对传统的继承突破中形成了现代工笔花鸟画的多元形,为以后的工笔花鸟画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祭奠。
绘画中的主要表现语言就是色彩和线条,它们是构成绘画艺术风格的基本要素,它一直是给人视觉冲击力首要手段。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绘画,色彩与线条在画面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始终是重要的构成因素。在中国工笔画中更是成为了重要表现手段。在现代西方的油画、水彩等各种绘画冲击下,中国工笔花鸟画不再拘泥于传统的有限色彩和构图形式,开始结合中国的成熟墨色,融会西方色彩运用找寻现中国现代工笔花鸟画的独立语言。
在构图上,全景式的作品日益见多,许多作品不再把花鸟从环境中抽离出来,而是将其置于它应有的生态环境之中。作品内容丰富,场面宏大,构图饱满,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受西画透视画的影响,许多作品着力于实现纵深的层次。而另一些作品,则从工艺美术及民间艺术中汲取营养,追求一种带有构成因素的抽象意味,在写实与装饰之间求平衡。
色彩上来看,现代工笔花鸟画家开始努力避免色彩的单一性和模式化,更新了“随类赋彩”的观念,改变了以“分染”、“罩染”为基本手段的“三矾九染”的过程,开始吸收西洋画的用色方法,以统一色调处理画面,注意黑白关系,色相对比,冷暖对比等关系,使画面丰富又不失统一。与传统工笔画家不同,现代的画家大多都经过美术院校的学习,汲取了许多西方的绘画营养,有着坚实的造型基础和色彩修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写实再现能力,提高了工笔画汲取现实生活的视觉能力。再加上对色彩的感悟,促使传统工笔画的色彩向现代发展
随着时代的转变,现代的工笔花鸟画画家更新了自己的创作观念,拓宽了创作题材,榕树、杂花、田野、蔬菜、水果、珊瑚等在传统绘画中不曾出现的对象也成了创作的题材。还有一些画家从自己画面装饰性的要求出发,大胆夸张变形,不受物象自然形态的束缚,如:陈之佛的《月雁图》,陈新华的《乡土》等都极具个性。
中国的传统绘画一直追寻的是求得人们在情感上的共鸣和满足,而不是追求绘画对象的现实性。这就与西方的追求写实性绘画相反,中国绘画的色彩被赋予了更多的主观意识,希望从中得到的是精神领域的愉悦。由于现代工笔花鸟画在题材内容、表现手法以及工具材料等的方面的新拓展,使得新的审美境界逐渐形成。以扩展空间来扩大花鸟画的感染力与表现力;变小情趣为感人意境,通过视觉冲击力触动心灵;画面内容的丰富提升自身的艺术感染力;抽象装饰性作品恰当的传达了现代人的审美趣味。
在中国传统文化下,在代代相传的艺术实践中,工笔花鸟画取像单纯,多为主体描写。造诣诗情化,借助联想与想象构筑充满感情色彩的诗境,以求“画外有情”。表现手法格式化,运用程式化手法造型、上色、布局、体现一定的装饰性。在追求“似”与“真”的前提下,表现对象的生命与特质,令其吁吁如生。反对被动的描绘花鸟,强调观察对象时内心的触动,创作则是对事物的感性寄托,唤起观众对生活的内心感受。发扬培养高尚情操与生活理想的高级艺术。
中国花鸟画在宋朝就已经成熟了“黄荃”父子便是工笔重彩花鸟画成熟时期的代表。到宋朝和元朝,不仅“勾勒着色” 一体为主流,而且又出现了纯以彩色的“没骨”和纯粹的“白描”体格。现代的工笔花鸟画不仅继承了优秀的传统,并得到了创新。很少有人再拘泥于传统的“折枝”“丛卉”,却取资于山水画或使用半截断开、不露天地。但画面并没有忽视花鸟作为主体的地位,明显的以大观小,使对象处于应有的生态环境中。依然重视造诣诗情,不再依赖花姿鸟态来引起观众的感兴
画家开始注重表现晨光、月色、露气、风雨下的花鸟情态。如李魁正的《晨露》、《春情》等。而且绘画技法不再单纯,结合中西,包孕古今。有的还借鉴日本画的精致雅淡。传统的勾勒、设色、白描等被许多画家综合运用。云母、日本色、广告色、炳烯等,以及撒盐、冲水、做纸等也都变成了一种表现手法,也以写意为旨,写实为体,以装饰为用,谋求全新的气氛与肌理感。工具材料的革新使现代工笔花鸟画的表现技法不断得到丰富,扩展了花鸟画的意境。
北京的于非阁、江南的陈之佛和巴蜀的张大千。于非阁的“勾勒着色”得法于两宋。陈之佛的工笔花鸟画也以“双钩着色”为主,受到日本绘画的影响,元代钱舜举的“疏淡含精匀”宁静淡雅的风格。张大千则自成一体,善于继承古人的好传统。田世光和俞致贞又受教于于非阁与张大千
陈之佛在工笔花鸟画领域的独到之处,在于他能在古旧里出新,他继承了宋朝时期的传统,借鉴传统中的造型、意识,造型以工整写实为主,在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将图案的装饰手法和日本的绘画设色特点相结合。画面追求唯美,表现雅静与淡泊之美。如:《雪雏图》、《月雁图》等。他的画依照不同的物象,不同季节,不同感受,采用不同手法画树杆,有的用皱檫渲染,显得挺拔有的用水渍法,运用水渍色彩的浓淡变化,显见苍润陈之佛的工笔花鸟画带有明显的装饰性。在描绘花鸟的客观基础上,恰当的运用了意象、夸张、变形的装饰手法。由于他在画面上运用了许多的装饰性手法,使他体现出了自己独到的个性与现代特征。中国画中的积水法,在其之前已经有很多画家运用,但他将这一“特技”普遍化,灵活去运用。自然流淌而渗化的水渍痕,具有着现代设计的肌理感,将要表现的内容与画面情调统一起来,既有了物象的质感又有了材料的表现。陈之佛的花鸟画色彩运用微妙,他在传统基础上吸收了许多外来的影响,清淡典雅而十分统一,在设色方法上,保持了传统的“三矾九染”,又能根据实际画面需要灵活运用。以色彩的淡薄来表现对象的远近、虚实,以及对象所处背景。
金鸿钧的花鸟画多方面收益于田世光、俞致贞、李苦禅和王雪涛等人,使金鸿钧在创作中深入领会了工笔重彩花鸟画的传统,继承了观察生活,把握大自然的认真、严肃的创作精神。在他的画面中虽是工笔画,但有着大写意的气势。用线,特别是白描同线,是工笔花鸟画中必不可少的造型手段和主要技法之一。在工笔花鸟画中,线要表现物象的结构和轮廓,要表现质感,要表现光色,要表现意境。前三者是客观表象,后者是主观情态。缺了前三者之一,便会失去视觉形象的完整,而缺了后者,便会失去艺术的感染力。从而用线表现情意是尤为重要和必不可少的。杨悦浦在为《金鸿钧新作选》所写的序言中称赞他的用线:“《牵牛》中的线的功力令我着迷,那用水分充足的深灰黑色勾出的铁蒺藜,我曾把全画面的每一根线都看了一遍,想搜索出一处败笔,结果没有找到,反到为在运笔用线之轻松、随意、流畅,以准确地表现了铁丝之质感和弯折、剪断、连接种种变化这种深甚功力而惊叹不已。”说明了金鸿钧的观物的细致和用笔的精微。《万紫千红》一画以偏冷的红色调统一整个画面,几组花分为曙红、紫红、玫瑰红、等色,而少用朱镖、橘黄。在画面的层次表现上依靠了色彩的轻重虚实变化和双勾、没骨两种画法的穿插结合解决。
《牵牛》、《红满香山路》、《枫叶白鸽》等作品都是赋予生活现代气息的作品,在摄取形象和表现手法上都显示着深刻的创作观念。前代画家在花鸟形象的择取上有一种规范化了的审美习惯:“凡花入画者,皆剪裁培植而成者”而《牵牛》、《红满香山路》等则是打破了传统审美习惯,截取生活环境中的一角,经过创造的新意象、新审美表现,就连原不给人美感的铁丝网,与白色的牵牛花,等组合在一起,也形成了有节奏的画面、和韵律。《牵牛》中墨绿的花用积水冲色法画出,最后用金色勾出叶脉,使画面有了装饰性的光泽,《枫叶白鸽》中的水泥地很难用传统技法来表现,金鸿钧用撕碎的泡沫塑料蘸上色彩在底子上拍打出斑点状,而后用统染方法来表现。
李魁正受教于俞致贞和田世光,俞致贞和田世光的花鸟画重在传统,善于提炼,传神,讲笔法,浓色泽。然而这种风格的确立,即没有艺术表现上的特长,也同时带来一些局限性。李魁正在跟随他们学习的同时在自己的风格方面摆脱了法式的束缚,树立了自家的艺术个性。在《金秋烁烁》中闪烁光芒的老干,把变形有序的果实映照得硕实累累,构图为平面分布,屏弃了大背景,冲破了古法的禁忌,由于加强了绘画效果,而更能使观众进入绘画的主题,感受灵光普照的精神世界。他弱化用线,强化色彩,形成他自己的“新工笔画”,孕育着“现代没骨画”的诞生。以新工笔画为主的《清气》,实际上已经是“现代没骨”了,它彻底扬弃了用线勾勒,在渍染中表现对象,甚至不乏水墨大写意气势。并且还充分发挥了色彩冷暖对比转换的精制表现力,由此李魁正倡扬并推出了“现代没骨画”,这一推出的风格随源于传统工笔没骨,但更丰富了色彩,加强了统调增加了光感以新工笔花鸟画中层层渍染、冲染、接染喷流等新技法,新语言技巧,使光色形韵进一步从双钩墨线中解放出来,在造诣抒情上取得了幽雅自然的效果。从《皎洁》、《生命》、《秋艳》、《晨露》,可以看出,他的现代没骨法中兼工带写,无线有骨,色调同一和谐,光感强烈而柔和,肌理丰富而别致,情韵精而圣洁,发挥了没骨花鸟画的特点。从“新工笔”到“现代没骨”,李魁正通过线的隐没和光色的发挥,更新了花鸟画视觉效果。
王广华从事花鸟画接近二十年,他的作品在意境上也相对传统有所变化。有的作品比较华丽,像海棠小鸟、山茶双鸽、曹洲牡丹一类。有的则比较清雅明快,如《白玉点韵》的昙花、《散点绿地》的荷花等。画面比较开阔,注意环境的衬托,意境清幽深远,《生生不息》,作者把握住了较大场景,处理多种树木花卉,都能繁简、疏密得益,大体与局部关系恰当,并无杂乱堆积之感。
在现代工笔花鸟画的探索中,已经不可避免的受到西洋绘画的冲击,如何较好的与中国传统绘画结合,吸取优良传统而发展自己的独立个性已经成为了现代画家们为之努力和创新的首要目标。现代工笔花鸟画画家的对传统的继承与突破形成了现代工笔花鸟画的多元形,为以后的工笔花鸟画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祭奠。
参考书目:《美术》、《国画家》、《李魁正泼墨》、《美术史》、《金鸿钧新作选》、《陈之佛画集》
《中国美院精品课程范本·工笔花鸟》内容简介:乘艺海风云,踏华光涯岸;工笔花鸟画流经岁月鸿途,勃然卓立于世界艺术之林。在现代,工笔花鸟画或有吸收装饰画法,或有吸取西方明暗处理,或有借用油画水粉的色彩运用,在技法范畴中呈现出多元的态势,而传统始终被奉为至上的珍宝。在开放的思绪里,我们已可预见工笔花鸟画一个极为宽广的技法运用天地。
明代初期,因太祖朱元璋对南宋院体画风青睐有加,花鸟画大致延续了宋代院体工笔画风格,没有新突破。明宣宗朱瞻基同宋徽宗一样,雅号诗文书画,尤好花鸟画。他在位期间,宫廷画院的花鸟画风格面貌多样,有延续南宋院体花鸟画艳丽典雅风格的工笔重彩画家边文进,有出自北宋徐熙野逸风格的没骨画家孙隆,有笔墨洗练奔放、造型生动的水墨写意画家林良,还有精丽粗健并存、工笔写意兼具的画家吕纪。不过,这些风格面貌大多沿袭宋代花鸟画,并无根本突破。从意境与格调方面看,这时期的花鸟画比宋代院体花鸟画略逊一筹。事实上,明代花鸟画的大突破直到中期以后才出现。
明代中期,文人越来越多地参与花鸟画创作,他们的创作风格一开始就与院体画大相径庭,最有代表性的是吴门画派。吴门画派的成就主要在花鸟画方面,代表人物有兼擅人物、山水、花鸟的“吴门四家”,即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沈周与文徵明主要延续宋、元文人画传统,疏简而不放逸;唐寅与仇英主要吸收南宋院体画风,并融入了时代的精神特质,体现了当时的市民趣味。他们的花鸟画在吸收前代大师成果的基础上发展出鲜明的个性特征,在美术史上颇有影响。
严格地说,吴门画派的花鸟画是对前代的延续,并没有开宗立派的意义。然而,到吴门画派的弟子一代,花鸟画在陈淳、陆治、周之冕那里结出了果实。陈淳早年习元代绘画,后学于文徵明,花鸟、山水兼擅。他将书法和山水画笔法融入花鸟画,运用水墨的干湿浓淡和渗透,巧妙地表现花叶的形态与阴阳向背,简练放逸又不失法度,开写意花鸟一代新风。如果说陈淳的大写意花鸟充分表现了笔墨的特征与画面的形式感,那么徐渭的作品泽充分发挥了大写意花鸟托物言志的功能,洗胸中块垒,抒澎湃激情。在绘画语言风格方面,他吸收宋、元文人画及林良、真州、陈淳的长处,兼融民间画师的优点,同时将自己擅长的狂草笔法融入绘画。在其笔下,梅兰竹石被赋予了他强烈的个性,以狂怪奇崛的姿态傲视万物。他是第一个使用生宣作画的花鸟画家,利用生宣良好的吸水性来控制画面水墨渗化效果,表达特殊韵味。他还以泼墨法作花鸟,用笔墨的纵横捭阖表达自身的愤懑情绪。徐渭开创了大写意花鸟的新体派,八大山人、石涛、扬州八怪、海派乃至齐白石都曾受其影响。他的成就超越了早于他的陈淳,后世将二人并成为“青藤白阳”。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