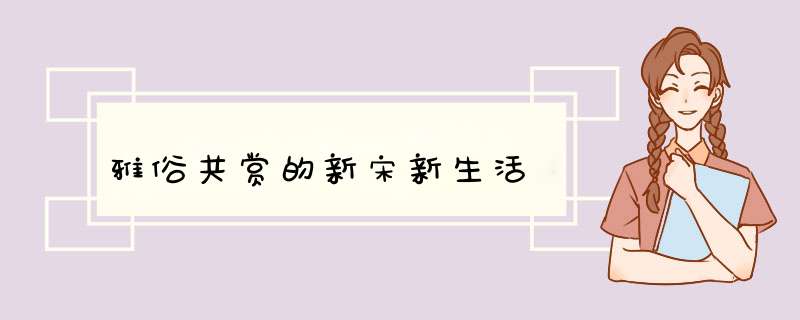
徐訏的创作和他的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研究过柏格森、弗洛伊德,也了解东西方哲学和宗教。徐訏各个时期的主要作品都蕴含着明显的哲学、心理学背景,因此,思辨特征贯穿其创作的始终。这种思辨特征以独特的方式展现在其作品中。如:现代文明与自然朴素状态的矛盾、精神自由与现实诱惑的两难对立、爱与美的憧憬、生与永生的烦恼等等。这无不成为作者借以展开小说情节的重要动机。并非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徐訏小说不过是些离奇曲折动人的故事,因为抽象的哲学命题与思辨过程要靠具体的故事框架来安放,繁复的感觉意象与心理描绘也需要情节来串联。可见,徐訏的思辨是一种与浪漫相结合的思辨。他以浪漫的爱情故事为载体,渗透进对人生的感悟,在其情感宣泄的微波巨澜中,总是浸润着一种哲理的思辨。
《鬼恋》可算是浪漫抒情与哲理抽象的奇妙结合,既有诗化了的奇幻与神秘,又有心理分析的体验与感觉,还有哲学上的思辨与彻悟。在作品中,叙述者“我”邂逅一位自称为“鬼”的女子,于是,“我”与“鬼”有了一场关于美和丑等哲学、美学、人生诸问题的讨论。随后,“我”便神魂颠倒地去求爱,也曾醉生梦死地失恋,甚至还虔诚地忏悔修行过,却始终突破不了人与鬼之间的屏障。接下来,“鬼”自白:她的“神秘的生命”是缘于“生成的鬼”。对此,“我”好像茅塞顿开,又仿佛迷离恍惚。最后,“鬼”远行,“我”则留在了“环境的空虚和月光的凄凉”之中。至此,一种人生本体论的抽象就己经完成。读者也就在这奇幻的故事与浪漫的柔情之中,看到一种哲学上的达观和尘世上的彻悟。因为它在揭示:人与“鬼”之间,是理想与现实、人性与神性、有限与无限的差别,是美丽与丑恶、高贵与庸俗、深刻与肤浅的差别,无论是爱情的力量,还是大自然的洗礼,都无法跨越两者之间的鸿沟。相反,只是完成从人到“鬼”的超越过程,抿灭肉体归入灵魂,牺牲个人皈依上帝,变人格为神格,才能实现人神合一的永恒,走进理想天国的神话世界。这无疑是一个纯粹由作者玄想出的爱情故事。但其中真正引起我们兴趣的则是另一事实。既然鬼决意脱离现世离群索居,却为何又演出与“我”交往的一幕呢?这恰恰体现着作者的良苦用心。与其说《鬼恋》是一个情节曲折扣人心弦的恋爱故事,还不如说是以离奇神秘的方式对现世与永恒进行思考。在“我”与“鬼”的往来过程中,始终交织着出世和入世的痛苦情结。“我”的奇遇本身,不过是陪衬与背景,而“鬼”的超脱,才是主旨之所在。情节自身的偶然性及不近情理性被人之命运的不倦探求掩盖了,人们不由自主地从故事中走出来,面对一个远为烦难而棘手的问题:到底是执著于现世,还是求助于永恒超脱绝对精神的自由究竟应当从哪里开始,难道仅仅依赖于简单的摈弃人生就能轻而易举获得吗历史上众多的先知圣哲早己对有形的现世发出过感慨叹息,而浪漫派的大师们也正是遵循上述道路拯救心灵的。《鬼恋》所强调的,则是在从有限跨入无限这关键的一步中,充满了难言的痛苦和悲伤。倘若说通过精神的玄想把人带入一个超凡脱俗的境界还不乏可能性的话,那么要想真正从生机盎然的尘世中消失退隐就显得艰难得多。《鬼恋》描写了这种困难,描写了火热的生命走进淡漠无为之门时体验到的苦闷难当。所谓“鬼”的超然物外,只不过构成了其行为的一部分,在“鬼”的潜意识中,仍然因世俗的欲望而倍受煎熬。“鬼”时常无法忍受尘世的寂寞与孤独,不得不在夜晚出来寻找着什么,并对与“我”的交往异常珍视,无法割断友谊的纽带,这构成了她与尘寰的脆弱联系。可另一方面,她对尘世间的一切又采取鄙视态度,多次声明人鬼之间的绝对界限,发誓永远不再返回人间,于是形成了感性的欲望和理智的追求间的一种内在紧张。小说中的“我”曾这样分析道:
那么她为什么要旅行正如她所说的是为我的健康与正当的生活么是的,但是最究竟的或者还是对自己情感的逃避。这时候使我顿悟到她内心的痛苦是有过于我了。因为我对于自己的爱,可以无底的追求,而她则只能无可奈何的讳避,其中痛苦的分量我同她是难以比拟的。我可以对她倾诉,而她则没有一个人可以谈及,只能幽幽地埋在自己的心中。
没有比这更能说明“鬼”的矛盾的心灵状态了,小说的魅力也由此而生。向我们揭示出走向永恒之路时的生之诱惑是多么难以抗拒。当然,在这出世与入世的反复较量中,“鬼”最终还是战胜了人性中的脆弱,毅然踏上了逃离人世的旅途,但却把“鬼”的心灵深处的极度痛苦,留给读者去品味。人生是什么永生是什么搅得人心烦意乱,灵魂不能不在这千古常新的题目面前而感到茫然,也许,答案本身就存在于人类自身的永无休止的求索中。
徐訏曾说:“我是一个最热诚的人,也是一个最冷酷的人,我有时很兴奋,有时很消沉,我会在狂热中忘去自己,但也有最多的寂寞袭我心头。我爱生活,在凄苦的生活中我消磨残缺的生命;我还爱梦想,在空幻的梦想中,我填补我生命的残缺。在这两种激撞之时,我会感到空虚。”[1]矛盾的撞击让徐訏沉浸在深沉的思考之中,作品便流露出思辨的色彩;而梦幻的填补,人生的思考往往又以宗教作为了皈依。因此,徐訏作品的思辨特征又与宗教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是其小说思辨的又一突出 特点。
《彼岸》以一种充满诗意的笔触,抒写其对人生极具哲理色彩的探索。作品以第一人称的视角,通过主人公“我”在爱情之路上的坎坷经历,抒写其在寻觅人生真谛之途中的种种具有哲理意味的思索。
小说中的“我”为所深爱的女子抛弃,从此不再相信还有爱情,在虚无状态中走向沉沦。在准备蹈海自尽时,却遇曾经照料过他的护士露莲,她真诚的爱拯救了他。在舞会上,他邂逅了过去的女友裴都,鬼使神差地凌晨四点赴约与裴都聚首,悲痛欲绝的露莲驾帆撞向岛岩葬身于大海,他陷入无尽的追悔、沉痛的自责中。在精神的极度苦痛中,他来到一个孤独的小岛上,与一位灯塔看守人相伴看守灯塔。在他虔诚的祈祷中,露莲在大海上显现了,他每天与她在海上会晤。他被困在风急浪高的孤岛上,幸为老人所救,露莲却再也没有出现,他在无底的仟悔中想毁灭自己,却又遇到海外归来的旧识“你”,在热吻中他又获得拯救,却觉得失去了自由。他又回到灯塔侍奉大海。小说并不以故事情节的叙述为主,在对种种人生问题的反复中推展了情节。
小说以“彼岸”为题,透露了作家对彼岸世界的思索与期盼,作品在对主人公“我”的坎坷人生的描写中,突出地袒露人物曲折丰富的心路历程,主人公“我”的所遇所思,使作品中分别展示了佛教、基督教、道教不同的宗教境界。小说中出现的高僧现
象身上,充满了佛教的精神。在“我”初遇这位白发白髯的高僧时,这样描写他:
高僧告诉我世界的虚妄,高僧告诉我不求外界的统一,但求内心的谐和;高僧告诉我神不在世上,也不在经内,而在自己的心中;高僧还告诉我真正的生命宇宙终极的谐和,世上的生命原无价值,听凭取你的取你,听凭吮你的吮你,蚊蚋与英雄在他是一样的幻觉,生命的历程就是克服肉体的要求,等肉体的痛苦与心脱离,灵魂的存在才与大自然融化。
“我”也这样探索人生境界,“我”失落了爱情走向堕落后,来到一个充满基督教色彩的小镇。这个小镇充满了安逸和幸福,然而受尽了人生苦难的孤独旅人“我”,却离开了这个小镇,昭示着主人公最终不能皈依基督,“我”还是注重对现世的叩问和探索,仍然难以摆脱日常的感情,难以靠近上帝。当在疯人院传道师与“我”谈上帝灵魂的问题时,“我”却不以为然,觉得他的教导是可笑的,认为“解救我肉身的痛苦何用上帝”,“上帝给我们一颗没有用的灵魂,这不是很多事么”“我”终究没有信仰基督,而一切顺其自然。
作品中的“我”最终选择了陪伴锄老在海岛上为灯塔守的人生。灯塔看守人的生涯是孤寂而清幽的,那个离海岸六哩的灯塔,“那面清净虚寂,明月清风,海浪云天外一无他物。这位守护灯塔己有四十年的锄老,做过渔夫,当过舵手,他关心的是海,注意的是海,心中只有海,他把自己的精神与海同化”。《彼岸》通过主人公“我”的坎坷人生经历的描写和心路历程的揭示,使作品完成对人生的多层次的思辨,因而借助对神人合一的精神本体的哲学思考成为徐訏小说思辨特征的又一体现。
如果说思辨色彩弥漫在不少小说之中的话,那么,这种思辨的实体性,内容则是与生命有关的生命哲理。关注生命,这是小说创作乃至所有文学艺术的神圣命题。
徐訏在小说文本中阐释的生命哲学的价值在于它真实地反映和表达了人的生存矛盾,既包含了生命历时性的智慧,同时也包含了生命共时性的智慧,寓示着徐訏对终极关怀的独立思考。徐訏对生命和存在的超越性思考,对心理世界的宏阔而幽微的探寻及在艺术表现上的复杂变异和对各种文化因素的整合,都构成了他与同时代大多数作家完全不同的艺术追求。这种追求甚至使徐訏形成了自己的语言体系,他因此在文本中反复地写到生命,对生命的关注,对生存的思索,对人的文化心理的剖析形成了他小说世界中一张可视的意象之网。透过重重叠叠的网面,潜隐着的是他心灵的孤独和无尽的人生感怀。
哲学基本问题与人的生存矛盾及对生存矛盾的理解的同一性,要求哲学以人的生存的基本矛盾为出发点去思考问题。人在现实社会中生存应该是物质性的生命与精神性的生命和谐地相融在一起,一旦产生灵肉分离意识,灵魂不死就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成了造成人心理焦虑的重要根源。
生命的终极究竟是什么,人类究竟能否主宰自己的生命,我们能否自由选择生命的存在形式,徐訏在他的小说世界中以哲学的冷静与睿智为我们追寻着这些难题的解答方式。人类世界充满悲剧和苦难,无从把握的存在背后是令人无所适从的命运。为人类寻找温暖的精神家园,探索人生与生命的深度因而成为徐訏小说的使命。他在自己冷静的理性世界中,以一颗热诚的心感受着人性的光辉与灿烂,他并没有拒绝感性的接受方式,在以哲学沟通他富于幻想的心灵与冷峻真实的存在时,他选择了非理性理想化的“彼岸”世界,作为自己的灵魂归宿。哲学的冷静思考与现实的无情压力是徐訏小说世界中的残忍的杀手,它使无数充满活力的生命为了追寻一种抽象的意味而放弃自己的生命;同时哲学又是一条环环相扣的锁链,把海兰、白蒂、地美、银妮、梅瀛子、白苹、海伦、越亮、普沙太太等人的生命连结成了一个息息相通的整体,她们都怀着同样的激情,寻找着冲出混浊人生的突破口。同时也把叙述主体的生命和心灵世界分割成了一段段飘泊的碎片,沿着哲学干枯冷寂的河道,在生命沉积的河床上,拖着那艘载满沉重思考的驳船,扬起爱的风帆,回归最初的生命港湾,用人性与丰富的生命形式及人类生存本身对话,是对生命与生存的自我发现。种种体验与理性认知密不可分,在这种状态下,凡其笔触所及,皆是他内心状态的真实写照。因此,面对茫茫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万相,生命的自我反省和内心体悟,就成了徐訏与外在世界沟通并达成谅解的一种主要途径。
春节习俗
传说,年兽害怕红色、火光和爆炸声,而且通常在大年初一出没,所以每到大年初一这天,人们便有了拜年、贴春联、挂年画、贴窗花、放爆竹、发红包、穿新衣、吃饺子、守岁、舞狮舞龙、挂灯笼、磕头等活动和习俗。
每到过年
时家家有贴春联的习俗。
春联,俗称“门对”,又名“春帖”,是对联的一种,
因在春节时张贴,故称春联。春联的一个源头是桃符。最初
人们以桃木刻人形挂在门旁以避邪,后来画门神像于桃木上,
再简化为在桃木板上题写门神名字。春联的另一来源是春贴,
古人在立春日多贴“宜春”二字。春联真正普及始于明代,
与朱元璋的提倡有关。据史料记载,有一年过年前,朱元璋曾下令每家门上都要贴一副春联,以示庆贺。原来春联题写在桃木板上,后来改写在纸上。桃木的颜色是红的,红色有吉祥、避邪的意思,因此春联大都用红纸书写。
春联堪称中华民族独创的艺术奇葩,它以雅俗共赏的特性深受世代人民喜爱。有人曾这样概括春联:“两行文字,撑天柱地;一副对联,评古涵今。”贴春联,是重要的年节民俗。春节前夕,家家户户都要贴上红红的春联,一副副透着喜庆和热烈的春联表达了人们迎新纳福、企盼新生活的美好愿望。
因为古代的乐器演奏有“雅乐”和“俗乐”之分,而古琴往往被演奏在郑重、严肃的场合,古筝往往是市井小民、普乐大众的音乐,所以被人们认为“一雅一俗”。但这并不说乐器或者音乐本身的地位高低,只是受众不一样。除此之外,古琴与古筝之间的区别还有演奏时的乐质,二者带来的情感体验迥然不同,所以音乐推广的范围就不一样。
首先,就如同读书品字一般,有的人喜欢阳春白雪,有的人喜欢下里巴人,不同的人喜欢不同的文字。音乐也是如此,古琴与古筝虽然外形相似,但实则有着巨大的差别。随着西周时期礼乐制度的确立,各类艺术都有了雅俗之分。按照雅俗的界定来说,雅乐就是高端人群、庄重的场合所演绎的,反之,俗乐就是说宫廷之外的演奏,受众广泛,意义大都为娱乐性质。
其次,古琴一直以来都是被儒家推崇的乐器,往往被贵族子弟作为一种感情的抒发,一种情感的寄托。古琴所演绎出来的音乐被称为“雅乐”,因为古琴的特点就具有雅乐的静态之美,空灵和缥缈的情感体验。古筝发扬之后,就被广泛地运用在各种聚会酒楼等地点,作为一种休闲性和娱乐性的音乐,被普通百姓所接触。古筝属于一种民间乐器物种,它的作用往往是为了烘托宴会氛围。
然后,古琴与古筝之间仅仅相差一个字,就本质上产生了巨大的差别。古琴与古筝之所以有如此明显的雅俗界定,有一部分原因就在于音乐的节奏感和情景。音乐演绎出来的不仅是曲子,更是一种情境体验,古有高山流水,古琴演绎出了一个人的一生,悠远而缥缈寂寥。而古筝的音质较为铿锵有力,在烘托氛围方面起到很好的带动作用。
最后,雅与俗之分不过是所适应的情境不同,并不是指音乐本身的雅俗。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