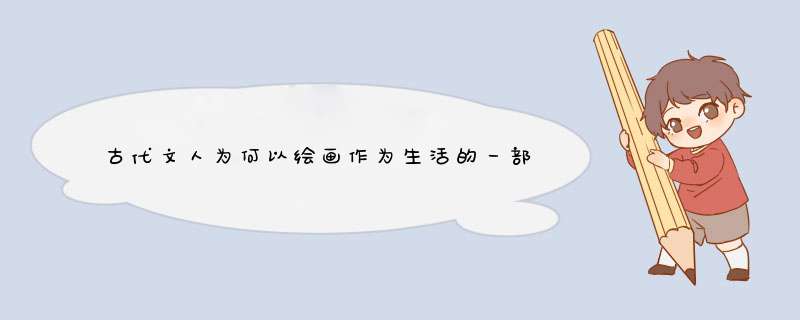
因为古代的文人的话,娱乐生活,然后一方面的话就是写诗,另一方面的话,可能就是画画,不过会画画的应该也不是太多,这个主要就是培养他们的那种士大夫的精神,从儒家的角度来看,君子有六艺,他们学会这几样也是很正常的,这都是符合当时对于师大夫的一个要求。
中国画以其描绘题材的不同,可以分为人物画、山水还有花鸟,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花鸟画是成熟最迟的。花鸟画是以动植物为主要描绘对象的中国画传统画科,又可细分为花卉、翎毛、蔬果、草虫、畜兽、鳞介等支科。但是从欣赏阶层和风格特点来区分的话也可以分为宫廷花鸟和文人花鸟。
文人画在南宋时期除了在理论上进一步展开讨论以外,在实践中也有令人瞩目的成就。米友仁的“云山墨戏”,扬补之的墨梅,赵孟坚的水仙兰花都为世所重。被称为“四君子”,时至今日仍被画家看重的梅、兰、竹、菊,在南宋时已基本成为文人画的固定题材。
两宋是古代花鸟画空前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宫廷中装堂饰壁务求华美,使花鸟画在贵族美术中占有重要地位。社会中上阶层需求及工艺装饰也促使花鸟画的发展和活跃。北宋的花鸟画,如同山水画一样是在五代花鸟画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五代著名的两大花鸟画家黄筌和徐熙都生活到宋代初年,其子孙黄居采、徐崇嗣等都擅长花鸟画,对宋代花鸟画的发展有很大影响。特别是由黄筌、黄居采父子所开创的细笔勾勒彩的写生画法,在宋初100年间,被宫廷画院当成花鸟画的一种规范。以后北宋的花鸟画家虽然不断有新人出现,如革新派花鸟画家崔白(11世纪),自称为“写生赵昌”的赵昌等人,在突破“院体”画题材的束缚等方面有所创造,但他们基本上还是保持着纯客观地描写。现存崔白《双鸟戏兔图》和赵昌的《蝴蝶图》就是明显例证。
以院体画为代表的北宋花鸟画,能客观描写,注重写生。由于愉悦统治者为目的,甚至连皇帝也亲自参加绘画创作,他们有极度的闲暇和优越的条件把追求细节的真实发展到了顶峰。如宋徽宗即是北宋著名的花鸟画家。他在控制宫廷画院的时候,要求画院的花鸟画家研究孔雀升墩是先举左脚还是右脚,月季花在不同时间要表现出花蕊、叶子不同的变化。像这种细节真实的追求,便是皇家画院的重要审美标准。北宋院体花鸟画的这种注重写生以至刻意追求细节真实的艺术风格,在整个宋代都是花鸟画的主流,同时,“院体”花鸟画的发展也对“文人”花鸟画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也是当时政体与绘画形成的必然。
在宋代宫廷画院之外,花鸟画还存在着另一股虽不占主要地位,但对后世文人花鸟画很有影响的潮流,那就是以文同、苏轼的墨竹、杨天咎的墨梅,以及郑思肖的兰花等为代表的不再强调踏实于写生,而是强调借物抒情的花鸟画。在这种艺术潮流影响下,传统花鸟画中的所谓:“四君子”(梅兰竹菊)题材日益流行起来,这种风气到了元代文人画大兴时,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后人知晓的“文人画”最早源于宋代苏轼提出的“士人画”。宋代文人画家都不是专业画家,是文人士大夫的业余创作。北宋中后期文人士大夫绘画形成了独特体系,他们的绘画抒情寄兴、状物言志,不完全拘泥于形式格法,多好水墨写意,爱画梅竹,以表现高洁品格;爱写兰菊,以示自我之胸襟,其完美趣味与精工的院体和职业画家不同。据传墨竹兴于晚唐五代,但取得重大成就而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是北宋的文同,他曾在京城任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后到四种陵州等地任地方官,后调湖州,未赴任而卒。苏轼称他的诗词书画为四绝。他爱画墨竹,对竹进行过深入观摩体验,自称“画竹必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色起从之,振笔直逐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虽是寄兴但却是酝酿成熟的。传为他画的《墨竹》轴造型真实画风严谨洒脱自然。他的墨竹开创了“湖州竹派”。文学家苏轼也擅长墨竹,传说他还画朱竹等。墨梅传说始北宋华光和尚,而杨补之成就最高。书法家欧阳询“以其笔画劲利故以之作梅。”他的墨梅有清雅闲逸、出尘绝俗的情致,与院画塑造的娇艳柔丽的形象大不相同。
在文人画的精神中赋予梅兰竹菊以道德品格,把绘画心态情绪言表于画里画外,诸如“四君子图”、“岁寒三友”等等。有时是“逸笔草草”,狂写自我。这在宋代已形成,至明清而大盛,成为传统画中的独特门类。
元代花鸟画的主流是向文人画情趣发展,绝少有画院之工笔重彩富丽细腻者,文人水墨写意及水墨梅竹勃然兴起,显示了花鸟画领域的巨大变化。而文人画作者虽前师宫廷,也入室重彩大师,却后在文人绘画里发展。此时的代表人物有王渊、张中、王冕、柯九思等人,像王渊早年师赵孟,特别是花鸟师宫廷画派大师黄筌,自己却以水墨画白描法画花鸟树石风格著称于世,花鸟以水墨中见精微严谨而清雅淡逸,显示了院体花鸟转向文人情趣的风格,其张中,亦工墨笔花鸟,比较王渊又显粗简淡逸,兼工带写,对明清花鸟画有一定的影响。
“文人”花鸟画形成已给中国传统绘画注入了新的意识,五代时期全国战事政乱,尽管如此,“文人画”也得到了上层和民间的认可,同时也在不断地发展。“文人”其代表性不只局限于绘画,其涉于各个文化领域,由此,给绘画中的花鸟画以良好的土壤,使“文人花鸟画”发展先于其它。而徐渭则是五代以来“文人花鸟画”的代表。他有怀绝世之资而遭遇不偶,有济世之才而无以施展之心态,故在写意花鸟画创作中兼吴派写意花鸟与林良写意花鸟之长而不为所衷,以狂草般的笔法纵情挥洒,泼墨淋漓,在“似与不似之间”的花木形象中着眼于生韵的体现,在文人绘画道路上长于诸家。八大山人是继徐渭之后又一“文人”绘画的杰出代表,他笔下的花鸟画完成是拟人化的表现手法,借画表心态,抨击当朝,指东骂西,以抒发心中不满之情,使文人绘画,特别是花鸟画达到了新文人画高度,对后世及现代影响极大。
文人绘画兴起,是与当时社会发展分不开的,绘画在士大夫层领域一直是玩偶,旧时画风束缚着众多画家,要用画表心境已远不及当时文人之心境,故众多画家,也包括宫廷画师,把作品转向文人画,把绘画心态调到文人画上来,以满足民众,满足文人画为士大夫气,从五代开始元代后期文人画风创作已渐成熟,从而对以后的中国绘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宫廷画家是皇家承认的画家,当时在社会占主流。而民间画家,也就是后来的“人文画家”也在花鸟画的历史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简要分析如下:
一:宫廷花鸟
中国花鸟画重视写生,以写生做为创作的基础。这种写生,并不是单纯的简单模仿现实的花卉禽鸟,而是在真实描绘客观对象的基础上,表现出花鸟的生命力和其各不相同的特征。就象表现人物画一样,不以外部的形似为目的,而是更重视传神。宋朝是花鸟画的高峰,宋代强调写生,宋徽宗赵佶控制宫廷画院时,对动植物的特点要求更加严格,甚至苛刻,如孔雀开平时是先抬左脚或右脚都是有讲究的。
具体作品如:
《花篮图》 宋李嵩
精致、典雅的籐篮里,一朵朵盛放的花朵,鲜丽而缤纷。大红的山茶稳坐居中,艳冠群芳;清雅的绿萼梅、闺秀般的瑞香,斜倚着身子相随于旁;白净的水仙、娇俏的白色丁香则好奇趴伏在篮缘。
中国人爱花,由来已久。到了宋代,赏花、插花更成为生活中的赏心乐事。当时在一般的酒楼、客栈、茶坊等地,时常可以见随四季变化的插花摆饰,到了春季,许多大都市的人们还争睹「蝴蝶会」、「万花会」等盛大的花会活动。民间如此,宫廷亦然;如画中这盆春意盎然的「花篮」,便由于它的主从分明、色彩鲜丽、枝繁叶茂、整体外形圆满丰盛,是宋代宫廷流行的「篮花」中杰出的佳作。
二:人文花鸟
中国的花鸟画出处透着一种深厚的人文底蕴。不同于宫廷花鸟的精致和繁琐。人文花鸟透着一种更为真实和厚重的感情色彩。
《墨竹图》 宋 苏轼
后人知晓的“文人画”最早源于宋代苏轼提出的“士人画”。宋代文人画家都不是专业画家,是文人士大夫的业余创作。北宋中后期文人士大夫绘画形成了独特体系,他们的绘画抒情寄兴、状物言志,不完全拘泥于形式格法,多好水墨写意,爱画梅竹,以表现高洁品格;爱写兰菊,以示自我之胸襟,其完美趣味与精工的院体和职业画家不同。据传墨竹兴于晚唐五代,但取得重大成就而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是北宋的文同,他曾在京城任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后到四种陵州等地任地方官,后调湖州,未赴任而卒。苏轼称他的诗词书画为四绝。他爱画墨竹,对竹进行过深入观摩体验,自称“画竹必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色起从之,振笔直逐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虽是寄兴但却是酝酿成熟的。传为他画的《墨竹》轴造型真实画风严谨洒脱自然。他的墨竹开创了“湖州竹派”。文学家苏轼也擅长墨竹,传说他还画朱竹等。墨梅传说始北宋华光和尚,而杨补之成就最高。书法家欧阳询“以其笔画劲利故以之作梅。”他的墨梅有清雅闲逸、出尘绝俗的情致,与院画塑造的娇艳柔丽的形象大不相同。
《墨梅图》 元 王冕
元朝著名画家王冕,他画的梅花充满生气,亲新可爱,具有鲜明借物抒情的特点,他的《墨梅图》提诗:吾家种树池头边,个个华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表明在元朝种族歧视的年代里,他那种不甘心受民族压迫、不愿与统治阶级合作的政治态度和自己的抱负。
相对西洋画来说,中国画有着自己明显的特征。传统的中国画不讲焦点透视,不强调自然界对于物体的光色变化,不拘泥于物体外表的肖似,而多强调抒发作者的主观情趣。中国画讲求“以形写神”,追求一种“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感觉:而西洋画呢?则讲求“以形写形”,当然,创作的过程中,也注重“神”的表现。但它非常讲究画面的整体、概括。有人说,西洋画是“再现”的艺术,中国画是“表现”的艺术,这是不无道理的。
中国画与西洋画相比有着自己独特的特征,还表现在其艺术手法、艺术分科、构图、用笔、用墨、敷色等多个方面。按照艺术的手法来分,中国画可分为工笔、写意和兼工带写三种形式。工笔就是用画笔工整细致,敷色层层渲染,细节明彻入微,用极其细腻的笔触描绘物象,故称“工笔”。而写意呢?相对“工笔”而言,用豪放简练的笔墨描绘物象的形神,抒发作者的感情。它要有高度的概括能力,要有以少胜多的含蓄意境,落笔要准确,运笔要熟练,要能得心应手,意到笔到。兼工带写的形式则是把工笔和写意这两种方法进行综合的运用。
从艺术的分科来看,中国画可分为人物、山水、花鸟三大画科,它主要是以描绘对象的不同来划分的。而中国画中的畜兽、鞍马、昆虫、蔬果等画可分别归入此三类。
中国画在构图、用笔、用墨、敷色等方面,也都有自己的特点。中国画的构图一般不遵循西洋画的黄金律,而是或作长卷,或作立轴,长宽比例是“失调”的。但它能够很好表现特殊的意境和画者的主观情趣。同时,在透视的方法上,中国画与西洋画也是不一样的。透视是绘画的术语,就是在作画的时候,把一切物体正确地在平面上表现出来,使之有远近高低的空间感和立体感,这种方法就叫透视。因透视的现象是近大远小,所以也常常称作“远近法”。西洋画一般是用焦点透视,这就像照相一样,固定在一个立脚点,受到空间的局限,摄入镜头的就如实照下来,否则就照不下来。中国画就不一定固定在一个立脚点作画,也不受固定视域的局限,它可以根据画者的感受和需要,使立脚点移动作画,把见得到的和见不到的景物统统摄入自己的画面。这种透视的方法,叫做散点透视或多点透视。如我们所熟知的北宋名画、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用的就是散点透视法。《清明上河图》反映的是北宋都城汴梁内外丰富复杂、气象万千的景象。它以汴河为中心,从远处的郊野画到热闹的“虹桥”;观者既能看到城内,又可看到郊野;既看得到桥上的行人,又看得到桥下的船;既看得到近处的楼台树木,又看得到远处纵深的街道与河港。而且无论站在哪一段看,景物的比例都是相近的,如果按照西洋画焦点透机的方法去画,许多地方是根本无法画出来的。这是中国的古代画家们根据内容和艺术表现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独特的透视方法。
在用笔和用墨方面,是中国画造型的重要部分。用笔讲求粗细、疾徐、顿挫、转折、方圆等变化,以表现物体的质感。一般来说,起笔和止笔都要用力,力腕宜挺,中间气不可断,住笔不可轻挑。用笔时力轻则浮,力重则饨,疾运则滑,徐运则滞,偏用则薄,正用则板。要做到曲行如弓,直行如尺,这都是用笔之意。古人总结有勾线十八描,可以说是中国画用笔的经验总结。而对于用墨,则讲求皴、擦、点、染交互为用,干、湿、浓、淡合理调配,以塑造型体,烘染气氛。一般说来,中国画的用墨之妙,在于浓淡相生,全浓全淡都没有精神,必须有浓有淡,浓处须精彩而不滞,淡处须灵秀而不晦。用墨亦如用色,古有墨分五彩之经验,亦有惜墨如金的画风。用墨还要有浓谈相生相融,做到浓中有淡,淡中有浓;浓要有最浓与次浓,淡要有稍谈与更淡,这都是中国画的灵活用笔之法。由于中国画与书法在工具及运笔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二者结下了不解之缘,古人早有“书画同源”之说。但是二者也存在着差异,书法运笔变化多端,尤其是草书,要胜过绘画,而绘画的用墨丰富多彩,又超过书法。笔墨二字被当做中国画技法的总称,它不仅仅是塑造形象的手段,本身还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
中国画在敷色方面也有自己的讲究,所用颜料多为天然矿物质或动物外壳的粉未,耐风吹日晒,经久不变。敷色方法多为平涂,追求物体固有色的效果,很少光影的变化。
以上谈的中国画的特点,主要是指传统的中国画而言。但这些特点,随着时代的前进。艺术内容和形式也随之更新,并不断地发生变化。特别是“五四”之后,西洋画大量涌入,中国画以自己宽阔的胸怀,吸收了不少西方艺术的技巧,丰富了中国画的表现力。但是,不管变化如何,中国画传统的民族的基本特征不能丢掉,中国画的优良传统应该保持并发扬光大,因为中国画在世界美术领域中自成独特的体系,它在世界美术万花齐放,千壑争流的艺术花园中独放异彩。中国画是我们民族高度智慧、卓越才能和辛勤劳动的结晶,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
有关中国绘画的起源问题,象有关中国历史的起源一样,令人不可琢磨。究竟中国的绘画开始于何时?何地?是何人所创造?这一谜团千年以来一直萦绕在历代美术史研究者的思绪中。唐代的张彦远在他的开创性著作《历代名画记》中,将中国绘画的起源追溯到传说时代,指出那时的象形文字便是书写与绘画的统一。而在他看来,图形与文字的脱离,才使得绘画成为一门专门的艺术,探讨绘画技巧的工作则晚至秦汉才开始,魏晋时名家的出现,才标志着绘画臻于成熟。这1000多年前提出的有关早期中国绘画发展的理论至今仍基本成立。所不同的是现代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史前和历史早期绘画形象的实物,不断增加着我们对早期绘画艺术的了解。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造型艺术,在彩陶及绘画、陶塑和雕刻方面,均有一定的成就。
我们习惯上把从公元前21世纪建立的夏开始,经过商、西周直到到春秋、战国的这一时间段统称为先秦。由于铜器和铁器的相继发明和推广,加上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各种手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除了为礼教服务的青铜艺术、商周的玉石雕刻及战国的彩漆木雕以外,寓有兴废之诫的庙堂壁画及人物肖像画,受到了先秦统治者的普遍重视。但直到本世纪初,对于先秦绘画的研究还只是凭借着那些并不完全和丰富的记载进行的。近年在长沙等地出土的帛画与漆画,为探讨先秦绘画艺术的面貌,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要欣赏中国绘画,对中国画中有名的“四君子”是不可不进行了解和研究的。
“四君子”是指中国画中的梅、兰、竹、菊,中国古代绘画,特别是花鸟画中,有相当多的作品是以它们为题村的,它们常被文人高士用来表现清高拔俗的情趣:正直的气节、虚心的品质和纯洁的思想感情,因此,素有“君子”之称。
我们先说梅。我们知道,梅花较耐寒,花开特别早,在早春即可怒放,它与松、竹一起被称为“岁寒三友”,人们画梅,主要是表现它那种不畏严寒、经霜傲雪的独特个性。那么,梅花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入画的呢?
据画史记载,南北朝已经有人画梅花,到了北宋,画梅就成了一种风气,最有名的是仲仁和尚,他创墨梅,画梅全不用颜色,只用水墨深浅来加以表现。据说他有一次,看到月光把梅花映照在窗纸上的影子,从中得到了启发,便创作出用浓谈相间的水墨晕染而成的墨梅。此后,另一画家杨补之在这种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画法。创造出一种双勾法来画梅花,使梅花纯洁高雅,野趣盎然。元明以来,用梅花作画更多。元代最大的画梅大师应该首推王冕,他自号梅花屋主,他的水墨梅画一变宋人稀疏冷倚之习,而为繁花密蕊,给人以热烈蓬勃向上之感。王冕的存世名作,是他的一幅《墨梅图》他用单纯的水墨和清淡野逸的笔致,生动地传达出了梅花的清肌傲骨,寄托了文人雅士孤高傲岸的情怀。
明清的画梅者举不胜举,如刘世儒、石涛、金农、汪士慎等,从风格来看,他们大体继承了宋人的疏冷和元人的繁密两种画风。
但是,要画好梅花,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画梅人还必须有画梅人的品格,有人称之为“梅气骨”,一种高尚的情操和洁身自好的品格,正所谓:“画梅须有梅气骨,人与梅花一样清。”
再看兰花。人们画兰花,一般都寄托一种幽芳高洁的情操。
如楚国诗人屈原就以“秋兰兮清清,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这样的诗句来咏兰。但兰花入画则比梅花晚,大概始于唐代。到了宋朝,画兰花的人便多了起来,据说苏轼就曾画过兰花,而且花中还夹杂有荆棘,寓意君子能容小人。南宋初,人们常以画兰花来表示一种宋邦沦覆之后不随世浮沉的气节,当时的赵孟坚和郑思肖,被同称为墨兰大家。
元代以郑所南画兰花最为著名,寓意也最为明确。据说他坐必向南,以示怀念先朝,耻作元朝贰臣;他画的兰花,从不画根,就像飘浮在空中的一样,人间其原因,他回答说:“国土已被番人夺去,我岂肯着地?”因此,欣赏绘画,也是必须了解历史背景的。而清人画兰,则以“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最为著名的了。郑板桥是一个注重师法自然的人,他画过盆兰。但尤嗜好画“乱如蓬”的山中野兰,为此,他曾自种兰花数十盆,并常在三春之后将其移植到野石山阴之处,使其于来年发箭成长,观其挺然直上之状态,闻其浓郁纯正之香味,因而得山中兰“叶暖花酣气候浓”的贞美实质。
竹入画,大略和兰花相当,也始于唐代。唐代的皇帝唐玄宗、画家王维、吴道子等都喜画竹。据说到了五代,李夫人还创墨竹法,传说她常夜坐床头、见竹影婆娑映于窗纸上、乃循窗纸摹写而创此法。到宋代,苏轼发展了画竹的方法,放弃了以前的画家们的双勾着色法,而把枝干、叶均用水墨来画,深墨为叶面,淡墨为叶背。以后的元明清时代,画竹名家辈出,只要是山水或花鸟画家,没有不画竹的,而且开始强调竹的整体气势。不过,在众多的画家中,郑板桥的画竹也堪称为一绝。
对于画竹,郑板桥曾写下了自己的体会:“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此机也。独画云乎哉!”因此,从竹子千姿百态的自然景象中得到启示,激发情感,经过“眼中之竹”,转化为“胸中之竹”,借助于笔墨,挥洒成“手中之竹”即“画中之竹”。郑板桥的作品,存世较多,流传也广,自清代以来,被世人行家所叹眼,成为“人争宝之”的珍品。
菊花入画则稍晚,大略始于五代,比起梅兰竹来说,表现菊花的作品则相对要少得多。根据画史来看,五代徐熙、黄筌都画过菊,宋人画菊者极少。元代苏明远、柯九思也有菊的作品。明清两代画菊的也不多。现有明代吴门画派中最享盛名的画家陈淳的一幅《菊石图》藏于首都博物愤,这是本来就较少的菊花作品中的珍品。
梅兰竹菊入画,丰富了美术题材,扩大了审美领域,它们不但本身富有形式美感,而且可以令人联想起人类的品格,所以它既便于文人们充分发挥笔墨情趣,又便于文人们借物寓意,抒发情感,因此,描写“四君子”之风至今不衰。
所以 都喜欢画这几样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