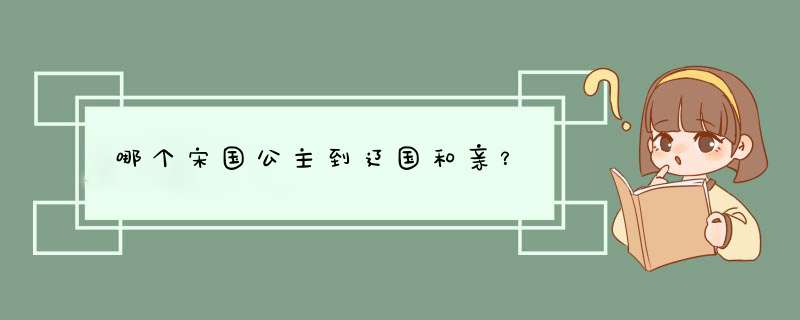
两宋从来就没有和少数民族政权(包括辽)和亲过!
从“大国”心态看宋朝的不和亲政策
传统意识里的“和亲”,一般是指政权间因为政治目的而进行的联姻。昭君出塞、文成公主入藏是我们熟知的和亲事件。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史上,存在着相当广泛的和亲现象,就类型而言,有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政权间的联姻、割据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间的联姻、割据政权间的联姻、少数民族之间的联姻、南朝与北朝之间的联姻以及从现今来看属于与外国之间的联姻。就朝代而言,有汉与匈奴、汉与乌孙、孙吴与蜀汉、隋唐与吐谷浑、隋唐与突厥、唐与吐蕃、辽与西夏、以及后来满蒙联姻等等。无论形式怎样变化,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即都是政治利益的驱动。纵观整个和亲史,两晋、两宋和明代无和亲现象,在政治分烈的情况下,宋朝为什么不与外族和亲呢?宋朝为什么能坚守住独立的婚姻阵地?本文拟从文化和经济方面分析其背景和缘由。
宋朝士大夫对与宋有冲突的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态度
一、外求谋和,内严守备,待机消灭之。
北宋宰相李昉持这样的观点:“……况天生契丹为患中国汉髙祖以三十万之众困于平城,卒用奉春之言以定和亲之策,以至文帝奉之弥优,外示羁糜,内深抑损,而边城晏闭,黎庶息肩,所伤匪多,其利甚溥矣。况獯鬻之性,惟利是求,倘陛下深念比屋之磬县,稍减千金之日费,密谕边将,微露事机,彼亦素蓄此心,固乃乐闻其事。不烦兵力可弭边尘。此所谓屈于一人之下伸于万人之上者也。伏望陛下裁之。”
钦宗时,开封尹程振对此也有类似的看法:“臣愿陛下结以诚信而沮其谋,遗金帛而厌其欲,外务谋和,而内严守备。数年之后,国富民足,将选士励车攻马良,然后徐议大举以刷吾耻,未为晩也。”…… 这些人没有强烈地反对和亲。
二、主张以物质厌其欲,反对和亲、割地等认为有辱国格的事情。
富弼、贾昌朝是持这类观点的代表人物。辽兴宗宗真曾派刘六符等南下宋朝议割地、和亲事宜,当割地的要求被北宋的谈判代表富弼等人拒绝后,他们提出了与宋和亲的要求。富弼借口婚姻易生嫌隙而婉言拒绝:“结婚易生嫌隙,本朝长公主出降,赍送不过十万缗,岂若岁币无穷之利哉?……”
贾昌朝对和亲的反对态度则溢于言表:“始昌朝馆伴契丹使者,建言:和亲辱国,而尺地亦不可许。朝议欲以金帛啖契丹,使攻元昊。昌朝曰:契丹许我而有功,则责报无穷,且以我市于元昊,昔尚结赞,欲助唐讨朱泚,而陆贽以为不可。后知吐蕃阴与泚合。今安知契丹不出此邪?于是命昌朝报使契丹,昌朝力辞。因奏此疏。”
三、主张因时制宜,其实质并不反对和亲。
两宋之交的胡舜陟明确表明了这一观点:“臣观汉唐以来御敌之策有五:曰和亲,曰守备,曰征伐,曰抚定,曰羁縻,皆因时而为之。和亲、守备则施于敌国强盛之时,汉高帝是也;抚定、羁縻则施于敌国衰弱之际,汉宣帝、光武是也;至于征伐或施于强或施于弱,必先以中国富盛兵甲精锐,我有万全之势,彼有可乘之隙,然后可举,汉武帝、唐太宗是也。今我国家承巨奸误,内侍持权之后,海内虚耗,帑藏空竭,军律不振,士不为用……”同是两宋之交的程瑀在奏状中也如是认为。综上所述,两宋的士大夫对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尤其是辽金)的态度是因人而异的。但终宋一朝,它是没有和周边民族实行实质意义上的和亲的。那么,两宋士人对和亲的态度又当如何呢?
宋朝士大夫对和亲的态度
在宋代的文献中,“和亲”的意思有两种:一种是联姻,一种是和好。据分析,大多数文献中的“和亲”是和好、亲善的意思。所以,仅通过文献,难以全面把握宋朝士大夫对和亲的态度。但终宋之际,并无和亲的事实,由此不难判断,宋代文人士大夫对和亲的主流态度,即对和亲持反对意见。
北宋是理学发端的时期,南宋是理学的兴盛期,故而两宋有不少士大夫把和亲与伦理道德相对立,像上文提到的贾昌朝,就认为“和亲辱国”。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把“中国结婚夷狄”视作“自取羞辱”8两宋以讲天理和伦常为主要内容的理学的兴起,使传统的夷夏之防观念深入人心。作为宋朝君臣,他们大多受狭义儒家道德观念的束缚,很自然地把和亲政策与伦理道德对立起来。所以,宋朝在与辽、夏、金议和时,宁可多给金帛,也不愿嫁女和亲。正因如此,在辽兴宗向宋提出以和亲、增币代替割地的要求时,宋朝允许增币,但拒绝和亲。在宋仁宗及参与谈判的大臣富弼等人的心中,割地无疑是丧权辱国,和亲则大失体面,因此才以各种理由加以拒绝,最后使“契丹不复求婚,专欲增币”。
没有(转)
从“大国”心态看宋朝的不和亲政策
传统意识里的“和亲”,一般是指政权间因为政治目的而进行的联姻。昭君出塞、文成公主入藏是我们熟知的和亲事件。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史上,存在着相当广泛的和亲现象,就类型而言,有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政权间的联姻、割据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间的联姻、割据政权间的联姻、少数民族之间的联姻、南朝与北朝之间的联姻以及从现今来看属于与外国之间的联姻。就朝代而言,有汉与匈奴、汉与乌孙、孙吴与蜀汉、隋唐与吐谷浑、隋唐与突厥、唐与吐蕃、辽与西夏、以及后来满蒙联姻等等。无论形式怎样变化,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即都是政治利益的驱动。纵观整个和亲史,两晋、两宋和明代无和亲现象,在政治分烈的情况下,宋朝为什么不与外族和亲呢?宋朝为什么能坚守住独立的婚姻阵地?本文拟从文化和经济方面分析其背景和缘由。
宋朝士大夫对与宋有冲突的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态度
一、外求谋和,内严守备,待机消灭之。
北宋宰相李昉持这样的观点:“……况天生契丹为患中国汉髙祖以三十万之众困于平城,卒用奉春之言以定和亲之策,以至文帝奉之弥优,外示羁糜,内深抑损,而边城晏闭,黎庶息肩,所伤匪多,其利甚溥矣。况獯鬻之性,惟利是求,倘陛下深念比屋之磬县,稍减千金之日费,密谕边将,微露事机,彼亦素蓄此心,固乃乐闻其事。不烦兵力可弭边尘。此所谓屈于一人之下伸于万人之上者也。伏望陛下裁之。”
钦宗时,开封尹程振对此也有类似的看法:“臣愿陛下结以诚信而沮其谋,遗金帛而厌其欲,外务谋和,而内严守备。数年之后,国富民足,将选士励车攻马良,然后徐议大举以刷吾耻,未为晩也。”…… 这些人没有强烈地反对和亲。
二、主张以物质厌其欲,反对和亲、割地等认为有辱国格的事情。
富弼、贾昌朝是持这类观点的代表人物。辽兴宗宗真曾派刘六符等南下宋朝议割地、和亲事宜,当割地的要求被北宋的谈判代表富弼等人拒绝后,他们提出了与宋和亲的要求。富弼借口婚姻易生嫌隙而婉言拒绝:“结婚易生嫌隙,本朝长公主出降,赍送不过十万缗,岂若岁币无穷之利哉?……”
贾昌朝对和亲的反对态度则溢于言表:“始昌朝馆伴契丹使者,建言:和亲辱国,而尺地亦不可许。朝议欲以金帛啖契丹,使攻元昊。昌朝曰:契丹许我而有功,则责报无穷,且以我市于元昊,昔尚结赞,欲助唐讨朱泚,而陆贽以为不可。后知吐蕃阴与泚合。今安知契丹不出此邪?于是命昌朝报使契丹,昌朝力辞。因奏此疏。”
三、主张因时制宜,其实质并不反对和亲。
两宋之交的胡舜陟明确表明了这一观点:“臣观汉唐以来御敌之策有五:曰和亲,曰守备,曰征伐,曰抚定,曰羁縻,皆因时而为之。和亲、守备则施于敌国强盛之时,汉高帝是也;抚定、羁縻则施于敌国衰弱之际,汉宣帝、光武是也;至于征伐或施于强或施于弱,必先以中国富盛兵甲精锐,我有万全之势,彼有可乘之隙,然后可举,汉武帝、唐太宗是也。今我国家承巨奸误,内侍持权之后,海内虚耗,帑藏空竭,军律不振,士不为用……”同是两宋之交的程瑀在奏状中也如是认为。综上所述,两宋的士大夫对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尤其是辽金)的态度是因人而异的。但终宋一朝,它是没有和周边民族实行实质意义上的和亲的。那么,两宋士人对和亲的态度又当如何呢?
宋朝士大夫对和亲的态度
在宋代的文献中,“和亲”的意思有两种:一种是联姻,一种是和好。据分析,大多数文献中的“和亲”是和好、亲善的意思。所以,仅通过文献,难以全面把握宋朝士大夫对和亲的态度。但终宋之际,并无和亲的事实,由此不难判断,宋代文人士大夫对和亲的主流态度,即对和亲持反对意见。
北宋是理学发端的时期,南宋是理学的兴盛期,故而两宋有不少士大夫把和亲与伦理道德相对立,像上文提到的贾昌朝,就认为“和亲辱国”。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把“中国结婚夷狄”视作“自取羞辱”8两宋以讲天理和伦常为主要内容的理学的兴起,使传统的夷夏之防观念深入人心。作为宋朝君臣,他们大多受狭义儒家道德观念的束缚,很自然地把和亲政策与伦理道德对立起来。所以,宋朝在与辽、夏、金议和时,宁可多给金帛,也不愿嫁女和亲。正因如此,在辽兴宗向宋提出以和亲、增币代替割地的要求时,宋朝允许增币,但拒绝和亲。在宋仁宗及参与谈判的大臣富弼等人的心中,割地无疑是丧权辱国,和亲则大失体面,因此才以各种理由加以拒绝,最后使“契丹不复求婚,专欲增币”。
1、唐代教训,如太平公主、安乐公主很多干政。
2、宋代理学发展,对于女子管理十分严厉,出家可以避免丑祸。
唐之覆亡,原因固多,强藩之难制,为其一;而皇族权势之盛、行为不检,也是重要原因。宋朝立国,对唐、五代之乱,深所警惕,对宗室、后宫、外戚和宦官有严格的限制制度。终宋一代,从未发生过公主擅=权的事情,甚至亦无私乱传闻。这首先在于宋朝的开国皇帝,对公主有严格的要求。按司马光总结的,对公主的要求是响当当的八个字:“导之以德,约之以礼。”
“导之以德”,是勤遵妇道,绝不能干政。不但不能干政,即使对公主的丈夫附马,也仅是授予清贵的荣衔,而不能授实职,既是所谓“遥领”。所以,真正有才华的男人,往往以尚公主为苦,因为那意味着,他个人在仕途上发挥才干的前程葬送了。这个问题,是非常值得后世借鉴、并好好研究的一个现象。同时,公主甚至连为自己的子女求官,也经常遭到皇帝的拒绝和训斥。咸平六年(1003),宋太祖的女儿秦国公主为她的儿子王世隆向她的堂弟宋真宗求“正刺史”,遭到宋真宗的断然拒绝,其理由是:“正刺史系朝廷公议,不可!” 绍兴四年(1134),宋哲宗的女儿吴国长公主向他的堂弟宋高宗,为她的丈夫潘正夫求开府,高宗不许,八年再求,宋高宗干脆说:“官爵岂可私许人?须与大臣商量,况今日多事,未暇及此。”拂衣而去。
为防公主干政,宋朝甚至规定,不允许官员私谒公主府,连公主的驸马交结官员,都是违法,所谓“家有宾客之禁,无由与士人相亲闻。”元丰以前,蜀国公主的驸马王诜与苏轼交好,经常往还酬作,互相馈赠。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查出王诜与他交往的事实,随即以此将他贬斥。绍兴年间,吴国长公主的驸马潘正夫要求会见宾客,宋高宗发了仁慈,也不过允许他“至所居州军,与知通州官相见一次。”这样严格防范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杜绝公主、外戚干政之途,防止唐代故事重演。
而所谓“约之以礼”,是为了预防公主秽乱的丑行。有宋一代,总共有88名公主,包括杜太后的女儿、宋太祖的妹妹秦国大长公主。其中的58人出家或早夭,有30人下嫁。在宋史资料中,从未见有公主秽乱的记载,也只有其中的两位公主,有再嫁的历史,而这两位公主,一位是宋太祖的妹妹燕国长公主,在宋开国之初,因丈夫米福德阵亡,而改嫁大将高怀德;一位是宋徽宗的荣德帝姬,被金军掳使北去,在丈夫曹晟死后,改嫁金人习古国王。可以说,在两宋300多年历史中,公主们从无干政的历史,亦无丑闻播行,甚至,她们对驸马的艳闻逸事,也大都采取了充耳不闻的容忍态度。在《宋史》的公主传里,似乎只有一位公主是天性嫉妒的;另有一位因老公太丑陋,不能得其欢心,夫妻关系恶劣,常往娘家跑,当然,她娘家在宫里。其余出阁的公主,仿佛皆能循规蹈矩。蜀国公主的丈夫、苏轼先生的至交王诜,甚至当着公主的面调戏姬妾,公主心中不欢,口中不言,积郁成疾,至于不起。宋神宗为着姐姐的身体,也只好强忍怒火,待公主死后,才拿王诜开刀出气,狠狠整治了他一番。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