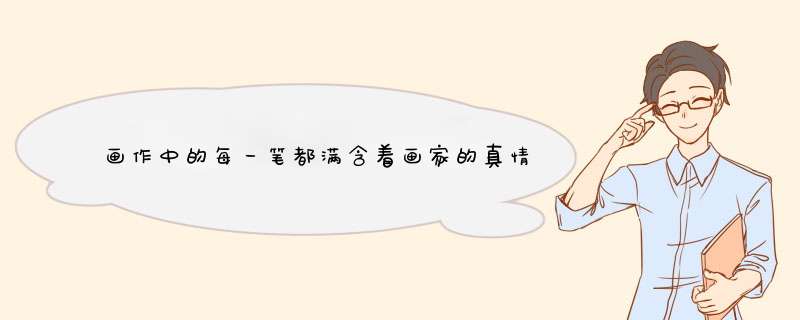
画家常常把辛勤创作出的作品比喻成自己的孩子,可见画家在创作中是寄予着满满的真情实感的。画家创作过程中的每一笔勾勒描绘都倾注着自己的思想感情,都和画家的脉膊一起跳动。
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巨匠达芬奇为了创作《蒙娜丽莎》,从构思酝酿到落笔完成用了14年时间。这幅画寄予了达芬奇太多的思想情感,仅是蒙娜丽莎的眼神和嘴唇他就修改了100多遍,最后创作出千古传奇令人无限猜想的蒙娜丽莎的微笑。至今这微笑的谜底都没有人能够解开。《蒙娜丽莎》成为巴黎卢孚宫的镇馆之宝。
无独有偶。法国十九世纪古典主义艺术大师安格尔非常擅长描绘女性形象,尤以人体艺术见长。他一直想创作一幅正面全身的人体油画,在他年富力强的50岁那一年,就有了《泉》的构想。但是追求艺术完美的他一直在思考这幅画每一个细节怎么表现,连画家自己都不敢想象,到这幅作品完成时他已经76岁高龄了。《泉》被世界许多国家列为人体艺术教学的范本。
后印象派大师梵高一生穷困潦倒,颠沛流离,他把全部思想感情倾注在艺术创作上,只有在画画时他才忘掉人世的痛苦,全身心地投入。荷兰十七世纪天才画家伦勃朗受雇为人画一幅画,画家按照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完成了画作却没有得到雇主的认可,雇主要求他重画,伦勃朗宁可打官司输掉官司也不肯改画这幅画,因为这画中盛满了他的感情。这幅画就是著名的《夜巡》。
画家的情感和想象力一样丰富,都是通过手中的笔凝聚于画中,有的外露,有的含蓄,浇灌着画家的心血和智慧。一枝一叶总关情,画家的每一笔勾勒描绘都是内心思想情感的流露,跟作家写小说,诗人写诗,音乐人谱曲是一样的。
水彩画创作不只是某种景物的复制,还是作画者情感世界表达的一种特别方式,每一幅水彩画作品中都包含作画者的情感,每一件艺术品背后都带有作画者心灵以及美与情感的交融。随着水彩画的不断融合、借鉴、继承,在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水彩画中的情感表达,与之相关的研究越来越广泛,足以说明水彩画中注入情感的重要性。
(一)取景
水彩画创作的第一步,便是选择景物,所以在绘画之前,作画者应当确定入画的景物,并重点凸显景物的光色与景物的内容。景物的不同以及景物观察角度的不同,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在操作过程中,作画者通常会将主观喜好和感受融入其中[7]。作画者确定好入画的景物后,便可以进入取景环节,与选景相比,取景更侧重于景物的“看”,需要作画者对景物展开与之相关的判断与观察。取景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局部、纵向与横向,局部取景主要注重以小见大;纵向取景主要注重高远;横向取景主要注重开阔性。
(二)观察
不同的景物、建筑物在水彩画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尽相同的,比如作画者选择的绘画主体为自然风景,那么就需要突出景物的特点,而建筑物只是作为辅助作用的存在;如果选择建筑物作为绘画主体,那么就需要让自然环境起到辅助作用。在对自然风景进行水彩画创作时,作画者可以将天空、云朵、山峰、水流作为创作重点,同时也能够将意境与气韵表现出来。
为了更好地体现水彩画主题,作画者必须认真观察入画的建筑物或者景物,首先在内心要产生一个整体的印象与感受,在观察的过程中,还需要善于发现感动点。在总体印象与感受形成方面,不管是春天里的草长莺飞,还是湖边的湖光水色,抑或者是山川河流、鸟语花香,作画者都能将其作为切入点传达自己的情感世界,使得客观景色与主观情感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作画者感受到的融合创作灵感与感受都能够为水彩画的情感世界表达奠定基础,而作画者在这个感受与观察的过程中,能够逐步对水彩画创作形成整体的印象与感受。在发现感动点方面,作画者不需要将看到的景物都表现出来,需要对所选景物进行取舍,同时做到有抑有扬。
“写意性”是中国画独特的艺术观。自从它两千多年前形成起,就贯穿整个中国画领域。中国画艺术的写意性,不但表现客观形物的形态特征(外在美)和内在精神(内在美),还表现画家自我的主观意识、精神、审美观、感情旨趣。既有具象的内容,又有抽象的成分;既有再现的形物,又有表现的意识;既强调客观的真实性,又强调主观的意志性。它们形意相融,主客相合,物我相契而又不互相排斥,构成了中国画特殊的审美艺术观。
一、形象,在画家的把握与引导下,借助笔墨表现出来,既反映了客观自然的美,又揭示了画家的心理世界。
善于绘画的人注重作品的写意性而不拘泥于形物,形只是传载“意”的载体,只要达到传载“意”的目的就可以了。所以形的抽象、具象、简约、繁密应该根据画家所要表达的精神思想、意境来决定。顾恺之便提出了“形神兼备 ”、“ 以形写神 ”的观点,这是对“存形”的补充和深化,要求不但要画得象,而且还要画出神气。这时期的绘画观仍然是形神并重。再往后南朝的谢赫的“六法论”又更进一步,强调了绘画要“气韵生动”,这给工笔绘画的发展,奠定了更高层次的理论基础。而当代的工笔人物画由于过多地吸收外来美术“形式”,加之部分画家传统技术的缺失和精神修养的不足,造成了工笔人物画审美方向的偏失和审美价值的丧失——认为工笔画在精神与内核都是一个“细”字而已,作品效果因为过“实”而“腻、僵、呆、板”。从而丧失了我们最为重要的“诗”的国度的情怀和“意”的精神的归宿。
中国画的用笔实即用线。作为最基本的造型手段的线,在形体的塑造中绝不仅仅是一种对轮廓线的描摹,它更能传递出物体的质感、量感和动感,以及精神感与情绪感等信息。比如在山水画中,斧劈皴给人坚挺硬朗的感觉;披麻皴则给人松软的感觉等等。线的运用,体现了中国画家对客观形象的概括、提炼和理解能力,体现了他们驾驭物象的巨大创造力。这种感觉在清代的画家任伯年那里得到很好的体现,他继承了文人画的笔墨,机巧变化地运用于工笔人物画的创作中,线条书写流畅自然,一气呵成,同时大胆吸收西洋画的技法,形成形、线、色完美结合的艺术表现形式。创造了雅俗共赏的风格,拓宽了人物画的创作途径。其作品从形式到内容都是中国式的,而其中吸收的西方绘画对形体结构的处理方法,恰倒好处又不露痕迹。确实对当代人物画家提供了巨大的启示,中西合璧,体现的却是中西分离。
二、在工笔画中,线及其塑造的形体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线条自身的品格特征与作者之间的沟通。
线条所具有的抒情写意性,是由于画家在运笔中出现的各种变化,使线条自身具有了千变万化的姿态。一方面,画家在运笔过程中个人情绪、意趣、思想的灌注,使得中国画中的线条具有明显的画家个性特征,达到抒情、畅神、写意,进而表现画家的审美理想、气质、心灵、人格。这就是古人所说的“画如其人”。另一方面,线条丰富多姿的形态可以唤起欣赏者对现实生活的万般物象中类似物体形态美的联想,使抽象的线条成为现实事物形体美的一种间接曲折的反映,因而唤起人们的不同感受。
唐代张彦远的“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的命题,把立意看作是用笔之“本”,在此强调了用笔与立意造型的关系。立意须造型、造型须用笔,用笔便成了中国画基础的基础。“意”包含着极其复杂的文化内涵,它是画家主观世界的复杂反映,即各种感情、理想、修养、气质等等。“意”是主观的,但又不是纯主观的臆造。中国画家就是通过线的运用来实现这种“抒情写意”的。
作为人的主观世界活动的“意”,其本身是不能直接“用笔”的,中国画以意使笔的要领,就在于以气使笔,以意领气,即所谓“意到气到”,“气到力到”。“意在笔先”就是说画家在命笔落纸之前即已形成立意构思,一旦笔行纸上,便意在笔中。中国画家往往就是在这种情态下来把握自己瞬息万变的情绪流程,抓住来去倏忽的创作灵感,保持创作冲动的新鲜性和连续性,不失画机,一气呵成。工笔人物画的用线唯此最佳。
以气运笔要求画者全身精力贯至笔端,下笔自然能产生力度,这就是“笔力”。中国画家在意在笔先、以气使笔中,创造出了形态有别,又各具韵致的种种笔法。笔法的变化也是以“笔力”的变化来体现的,大自然与人类生活的多姿多彩又给中国画家提供了“笔力”的创造源泉。由于构成画家的“意”的气质、涵养、情感、思绪不同,贯于笔端之气也会不同。以气使笔的“气”不同,也就造成了用笔“笔力”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多变性。
王羲之从鹅颈的回转感悟到了笔力的弹性变化,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而悟出狂草之笔法,而苏轼、黄庭坚又分别从逆水行舟与船夫荡桨中悟出了笔力的奥秘。中国画家在运气使笔时,笔随气行,画家的天机才华,全在有意无意间自然流溢。清代王原祁说:“神与心会,心与气合,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绝无求工求意之意,而工处奇处蜚然与笔墨之外。”中国画家在作画的过程中,常说要排出杂念,保持松静自然的身心状态,就是要使气运笔端,笔笔畅通,笔笔见力。工笔人物画的用线以此心境勾勒,匠俗之气绝难出现。“吴带当风”,“曹衣出水”。这些既是形式的,又是意境状态和精神状态的统一,实际上也就是写意性的。
三、中国画的墨色处理,主要是运用墨色变化的技巧。由于笔中含水墨量的差异,便产生干、湿、浓、淡的变化。
以墨代色,产生了墨分五色及墨分六色之说,清代的唐岱在《绘事发微·墨法》中谈道:“墨色之中分为六彩。何为六彩?黑、白、干、湿、浓、淡是也。”又云:“墨有六彩,而使黑白不分,是无阴阳明暗;干湿不备,是无苍翠秀润;浓淡不辨,是无凹凸远近也。”足见中国画墨色变化的丰富程度是可想而知了。
长期以来水墨画为主流绘画的历史已经使人们弱化了色彩感觉,同时,“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的古训还在主导我们对于中国画的价值评判。我们要抛弃色彩视为“粉气”、“匠气”的观念,而切实认识色彩在中国画中的美学价值,发扬并利用中国画色彩学的传统资源,同时适当地吸取外来艺术在色彩应用上的合理性,从而建立起现代中国画的色彩新体系。
中国画古称“丹青”,实即色彩的“冷暖”,这是一种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色彩对比关系。中国画讲究“随类赋彩”的同时,还十分重视空间环境对物象的影响,随着空间环境的变化,物象的色彩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南朝萧绎对这一现象曾作过仔细的观察,在《山水松石格》中谈到:“炎绯寒碧,暖日凉星。”这是我国最早说明季节、气候的不同,所以引起的物象色彩的变化,特别是冷暖色调的变化。宋代郭熙的《林泉高致》中则概括了季节的变化对水色和天色的影响:“水色:春绿,夏碧,秋青,冬黑;天色:春晃,夏苍、秋净,冬黯。”清代的唐岱《绘事发微》更是形容得有声有色:“山有四时之色,风雨晦明,变更不一,非着色以像其貌。所谓春山艳冶面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淡,冬山惨淡而如睡,此四时之气也。”这些都概括了中国画色彩方面的基本原则——主体对客体的情感反应和意向认知及感受的表达。
中国绘画,特别是工笔人物画,历来都十分讲究色彩的运用,中国画设色,是以物象的固有色与环境变化而产生的影响结合起来加以考虑。这以物象的种类不同而赋以不同色彩的理论,便是中国画用色的基础。清代沈宗骞在《芥舟学画编》中对人物设色作了极其详实和实用的阐述:“人之颜色,自婴孩以至垂老,其随时而变者,固不可以悉数,即人各自具者,亦不可以数计……此则苍、黄、红、白之不同者也。”反映了中国人的观察习惯——对于事物的深入观察和长期积累总结,形成意向共识。这种共识有客观的一面,如:人物年龄、性别差异而形成的肤色特征;也有主观的一面,如:对不同肤色的处理有一定的色彩搭配关系。而后者在中国画的色彩运用中更为重要,就象芥子园画谱中对人的肤色的要求:“红色主血,**主气”,肤色中要有红色和**,画中人物就有了气息和血脉,人就鲜活生动了。这种认识的本身也具有写意性,并带有浪漫色彩。
同时,色彩的运用又以线条的形式差异,而分别着以重彩和淡彩。与重彩协调的是线条的挺拔粗壮和组织的严谨有序;与淡彩协调的是线条的细劲装饰和组织的概括松活。重彩是工笔人物画的主流。工笔画中线条是“筋骨”,色彩是“血肉”,“血肉”可薄可厚,可丰可瘦,而“筋骨”则必须结实坚固,挺拔舒展。
色彩与线条之间彼此的依赖、互补以及协调、相融的关系,是工笔人物画最基本、最直接影响作品风格和品位的技术范畴、思想范畴的内容。线条的启承转合的状态,为色彩的晕染形式和方法给出了约定和依托。一般情况下,线条变法较多,且抑扬顿挫较强的作品,色彩是为线条服务,线的构成关系为主,处于支配整幅作品的地位,色彩则是尽力地呼应线条的节奏,辅助画面达到厚重、充分的艺术效果;线条变法较少,且不注重“书写性”的平铺直叙式的表现,则色彩往往处于主要的地位,线条只是起到收敛色彩,分割形块的作用,色彩的晕染较朦胧,虚幻,自有一番飘渺梦幻般的意韵。
《画》是宋代佚名诗人(一说唐代王维或南宋川禅师)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此诗描写的是自然景物,赞叹的却是一幅画。前两句写其山色分明,流水无声;后两句描述其花开四季,鸟不怕人。四句诗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山水花鸟图。全诗对仗工整,尤其是诗中多组反义词的运用,使其节奏清晰,平仄分明,韵味十足,读着琅琅上口。
白话译文
在远处可以看见山有青翠的颜色,在近处却听不到流水的声音。
春天过去了,但花儿还是常开不败,人走近了,枝头上的鸟儿却没感到害怕。
创作背景
此诗为诗人赞画之作。关于这首诗的作者,有多种说法。一说是唐代王维所作,但在王维的作品,或在《全唐诗》都没有此诗;一说是原为南宋僧人川禅师为注释佛教经典《金刚经》所作的偈颂诗的一部分;一说为宋代佚名诗人所作,如上海市一年级小学语文等教材中编入此诗时,作者一栏里即是“宋·佚名”。
跟写作一样,即触景生情,在风景画中,作者看到眼前的景致,对于一个绘画的人来说就一种原始心中的想,想表现的这景色的一种冲动。那一种冲动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灵感,这样的灵感能使画者在一瞬间表现出丰富的色彩,即色彩感觉。那一刻就是情感的自然流露。这是一条有机的线型,缺少啦其中任何一样都是不能表达出来的。也就是说在画画时没啦这些就不能将色彩画好,即便是画出来啦也只有素描的关系,而没有色彩关系。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